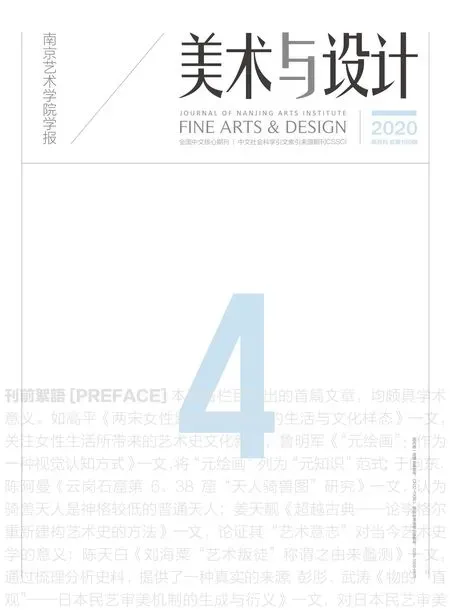“主题性”美术与国家形象的视觉建构①
2020-12-07吉爱明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0013
吉爱明(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0013)
中国“国家形象”,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如同“显影液”,使其由模糊逐渐清晰。这百年的中国历史,既有制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裂变,更有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飞速发展而呈现出的崭新国家形象。它折射出具有影响力的东方古国,在世界背景下对“国家”意识觉醒、构建、现代化与新实践。美术创作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它以自己特有的“视觉”形象的直观图景,借助审美与意趣的方式建构并传播着国家形象。中国美术作为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开始了由传统美术形态向现代美术形态的转换与建构。这种转换与建构始终与中国社会变革紧密相连,与百年来救亡图存、文化启蒙、制度革命、社会文化改造和经济建设的时代主题相呼应,形成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美术,也完全有别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国现代美术体系,这一体系也逐渐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力量。
进入新世纪,尤其近十年,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意义作用逐渐清晰。“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最具特色也是重要的创作力量,中华文明、中国历史及各类重大题材、全国及各省市专题性创作以及建党、建军、建国等特殊主题性创作,围绕“古老的文明大国、崛起中的东方大国、热爱和平的负责任大国和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1]等四种不同角度的形象概念展开,产生了许多紧贴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优秀作品,在国内起着引领作用,对外发挥群体传播效应,有效地廓清了中国国家形象。新世纪美术创作一直秉持国家文艺方针与政策,扎根人民,抒发艺术家的共同心声,在国家形象塑造中,于内引导民众形成广泛共识,于外重塑中国形象、传播国家意识。
一、“主题性”及其历史经验
“主题性”艺术在中国的出现是上世纪50年代,受前苏联艺术创作的影响,一般指带有情节的历史题材画、风俗画等都属于主题性创作。这里我们要清晰区别“主题”与“主题性”的差异,因为一切绘画都有主题,中国的山水与花鸟、西方的风景与景物等都有其主题,即使是所谓“无题”的抽象绘画,其实也内凝着隐性的主题,没有主题的艺术作品是不存在的。“主题性”则更为强调“主题”在表达中的特殊意义,属于为了彰显“主题”而展开的绘画,它区别于“非主题性”绘画的即兴与随意性,带有一种严肃性与稳定的情感驻留。比如主题偏重于“宏大叙事”,表现革命历史、英雄人物或领袖形象的作品都可以归为“主题性”美术创作。这种严肃性与情感的稳定性并非局限在这些规定的题材中,日常生活也会触发作者去表达的一种题材,它诱发必须以严肃的态度与稳定的情感去驾驭,比如一些平凡的劳动者,他们的某种行为或方式具有震撼感与典型性;还有一些看似平常的场面但却富有很深的意味,也可以从“主题性”创作的角度去开拓。最近几年的一些重大题材创作与全国美展都有表现现实生活场景的作品,象征着人民的富裕与幸福,就是标准的“主题性”创作。可以说,只要作品具有感染力且引起广大受众的集体性共鸣,就可以看做是成果的“主题性”创作,其核心主旨是作品有更多的民众愿意接受并深深感染。
由此,“主题性”美术创作以各类题材、多种手法表征出国家在各领域、各方面所取得成就的代表性视觉形象,通过作品的被接受而凝聚了人民的情感、传播了中国在世界时空中的真实形象。“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性、表达的艺术性以及情感的真挚,无疑将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最佳载体。“主题性”美术创作,其主旨当以“人民”为中心,“扎根生活”,必须深含浓郁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要做到历史、现实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相融相合,具有宏大叙事恰如其分的艺术表达。“主题性”美术创作是一种集体记忆的视觉再现,或是当下情境的共同体验,一次创作就是一次留存,一次经典化的过程,力求作品具有史诗般的震撼感与触及心灵深处的感动。
“主题性”美术创作不单是个人行为,它需要国家文艺政策的引导与文化部的组织与动员,提供反复研讨、论证,这样创作的作品才可能达到上文所论述的“主题性”美术作品的价值与建构国家形象的功能。建国后,围绕特定“主题”的创作一直从未间断,虽然没有明确的“主题性”指称,但很多作品在今天来看仍然属于“主题性”创作的精品力作。比如20世纪下半叶创作的作品: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王式廓《井冈山会师》、石鲁的《转战南北》、王盛烈《八女投江》等,均属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历史经典。
二、新世纪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对国家形象的建构
进入新世纪,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冷落和边缘化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国家通过内外文化情境的全面观察予以顶层设计,以国家组织的一系列重大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陆续启动。1999年9月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了“21世纪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研讨会”,对“主题性美术创作”进行了世纪性回顾与展望,从五个学术向度给21世纪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理论建构指明了方向和奠定了基础。这五个方面是为:20世纪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历史传统、发展现状、成就以及出现的问题;主题性美术创作与中国美术史的意义价值;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社会与审美功能;中西方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比较研究;创作主体以及个案研究。[2]这次研讨会既是一次理论研讨,也是象征性的全国动员,自此,新世纪“主题性”美术创作拉开了序幕。
中国文联、文化部以及各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均围绕“主题性”美术创作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工作,设定了带有指向性“主题”“任务”等,并给予创作经费支持。比较重要的有:2005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2年,“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6年,“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9年,“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中华家园”美术创作项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创作项目、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等,各省市也相继推出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如“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美丽湖南·三湘巨变”湖南省美术创作工程、宁波市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
以2016年“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为例,该项目自2016年启动,历时近3年,完成第一阶段的创作任务。据中国新闻网2019年11月6日报道,该项目旨在进一步加强对重大题材特别是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的引导和扶持,推出一批优秀现实题材美术作品和中青年创作人才。经过近3年努力,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共完成作品134件,包括中国画38件,油画61件,版画9件,雕塑26件。其中,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成就、重大事件现实题材作品超过70%,180余位中青年作者参与了创作。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是继原文化部2005年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组织实施的现实题材美术创作项目。2019年国庆节期间,这批现实题材作品首次在“伟大历程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上集中展出,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现实题材美术创作成果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展示,对于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3]这批作品精品迭现,如:马佳伟的油画《唱响明天——打造千年雄安》,许杨、廉南宁的油画作品《辽宁号航母》,彭汉钦的雕塑作品《石榴花开》,范春晓的中国画作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C919大飞机》,蔡超、边涛、李鸿莉的中国画作品《高铁进山啦》,周吉荣的版画作品《中国“天眼”》,沙永汇的版画作品《天下飞桥:港珠澳大桥》等,均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时代同行,彰显中国特色与发展现状,承担起“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的美术创作之责。
新时期主题性美术创作超越了20世纪80、90年代单一视角的观察、呈现与线性思维,较多注意主客体之间的、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而有了更全面的思考与深度挖掘。这是创作者避免跟风与模式化创作的创新,既表征出视角的客观性,又能结合自己的深度体验而激活情感的参与,作品避免了简单的生活直白与现在的照搬,艺术性与思想性都有了新的高度。在国家形象建构中,创作者既设定了“我”的观察与思考,又能贴近生活实际与社会的变化,围绕着接受去呈现,这是他者之“我”,其视觉传播与认同的价值发生了根本改变。也就是说,作为艺术家的个人体验与感受,在更广更高的视野中,围绕着新时期国家形象建构而学会了“讲故事”,讲好故事,讲出真情实感的故事。能打动人,让人信服,且被故事感染而接受。
三、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新使命
新时代,对“国家形象建构”的看法、态度、印象和评价均发生着新变并获得进一步提升。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励精图治、改革创新,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形象大为提升。这一期间,国家形象建构所依赖的文化软实力应成为更为关注的对象,美术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围绕这一使命,新时代的美术创作在观念与实践上,更应秉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原则,努力实现国家强盛、树立大国形象与文化自信。这一切不仅是创作的现实路径,更是创作价值的基点。换言之,理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与“国家形象建构”策略的美术创作,就在于其深入的程度决定情怀的温度,扎根的深度决定立意的高度。故而,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与“国家形象建构”的意识的美术创作,可以说是未来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其关注的重点应始终围绕新时代国家建设、科技发展、经济振兴的伟大实践与生活富裕、人民幸福与文化繁荣现实景象,通过美术创作的独特视角,讲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大故事,讲好广大群众寻梦追梦圆梦的平凡历程,为伟大时代描绘最新最美的精神画卷。由此,新时代中国美术不能单纯囿于美术创作的形式、风格、功能等创作本体范畴之中,而是与观念史及社会学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文化学中的进化学派紧密联系,将其提升至艺术观念与艺术实践相互融合的高度进行综合探究。所涉及的乃是以国家与人民利益贯通体现的新时代美术主体建构的命题。其具体要求,正如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群所指出的:“一是聚焦新时代,浓墨重彩抒写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矢志不渝地创作人民需要的主题性美术作品;三是提高艺术质量,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精品;四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主题性美术作品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作用。”[3]
新时代,围绕“人民”与“国家”核心定位,在“国家形象建构”的美术创作应努力做到:第一,从超然遁世转向现实关注。要以为国为民的宗旨引领艺术关注现实,反映民众的情感、生活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坚持生活是艺术创作源泉的思想来源与创新性发展;努力表现时代语境中的图像与图像中的历史。第二,超越文人意趣,抒写家国情怀。坚守民族自强意识的自觉与美术创作的价值导向;做到对传统文人意趣的扬弃与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高扬;实现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国艺术现代性的探索;秉持主题性创作与民族国家形象建构。第三,超越精英意识,引领大众化思潮。认同从平民美术到人民美术的观念演变;坚持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现实主义美术观的持续发展;充分理解人民“喜闻乐见”的美术创作与作为创作主体的大众在新时代的新内容新意义;实现革命时期的大众化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的大众化观念的延异与转换。第四,增强国家认同感,塑造民族气派。践行中国美术现代化与外来艺术民族化的时代诉求;进一步探索“本土西行”与中国现代美术的民族化探索实践;力求激活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当代美术身份建构的意识。第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态度。维护并执行国家文艺政策与对于中国传统美术的态度;进一步唤醒文化自觉意识与民族民间美术的价值重构;努力做到对优秀世界艺术成果的借鉴与吸纳;实现美术在对话与交流中确立民族美术的方位价值。第六,主旋律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围绕百年历史与社会变革主题构建艺术图像;实现主题性美术创作与民族文化记忆重构;积极展开主旋律美术创作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美术创作的关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文艺的性质、品格、任务与目标作了高屋建瓴的阐述,其中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国家形象建构”作了重点的强调,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的思想,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国家形象的一种表征。“以人民为中心”“建构国家形象”的文艺思想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对中国现代美术品格的高度提炼,对于指导中国美术新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新时代的美术创作已经取得了可贵的成就并显示出极好的发展态势。除了前面我们例举的2016年“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精品之外,在“中华文明历史题材创作工程”项目中,俞晓夫的油画《司马迁与〈史记〉》、何红舟的油画《满江红》,冯远的中国画《楚辞》、任惠中的中国画《文景之治》、唐勇力的中国画《唐宋书画艺术》,卢雨的版画《秦王扫六合》、戚序的版画《营造法式》、袁庆禄的版画《史可法殉城》,吴为山的雕塑《老子道德经》、龙翔的雕塑《马可波罗像》等均为“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标志性作品。此外,在其他项目中还有林蓝的中国画《诗经一长歌清唱》、袁武的中国画《大风歌》、李象群的雕塑《元四家》、王宏剑的油画《楚汉相争》、李先海的雕塑《中华医学》、戴政生与黄静的黑白木刻《孝治天下》等均是一流的佳作。这些作品贴近生活与现实,表现了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有效地展现了中国美术的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国家形象建构的积极意义。
四、结语
中国现代美术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国现代美术形态在实践层面的建构,得益于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转换与变革,得益于美术理论与美术创作在实践层面的共生互动。中国现当代美术演变发展与品格塑造,与国家的文艺思想、观念与政策方针的引领是分不开的。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与追求,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和追求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崭新篇章。百年来的中国美术,不仅形象生动地记载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变革,使时代变革与发展涛声回荡于中国现代美术奔涌的潮流中,更重要的是,这一个多世纪的时空跨越,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重视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建设,将文化建设作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彰显社会发展与进步、提升民族精神和塑造国家形象的武器和重要方式。在每一个阶段,都对包括美术在内的中国问题注入了全新的观念、思想,并形成了符合现实与时代需求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美术始终贴近国家的发展与新变,并以“作品”表征出中国国家形象同步建构的过程。20世纪之前及其上半叶,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觉醒,美术创作呈现为“中西”“古今”的矛盾与冲突,较为真实地还原了特定历史时期艺术家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诞生,建国17年与1978年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美术,前者围绕“人民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为新生共和国形象“造型”,后者带着走出“文革”的伤痛,无意中也扩大了反思与怀旧的情结,客观上却偏离了真正意义上的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出发点。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无论在艺术的功能观、艺术表现的内容、艺术的价值取向、艺术风格、图式等方面与中国传统美术和西方现代美术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塑造了中国当代美术独特的面貌。通过对时代背景、文艺政策与美术作品三者互动的全面观察,新世纪中国美术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美术创作理念与通过美术作品塑造“国家形象”、彰显“文化自信”的核心命题。通过中国美术塑造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不可触摸的目标,不是一个在语言上空喊的口号,不是一些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或是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各种元素的简单累加、堆砌。塑造中国形象,需要树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需要致力挖掘本土化文化的内涵,这是以国家的发展速度、生活质量、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先获得国内人民的情感认同,才有可能最终成功地在国际上呈现富于中国精神和魅力的文化艺术。[4]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发生与演变,清楚表明,围绕“主题性”与现实的真实性去反映中国现状与对未来的憧憬,正是建构国家形象的实际行为,还原历史史实,把握演变规律,将明鉴于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