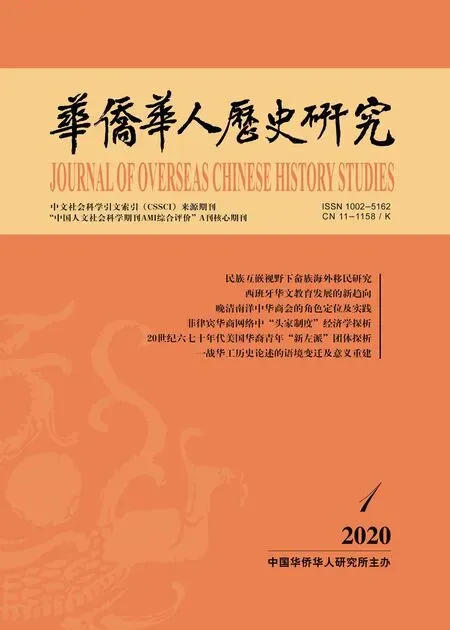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裔青年 “新左派”团体探析*
2020-12-06李爱慧
李爱慧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在当代美国主流学界和媒体的笔下,华人和其他亚裔群体往往被塑造为“模范少数族裔”:他们忍辱负重、安静缄默、努力工作,成功实现了“美国梦”。但是,“模范少数族裔”论不仅忽略了华人内部的阶层分野和依然遭受的种族歧视,也“淹没”了华人争取平等权利与公正待遇的“声音”。实际上,美国华人一直不乏反抗种族歧视的勇气和斗志。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国内黑人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新左派运动、反越战运动等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主流社会的种族主义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也唤醒了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权利意识,激励他们开展集体政治行动,争取本族裔的平等权利。如,土生华裔青年联合一些日裔、菲律宾裔青年,建立亚裔美国人政治团体,在大学中发起罢课运动,争取设立亚裔历史课程和研究系,并取得了胜利。在这种胜利的鼓舞下,这些华裔青年大学生又联合一些社会活动家,成立了一批“新左派”团体①所谓“新左派”团体,是相对于1950 年之前成立的“老左派”团体来说的。20 世纪前期,美国华社中曾经建立起一批“老左派”团体,如加省华工合作会、旧金山华侨民主青年团(民青)、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衣联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表示支持和拥护。中美断交之后,在美国当局和国民党驻美支部的联手打击下,这些老左派团体相继解散,亲国民党的保守力量基本控制了华社。,深入到唐人街等亚裔社区,为当地底层的华裔及亚裔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还积极动员华人新移民劳工举行罢工,反抗歧视和剥削,争取华人劳工的正当权益。
在美国学术界,已故著名华人史学家麦礼谦(Him Mark Lai)对此问题最早作过较系统的研究,但其研究重点是“老左派”团体,对20 世纪60 年代的新左派团体着墨不多。[1]邝治中(Peter Kwong)对纽约20 世纪30—50 年代的劳工团体开展过专门研究。[2]而于仁秋则对纽约最有影响力的“老左派”团体——“华侨衣馆联合会”早期的历史进入了深入的探讨。[3]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一批亚裔学者不断挖掘相关史料,对长期被忽略的亚裔美国人运动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论文和史料集,[4]力图揭示这场运动在美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这些论著多将华裔纳入到亚裔美国人的整体研究中,较少对华社的“新左派”团体作专门论述。而在国内学界,相关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董娣对亚裔美国人运动的根源及其影响作了探讨,[5]其中涉及亚裔(包括华裔)青年学生的校园罢课运动。何慧以“民青”和“义和拳”为例,探讨了冷战时期美国华人左翼青年团体的变迁。[6]本文在吸取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兴起的美国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进行研究,重点揭示他们在争取华人平等权益上的历史贡献。
一、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华人社群却似乎“平静如水”,埋头努力工作。但实际上,华人社区中一些自由派人士,如《太平洋周报》主编胡景南、《东西报》(East West)社长刘池光、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王灵智等人一直密切关注黑人民权运动和美国当局民权立法的进展,不时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支持性的评论。与此同时,一些战后成长起来的土生华裔也不可避免受到反“白人优越论”思潮的影响,开始认真审视本族裔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遭受的种族歧视问题。他们的平权意识逐渐觉醒,决心挑战旧有的种族和阶级秩序,为唐人街底层民众争取应得的权益和福利。
(一)美国社会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激发了华裔青年的平权意识
20 世纪60 年代,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国家)来说,都是个急剧变革和动荡的时代。在美国国内,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和马尔科姆·X 领导的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②与金的非暴力斗争策略形成鲜明的对照,马尔科姆·X 主张通过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取黑人的权利。点燃了各种社会运动的火焰,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新左派运动、妇女运动交织在一起,人们发动游行、静坐、示威,挑战并抨击主流的种族主义思想、政治理念、外交政策、阶级分化、性别歧视等等。而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则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有32 个国家相继摆脱欧洲殖民者的统治获得独立。国内外的运动遥相呼应,对美国社会的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形成巨大的冲击。上述运动,尤其是黑人权力运动,对正处于思想和价值观塑造关键期的亚裔(华裔)青年大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唤醒了他们的平权意识,由此,在全美涌现出了一批带有“新左派”色彩的华裔青年团体,他们纷纷开展集体政治行动,为本族裔争取平等权益。
(二)大学校园内少数族裔学生争取平权的胜利鼓舞了华裔青年
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出台了有利于华人妇女入境的移民政策,加上随之而来的“婴儿潮”,到20世纪60 年代,美国土生华裔青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上升,①二战后初期,美国政府颁布了《战争新娘法》《外籍未婚夫与未婚妻法》和《美国公民华裔妻子法》,规定华裔退伍军人和美国公民的妻子可以不受每年105 名移民配额的限制。这些“战娘”的到来,使华人社会的性别比例趋向平衡,同时也为土生华裔人口的增加奠定了基础。大多数华人女性移民处于20~39 岁生育年龄段,从而带来一个婴儿出生潮,使得美国土生华裔比例稳步上升,到1960 年,土生华裔已占到美国华人总人口的60%。这种人口代际结构的变化到20 世纪80 年代后中国大陆新移民大量涌入之后才发生根本改变。力量不断壮大。这一批战后出生成长的华裔当时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在学校里耳濡目染了黑人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新左派运动的风潮,有些还亲身参与这些运动,权利意识和变革意识日益增强。他们不像老一辈华侨那样深陷“中国政治”纷争的泥潭,又有改变华人(亚裔)受歧视现状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于是联合其他有共同志向的亚裔青年,发起了一场亚裔美国人运动。
他们首先在校园内掀起罢课示威行动,争取设立亚裔历史课程和研究院系。最先行动起来的是美国西部的亚裔学生(以华裔和日裔为主),他们采取了与其他亚裔和少数族裔学生结盟的形式。1967 年,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华裔学生率先成立了“校际华裔学生社会活动委员会”,以组织和协调华裔学生的社会运动。1968 年5 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裔学生成立了第一个亚裔政治组织——美亚裔政治联盟。其宗旨是反对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支持“亚裔自决”的权利,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第三世界民族的自主权,建立一个平等、合理、人道的美国社会。[7]不久,该组织得到了加州其他学校的亚裔学生的响应,很快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成立了第二个分部。
1968 年11 月,“校际华裔学生社会活动委员会”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亚裔政治联盟”分部与墨西哥裔、非洲裔、印第安裔等少数族裔学生联合组成“第三世界解放阵线”(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简称TWLF),向学校当局要求成立“少数族裔研究院”,增设少数族裔历史课程,制定优惠政策接纳有色种族裔学生入学,并雇佣更多少数族裔教职工。[8]虽然华裔学生在大学校园里传统上属于比较沉默的群体,但他们在这次运动中也大胆参与示威、静坐、游行、集会演说等抗议活动。这场学生罢课运动一共持续了4 个月,直到1969 年3 月校方才与学生达成协议,基本满足了学生提出的要求。旧金山州立大学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少数族裔研究院”,其中包括美亚裔研究系,分为华裔、日裔、菲律宾裔三个研究室,首次开设美国亚裔历史、亚裔文学等课程。[9]旧金山州立大学少数族裔学生的罢课运动很快蔓延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69 年1 月,伯克利加州大学也爆发了类似的学生罢课运动,持续了近一个月,迫使校方开设少数族裔研究课程。
在美东,纽约城市大学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华裔学生于1971 年组成了地下工作室。1972 年3 月,该组织与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的支持者,发起了一次抗议行动,占据了大学的行政大楼十三天,要求为唐人街的青年实行特殊教育,并在学校设立亚裔研究系,设置相关课程。当时,正在城市大学就读的陈倩雯也积极投身这场学生运动,争取在学校设立亚裔系。最后,学校当局被迫回应,很快设立了一个亚裔美国人研究项目。[10]
美国其他高校少数族裔学生运动的激烈程度稍微弱一些,但提出的要求相似。为了确保赢得平等的机会,华裔青年与其他少数族裔青年联起手来,争取进入著名高等学府的入学名额。作为回应,加州、夏威夷、纽约和华盛顿等州不少大学都对学校招生制度和课程做了修订,建立起少数族裔研究院,其中设置亚裔研究系(中心)或开设亚裔历史课程。校园斗争的胜利,让华裔大学生备受鼓舞,他们开始寻找新的社会变革运动“试验场”。
(三)唐人街居民恶劣的生存境况触发了华裔青年改变现状的“使命感”
华裔青年把目光投向本族裔聚居区——唐人街,发现那里的底层民众正在遭受种族和阶级双重剥削,生活非常困顿,却为主流社会所忽视。1966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一个模范少数族裔的成功历史》(Success Story of One Minority Group)的文章,高度赞扬华裔美国人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突出成就。该文以统计数字为证,从教育、就业、工资、犯罪率等诸多方面将华裔与白种人和非洲裔对比,盛赞全美30 万华裔勤劳节俭、吃苦耐劳、努力向上,依靠自力更生取得了成功。不可否认,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土生华裔、中国留学生确实能够在主流公司、主流科研院所找到专业技术工作,并慢慢融入主流社会,跻身中产阶层。可主流媒体只看到(或者说刻意突出)这些“成功”的华人,就给所有华人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桂冠。但这一“赞誉”掩盖了华人社会内部的阶层分野和唐人街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
实际上,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唐人街居民的生存境况,与非裔美国人贫民窟相差无几。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住房拥挤、社区卫生环境差、贫困、失业、青少年犯罪、教育不公、工作环境恶劣、工资低廉、养老和医疗福利匮乏等。根据1969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纽约曼哈顿唐人街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为4000~4900 美元,而当时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7436 美元。旧金山唐人街的状况也一样糟糕,每英亩的人口密度为885.1 人,而全市为189 人。67%的华人住房条件非常简陋,远远超过其他城市19%的水平。由肺结核引起的死亡比例占到总死亡人数的21%,是其他城市的3 倍。25 岁以上的居民之中,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长平均仅为一年零七个月。战后初期,赴美投靠丈夫的华人移民妇女只能在服装厂内工作,虽然她们每天苦干12~15 个小时,但连最低工资都拿不到。社区中赤贫的独居老年人不计其数。41%的唐人街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11]那些家境不好或资质欠佳的华裔青少年则深受辍学、失业、贫困等问题的困扰,极易被街头帮派组织所诱惑,打架斗殴现象时有发生。但当时唐人街中以中华会馆(公所)为代表的“当权阶层”,由于受国民党驻美支部的控制,忙于“反共”,基本无视上述社会问题的存在。
正是唐人街恶劣的状况促使许多华裔青年回到那里,力图以实际的政治行动改变华社面貌。正如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早川校长所言:“大学生们认为他们是精英,改变一大部分饱受贫困之苦、没文化的农民的处境正是他们的‘使命’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起来反抗现有制度并推翻它。”[12]
二、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的兴衰与转型
当时,一批华裔青年(以土生华裔为主,也包括少量留学生)深受当时黑人权力运动、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影响,宣扬社会变革,主张通过游行示威、罢工等斗争方式争取平等权利。他们深入唐人街等亚裔社区,为当地底层的华裔及亚裔居民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免费医疗、廉价食物和农产品、免费法律咨询、为青少年提供无偿律师援助和课外辅导、英文学习班、表演话剧放映电影等。一些华裔青年还积极动员在制衣厂工作的华人新移民劳工举行罢工,反抗歧视和剥削,争取华人劳工的正当权益。旧金山和纽约的华裔青年率先行动起来,成立了“红卫兵党”“义和拳”“纽约亚洲人就业平等会”等带有“新左派”色彩的华裔青年团体,深入华人社区,开展一系列为社区谋福利、为华人社区居民服务的活动。他们发动唐人街的底层普通劳工,积极组织或参与各种争取公共住房、租客权利、教育权利、劳工组织权利、社会服务的社区活动。尽管这些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大多存续时间较短,但他们的变革性行动却为华社注入了一股崭新的空气。
(一)“红卫兵党”和“义和拳”:昙花一现的华人民权先锋
旧金山的第一个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是“红卫兵党”,它是由“清流社”演变而来。20 世纪60年代,旧金山失业的华裔青少年帮派(如“华青帮”)犯罪问题非常严重,已经影响到华人社区的正常生活。有鉴于此,一批土生华裔青年成立非盈利组织——“清流社”,主要举办一些青少年所喜爱的文娱活动,并帮助他们找工作,协助他们进入社区大学就读,避免他们走上邪路。该组织的一些骨干曾参加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少数族裔学生罢课运动,同时还受到“黑人权力”(Black power)运动的影响,尤为推崇黑人激进组织——“黑豹党”的思想。①黑豹党反对美国政府,坚持武装斗争和黑人自治(实际上就是在黑人聚居区建立黑人革命政权),认为改变世界必须通过对民众的长期组织和动员。该党在黑人社区提供穷人小孩免费早餐,试图以革命思想武装黑人民众,潜移默化地改变底层黑人的想法,并赋予他们力量。他们以黑豹党的十点政治纲领为蓝本,于1969 年2 月成立“红卫兵党”。该党虽然借用了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一名,但其思想和行动与中国的“红卫兵”并无直接关联。该团体的宗旨是争取美国亚裔社群享有自决的权力,口号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他们认为自己是华人社区的守卫者,要为华人争取公正平等待遇。[13]
“红卫兵党”开展了一系列深入华人社区、为社区服务的活动。他们设立了两个“为人民服务”的项目,分别是儿童免费早餐和午餐。他们还组织参与了很多为华人争平等权利、谋福利的请愿和运动,如阻止拆除冈州古庙、发放传单阻止大资本家和开发商拆毁国际旅馆、抗议尼克松政府关闭华人社区肺医疗中心等等。[14]
虽然“红卫兵党”设立了为华社底层民众服务的各种项目,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福利。但是其“革命”主张并未获得华社居民的响应,即便在组织内部也没有得到全体成员的认同,这严重制约了“红卫兵党”的发展。由于“红卫兵党”是仿照黑豹党建立起来的组织,言论和行动上都与黑豹党极为相似,这与唐人街老华侨一贯保守的言行举止有很大的差异,更挑战了华社传统侨领的权威,受到后者的敌视和诋毁。同时,“红卫兵党”的活动自始至终都受到美国警察的监视和打压,使得一些成员认为,除了建立武装来“杀猪”(指“杀警察”),已别无他法了。而这一“激进”主张脱离了美国的实际,得不到普通华人的支持,从而使得“红卫兵党”失去了群众基础。由于组织内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红卫兵党”只存在了两年多,就于1971 年7 月解散。[15]
在纽约,与“红卫兵党”类似的一个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是1969 年成立的“义和拳”(IWK),它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沙拉劳伦斯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的部分亚裔学生组建而成。他们出身中产阶层,入读名校,“自豪、聪明、有政治意识”,他们将中国视为第三世界人民自力更生和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压迫的象征。该组织借用清末中国底层民众建立的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团体——“义和拳”来命名,以“黑豹党”和“青年洛德党”为榜样,为唐人街底层民众谋权益。义和拳在华人社区建立了“赤脚医生”诊所,以此为依托开展了多项活动,如提供免费的肺结核和铅中毒检验、设立托儿所、并义务教授英语课程等,同时,还为亚洲青年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义和拳成员创办了中英双语报《团结报》 (Getting Together),介绍华社新闻和中国时事,帮助社区居民了解华社动态和中国近况;同时也报道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宣传革命斗争思想。可是,与“红卫兵党”的遭遇一样,义和拳提出的“争取亚裔美国人民自决”“解放第三世界所有人民,解放一切受压迫者”“社区自治、自建制度、自管土地”“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等革命口号完全脱离美国现实,难以引起普通华人的共鸣。[16]
1971 年,“义和拳”到美西发展,设立了美西旧金山分部,吸纳了原“红卫兵党”的骨干成员。该组织意识到,如果作为纯粹的新左派团体,在唐人街是无法立足的,于是加强与自由派人士的团结联系。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义和拳”联络华人社区进步人士于1972 年12 月在旧金山唐人街成立了“华人进步会”(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该会的宗旨是:团结华人进步人士,特别是工人、学生和爱国侨胞,争取进步,改善华社,支持美国工人及少数民族和世界上一切进步人士为争取平等自由而斗争,促进中美友谊。[17]七年后,华人进步会在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建立了分会。[18]华人进步会设有中英双语法律权益援助中心,为华人和少数民族争取平等待遇;为新移民讲授法律、英语、粤语等课程,帮助解决新移民的各种困难;同时,还举办各类参观、旅行、联欢等活动,活跃华人文化生活。
(二)纽约亚洲人就业平等会:由“激进”走向“温和”
纽约亚洲人就业平等会(Asian American for Equal Employment,AAFEE)是由激进团体逐步走向温和的民权组织及社会服务团体,存续的时间最久。该组织的前身和核心成员是1973 年成立的亚洲研究小组(Asian Study Group,ASG),主要发起人是曾参加过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华裔唐·杰里(Jerry Tung),其成员多为纽约城市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亚裔青年(以华裔为主)。亚洲研究小组本属于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小型学术团体,他们希望找到实践自己思想和施展抱负的社区平台,于是在1974 成立“亚裔美国人就业平等协会”,1976 年更名为“纽约亚洲人平等会”(以下简称“平等会”)。“平等会”的主要成员和负责人都是土生华裔,如现任纽约市议员的陈倩雯(祖籍台山)就是该组织的初创人之一。她一直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还于1982—1986 年担任该会会长。[19]
“平等会”力图广泛招募华人社区群众加入,用革命思想武装他们,并把其中的活跃分子收为核心骨干。1974 年初,“平等会”与纽约房产开发局进行交涉,要求承建华人社区孔子大厦的建筑公司履行联邦政府合约,为当地华人社区工人提供培训和工作岗位。“平等会”从华人社区几百个工人那里征集了签名呈交给建筑商,然而,建筑公司拒绝雇佣这些工人。“平等会”随即与黑人经济复苏组织、波多黎各建筑工人联盟团结起来,在孔子大厦施工现场举行集会抗议活动,赢得了华人社区和少数族裔的支持。据《纽约时报》报道:抗议活动每天都在上演,示威者人数众多,有时多达好几百人。他们来自各个年龄段和阶层,从拿着书本的女学生到华人老年俱乐部的枯瘦老人,他们列队前进,高声呐喊“亚洲人可以修筑铁路,为何不能建造孔子大厦?”甚至连一贯对主流政治有所顾忌的中华会馆也公开声援工人的就业要求。经过几个月的抗战,最终建筑公司只好让步,答应雇佣40名亚裔美国工人,其中华裔工人有24 名。[20]市政府还聘请亚裔监管员前往孔子大厦施工现场,对雇佣情况进行监督。1975 年,“平等会”组织华社民众抗议警察局虐待华裔工程师于皮特(Peter Yew)的暴力行为,发起两次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第二次的示威游行中,中华会馆还予以大力声援,动员华人社区商人罢市参与集会,抗议者多达2 万人。[21]最终,警察局和市政府被迫出面道歉并赔偿。
这一系列胜利为“平等会”赢得了一片赞誉,它也因此吸引了大批亚裔学生加入。当然,这些胜利也离不开讲粤语的侨领和普通华社民众的不懈努力。为博得华社民众的信任,“平等会”实施了一系列服务项目,诸如提供免费英语服务、无偿提供房产问题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等等。由于“平等会”核心领导层的亚洲研究小组一心要强化阶级斗争和共产党领导的意识,于1979 年成立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Worker Party)。后来,该组织内“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26 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异见分子被开除, 20 世纪70 年代末走向分裂。[22]
到20 世纪80 年代初,“平等会”收敛了锋芒,接受了美国主流政治的游戏规则,加入支持杰西·杰克逊总统竞选的彩虹联盟,为其竞选效力。[23]应当说,“平等会”之前动员“草根阶层”的经历为其登上美国主流政治舞台增添了明显的优势。他们对美国政治知根知底,对政治术语了如指掌,对如何吸引媒体的眼球了然于胸,因此,在主流政治环境中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此外,他们原先的背景和关系也十分有用,让他们能和民主党内的自由派、改革派、劳工派以及少数派系结成盟友。
“平等会”改走温和派路线后,积极参与主流政治,并得到一定的回报。1988 年,因为支持马里奥·科莫竞选州长成功,“平等会”首次从纽约州社会福利部门获得100 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搭建收容所,照顾无家可归之人。后来,纽约州住房与社区建设局向“平等会”提供专项资金服务唐人街社区,其主要项目也转移到了房产开发领域。为了开发保障性住房,“平等会”与当地银行、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及房地产公司有了密切的业务往来。9·11 事件后,“平等会”从曼哈顿下城联邦发展公司获得资金,与享受减税政策和拥有房产开发资质的私人开发商合作,当然,其中一部分是为低收入群体建设保障性住房。[24]
“平等会”经历了40 多年的风雨历程,其性质、宗旨、目标和活动内容几经变化,由“激进”走向“温和”,现今依然存在。它尽力为纽约华人社区普通劳工争取就业上的平等权利,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华人中赢得了一定的赞誉。
三、结语
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作为亚裔美国人运动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从校园斗争转向唐人街“草根阶层”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斗争勇气,努力为整个华裔尤其是底层“沉默的大多数”争取平等权利、谋取福利、赢得社会公正。但是,由于刚经历过“麦卡锡主义”,华社居民“噤若寒蝉”,不敢发表任何反对美国政府的言论。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遇到了一个共同问题:即尽管华人社区居民乐于接受他们的帮助,且对种族歧视和剥削深有体会,但对这些团体的“革命思想”都无法理解和认同。到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绝大多数华裔新左派组织自行解散,其中一部分人加入白人领导的一些左翼政党团体,如美国共产党、社会工人党等。少数华裔(亚裔)新左派团体,如华人进步会、纽约亚洲人平等会则逐渐转型为温和的民权组织,仍然致力于为华人(亚裔)乃至所有的少数族裔争取平等和公正。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不再具有“激进”色彩,而是遵循主流的政治游戏规则,采取法律诉讼、和平示威、集体协商、递交陈情信,以及动员普通华人选民参与投票选举等多种方式争取和维护在美华人的权益。
尽管华裔青年新左派团体存续时间很短,但却留下了重要“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些华人民权先锋无私无畏地斗争,并发挥教育和引领的作用,才使得普通华人民众的维权意识有所提升。他们服务社区的意识也开始在华社薪火相传,此后,社区中的民权团体和专业服务组织日益增多。可以说,今天整个美国华人社会之所以能在教育、就业、住房、选举、医疗保健等方面能够享有较为公正的待遇和均等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这些民权先锋的努力。
[注释]
[1] Him Mark Lai, “A Historical Survey of Organizations of the Left Amo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972;Him Mark Lai,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Press, 2010.
[2] Peter Kwong,Chinatown, New York: Labor and Politics, 1930-1950s, The New Press,2001.
[3] Yu Ren Qiu,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o f New York, 1930s-1950s, Philade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关于亚裔美国人运动的主要英文著作有:Yen Le Espiritu,Asian American Panethnicity: Bridging Insititution and Identities,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illiam Wei,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Fred Ho eds.,Legacy to Liberat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Revolutionary Asian Pacific America,S.F., Ak Press and Big Red Media, 2000; Steve Louie & Glenn Omastu,Asian American: The Movement and The Moment, 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Press, 2001; Michael Liu,The Snake Dance of Asian American Activism: Community, Vision and Power, Row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ing Inc, 2008; Daryl Maeda,Rethinking 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 Routledge Publishing Inc, 2011; Karen l. Ishizuka,Serve the People, Making Asian America in the Long Sixties, Verso: Imprint of New Left Books,2018;部分著作的评述另参见李爱慧:《美国学界对亚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研究的述评》,《世界民族》2012 年第5 期。
[5] 董娣:《亚裔美国人运动的缘起和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 年第2 期。
[6] 何慧:《冷战期间美国华人左翼青年团体的变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4 期。
[7] Shih-Shan Henry Tsai,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 p.169; Irene Natividad and Susan B. Gall eds.,Asian American Almanac, U.X.L: Thomson/Gale, 2004, p.112.
[8] Harvey Dong, “Third World Liberation Comes to San Francisco State and UC Berkeley”,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2009,p.95
[9] William Wei,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5.
[10] Tsung Chi,East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 : ABCCLIO, 2005, p.36.
[11] Peter Kwong and Dusanka Miscevic,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The New Press,2003,pp.283-284.
[12] [美]罗布·柯克帕特里克著,朱鸿飞译:《1969:革命、动乱与现代美国的诞生》,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5 页。
[13] William Wei,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p.14,pp.207-208.
[14] “大埠‘红卫兵党’政治史略(中)”,《团结报》(Getting Together),1973 年3 月3 日,第7 页。
[15] “大埠‘红卫兵党’政治史略(下)”,《团结报》(Getting Together),1973 年3 月17 日,第8 页;William Wei,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3, pp.98-110.
[16] Peter Kwong and Dusanka Miscevic,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pp.283-284。
[17] 《华人进步会成立》,《团结报》(Getting Together),1973 年1 月6 日至19 日,第8 页。
[18] William Wei,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p.216.[19] 《台山人在美国》第四期(2012 年),http://www.usa-taishan.com/ts04page02.php。
[20] William Wei,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20.
[21] Peter Kwong and Dusanka Miscevic,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p.293-295.
[22] William Wei,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p.222.
[23] Peter Kwong and Dusanka Miscevic,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p.296
[24] Peter Kwong and Dusanka Miscevic,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p.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