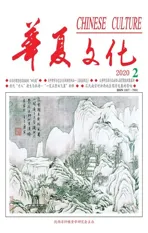义利并举:晋商票号的商业文化鸟瞰
2020-12-06张永华
□张永华
“票号”是近代银行的前身,由明清时期的晋商所创,承担着资金汇转、货币结算、商业信贷的重要职能,其产生远袭唐代的“飞钱”、宋朝的“交子”,近承明代中叶的“账局”,衰落于清末民初的中西文化交汇之时。作为中国近世商业资本演变的参与者、见证者,晋商的票号业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样貌,对票号兴衰历程加以鸟瞰,提炼其中的核心文化理念,有益于为今日探索中华商业文化的民族传统提供相关的历史经验。我们将从票号的兴衰、运行方式、文化理念三个方面梳理相关内涵。
一、票号兴衰
山西票号创立于道光三年(1823),是清代后期国内市场扩大和长途贸易发展的产物。票号成立伊始,主要是进行埠际贸易之间的商业汇兑,而此前的账局(票号前身)只经营存放款,不涉及汇转业务。票号的诞生,旨在弥补“汇兑”功能,至此形成了“存”“放”“汇”三位一体的中等银行业。
明清之际,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城市工商业取得一定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资本、商业信用、国内贸易的发展使得埠际之间货币流动量大量增加,单纯依靠现银的运输、结算难以满足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此契机下,晋中商帮中的平遥颜料商率先发明了“票号”结算业务。平遥颜料商主要经营丝绵制品的印染业务,据光绪年间的《山西通志》载,早在元朝时期,翼城县、襄陵县已“各设有织染局”(《山西通志》卷一〇〇《风土纪》)。到明代中叶,在两京织染局的基础上,又“置四川、山西诸行省,浙江绍兴织染局”(《明史》卷八十二),山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史载“明季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乾隆《潞安府志》卷八),丝机的增多,带来了生丝原料及丝绸产品的全国性调运,由此形成了生产、加工、贸易于一体的早期商业化局面,“海内殷富贡筐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平遥颜料商在其中拔得头筹,在平遥、北京、天津、汉口、吴城(江西)等地均有分社,这只是晋商所经营的诸多业务之一,由此可见山西商帮的茶叶、丝绸、印染、药品等各类商业网络已遍及全国。商业运转,必然伴随着赊贷行为,由此诞生了工商会票。平遥商会的西裕成(即“日升昌”)抓住机遇,遂创办票号,使得复杂的运现清算转变为更加便捷的汇兑清算,并为晋商的广域经营提供了资本运营的新平台,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商业贸易的新纪元。马寅初评价“今之谈商业者,每谓欧美银行组织完善,发达迅速,而吾国之银行业尚属幼稚,无足述者。尝考吾国银行业发轫于山西。盖山西出产,以盐铁大宗,丝煤次之,自给之外,余额悉运销于省外,年复一年,获利甚厚,遂成为中原富庶之帮。但经营盐铁在外省换得之现银,不可无特殊之机关以任运送保管之责,于是山西票庄兴焉”(《吾国银行业历史上之色彩》,《银行杂志》第1卷,1923年)。
二、运营方式与文化理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的表现形态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并强调资本在逐利的过程中客观上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我们回望票号诞生之际,能够发现明清时期的山西商团创造性地将传统社会依靠的血缘纽带、商品经济要求的劳资分离相结合,形成了信誉为上、义利并举的价值理念,由此构筑了票号的运营机制和文化根基。
受自然环境所限,晋商需背井离乡、辗转经营,由此造成了晋人勤俭朴素的精神,宋儒朱熹云“其地土地贫瘠,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诗集传》)。此外由于传统社会对于商业行为缺少有效的融资和监管方式,山西商团依据宗族、血缘、地域的纽带,创造性地形成了“劳资分离”股份化的票号经营模式,其特点是以“信”“义”为基础,追求“义利并举”的商业道德。“信”“义”的理念源于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其内涵多与“诚”相涉,如:“信,诚也。”(《说文》解字);“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白虎通·情性》);“定身以行事谓之信”(《国语·晋语》),其共通之处在于强调做事遵守承诺、认真负责、专心致志。“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为浮云”(《论语·述而》),儒家强调义利之辨,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故“义”的核心内涵要求责任担当、行动正义。“信”“义”构成了晋商票号所遵循的价值理念,更是其生产机制的道德基础。票号在架构上实现了投资(东家)与经营(掌柜)的分权制,投资方往往由山西本土的宗族、同乡、故交共同融资组成,经营则交由总号掌柜全权负责,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契约关系,但起到支配作用的是“信”“义”理念,因此“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成为晋商票号业共同的价值认同,清人刘锦藻云:“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清续文献通考》卷六十五)
晋商票号业将“信”“义”理念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如在经营管理人才的选择上遵循“任人唯贤”的原则,强调“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票号的业务对象多以山西商帮为根基,虽然票号的商业活动已脱离传统宗族故土,但宗族间、乡里间的血缘及宗族纽带依然紧密相连,形成了注重乡土亲情、共帮互助的营商理念。另外,在劳资分离的基础上,晋商票号业又逐渐形成了“学徒制”“阅边制”“顶身股”等管理模式,有力地将宗法血缘与股份化管理有机融合,使得原本相对冰冷的、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嫁接了宗法伦理的“仁义”理念,形成了“离土不离乡”(地缘性的行业共同体)的“分股共盈利”(股份化的利益共同体)的运营机制,促发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初期商业贸易的高峰。
三、晋商票号商业文化的历史意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形态划分为包买商、工场手工业、机器工业三个阶段,“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活动的增长”(《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4页)。晋商票号业的出现反映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初步发展,使得早期手工业场产品生产与全国性乃至初级国际化的工商贸易活动相结合,但其业务并没有完全围绕各地手工业场、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夹杂着鸦片结算、卖官鬻爵、军饷集转、筹措赔款等封建性的非商业性活动。清人李遂说“(乾隆六十年)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如放官债。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京师游手之徒,代侦某官选某缺,需借债若干,作合事成,于中分余润焉,曰‘拉纤’”(《晋游日记》)。侯外庐先生强调晋商票号业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初期殖民制度所为‘甜蜜的买卖’在中国古典经济基础分解过程中积极发展出的一种特殊的封建的剥削制度”(《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冬季号),这种封建性的依附关系,严重阻遏了它的转型与发展。故当清末西方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之际,晋商票号由于与清廷官僚资本的过度捆绑,加之经营业务的过于狭窄,一次次错失与现代工业资本相结合的机遇,遂没能实现向现代商业银行的转换。
总之,晋商票号的成功与衰落为我们呈现了在前现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一幅独特镜像。“义利并举”的道德理念使得传统社会的血缘纽带与商业管理得到有效整合,促成了晋商票号业的初步繁荣,总结相关的成败经验,对于今日民族商业文化的复兴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