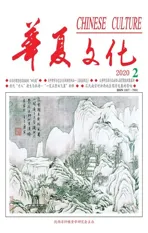义净所见西行求法僧人籍贯聚集现象探析
2020-12-06张少锋
□张少锋
唐贞观年间,玄奘西行求法之事震惊朝野和整个佛教界。玄奘西行求法事件的发生,实则为应对国内佛教发展困境而为之,是时佛教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且相关教义漏洞百出,一些僧人在如此困境之下将视野转向佛教发源地。有唐一代国力强盛,陆上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疏通和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则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渐趋兴盛。除此之外,安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使唐初得以休养生息,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国内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在此种主观和客观情况双重利好境遇下形成了前往印度求法的高潮。
一、僧人籍贯的分布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成书于盛唐时期,为义净所著。义净自幼出家,咸亨二年(671年),由海陆出发前往印度,其在那烂陀修行十余年。因武后称制,急需“称述符命”,特招义净回国,史载“天后敬法重人,亲迎于上东门外”((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三,第185页,引自《大正新修大藏经》,vol.55,No.2157)。
求法高僧传中记述了唐贞观年间至武后四十余年间五十六僧的西行求法事迹。该书成为研究是时中西海上交通,以及沿线国家风土人情的重要交通史料。此书之中对各僧籍贯进行了详细记述,其中共有唐僧三十四人,这些人中竟有十九人出自南方,而荆、益二州又独占十一人,占义净所见西行求法唐僧的近乎三分之一,占南方西行求法人众半数以上。何以荆、益二州倍出西行之人,尚需从两地佛教之发展谈起。
二、唐代荆、益两州佛教发展状况
中国南方地区佛教发展起于三国时期,而兴盛始于东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传统的政治经济要地中原地区战乱频发,人民流离失所,向北则为蛮夷之地尚不足以迁徙,而此时的南方地区则在孙氏政权的控制之下呈现出安定祥和的景象,促使北人南迁。已于东汉末年兴起的佛教也在此过程中传到南方地区,史载北方著名僧人支谦“以汉末沸乱,南渡东吴”((梁)释僧佑著:《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经记》,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6页)。此外,东吴统治者也对佛教采取一种较为开明的态度,支谦亦受到吴主的赏识,是时“吴主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即召见之……权大悦,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梁)释僧佑著:《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合首楞严经记》,《支谦传》,第192页)东宫之主即为之后的吴主孙亮,这对于佛教在南方地区的传播大有裨益。除此之外,尚有安世高和康僧会等人对南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东晋时期,北方地区的战乱使得人口进一步南迁,其中不乏高僧大德,钱大昕言谓“晋南渡后,释始始盛”((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一)佛教义理之学的兴盛
东晋时期南方玄学大兴,玄学在南方地区作为高品之学而在南方士族中广为流传。此时“善谈名理者,挟其所学,南游江淮。……捍卫之间,两晋之际,俱有学士名僧之南渡。学术之迁徙,至此为第三次矣。自此以后,南北佛学,风气益形殊异。南方专精义理……”(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页)。而佛教的传入,为适应当地文化氛围而向玄学靠拢重义理。唐长孺先生曾经指出“江南佛学之发达及其特点却与玄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南朝之所以重义解,也正是在玄学盛行的气氛中形成的。尽管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佛学义理日益明显,脱离佛经本义的玄学化倾向不再继续,但南朝佛教之重义不仅出于玄学,而且继续受到玄学的影响,并最终在更高的基础上玄学化”(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南方地区佛教义理化的发展对激发该地僧侣产生西行取法之宏愿发挥了重要作用,义净法师书中所载道琳法师西行求法源于“后复概大教东流,时经多载,定门鲜入,律典颇朽,遂欲寻流讨源,远游西国”((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33页)。润州玄逵法师,则“边闲律部,偏务禅寂。戒行严峻,诚罕其流。听诸大经,颇究玄义”((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45页);会宁法师亦“敬胜理若髻珠,弃荣华如脱履。薄善经纶,尤精律典。思存演法,结念西方”((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二卷,第76页)总而观之,南方地区佛教的义理化,致使南方僧人思辨能力普遍提高,通过对经义的详细研读,发现其问题所在,由此便产生了寻求原本之佛经的念头,使得其中的有志之士将目光转向了佛教的发源地,以期西行获求真知。
(二)荆州佛教发展概况
荆州“府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路,襟带江、湖,指臂吴、越,亦一都会也”((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52页),荆州之地地处交通要地,亦为南北交流枢纽之地。荆州佛教在汉魏时期已经开始流传,直到东晋时期,荆州佛教开始崛起。北方佛教南传之时,前往荆州及途径荆州之高僧大德数量可观,对荆州佛教之传播大有裨益。
东晋哀帝时期,释道安前往襄阳,宣扬佛法,“四方学士竞往师之”((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一卷,第177页),由此襄阳地区佛教大盛,其弟子亦积极向四周弘法,极大地促进了周围地区佛教的发展。两晋时期荆州佛教的活跃程度已经可以和长安等佛教重镇相媲美。据《高僧传》统计,两晋时期于荆州弘法的“义解”高僧达29人之众,远多于长安和健康地区的18人和12人(许展飞、陈长琦:《东晋荆州佛教崛起原因考》,《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第157页)。至隋及唐初期,荆州地区因其浓厚的佛教底蕴,吸引着高僧大德纷纷来此讲学,亦促进该地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智觊法师于开皇十三年(593年)前往荆州开坛讲经,是时“道俗延颈,老幼相携,戒场讲座,众将及万”((梁)慧皎等撰:《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盛况空前。至唐代,玄奘前往荆州讲学时盛况亦如同前,“时汉阳王以盛德懿亲,作镇于彼,闻法师至,甚欢,躬申礼谒。发题之日,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艺之士,咸集荣观。”((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页)
(三)益州佛教发展概况
佛教传入益州地区最早应在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至东晋时期,四川地区的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高僧慧远弟子慧持“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乃到蜀,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并络四方,慕德成侣……时有沙门慧岩、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倾盖,及持至止,皆望风推服。”((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六卷,第230页)开巴蜀佛教传播之风气。隋末唐初,战乱频发,此时江南之地亦受战乱波及,而四川地区则因相对安全而吸引着大量人口的迁徙,所谓“四方多难,总归绵益”((梁)慧皎等撰:《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其中迁徙之人中不乏僧侣。
蜀地的安定祥和,使一批高僧大德纷沓而至,在此地讲学立说。玄奘法师亦曾居于蜀地数年以宣扬佛法,“讲座之下,常数百人,法师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7页)。释神迥“拥锡庸蜀,流化岷峨……春秋六十五矣,四众哀恸,悲其来法来仪,未几而终,素怀莫展。益州官庶士俗,以同舟列道,争趋奔于葬所。素幢竞野,香烟蔽空;万计哀号,生动天地”((梁)慧皎等撰:《高僧传合集》,第206页)。
蜀地僧人外出求法至唐代已历数百年的时间,无论是僧人对外出求法的接受程度,还是其先辈经验的榜样作用均高于他处。四川为高山环绕,交通不便,从而导致蜀地佛教的发展较为闭塞。始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惟蜀中距当时佛教最盛之国都建康太远,义学水平不高,故蜀中有志之士每嫌‘州乡术浅’,下三峡趋建康,从名师进修多年,再西返乡土,始能盛为讲说”(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高僧传》之中亦载有释道汪“后闻河间玄高法师禅慧深广,欲往从之。”(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七卷,第283页)之思索者,亦有释法琳“常恨蜀中无好宗师,俄而隐公至蜀,琳乃剋己握锥,以日继夜。及隐公还陕西,复随从数载。”(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十一卷,第437页)四川地区佛教的发展促进当地僧侣集团以及佛学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佛教在基层的传播,使四川地区佛教拥有着较为广泛的信众。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则又激起了川蜀僧人向外求法之心。
四、结论
西行求法的僧人籍贯以荆、益两州为多。究其原因,其一,是佛教本身向外传播的需求。其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盛行玄学,佛教为适应当地文化氛围,故而在南传的过程中逐渐义理化。其三,荆、益二州的佛教发展基础较好。总而观之,因荆、益两州佛教发展使人们对于佛教适应社会的需要更加迫切,但在此过程中由于本土佛教逐渐陷入僵化,弊端丛生,从而激起了僧众思念印度之情,以求取真经,促使佛教不断被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