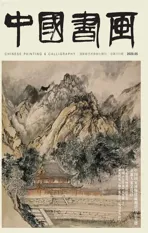祝允明论“胸中要说话,句句无不好”
2020-12-06樊波
◇ 樊波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自号枝山,江苏长洲即苏州人),明代著名书法家,著有《怀星堂集》,为后人所编。其中包含了他关于书法的重要见解。这些见解大都以题跋和记叙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系统,但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书法美学思想。他在“书述”一文中以“史”的框架视角对晋唐以后(尤其是宋人)的书法大加贬斥,从而表现了一种尖锐的批评意识。但他在具体论及宋人(如苏舜钦、苏轼)时又能作出中肯的评价。上述命题就与对宋人书法评价息息相关。
祝允明在一首诗中写下这一则命题。现节录如下:
多处不可多,少处不可少。大处不可大,小处不可小。胸中要说话,句句无不好。笔墨几曾知,闭眼一任扫。(《题草书后》)
一般来讲,书法理论比较注重用笔、结构以及章法布局等形式因素的探讨,而往往忽略对书法抒写内容的考究。这种倾向在明清的书法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中国诗歌理论有“辞情”和“声情”之分的说法,前者比较注重内容,后者则比较偏向于形式,但其实两者不能截然分割。书法艺术也比较偏重形式(声情),然而也不能忽略内容(辞情)的传达。唐代韩愈对于张旭草书的称赞以及对高闲书法的批评,就表达了这种审美诉求。祝允明上述诗跋命题同样重申了这一审美诉求。
所谓“胸中要说话”,就是书法家主观情意所构成的内容(这不等同于对书法形式筹划的“立意”),类似诗歌的“辞情”。在祝允明看来,这一内容的构成是决定书法成败的关键,只有做到“胸中要说话”,才能实现“句句无不好”。晚明李日华在论述绘画时也发表了类似见解:“古人绘事,如佛说法,纵口极谈……要在胸中实有吐出便是。”这里讲的“句句”之义,既指涉内容(胸中要说话),但主要是指形式。“句句”要做到“好”,关键在于内容的真实、充盈,从而遂泻发为“无不好”的形式表达。换言之,一旦有了真实、充盈的内容(胸中实有),那么形式表达就能做到“纵口极谈”,自然喷涌吐出,可谓“笔墨几曾知,闭眼一任扫”。
与这一诗跋命题相关,祝允明还多次提到“信札”这一书法体裁方式。孙过庭在《书谱》就曾提到王羲之“翰牍仍存”,还说“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翰牍”“翰札”就是指“信札”(还包括公文之义)。唐代张怀瓘在《书议》中也说:“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惟叙事。”这同样指出了信札尺牍达情叙事的功能。这些论述显然会对祝允明产生影响。在祝允明看来,信札书写所记载的内容最真实,也最贴切书法家的生活状态和主观心意,这就决定了信札的形式表达与其内容往往能够浑然一体,从而焕发出真切感人的自然情韵。祝允明在《跋文潞公三帖》中说“右潞公 手札之札,不过数十字,而辞意蔼然”,就是对这种情状的很好说明。继而他在谈到苏舜钦的“笔札”时作出了进一步描述:
苏氏父子、兄弟以文学鸣汴都,盛时传家笔札,擅声翰府。子美尤称独步。赞者谓“花发上林,月滉淮水”。其既遭一网之打,残章碎简,留迹极寡……允明在南京,中丞出示,抚玩竟日……如其锋颖秀削,清劲动荡,则“花月”二语颇得之。(《跋苏沧浪草》)
所谓“盛时传家笔札,擅声翰府”,是指苏舜钦所书写的“信札”具有很高的声誉。《宣和书谱》言:“断章片简,人争传播。”苏舜钦这一时期仕途顺达(盛时),并且放浪形骸。米芾曾说他“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这既是对他书风的描述,又是对他生活状态的写照。因而他的笔札“时称独步”,“其锋颖秀削,清劲动荡”,犹如“花发上林,月滉淮水”。这正表明苏舜钦的“信札”(笔札)是他顺达放浪生活的真实表露,信札的形式表现与其人生状态是息息相通的,这是一个正面的例证。祝允明还记述了一个反面的例证:
杜舍人以当时措置亡术,失山东巨镇,作罪言,信善论大事者邪?……因寓怀于挥写间,是固非漫浪为之者矣。太宰太原公取而珍玩之,盖特重书耳。(《跋太宰王先生藏饶参政书罪》)
这是一件“言罪”(措置亡术,失山东巨镇)自谴的书札。因此“挥写”与“寓怀”之间显然具有更为密切的关联,也更为真切地透露了作者的心态。而“非漫浪为之者矣”。
此外,祝允明还提到苏轼帖札所书皆为“报答十事”(如“极言蚝之美”,蚝者,毛虫也。或“言歙研发墨滑润”)。然而,作品却有一派“高逸之韵”,观之“属尤可敬爱”。还有一些“古人手札,书写内容或专谈国事”,“问及时政”,或为“日常事然”,“咨官业,谋家务”,如此等等。而形式表现则或“庄安宽博”,或“真率简古”,或“丰润茂密”,“短长意度,宽猛大小”,皆为“胸中要说话,句句无不好”。
祝允明所举的这些例证提示了一个道理,书法创作不能仅仅过于关注形式因素。书法的形式因素只有赋予了充实的内容才会获得真正的生命和更高的审美价值。而信札(手札)就是这样一种典型样式。实际上,魏晋至宋以来的许多优秀书法作品(如王羲之、颜真卿、苏轼)都是以“信札”(手札)方式流传下来的。它们的内容也多为“日常事然”,且辞意蔼然,辞情真切无饰,所以书写形式更加随意自然,因情而生,寓怀挥写。有的虽为残章碎简,但却被人视为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珍玩妙品。
我们看到,尽管祝允明在《书述》对宋中叶以来的书法作品作了无情批评和贬斥,但上述所提及的不少信札作者皆为宋人,可见书法作品一旦拥有了由真情实感所构成的充实内容并诉诸相应的形式表现,就会打动人,也会使他打破原有的偏见。
祝允明这一命题对于当今书坛一些人片面注重形式技巧而忽略真情实感,即将两者不是真正融为一体而是相互隔绝的倾向,也显然是一个并不过时的重要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