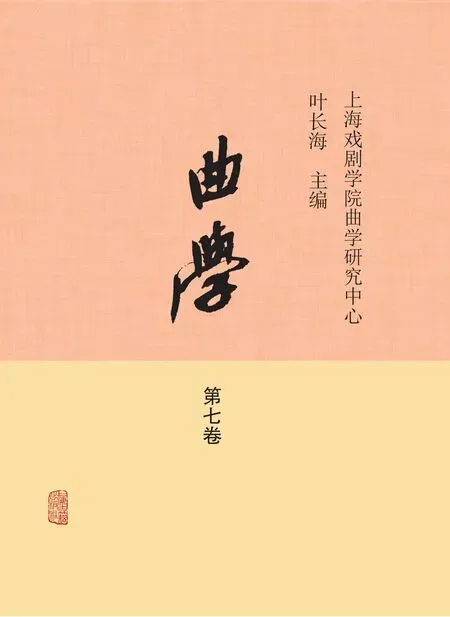试论清代前期的戏曲评点者*
2020-12-05张勇敢
张勇敢
评点者是戏曲评点的行为主体,其身份、思想、知识结构、评点动机影响甚至决定着评点视角与价值。在中国戏曲评点史上,最早的评点者是以书业射利、谋生的书坊人员。他们标榜“新镌”“新刊”,宣称“古本”“元本”,推出了大量集图像、音释、校注、评点于一身的评本,客观上推动了戏曲评点的发展。无论是今知最早的戏曲评本《古本西厢记》(嘉靖二十二年,1543),还是今见最早的戏曲评本《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万历元年,1573),都是出于书坊人员之手的商业型评本。大约在碧筠斋推出《古本西厢记》十年后,徐渭开始了“随兴偶疏数语上方”(1)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云:“先生居与予仅隔一垣,就语无虚日,时口及崔传,每举新解,率出人意表。人有以刻本投者,亦往往随兴偶疏数语上方。”按: 据徐朔方先生考察,徐渭“嘉靖三十一年迁居目莲巷,与其弟子王骥德仅一垣之隔。盖三十七年冬迁塔子桥,三十八年即徒(徙)”。参见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徐渭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8页。的评点工作,戏曲评点史上的文人评点由此滥觞。承继徐氏,李贽以强烈的批评意识进入评点领域,对《西厢记》《琵琶记》予以“涂抹改窜”(2)李贽《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云:“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惜不能尽寄去请教兄;不知兄何日可来此一批阅之。……《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参见《焚书 续焚书》,中华书局,2013年,第34页。,深化了徐渭奠立的文人评点传统。徐文长、李卓吾以名士身份从事戏曲评点,改变了万历前期重释义、轻评论的评点风貌,确立了源远流长的文人型戏曲评点。在徐渭、李贽戏曲评本声名远播的时候,书坊人员汲取名士评点资源,伪以“名公”之名评刻、刊售戏曲,戏曲评点迎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名公”评点时期,署为“徐文长”“李卓吾”“王世贞”“陈继儒”“汤显祖”“袁宏道”“魏仲雪”“孙鑛”的评本风行天下。
从明至清,戏曲评点的从业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书坊主及其周边文人的退出,又如“名公”评点之消歇,与此对应的则是文人评点的繁兴。清初圣叹先生的名号可与李卓吾比肩,清代书坊多次刊刻金批《西厢》,但却没有刻印“金圣叹先生批评”的其他评本。依此可说,昔日的商业元素已为戏曲评点界祛除,“书坊”这一特殊主体退出了评点前线,转居幕后而专心从事戏曲评点的出版、发行工作。时至清代前期(本文指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文人取代书坊人员,成为戏曲评点的主导力量,戏曲评点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清代前期的文人评者或许不如晚明评点群体精彩纷呈,但却有不容忽视的独特性,其评点话语、视角、理念呈现出全新的风貌。文人评者在完成格局调整后即流露出独特的评点意识,他们或者以“评”为“著”,或者自许“知己”,或者协作“合评”,或者倡导“参评”,为戏曲评点之繁荣与深化奠立了基础。
一、 “著述”: 主体意识的高涨
中国戏曲界流传着“曲无定本”的说法,不少作品问世后即步入流变历程,书坊刊刻校订之,优伶搬演删削之,文人亦出于一己兴趣进行改编。“评点”亦有增饰或删削戏曲作品的习惯,晚明臧懋循、冯梦龙、徐奋鹏诸人多有评改本传世。时至清代前期,一批挚爱戏曲的评点家,他们殚精竭虑地从事戏曲评点工作,或明或暗地透视出以评点为著述的意识。这种意识赋予评家自主评改、阐析作品的权利,评点据之突破了自身固有的批评功能,俨然成为一种文艺创作活动。
金圣叹是中国戏曲评点史上的评点名家,其《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具有典型的著述意识。在金氏撰写的《序》《读法》中,屡屡出现“圣叹《西厢记》”“此本《西厢记》”等表述,他有时更明确宣称“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金圣叹标举金批《西厢》,不是侵占他们作品,而是有其内在理据的。其一,金氏从作品演变的视角论证《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合法性。金氏《读法》有云:“《西厢记》是《西厢记》文字,不是《会真记》文字。”王实甫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理念,重新诠释《会真记》中的崔、张之恋,《西厢记》因之成为不同于《会真记》的新作;金圣叹以“空”“无”观念“腰斩”续四折,以自我意识释解《西厢》文意,以文法思想剖析《西厢》结构,其评改后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在文体形态、文学思想方面迥异于《西厢记》。从《会真记》至《西厢记》,再到“圣叹《西厢记》”,《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新著性质逐步确立。其二,金圣叹强调读者(包括评点者)能动性,认为读者的鉴赏、感悟可以构建新作。作为王实甫《西厢记》的读者,金圣叹坚称其品读生成为一部新《西厢》。他又在此基础上,将著述意识推而广之:“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3)以上引文见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首,顺治年间刊本。金圣叹彰显读者自主意识,认为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阅读活动之于文本生成的意义由此确立。借助金圣叹的评点理念与实践可知,读者的阅读、论者的评议都有撰著性质,评者的自主评点更具“创作”品格与意义。
金圣叹为自主评改、阐释寻求理论支撑,衍生出以“评”为“著”的著述意识,这种理念得到评点家的支持与拥护。首先响应著述意识的是毛声山,他从文法视角剖析《琵琶记》,正伏、反跌、顺补、逆补、相犯、相避等笔法构成了毛批《琵琶》的主要内容,古代戏曲的文体特征完全被文法思想淹没;另一方面,毛声山重拾《琵琶记》讽刺王四之主题,以“高东嘉为讽王四而作”之语开启“总论”,剧中诸多情节被牵强附会地与“讽王四”联系起来。以此可见,毛批《琵琶》富含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无论是戏曲结构之阐释,还是戏曲主题之诠解,都直观呈现了评点本不同于原著的一面。毛声山细分缕析,经其评批之后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已成“声山今日之书”,彭珑《第七才子书序》就此说道:“声山之前,无评此书者,而作者之才不出;声山之前,未尝无评此书者,而作者之才,终亦不出。自声山评之,而吾读之,使紬之绎之,击节而叹赏之,是《琵琶》之为《琵琶》,非复东嘉昔日之书,而竟成声山今日之书。”(4)彭珑《第七才子书序》,《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卷首,康熙年间刊本。该序高度评价毛批功绩,认为蕴含毛氏才学、思想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已非高明所著之《琵琶记》。彭珑不仅肯定毛声山的品评,而且高调宣称自己的阅读鉴赏,其间体现的正是接受者的能动性,这与金氏著者——评者——读者的建构理念一脉相承。
著述意识赋予评者自主阐析文本的权利,强调读者在新文本生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种以“评”为“著”的思想在清前期戏曲评点中持续发酵。作为《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评者之一的陈同,她痴迷于《牡丹亭》构设的“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生死情恋,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审美感悟融入其中,以此探寻作家的心灵世界和作品的艺术魅力。吴人认为陈同“评语亦痴亦黠,亦玄亦禅,即其神解,可自为书,不必作者之意果然也”(5)吴人《题序》,《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卷首,康熙年间梦园刊本。。除了吴人评以“可自成书”外,谈则也以“非必求合古人”(6)谈则《题序》,《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卷首。谈论陈同的戏曲评点,诸此都是对陈同恣意诠释的认可与表彰,也是对三妇评本文本生成的宣告。继此之后,评者程琼又表达了评、著一体的观点,她在《批才子牡丹亭序》序中明言:“信笔所至,可自成书,正不必尽与作者腹貌相属。”(7)程琼《批才子牡丹亭序》,华玮、江巨荣点校《才子牡丹亭》,(台湾) 学生书局,2004年。综上可见,诸多序跋者、评点者先后阐述自主品鉴、批评之意愿,无论是“不必作者之意果然”“非必求合古人”的三妇本《牡丹亭》,还是“不必尽与作者腹貌相属”的《才子牡丹亭》,都是对评者自由品评、自主论断的权利的诉说。依据这种诉求,评者可以根据阅读感受、人生体验评注曲意和剧情,陈同的“痴”“黠”“玄”“禅”批语或与汤显祖原意相左,程琼的亵喻批语或与《牡丹亭》文意相悖,但它们都是评者独特鉴赏感悟的记录与呈现,在此层面上这些评本“可自为书”。
在中国戏曲评点史上,明代戏曲评点家已经大刀阔斧地评改戏曲作品,清前期评点家不仅继承了这种“评”“改”合一的体式,而且宣扬以“评”为“著”的理论主张。他们堂而皇之地标榜著述意识,为评者自主诠释、改定提供内在依据,从理论层面确立了戏曲评改的合法性。著述意识为清前期的戏曲评点带来了勃勃生机,评点家们校订文本、增饰关目、重塑作品内涵,以艺术创作的理念细细品评,促使戏曲评点从先前的直书感悟走向深度阐释。
二、 “知己”: 评撰关系的期许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评点是一种个体化行为,评者可以自由择选品评视角,可以随兴发抒一己感悟。但对于处于流通领域的评点而言,它又有一种公共性质,为此评者不得不考虑剧作家、评论家的反应,不得不虑及万千读者的看法。如若评点不当,便会致使评撰关系趋于紧张,沈璟的评改行为便遭到汤显祖的嘲讽;同时也会导致评者与读者的对立,臧懋循的“四梦”评改即遭致不少读者的驳斥。在清代前期文人主导的评点格局中,古代文艺批评史上不绝如缕的“知音”论,作为一个议题进入戏曲评点界,成为评家争相标榜、引以为傲的头衔。沈西川评点程镳《蟾宫操》,说其“情文、结构,知音者自解”,自己作为“知音”群体的一员,只是借助评点形式“书其大概”(8)(清) 沈西川《评林》,《蟾宫操》卷首,康熙四十五年刊本。。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故设疑云,营造宾朋好友评点《桃花扇》之假象,其“重知己之爱”(9)孔尚任《桃花扇本末》云:“读《桃花扇》者,有题辞,有跋语,今已录于前后。又有批评,有诗歌,其每折之句批在顶,总批在尾,忖度予心,百不失一,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今皆存之,以重知己之爱。”道出了剧作家对知音评点的珍爱与赞扬。沈西川、孔尚任分别从评点家、剧作家的立场提出知己之评,表达了戏曲界对知己之评的重视。评者希望自己的评点工作称得上知音之论,剧作家乐于看到作品得到知音人士评析,那么知己之评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立足清前期的戏曲评点,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点:
其一,评点家熟悉剧作家,能够有效地评论作家、阐述作品。在中国文艺批评中,“知人论世”之说源远流长,戏曲评点中的“知己”说即导源于此。大体来说,评点家熟悉剧作家对于评点工作的开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对于评点质量的提升也不无裨益。在清代前期的戏曲评点中,吴人的《长生殿》评点堪称典型的知音之评,此以评者、著者的相似观点为例证。试观洪昇《自序》与吴人《长生殿序》: 洪昇自述《长生殿》的取材原则为“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10)(清) 洪昇《自序》,《长生殿》卷首,《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本。,吴人概括剧作的创作方法为:“采摭天宝遗事,编《长生殿》戏本。芟其秽嫚,增益仙缘。”(11)(清) 吴人《序》,《长生殿》卷首。洪昇强调《长生殿》“乐极哀来,垂戒来世”(12)(清) 洪昇《自序》,《长生殿》卷首。之寓意,吴人阐析作品“虽传情艳,而其间本之温厚,不忘劝惩”(13)(清) 吴人《序》,《长生殿》卷首。之深层内涵。从材料择选到作品意旨,吴人的见解与洪昇的观点惊人地一致。非但如此,吴人对《长生殿》文本细节的分析、评述,如戏曲脚色之调配、关目结构之布局等,更令洪昇啧啧称善,最终赢得洪氏“发予意所涵蕴者实多”(14)(清) 洪昇《例言》,《长生殿》卷首。之赞誉。吴人之所以能够有效揭橥《长生殿》的思想意旨和艺术魅力,这与评者、著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能分开。吴人与洪昇本为同窗挚友,两人师承毛先舒;吴、洪两家又系“通门”,洪女之则尊称吴人为“四叔”。吴人不仅评点洪昇的《长生殿》,而且评点了洪氏《闹高唐》《孝节坊》等剧,此亦两人密切关系之体现。可以想见,同窗攻读,饮酒作乐,诗文唱和,当为两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关系当为吴人有效评点的重要保证。清初以来,评点家与剧作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同窗、社友之评越来越多,廖燕《镜花亭》署“同学诸公评定”,汪光被《芙蓉楼》题“同人评校”,徐石麒《大转轮》《浮西施》分别题“同社诸子评订”“同社诸子评阅”。这些“同学诸公”“同社诸子”彰显着评点者与创作者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为知己之评奠立了基础。
其二,评点家能够客观审视原著,对其思想、艺术予以全面、公正地评判。明末《快活庵批点红梨花记》序言有云:“余见《梨花》传奇有两种,一为武林,一为琴川,实一事也。第曲白似临川者胜,而结构似武林者胜之。……予以评章如此,不知两家以我为知音否也?”(15)快活庵《梨花记序》,《快活庵批点红梨花记》卷首,明刊本。徐复祚、王元寿皆有《红梨花》传世,快活庵从“曲白”“结构”“奇快”“当行”等方面评判两剧,客观指陈二者的优劣长短。快活庵虽有诘问,但其心中早已自诩“知音”。其言论告诉我们,评者不能一味颂赞或批驳,而要从正、反两个维度全面审视文本,做到不溢美,不护短。从中国戏曲评点实践来看,这种公正原则难以真正贯彻,评点家或者只从自己偏爱的特定角度切入评点对象,或者仅仅从正面讴颂戏曲作品。前者如评者以词论曲,又如以文解曲,无视戏曲文体的独特特征;后者则以热情洋溢的颂词,夸饰戏曲文词之美、关目之佳,对作品讹陋之处避而不谈。合而言之,戏曲评点夹杂着评者过多的感情色彩,这种主观的、感性的品评反倒成了评点的一个突出特征,而评点批评所应秉持的客观原则则难以有效遵从。对于明清时期数量繁多的《西厢记》评点而言,绝大多数评者都有重前轻后、赞王贬关之情结。他们不遗余力地嘉奖前面四本,对第五本的四折内容则贬抑过度,致使有失公正的偏激之见屡屡出现。对此曲学史上的“王著关续”公案,清前期的毛西河表现出通达的态度,认为刻意扬前抑后非为知音所为:“若过为升降,极訾续貂,则又岂知音者哉?”(16)(清) 毛西河《论定西厢记》第十八折夹批,康熙十五年浙江学者堂刊本。毛氏觉察到《西厢记》前四卷与第五卷的差异,但他仍认为不能抹杀最后一卷的价值。在这样的理念下,毛西河相当公平地对待《西厢记》的各个部分,以校注、释解方式“论定”《西厢记》,实践着他所宣扬的知音式评点。
知己之评是一种理想的评、撰关系,快活庵、毛西河之诘问,是对这种关系的期许,它隐含着评家对率意而为的评点行为的质疑、不满,寄托着戏曲评点界构建公正原则之意愿。就中国戏曲评点而言,无论是书坊人员的鼓吹,还是文人学士发抒个体心性的品评,都容易偏离戏曲评点所应遵循的客观原则。与任意鼓吹、自主评判的评点不同,“知己”论潜含着戏曲评点界的另外一种声音: 公正。在他们看来,评者固然可以直书阅读感悟,但却不能脱离剧作的客观实际,不能违背作家的创作初衷。
其三,评点家与剧作家“才”“心”相若,有能力洞察、揭橥戏曲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知己”论对评者提出很高的要求,除了熟悉作家、公正品评外,评者自身的文艺修养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关乎着评家是否具备揭示作品奥妙的能力。李渔谈及金批《西厢》时说道:“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17)(清) 李渔《闲情偶寄》,《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第一集),黄山书社,2008年,第291页。王实甫《西厢记》流播四百年,赞其精妙者代不乏人,尊其曲坛魁首者不计其数,但只有金圣叹能够道出剧作美之所在。金氏“析毛辨发”“穷幽晰微”地品评《西厢记》,透析王实甫深心,理出《西厢》“三昧”,堪称王实甫《西厢记》的千古知音。
对于金圣叹、王实甫的知音关系,张雍敬《醉高歌自序》论述地更为明晰。人生难觅知音,文章同样难遇知己,张序即以“甚矣,文章知己之难”开启。在张雍敬看来,金圣叹拥有王实甫同样的“才”“心”,所以能够抉发作品魅力:“作者有其意,而读者或未之能解,圣叹独能解之;即作者未必有其意,而圣叹别以己意解之,能使读者皆信为实有其意。盖不唯使作者之精神尽出,而并使读者之精神与之俱出,斯岂非心即实甫之心,才即实甫之才,而两人如一人者與!”金、王“才”“心”相若,故圣叹能解普通读者之未解,能发作家内心之未发,且能令读者相信作家、作品原是如此。王《西厢》问世三百年得遇金圣叹,可谓“幸”“憾”参半。幸者为天生王实甫之后,又生一“心相同”“才相若”的金圣叹;“憾”者为实甫、圣叹前后相间三百年。鉴于上天不会同时降生两个才、心相同之人,与其等待数百年后的知己,不如自任知己,况且数百年后的知己也不如自己了解自己。在此理念下,张雍敬同时兼任“王实甫”“金圣叹”职责,动手评点三十年前创作的《醉高歌》:“第觉当日所命之意,皆今日我意之所欲吐,当日所造之语,皆今日我口之所欲宣。欣赏之至,爰为评之点之,是天生我于三十年之前,使我即为实甫;留我于三十年之后,是我即为圣叹,则亦造物之奇也。”(18)以上俱见张雍敬《醉高歌自序》,《醉高歌》卷首,乾隆三年灵雀轩刊本。至此,张雍敬从感叹知己难遇到自己充任知己,完成了从知己之评到自撰自评的过渡。在清前期戏曲评点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组作品: 丁耀亢《化人游》、丁耀亢《赤松游》、丁耀亢《表忠记》、朱瑞图《封禅书》、邹式金《风流冢》、张雍敬《醉高歌》、孔尚任《桃花扇》。这些剧作皆为自作自评之作,其中《表忠记》《桃花扇》《醉高歌》三种取得了很高的评点功绩,鲜明地体现了自评体优势。
在戏曲评点走过百年历程的清前期,戏曲界对戏曲评点的性质、价值有了明确的认识,对戏曲评点存在的问题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其间的有识之士,透过欣欣向荣的评点事业,看到了评点自身面临的危机。他们立足评点,发表了一些关乎评点态度、评点方法的言论,其间的“知己”说启发了评点界对评点原则的关注与思考。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评撰关系,知音之论的萌生寄托着构建评点公约的意识,评点家结合评点实践,给出了知人论世、公正客观、“才”“心”相若等答案。遗憾的是,这些评点原则难以真正落实,比如公正原则在清前期乃至清代戏曲评点中损丧严重,评者完全从赞赏角度评论剧作,缺少批驳否定的一面。以此而言,戏曲评点中的“知己”说虽然符合文艺批评之规律,但未能纠正、扭转一味赞颂的评点习气,故在戏曲评点史上的理论意义远胜于实践意义。
三、 “合评”: 评点主体的合作
万历三十八年,起凤馆刊刻了“李卓吾”“王世贞”合评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元本出相南琵琶记》,标志着戏曲“合评”体式之确立。明代末期,无论是署为“汤沈合评”的《西厢会真传》,还是标曰“合评”的《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三先生合评元本琵琶记》,都以“合评”方式刊、售戏曲文本。到了清代前期,文人从书坊手中接过戏曲评点的主导权,戏曲评点的机制、功能随之发生改变。此时评者往往对戏曲作品颂扬过度,有时更采纳合评方式极度彰显作家声名或作品意义,对文本予以超乎真实价值的判定。这种合评体式有两人合作而评,有三四人协作而评,又有众人分别题写批语的共评,诸此皆有颂扬作家、夸饰作品之功能。
“评点”理应是评点主体的个体行为,是评者基于文本优劣而自然而然地书写的品鉴感悟。但在戏曲评点中,诸多评本并非仅有一位评点家;一些情节简略、篇幅简短的杂剧作品,也常常冠有多位评点家的名字。顺治五年(1648),丁耀亢《化人游》刊发,对于这部十出的戏曲作品,其评者有宋琬、陆玄升、张词臣、丁耀亢、丘海石等人。更有甚者,叶承宗的四折一楔杂剧《狗咬吕洞宾》,参与评点的有叶承祧、一梧、林宗、黔僧、缨湖主人、情痴子、颠墨生等数人。对于上述两部作品,它们是以艺术魅力折服了多数评者,从而引发众位评家的一致好评,还是众人出于维系情谊之心理,对作品予以不切实际的好评呢?从作品自身和评点内容来看,我们更倾向于后面的一种推测。无论是成连大师度化何生的《化人游》,还是吕洞宾点化石介的《狗咬吕洞宾》,它们都不具备数人共颂的基础,尽管二者渲染的出世思想谙合部分文人的心理,哪怕二者的典雅文词、优美意境契合文人群体的欣赏口味。这种协作共评现象表明,以鉴赏、批评为旨的评点已然成为文人增强交际的媒介,并起到了扩大文本影响的传播功用。
不止上述二者,清前期出现了大量的合评本: 杂剧方面有吴园次、罗然倩、刘雨先评点的《买花钱》,有彭孙遹、王阮亭、曹顾庵评点的《桃花源》《黑白卫》;上述三部篇幅简短的杂剧皆为三人评点,传奇方面的三人评本有査慎行、胡季子、谈秋帆评点的《洛神庙》,有范梧、罗岱山、李凯评点的《寒香亭》,四人共评之作如瘦时山人、率真居士、灏川、升东评点的《温柔乡》,如陈同、谈则、钱宜、吴人合评的《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又如陈灿、汪上薇、吕璟烈、丁有庚合评的《四友堂里言》。在评点成员之多方面,《雨蝶痕》以评者众多独步于戏曲评点史,其罗列“参阅品评姓氏”达123人,详其姓名、字号与籍贯,其中不乏黄周星、李渔、吴伟业等戏曲名家。
晚明书坊以“名公”评点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名公”合评更是征服了千万读者的内心,比如起凤馆刊本“一得二公评后,更令千古色飞”,其“朝品评、夕播传”(19)起凤馆《元本北西厢记》序云:“自来《西厢》富于才情见豪,一得二公评后,更令千古色飞。浮图顶上,助之风铃一角,响不甚远与!朝品评、夕播传,鸡林购求,千金不得,慕者遗憾。”见曹以杜《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万历三十八年起凤馆序刊本。的流播情形见证着读者对合评本的欢迎。在商业因素淡出戏曲评点界的清代前期,旨在扩大文本影响的共评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借助文人之手异军突起。或许是剧作家主动向好友推荐并索评,或许是评点群体出于交际目的而言不由衷地颂赞,抑或是评家们确实深受感染而不由自主地批写,这些原因都与戏曲合评不无关系。合评可以有效地推动文本流播,评点者众多即意味着文本流传范围广,评点家的夸饰、赞叹又具有很强的鼓动效应,故多人共评隐含着文本传播之功利色彩。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合评建立了一种网络空间,它以评点对象为关联纽带,把评点者、创作者连接起来,成为维系、深化评点者与剧作家固有关系的工具。对这部分评点家而言,他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出文本价值的评价,评点俨然成为一种交际媒介;评点者、创作者在评点构建的文字世界中,加强了联系,维系了情感,评点因之超越了自身的品评功能。
四、 “参评”: 评点主体的对话
顾名思义,“参评”当为参与评点之意,是评者在他人评点的基础上从事评点之业,或对前评予以丰富与深化,或对前评予以批驳与修正。“参评”行为不始于清前期,但戏曲评点史上明确的参评意识却是清前期阐发的。毛声山论及参评甚详,其《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云:“以上前贤评语,章章如是,而予更有所论次者,举其引端之旨而畅言之,又举其未发之旨而增补之者也。予因病目,不能握管,每评一篇,辄命岗儿执笔代书,而岗儿亦有所参论,又复有举予引端之旨而畅言之,举予未发之旨而增补之者,予以其言可采,使亦附布于后,以质高明。”(20)(明) 毛声山《总论》,《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卷首,康熙年间刊本。毛批《琵琶》卷首《总论》列举“前贤评语”数则,这种引录或有尊重前人评点的意思,或有据以抬升自家评本的意图,但更重要的还是凸显自己对前贤的“畅言”和“增补”,从而彰显毛批《琵琶》独特的新意和价值。以其所论,“畅言”是对前人评点意趣的引申与深化,“增补”是对前人评点内容的增饰与补充。在《琵琶记》评点的历史长河中,毛声山“畅言”“增补”前贤未论之旨,相对于前贤之评,声山之评可谓参评;毛宗岗又“畅言”“增补”毛声山未虑之意,相对于父亲的评点,毛宗岗的“参论”亦为参评。
除《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外,《朱景昭批评西厢记》也呈现出显著的参评意识。钱季平《西厢记序》认为朱本“大都采辑诸家评论,而参附以己意”(21)钱季平《西厢记序》,《朱景昭批评西厢记》卷首,吴书荫主编《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第1册,学苑出版社,2004年。,张珩《录西厢记序》说朱景昭“以己意而合众人之说,以众说而参一己之意”(22)张珩《录西厢记序》,《朱景昭批评西厢记》卷首。。两序指出,朱景昭通过摘选批语的方式建构《朱景昭批评西厢记》,并在此基础上“参附以己意”。通览全本,剧中仅有少量朱景昭评点文字,大多数眉批、出批袭取金批《西厢》,卷首《西厢记总论》亦摘录金批《西厢》“读法”而成。朱景昭建立了一种集众说于一体、立己意于众评的新型评点方式,它对自己的参评工作毫不避讳,其《西厢记序》有云:“予因特检原本(金批《西厢》),取其评注之得当者,另录一编,间有缺略,散漫者附以臆见,稍为增损,如览之者如疏决河堤,悉遵故道。……又取明季诸先生各本,凡评论之有裨于文艺者,汇录焉。”(23)朱景昭《西厢记序》,《朱景昭批评西厢记》卷首。朱氏摘取金批《西厢》之佳批,并对其散漫、缺略处予以修正、增饰,摘录批语与参附评语合为一体。基于此,我们可以将《朱景昭批评西厢记》视为朱氏参与的、以摘录为主的参评本,上述“参附以己意”“参一己之意”即为参评的同义表述。
从毛声山的“畅言”与“增补”、毛宗岗的“参论”到朱景昭的“参附”,戏曲评点的参评意识渐趋明确,《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正式标出了“古荡钱宜在中参评”的旗号。该本上卷署“黄山陈同次令评点,古荡钱宜在中参评”,下卷署“清溪谈则守中评点,古荡钱宜在中参评”。就三妇评点而言,陈同在“情”的感召下不由自主地品评《牡丹亭》,并通过幻化为剧中角色的方式体悟、评议文本情事,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饱含感情色彩的批语。谈则对陈批爱不释手,于是“仿同意补评下卷”、“仿阿姊意评注一二”(24)谈则《题序》,《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卷首。,其间既有延续陈氏“情”“梦”解读、人物评议方面的评点,又有戏曲关目方面的阐释、评论。继陈同、谈则之后,钱宜“偶有质疑,间注数语”(25)钱宜《题序》,《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卷首。,增加了社会文化批评和校注方面的内容,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补充意识。吴人三妇先后参与《牡丹亭》评点,对于先评者陈同而言,次评者谈则之评即为参评,至于后来的钱宜之批更为参评,“古荡钱宜在中参评”即是对其评点性质的说明。
在中国戏曲史上,《西厢记》《琵琶记》等剧被人反复评点,各剧评本大都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就形成了纵向的评点序列。基于此,不同时空的评者实现了交流与对话,位居进程中的评点个体成为评点脉络中的一环,评点因之成为绵绵不绝的批评事业。处于链条中的评点者,他们择取前代批语,或铺排于评本之前,或引录于评本之中,建构了一种古今交流的评点模式,此二者分别以毛批《琵琶》、朱批《西厢》为代表。除了上述评本外,清初《西厢记演剧》中既有署曰“汪蛟门云”“李书云云”的批语,又有冠以“金圣叹云”“毛大可云”的评语。汪、李选录金圣叹、毛大可两位评点大家的评语,自然不是为了表彰他人评点功绩,而是在有理有据的臧否之中,更好地彰显《西厢记演剧》的评点思想、特色与价值。参评既包括上述跨时空引录,又包括那些援引亲朋、好友话语的评点行为。如《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之“吴曰”批语,表明吴人也参加了三妇评本的构建;又如金批《西厢》中的二十余处王翰(“斫山”)言论,涉及他对《西厢记》、金批《西厢》的评价问题,它们是“王翰直接、间接地参与《第六才子书》批评工作的力证”(26)陆林《金圣叹清初事迹编年》,《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3期,第234页。,若此则《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亦可纳入参评之列。
作为一种特定的评点体式,参评与合评多有不同,也与评点史上的评林有异。合评、评林是诸多评点家不分先后次序地评点作品,评者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明代的“三先生合评”系列即是多位评点名家批语之合刊,清前期数量众多的合评本亦是如此。参评这一术语本身隐含着明确的评点主次问题,且评点次序之意识十分突出。从主次方面来说,评者除了自己评点外,还会适时引录他人评论,这种偶一为之的摘引可以印证、补充主评的论点;从次序方面来看,后世评家相当重视前人的评点工作,这种引录可以凸显评者对已有批语的修正和引申。参评的评点意义在于: 戏曲评点是一种长久性的公共事业,评点家可以在他人评点基础上继续评点: 或者深化前人未尽之旨,或者增补时人未言之言,或者否定前人不确之批。借助“参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评点家,对某一评点对象产生的相同、相近、相反的观点,从而厘清某一文本评点的历史进程。在此类评点本中,读者可以看到各种观点的区别与联系,在比较中加深对品鉴对象的理解。在参评类评点本中,评点者不仅要与作者、读者展开对话,还要与以往的评点者进行跨时空交流,这一评点类型无疑具有深化戏曲命题、丰富评点体式的意义。
余 论
在中国戏曲评点史上,评点主体经历了颇为一个颇为显著的变化历程。晚明时期的戏曲评者不仅有以射利为目的的特殊评点群体——“书坊”,有引领戏曲评点风潮的文坛名士,有伪托文艺名家名号的“名公”,有深谙演剧、约定创作的戏曲行家,这为戏曲评点的快速兴起、持续兴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时至清初,戏曲评点主体的类型愈来愈少,文人化色彩越来越显。值得称颂的是,清前期戏曲评家的类型虽然有限,但其身份意识、自我定位颇为突出: 他们或者以“评”为“著”,赋予评者自主阐析、改定作品的权利;或者自许“知己”,试图建构知人论世、公正客观、“才”“心”相若之公约;或者协作“合评”,以超越文本价值的颂赞促进文本传播;或者倡导“参评”,借助古今对话的方式丰富、深化他人之评。上述鲜明的评点意识到了清代中后期逐渐退却,其间只有周昂部分承袭了前贤的评著意识,但却舍弃了更为重要的率性习气和创新精神;此时的绝大部分评点家与剧作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友朋、叔侄、夫妻、女父、师生、兄弟等评、撰关系不断涌现,戏曲评点很多时候成为宣传鼓吹、维系情谊的媒介。在这种情况下,评点家们亦步亦趋地品评文本,或者品味曲词,或者阐析文法,内涵丰富、视角多元的戏曲评点最终走上了彻底文人化的道路。时至清末,韩文举、洪炳文、剑光、杞忧生等社会型、政论型评点家崛起,他们借助评点体式抨击时政、评判现实,为古代戏曲评点带来了最后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