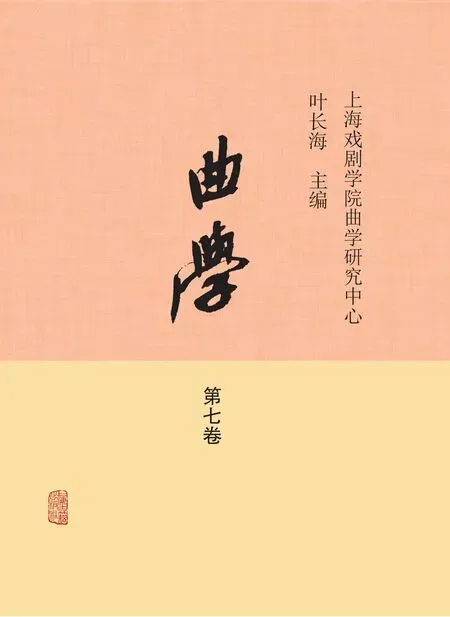昆曲源流及其变革*
2020-12-05俞振飞
俞振飞
香港中文大学要我讲讲昆曲源流及其变革,使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是这个题目,并不容易讲,所以又有些为难。难在哪里呢?第一,昆剧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过哪些著名作家,哪些著名作品?等等等等,很多文学史和戏曲史里面,已经叙述得很仔细,现在由我再来讲,不免“老生常谈”之感;第二,如果撇开这些,要谈曲律、唱曲、表演等等方面的源流和变革,有些问题由于缺乏具体资料可作根据,目前还讲不清楚。面临这两个困难,怎么办?我考虑再三,还应当按照自己的知识水平,对这个题目,试作解答,尽可能采取一些别的角度,谈谈个人的看法,或许详别人所略,略别人所详,以求正于各位方家。不然,不少地方,还会同别人重复,还会讲不透彻,这也该实事求是,承认是一种难以完全解决的遗憾,还请各位原谅,并加指教。
一、 昆剧的起源
昆曲又名昆腔、昆山腔、昆山腔水磨调、水磨腔、磨调等等,这是就声腔的音乐形成而言。如果作为戏曲艺术的一个剧种,就该把表演、舞台美术包含在内,它的别称则是: 昆腔戏(内分文武戏、武班戏两种)、昆剧。
大家都知道,中国戏曲的剧种很多很多,据解放以后的调查,达三百多种。多个剧种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有所不同;但决定一个剧种的主要因素,在于声腔。由于声腔不同,它们的歌唱、表演的手法和风格,就随之而出现千差万别。因此,声腔对剧种的构成条件来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昆曲,即今天所看到昆剧中的音乐形式,按照一般的历史记载,说是起源于明代嘉靖年间,公元十六世纪前期。当时有一位寄居江苏太仓的江西豫章人魏良辅把流行的四大声腔之一昆山腔,进行改革加工,成为一种新声,其特点是“转音若丝”、“流丽悠远”,这就是所谓昆山腔水磨调。但是,近年来发现了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金坛曹含斋跋语的魏良辅所著《南词引正》。魏良辅在此书中明确说昆山腔是元末昆山人顾坚所创,没有说成是自己创造了昆山腔,也没有说自己根据顾坚的昆山腔改革为水磨调。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原来南戏中昆山腔的曲谱,因此无法具体说明水磨腔前后的昆山腔有什么不同,起了哪些变化;我们只能暂时地根据一般记载,笼统地说,昆曲(或者说昆山腔水磨调)起源于明代嘉靖年间,由魏良辅在原有的昆山腔基础上改革而成。我们迫切希望通过文物工作的不断前进,能够获得确实的物证来进一步地、充分明确地解答这个悬案。
二、 昆曲的传布与兴衰
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徐渭(字文长,号青藤),也是一位剧作家,所著杂剧《四声猿》中的《狂鼓史》,别称《击鼓骂曹》,至今传唱。他的中年,正是嘉靖年间,写了一本《南词叙录》,对当时四大声腔中的弋阳、余姚、海盐三腔都不喜爱,唯独赞美昆山腔。他说:“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是荡人。”按照时代推算,他所推许的,正是魏良辅创改后的昆山腔水磨调,“流丽悠远”四字,也很符合水磨调的特点。他说“昆山腔止行于吴中”,也和水磨调初起时的情况吻合。这里的“吴中”两字,恐怕是指明代的苏州府,其中当然包含着昆山县。还有一个旁证是,当时另一位著名剧作家山东章丘人李开先所著的《宝剑记》传奇中,有一出《夜奔》,还在昆剧舞台上演出,这是大家熟悉的。但是,当他询问另一位词曲行家太仓王世贞: 你看我写的《宝剑记》《登坛记》,比起《琵琶记》来,怎么样?王世贞说: 你的文字很美,不必提了;不过要让吴中教师(指艺人)十个人唱一遍,随着唱腔把字句改得妥当些,才能传之于世。李开先听了,大为扫兴(见王世贞所著《曲藻》)。从这个故事看,昆山腔水磨调一开始,确实还有地区性的局限。
但是,时隔不久,到了万历年间(即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就迅猛地出现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新局面。应当肯定,明代万历一个朝近五十年中,是昆曲发展、扩大的鼎盛时期,它不仅在江、浙两省广为传布,而且一直传到北京,那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也都为这种新声而陶醉,设宴请客,都要“吴优”演出昆曲。王骥德《曲律》中所谓:“燕赵之歌童舞女尽效南声,咸弃其捍拨,而北词几废。”“南声”指昆曲,“北词”指弋阳腔。
与此同时,昆曲的旺盛气象,除了体现在专业艺人的舞台演出方面以外,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掀起了业余唱曲的高峰,更足以说明昆山腔水磨调这一种新颖的戏曲音乐形式所发出的影响,形成了极为普遍的人民文化艺术活动。
本来,从元代起就有许多唱“清曲”的专家,比如有一位燕南芝庵(真实姓名失传)曾写过一部《唱论》。大部分论的是宋元时期戏曲声乐理论、歌唱方法,原文太简约、晦涩,不易看懂,但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歌曲家的经验之谈。这一类专家,称为“唱家”。到了明代,延绵不断,名家辈出,蔚成风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每年中秋,苏州虎丘山千人石上的唱曲大会。沈君徵(宠绥)、袁中郎(宏道)、张陶庵(岱)、张山来(潮)、李笠翁(渔)等人都有诗文详细描写过这种唱曲大会的盛况。清初诗人莱阳宋琬(玉叔)有一首诗,虽只短短四句,二十八字,却能高度概括:
虎丘三五月华明,按拍吴儿结队行。一曲凉州才入破,千人石上夜无声。
既然万人争唱,怎么说是“夜无声”呢?难道是没有在唱曲?不是。这恰恰是因为高手在发挥绝艺,使环坐而听者屏息禁声,甚至“不敢击节,唯有点头”,进入了沉醉的境界中去了。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说过,清唱叫做“冷唱”,不比戏曲,因为没有锣鼓,没有表演,也没有躲闪掩盖之处,所以最见功夫。这种“冷唱”,在明代又称“冷板曲子”;后来把唱家唱的叫做“清工”,演员唱的叫做“戏工”。我父亲就是清末民初唱清曲的专家,后文还要谈到。
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直到南京的福王时期,昆剧仍是主要剧种。我们看到《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不是还请苏昆生教唱《牡丹亭·游园》吗?阮大铖不是写了《燕子笺》等四本传奇进呈福王御览吗?福王不是还把沈公宪、张燕筑、寇白门、郑妥娘等人选进宫去,演戏承值吗?演的《燕子笺》,还是昆曲。但是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这时昆曲的声势,已大不如嘉靖、隆庆、万历年代了。加上明皇朝覆灭,清皇朝入主中原,兵荒马乱,民生凋敝,梨园生涯大受影响。所以清初的李笠翁带了戏班,奔走江湖,尽管自编新戏,设计了灯彩场面,以图招揽观众,但也成绩不大。进到清代康熙中期,先后出现了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个剧本,文词非常优美,演出大受欢迎,昆曲的势头出现了新的气象。可惜,由于《长生殿》在皇后丧期演出,洪昇就遭遇不幸,削去国子监生,回到杭州,潦倒而死。孔尚任则起先很受康熙赏识,屡次升官。不过,后来皇帝看出了《桃花扇》中含有亡国之痛,不出半年,也被罢职回家。《长生殿》虽然传演到今天,而《桃花扇》就渐渐无人能演了。在此以后,还有一班官宦和富商(特别是扬州盐商)爱好昆曲,蓄养家班,而总的趋势已露出不祥的兆头,这是因为秦腔、徽调等地方戏曲开始抬头,观众的兴趣已有转移了。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庆祝皇帝万寿,形势急剧变化,秦腔、徽调、京戏等等兴起,北方剩一个昆弋社,时演时停,风雨飘摇,奄奄一息,濒于消亡。不少关心、爱好昆曲的人士,面对这样可悲的现象,除了叹息之外,也都束手无策,只好听其自然了。幸亏一九五六年,浙江国风苏昆剧团(现名浙江省昆剧团)整理改编了全本《十五贯》,演出以后,获得好评,并且成为“推陈出新”的榜样,把这一古老剧种救活了。现在全国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院、团,得到中央文化部批准,采取重点保护措施,沿着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不断前进,使我国古老、优秀、稀有的剧种——昆曲发出了复兴的光彩。
以上就是昆曲源流的历史概貌。我这样扼要地叙述,目的在于使大家先有一个总体了解。下面我将进一步对昆曲的主要构成因素,就剧目、格律、歌唱和表演四个方面,分别谈谈它们的源流和变革,有详有略,或简或繁,实事求是地加以介绍。
三、 昆曲的剧目
昆曲剧目的来源,最远可从宋、元南戏和元代杂剧算起;近则是明、清传奇和极少量的杂剧。在时间的跨度上,几乎包罗了整部戏曲史。因此,从昆曲的声腔创始人魏良辅算起,是四百多年;从剧目来说,将有八百年历史,就更悠久了。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剧作家,像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高则诚、施惠、徐渭、汤显祖、李玉、吴炳、洪昇、孔尚任等等,他们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像《单刀会》《汉宫秋》《倩女离魂》《墙头马上》《西厢记》《琵琶记》《幽闺记》《四声猿》《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清忠谱》《一捧雪》《西园记》《疗妒羹》《长生殿》《桃花扇》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是足以列入世界戏剧艺术之林而毫无愧色的,有些剧本也早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在世界各国了。根据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庄一拂所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的统计,共有戏文(即南戏)、杂剧、传奇总数四千七百五十余种,其中原本失传的三千多种,现存的一千七百多种,包括国内、国外的公家和私人所藏。这个数字,还是可说很丰富的。
但是,非常遗憾!这一千七百多种存本之中,除掉经过近年来整理改编的少数几种,像《十五贯》《牡丹亭》《墙头马上》《西园记》《西厢记》等等以外,绝大多数的整本戏,早已在传统昆曲舞台上失传了;换句话说,在上述那些整理改编本出现以前,以我近八十年的看戏经验来说,没有一个整本戏演出过,至多是几个折子连在一起演,传统叫做“叠头戏”,止此而已。举例来说,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牡丹亭》能演的折子较多,也不过《学堂》、《劝农》、《游园惊梦》(原是一出)、《寻梦》、《冥判》、《拾画》、《叫画》、《问路》、《硬拷》等几折,《南柯梦》只有《花报》、《瑶台》两折,《紫钗记》只剩《折柳阳关》一出。洪昇的《长生殿》总算保留得很多,也只是《定情赐盒》(原是一出)、《疑谶》、《絮阁》、《密誓》、《惊变》、《埋玉》、《闻铃》、《迎像哭像》(原是一出)、《弹词》等几出。再说,明、清两代的杂剧,虽不比元代那样兴旺,但作品也还不少,可是传统昆剧舞台上,明代杂剧只有徐渭的《狂鼓史》(即《骂曹》)一折,清代杂剧只有蒋士铨的《四弦秋·送客》和杨潮观的《吟风阁·罢宴》各一折。除此以外,再无别的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现存的一千七百多种本子,包含多少出(折子),姑且不论,就以这一千七百多种为基数,再来看看: 过去苏州全福班老艺人,号称能演八百出折子戏,岂不是在存本一千七百多种之中,每种演不到半出戏吗?后来仙霓社“传”字辈能演四百七十出,岂不是每种只能演四分之一出戏(略多些)了吗?当然,到目前,南北昆曲剧院团中青年演员能演的就更少了。
如果说,那么多的著名和较著名以及不著名的作家们,写出了那么多的优秀作品或者不是太优秀的作品,应当肯定昆曲剧目的“源”,是久远的、广大的,人们常提到的家底丰厚,对剧目来说,十分确切。至于剧目的“流”,反映在整本戏不能演,折子戏数量下降这两个问题上。昆曲由演整本到演折子是有“得”、有“失”的。由于折子戏的盛行,促使昆曲的表演艺术的提高,形成精美细致的艺术风格,这是很鲜明、很成功的“得”(这个问题,下文还要细谈)。然而剧目上的“失”,也是十分明显的。许多剧目,无头无尾,真是“前不把村,后不把店”,情节不贯串,不完整,叫人怎么看得懂?略举一二为例: 《西楼记》往往把《楼会》《拆书》《玩笺》《错梦》四出联成“叠头戏”,其实这四出之间,都有情节间隔,并不紧密衔接。特别是于叔夜在刘楚楚家,涂坏了赵伯将的歌谱,赵怀恨在心,到于叔夜父亲面前搬弄是非,使于叔夜不能再和恋人穆素徽见面。穆素徽只好剪了头发,寄给于叔夜,表达情意。在这里可以看出,于叔夜同赵伯将的不和,起了推动后面剧情发展的关键作用,但是于叔夜涂坏歌谱,赵伯将丢失面子,这场纠纷却在舞台上看不到,就使观众无法理解。又如《钗钏记》中,在《相约》以后,应当有《讲书》《落园》两出,再接《讨钗》,情节就很清楚。史碧桃小姐的父亲嫌贫爱富,意图赖婚,要女儿改嫁魏枢密家,史小姐不愿改嫁,差遣婢女芸香,去至皇甫吟家,约他中秋夜到史家花园来见面。芸香因皇甫相公不在家,就请皇甫老夫人转告,这是《相约》。皇甫吟与同窗韩时忠讲书,说起了这个约会,韩时忠力劝他不要赴约,这是《讲书》。韩时忠冒名赴约,与史小姐见面,史小姐以为来者是皇甫吟,助他结婚费用,钗钏及银两。韩时忠意图非礼,被史小姐拒绝,这是《落园》。史小姐不见皇甫吟前来迎娶,再命芸香去皇甫家询问,说起赠钗钏之事。皇甫吟未去赴约,哪里接受过钗钏?于是芸香要讨还钗钏,同老夫人吵了一架,这是《讨钗》(有的剧种称做《相骂》)。四出折子连起来演,情节非常贯串。可是在传统舞台上,有时只演《相约》《讨钗》(现在还有这样演法的),使观众看了,真是莫名其妙,为什么上一场是“相约”,客客气气,下一场就“相骂”,吵吵闹闹起来?好像这个丫头的神经不太正常。正因为舞台上删掉了三个人物(皇甫吟、韩时忠和史碧桃)和他们的行动(泄漏机关、冒名顶替和私赠钗钏),使这样一本以情节曲折为主心骨的戏,就失去了应有的特点,而大大减弱了观众的欣赏兴趣。
这种剧目上的“失”之所以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剧本篇幅冗长,结构松散,一本传奇二三十出还算是小的,四五十出的比比皆是;最长的像清代的《升平宝筏》《劝善金科》《昭代箫韶》等,整本戏达二万零四十出,请问如何演得全?如何看得完?就是那些二三十出和四五十出的整本戏,也只能适应豪门富户的需要,才能一连几天,吃酒看戏,通宵达旦,欣赏它的全貌。一般群众,怎能办到?因此,从当时(明代中后期)开始,已经产生了散出戏的上演,并且印行了许多种选集: 清代乾隆年间的《缀白裘》是典型的选本,流传甚广。我们可以从不少文集、笔记、日记之中,以及《红楼梦》里面,看到有关这种情况的叙述。
在剧本结构存在弊病的影响之下,许多本子无法演出,绝迹舞台。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损失!
我认为,从演整本到演折子,是演出剧目的一次变革,特点是“化整为零”,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两方面都值得重视。根据现在的需要来看,应当对演出剧目,再来一次变革。这第二次变革的特点是“缩长为短”,要比较自觉地吸取第一次的经验和教训,把剧本整理改编得完整紧凑,把表演处理排练得精当优美;在曲白的文学、声腔和唱念技法上,既要符合格律,又要容许在格律、范围内灵活掌握。我想,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一定会使许多传统剧目,出现新的面貌,从而受到观众欢迎。那么,这第二次的剧目变革,将是对昆曲优秀传统的最好的继承,也是最好的革新途径之一。
四、 昆曲的格律
文学艺术的一切品种都有它的特定形式,都有它的特定格律,戏曲艺术也不例外。戏曲艺术中的声腔是不同剧种的决定因素,所以声腔的格律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戏曲声腔分两大类,一类是曲牌体系,另一类是板腔体系。板腔体系的剧种很多,像京剧、徽剧、汉剧、越剧、淮剧、沪剧等等。曲牌体系的剧种已经很少,据说福建的梨园戏是其中之一,我很不了解;而昆曲是曲牌体系的剧种,则是人所共知的。下面谈谈昆曲曲牌体系格律的源流和变革。
曲牌体是昆曲的声腔形态,其结构很复杂,格律也很严。从结构的总体来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它有曲牌和联套两个层次,就是以一支一支曲牌为唱段结构的单位,比如一支[折桂令]是一个单位,一支[步步娇]又是一个单位,这是第一层次;几支曲牌联成一套,比如把[新水令]、[驻马听]、[折桂令]等几支曲牌联起来,叫作[新水令]套,把[步步娇]、[醉扶归]、[皂罗袍]、[好姐姐]等几支曲牌联起来,成为[步步娇]套,这是第二层次。作为一种声腔体裁说,总的结构情况就是这样,似乎是很简单的。
但是,谈到昆曲曲牌体的声腔格律,那就非常复杂了。因为曲牌体的具体运用是在曲词和音乐两方面体现的。对曲词方面来说,曲牌体就是昆曲的词式;对音乐方面来说,曲牌体就是昆曲的格律。词式和乐式,乃是昆曲曲牌体系的内涵。而词式有词式的格律,乐式有乐式的格律。词式和乐式既是“各有所司”,又要“互相合作”。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好像是商业上的联营机构。正因为如此,就要求词式的格律和乐式的格律之间,必须相互配合,紧密协作,不要彼此矛盾,破坏对方的格律。
所谓词式的格律,就是每一支不同的曲牌都有其一定的句数,每句有其一定的字数、四声位置和押韵位置。每一个不同的联套,都有其规定的多少曲牌、哪些曲牌,和这些曲牌的前后次序。关于词式方面的专门著作很多,比如: 《太和正音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南词定律》《钦定曲谱》《南北词简谱》等等,可以查阅。一般来说,这些著作要求既严格、烦琐,而且非常呆板,有些僵化,使人望而生畏。根据实际运用情况看来,词式之中,确实有其灵活变通的另一面的,但是长期以来,没有人把词式的宽和严的道理揭示出来,这样就造成两种各趋极端的结果: 一种是完全保守的、封闭的,死死抱住上述几本专著曲谱不放,好似荆棘丛中,难以举步;另一种则是去掉一切格律,独行其是,表面看来倒是“开放性”的进步和大胆行为,但是,他们落得一种订谱者无从下笔、演唱者难于张嘴的效果。即使勉强做了,还是不像昆曲,所以这是种鲁莽决裂的做法,不能为有识之士所接受。
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 历来所有的专著曲谱是不完整的,它们只是列出了曲牌体格律的一个方面: 词式,而缺少了重要的另一个方面: 乐式。这不是配套成龙的发电机组,怎么能够叫它运行起来发出电力呢?曲牌体的格律之中,何处应该严格遵守,何处容许灵活运用,必须要从词式和乐式两方面来寻找答案,才能解决。否则就像一辆汽车只有一边两个轮子,另一边没轮子,是永远行驶不起来的。但是,偏偏古人没有一部讲乐式的曲谱传下来,还不知道是不是从来就没有人写过。我们常用的几种曲谱,像《遏云阁曲谱》《六也曲谱》《春雪阁曲谱》《集成曲谱》《与众曲谱》,以及我编的《粟庐曲谱》《振飞曲谱》等等,都是唱曲用的谱子,不是乐式的曲谱,不能解决乐式的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对昆曲声腔传统的继承和改革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昆曲声腔的来源,许多戏曲史、音乐史上都说是受到了唐宋大曲、鼓子词、转踏、唱赚、诸宫调等等古代歌舞音乐和说唱音乐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这个说法,在许多古典论著中也曾写到,不能说没有根据,但这仅仅是文字叙述,谁也没有见到过这些唐宋乐谱,连元代的杂剧所唱北曲也没有传下一本谱子,那就缺少实物来作根据,没有办法具体地论证清楚昆曲声腔的来源。现在昆曲所唱的北曲中,还有几出元杂剧折子,像《刀会》《扫秦》《认子》《借扇》《五台》等等,但都已是昆曲化(水磨调化)的,有没有保留若干元曲声腔的原来面目在内呢?谁也不能指点明白,可又谁也无法否定。不仅如此,就说魏良辅创造了水磨调吧,也何曾有过具体物证——他写的曲谱留下来?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认为,还是当时的封建社会对艺人创作不重视,以致造成这样“文献不足”的严重后果。
因此,如果现在要研究昆曲的乐式格律,只能从其“流”来着手,也就是以现存的唱曲用的乐谱为根据,加以分析,提出理论,才有说服力。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到清代乾隆年间的叶堂(字广明,又字广平,号怀庭,苏州人)。有的论著中称他为“杰出的昆腔研究和整理者”,是完全恰当的。他生平整理校订和创作的曲谱有《纳书楹曲谱》正集四卷、续集三卷、补遗四册,《汤临川四梦全谱》;此外,还创作了《北西厢曲谱》,所谓“从来未歌之曲,付之管弦”(关于叶堂的唱曲艺术,留待后文再谈)。
从叶堂整理和创作曲谱这一事实上,可以看到三点,都是有关昆曲声腔变革的:
第一,叶堂对许多流行剧目的乐谱加以整理校订,总的精神是改正原谱的错误和加工提高质量,使之比前更为优美悦耳。他这项工作,虽然为当时“清工”唱曲艺术服务,但后来也促进了“戏工”的歌唱。他的“第一弟子”钮匪石(名树玉,苏州人),教授过著名艺人金德辉,还当场示范,把曲子的节拍和表演动作的腰肢、手脚尺寸紧密结合起来,加以指点,讲得头头是道,使金德辉佩服得五体投地(转引自陆萼庭著《昆剧演出史稿》)。
第二,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原是为江西的宜黄腔写的。虽然也采用曲牌联套体,但未能符合昆曲声腔的要求。有人把《还魂记》的曲文作了改动,汤显祖大为不满,由此与沈璟之间引起一场所谓的“汤沈论争”,成为戏曲史上一件著名的“公案”。叶堂则对“四梦”(当然包括《还魂记》在内)中不符昆曲格律的曲词,采用“集曲”的办法,订出了昆曲的乐谱,不仅恰当妥帖,而且精细优美,超过前人。周贻白曾在所著《中国戏曲史》中,把《纳书楹》同《吟香堂》两种曲谱举例比较。叶堂所用“集曲”方式是早已有的,但他这样运用是一种变革。
第三,从上引“以从来未歌之曲,付之管弦”来看,王实甫《西厢记》在清代乾隆年间早已无谱可依,无人能唱了。而叶堂把这部长达二十折的名著,订出了全谱,尤其是在元曲唱法完全消亡以后,进行这项工作,太不容易了!尽管这个乐谱,可能已非元曲面目,但对昆曲声腔的变革,正是一个重大贡献。叶堂所校订、创作的曲谱,流传至今,是份宝贵的音乐艺术遗产。所可惜者,他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升华为理论,为后人研究昆曲的乐式提供资料、指引道路。
说到这里,我可以报告一个消息。我的朋友王守泰、朱尧文、樊伯炎、陆兼之等十多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花费了三四年的时间,对昆曲乐式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探索和科学的分析,集体编写了一部《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南曲部分八集,共计一百四十万字,已经脱稿一年;北曲部分尚在进行之中。虽然几位看到过书稿的专家学者,对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一致给予充分肯定。但是由于资金困难,至今未能付印,使我深深感到惋惜。(1)编者按: 《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南套”部分,199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北套”部分,1997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然而,这部著作的编写成书,事情的本身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因为作者对南曲的近三百支曲牌,从音乐角度出发,把句逗、词段、主腔、板拍、旋律变化等事项,分析得非常清晰;对南曲若干联套方式,把首牌(主曲)、次牌、套牌、孤牌单套、合套、覆套、曲式等等,叙述得十分明确。全书有理论,有范本,有谱式,有例证,确是一份丰厚而珍贵的艺术财富。我在前面谈到昆曲乐式的奥秘,前人没有揭示,现在这十几位编写者努力写成此书,指出乐式和词式的紧密关系,为昆曲音乐艺术的继承和变革提出理论,开辟途径,将起到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我的老朋友们做了一件前人没有做好的工作,他们的贡献,绝不低于清代的叶堂。因此我乐于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想,曲牌体的词式,也需要有人把古代相传的几部词式曲谱,进行一次清理工作,结合乐式的研究成果,对词式的规范和法则,进一步地加以探索和总结。唯有这样,才能摸清昆曲音乐的规律性,这就是前人所谓的“声律奥秘”。然后在此基础上,搞突破、搞创新,有了优秀传统的继承性、延续性,这样的变革才能站住脚,是有益的和有效的了。
五、 昆曲的歌唱
上文说过,在宋、元时代,就有专门研究唱曲的“唱家”。在魏良辅时期,吴中著名的老曲师有袁髯、尤驼;同时娄东(太仓)张小泉、海虞(常熟)周梦山、梁溪(无锡)潘荆南都附和魏良辅的水磨调。还有张梅谷、谢林泉善吹箫、笛,为魏良辅伴奏。这些都在明代后期沈宠绥的《度曲须知》和余怀的《寄畅园闻歌记》中提到的。《度曲须知》中还说魏良辅所唱的曲子,其中有“拜星月”一支。这支曲子是《幽闺记·拜月》里闺门旦唱的,因此现在有人确定魏良辅是唱旦角的。不过,《度曲须知》中还举了“折梅逢使”、“昨夜春归”,应当属于散曲,不属于哪一个行当(家门)。根据我的亲身经历,理解到“唱家”有专工一个行当,也有泛唱各个行当的。我的父亲就能唱生、旦、净、丑,而以小生(包括官生、巾生、雉尾生、鞋皮生等)为侧重点,他教我习曲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认为,各个行当都有好曲子,都应当学,才能融会贯通,提高自己的唱曲艺术。所以,净角的《刀会》,老生的《酒楼》《弹词》《骂曹》,旦角的《游园惊梦》《断桥》《认子》《思凡》,丑角的《扫秦》《问探》等等,我都向父亲学过。当然也和父亲一样,以小生为主要习曲对象。我所熟悉的老曲友中、“传”字辈老艺人中,都有一些“多面手”,因此他们的昆曲知识就能随之而积累丰富。如果现在搞编剧、导演、谱曲工作的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将会对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好处。
正因为“唱家”历史悠久,所以“清曲”(“清工”)非常值得肯定。
第一,历代清工对唱曲艺术贡献很大。他们加工提高,并写出讨论唱曲的专门著作,如明代沈宠绥的《度曲须知》、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内容丰富精辟,对某些毛病和错误,加以揭示和纠正,直到现在,还有实际指导意义。
第二,在昆曲由盛转衰的近两百年中,专业艺人的舞台演出逐渐减少,而业余爱好者组织(曲社、曲会)的唱曲活动仍然活跃。且不提过于遥远的,就从我六岁开始习曲说起,八十个春秋之中,我在苏州、上海、北京等地,参加过好多曲社;就在本港,也和不少朋友一起唱过曲子。到了今天,不仅国内,甚至美国,不也有包括美国朋友的许多爱好者在展开唱曲活动,从而使我国这一优秀的文化艺术传布得愈加面广了吗?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南昆全福班散歇以后,就是由苏州、上海那些老曲友(张紫东、徐镜清、贝晋眉、穆藕初等)出资创办了苏州的“昆剧传习所”,于1921年秋季成立,开始教学昆剧。后来上海曲友们又成立了“昆曲保存社”,并为传习所继续筹募经费。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培养出了一大批“传”字辈艺人,今天他们都已七八十岁高龄了。现在昆剧舞台上的主要力量、一批一批青年演员是再由“传”字辈老师们培养出来的,昆曲艺术终于传了下来。所以,不能不说唱曲艺术的延绵不断,正是对剧种的薪火不绝,起了很为深远的积极作用。
具体说到昆曲歌唱的源流、变革,我必须回过头来,谈谈乾隆年代的叶堂和清末民初的我的父亲俞粟庐这两位昆曲界前辈。
过去,田汉曾经说过,昆曲有“四定”: 即定词、定谱、定腔、定板,是其他剧种所没有的。田汉这一评论,是非常符合实际的。所谓定词、定腔、定板都综合体现在定谱之中。明代人唱曲用的曲谱,我未曾听到过,可能已经失传了。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唱曲可用曲谱就是上文提到的《吟香堂曲谱》,刻印于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现在可以假设它属于明代曲谱的系统,继承了某些明代唱腔。隔了三年,即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叶堂的《纳书楹曲谱》刻印行世,在唱腔上有所不同。前面说过周贻白曾作比较。再隔一百六十一年(一九五三),我在香港影印了《粟庐曲谱》,是继承我父亲的渊源的。前后三种对比起来,就可以看出这些唱腔在随着时代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着。虽则“移步”不“换形”而一步步地在趋向精细,增高美感。这是一种曲谱上的变革。
至于具体如何唱,有了曲谱,还要会唱,就是要靠歌唱技巧,技巧有不同,效果也有高下。叶堂是著名的清唱专家,当时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说:
近时以叶广平(即叶堂)唱口为最著,《纳书楹曲谱》为世所宗,其余无足数也。
道光年间的龚自珍在《书金伶》一文中也说:“乾隆中,吴中叶先生(叶堂)以善为声老海内。”叶堂的“第一弟子”钮树玉曾教过苏州集秀班名旦金德辉(即龚自珍文中的金伶)唱曲,金德辉放弃原来的唱法,改学钮树玉的技巧,唱起来如醉如痴,声音细若晴丝,一字唱做几十个转折,结果把听客都唱跑了。金德辉烧掉了钮树玉的谱,钮谱竟至不传。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 第一,昆曲唱法确实有过流派,钮树玉唱的就和金德辉原先唱的不同,所以改学;第二,钮树玉的唱法不仅与一般不同,甚至和他老师叶堂也不一样。否则,为什么叶堂的唱口被人推崇,而钮树玉教了金德辉,金德辉却弄得狼狈不堪?第三,我的父亲是向华亭(松江)韩华卿学的曲子,韩是叶堂的再传(或三传,不清楚)弟子,所以吴梅(瞿安)先生称我父亲唱曲是叶堂正宗,而我父亲的唱法,并没有钮树玉的毛病;第四,曲谱是死的,唱法是活的,关键在于运用。我父亲的唱法,在《度曲一隅》昆曲保存社同人的跋文中,有很好的概括:
其度曲也,出字重,转腔婉,结响沉而不浮,运气敛而不促。凡夫阴阳清浊、口诀唱诀,靡不妙造自然。……试细玩其停顿、起伏、抗坠、疾徐之处,自知叶派正宗,尚在人间也。
所谓《度曲一隅》,是我父亲七十五岁那年(一九二一),为百代公司灌制十三面唱片的曲谱,由我父亲亲笔书写,合订成册。可惜当时录制技术水平不高,尺寸又快,效果不能和今天的录音带相比。“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人为我翻录了磁带,音质很不理想。由于我父亲教授不少学生,称为“俞派”,在江南、浙西的影响很大,人称“曲圣”。连印度泰戈尔纪念馆中,至今还保存着他的一张唱片《三醉》和《拆书》(引自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上述《度曲一隅》跋文所说“出字重,转腔婉,结响沉而不浮,运气敛而不促”四句,是我父亲唱曲风格的特点,对于有些唱口一味在高而细上追求所谓“效果”、“味道”,正是一种变革。请问,如果音色、音量,不亮而暗,不堂而瘪,使听者侧耳不闻,怎么还有美感?我从小接受了父亲的教诲,可以说至今还是守着“家法”的,下面就扼要介绍一些“俞派”唱法。
我父亲教授昆曲,曾经指出必须重视字、音、气、节四项。所谓“字”,是指咬字要讲四声、阴阳、清浊、尖团、出字、收尾、双声、叠韵等等,也就是《度曲一隅》跋文中的“凡夫阴阳清浊、口诀唱诀”。所谓“音”,是指发音部位、音色、音量、力度等等,就是跋文中的“出字重,转腔婉,结响沉而不浮”。所谓“气”,是指运用“丹田气”来运气,以及呼吸、换转等等,就是跋文中的“运气敛而不促”。所谓“节”,是指节奏的快慢、松紧,以及各种特定腔格的运用,就是跋文中的“停顿、起伏、抗坠、疾徐”。关于“字、音、气、节”四个方面的详细内容,我在《振飞曲谱》前面的《习曲要解》中逐一作了分析和叙述,可请参考。因为篇幅较大,不在这里多说了。
现在需要提出的是,“字、音、气、节”四项属于唱曲的技巧法则,掌握和运用这些技巧法则的目的则是表达曲情。我父亲在《度曲刍言》中说过:
大凡唱曲,须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一种神情。问者是问,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消,不至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不至稍有瘁容。宛若其人自述其情,忘其为度曲,则启口之时,不求似而自合,此即曲情也。
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戏剧中的人物,有悲欢离合的各种遭遇,这是故事情节;在不同的遭遇中,就会产生喜怒哀乐的不同感情,这就是人物内含的“意之所在”;当他以歌咏形式向外表达之时,声音中含有各种情绪,这就是“唱出口时,俨然一种神情”。唱曲者应当把人物的感情体会深入,才能达到“曲曲传情”的地步。试举一例: 唐明皇李隆基对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极为真挚、深厚,但在整个相爱过程之中,不同阶段的具体情节在变化着,因而他的心情也随之变化。以后半部的《惊变》《埋玉》《闻铃》《哭像》四出戏来作比较: 《惊变》前段《小宴》时,御花园中饮酒歌舞,何等欢悦;《埋玉》中兵荒马乱,气氛紧张,唐明皇迫于兵变形势的威胁,不得不割恩正法,赐杨贵妃吊死在梨花树下,既是悲痛,又出于无奈;《闻铃》是在蜀道中逃难,路经剑阁,听到雨中铃声和杨树萧萧之声,一片凄凉,痛定思痛; 《哭像》则身居成都,为贵妃建立祠庙,看到用旃檀香刻的神像,宛然杨玉环生前一样,愈加增强他晚年的凄怆心情。同是这位风流天子,前后精神状态各不相同,这就是剧中人物在不同环境里的所谓“心理层次”和“感情层次”。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是同一个曲牌,还应当唱出不同性格,这也可以举例说明之。[红衲袄]是散板曲,在《琵琶记·盘夫》《连环记·掷戟》和《西楼记·拆书》中都有。三个人物,三种性格,各有特点: 《盘夫》蔡伯喈中了状元,皇帝赐婚,入赘牛府,虽然富贵荣华,倒还想家中父母妻房,心中矛盾重重,可又不敢声张,是一种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懦弱性格。在牛小姐的盘问之下,他还吞吞吐吐,躲躲闪闪,不敢讲真话。《连环记》中的吕布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反复小人,又是无耻的好色之徒,见到董卓在凤仪亭上调戏貂婵,醋劲大发,打算和董卓拼命。他的[红衲袄]就要唱出狂妄急躁的性格和剑拔弩张的气氛。至于《西楼记》的于叔夜则十分痴情,是古代官家子弟和读书相公的一种典型。他眷恋名妓穆素徽,被父亲发觉,拘禁在家,不能与恋人相会。穆素徽暗中送信,信里并无一字,只有一幅素纸,一股头发,使于叔夜大惑不解,更加烦闷。他唱的[红衲袄]夹有念白,比较别致,要刻画出他拆封前的惊喜和拆封后的不安,同时揭示其性格特征。《掷戟》的一段念白和《拆书》的[红衲袄],我早年有过唱片,时隔多年,恐怕早已很难找到了。
在唱曲艺术中,“字、音、气、节”和“曲情”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紧密关系,忽视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有的人只知道讲究技巧,满嘴的“上尺工凡”、“鸡鸭鱼肉”,而不体现曲情,且我父亲的说法这是“叫曲”,而不是唱曲。反过来说,有的人自以为懂得人物的内心世界,只用声音来硬挤感情,其实一点儿没有技巧基础,我觉得这是“用钝刀子割肉”,没有办法使观众接受的,更谈不到艺术欣赏。如果这样也叫“变革”,那就变坏了,只是一种损害昆曲的“变革”,当然是不足取的。
六、 昆曲的表演
我国戏曲的表演艺术的来源,有人追溯到唐、宋大曲中的“乐舞”,有人考证了宋杂剧、元杂剧的表演,不管这些和昆曲表演的关系是远还是近,是间接还是直接,我既尊重这些论著文章是有根有据的,但同时又觉得根据不太足够,因为遥远的唐、宋、元时代怎么能像今天那样有照相、电影、录像的科技条件?又怎么能拿出具体的形象资料来阐述清楚呢?这是无法解决的遗憾。那么,明代中叶昆曲盛行以后,艺人们是怎么演的呢?我们也只能在某些散文、笔记之中看到一鳞半爪的记载,想象当时确已有边唱边做(也就是“载歌载舞”)的表演方式,然而还不是完整的资料。直到清代道光时代,出了一部书,名为《审音鉴古录》,它记下了几十出折子戏的剧本,在曲白的下面和行与行之间,注明了身段动作,有的戏还有眉批和总批,这才有了整出戏的“身段谱”(据说另有一种周明泰写的《昆曲身段谱》,藏在上海图书馆中,我没有见过)。这部《审音鉴古录》记录的都是乾、嘉时代艺人的实际表演,我想,到现在为止,如果要找昆曲表演之“源”的话,这部书还好是比较具体的仅存资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存在两点情况: 其一,书中记录的《牡丹亭·游园惊梦》的身段动作,和今天舞台上见到的还有不同,很可能后来又经过加工而更丰富了。所以,前面的表演,只能是仅仅对后人的表演起了“开源导流”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是非常了不起的。其二,书中记录了《荆钗记·上路》一出,是乾隆年间扬州“老徐班”演老外的孙九皋所首创的身段动作。原来的苏州全福班没有这出戏,后来我亲见全福班老艺人沈月泉和苏州曲友张紫东两位(沈是我的老师,张是我的挚友),按照《审音鉴古录》的记录,一字一句地共同“捏”(即排戏,又名“踏戏”)出来。后来就连前面一出《开眼》演出,成为南昆的传统剧目,动作繁重而优美,至今上海每演必得好评。从这个意义来说,《审音鉴古录》的记录就成为“源”了。
全国解放以后,我的老友徐凌云记录了《昆剧表演一得》三集(第四集原稿已在十年动乱中损失了),华传浩记录了《我演昆丑》,都有身段动作,也有心得体会,是可贵的具体资料。据闻浙江的周传瑛、王传淞两位也记录了他们的表演艺术,有待于出版问世。当前,昆曲界已经采取录像的方式,录下了若干戏的演出实况,当然更为具体,更为完整。倘若持之以恒,逐步积累,将使昆曲艺术的资料宝库,日益丰富起来。
下面介绍一些昆曲表演手段和个人点滴体会。
昆曲和其他剧种一样,舞台的表演是有一定程式的。曾经有一段时期,评论界较多的看法认为,戏曲是表现的艺术,不是体验的艺术,所以比较虚,比较假;特别提出“程式化”这一概念,作为戏曲表演的最大缺点来加以批评,从而主张否定掉程式。自从黄佐临先生指出: 斯坦尼体系是“体验派”,布莱希特体系是“表现派”,以梅兰芳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则是“体验”和“表现”的结合,具有中国戏曲艺术的特色,是自成体系的。佐临对此,作了详细透辟的阐述,大家的认识逐渐一致起来了。至于程式和程式化的问题,我曾在广州的《羊城晚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谈了一些看法。我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有其特定的形式,也可以称作“程式”,运用程式的目的在于表现内容。对戏曲表演艺术来说,就是塑造舞台上的人物形象。手段的运用有高有低,这是舞台效果好坏的原因之一。所以程式本身,不应当对效果好坏负责,该负责的是演员的运用恰当与否,完美与否。我反对人物的“程式化”,主张程式的“人物化”,就是说不必取消程式、废除程式,而要求运用程式来很好地表现人物、塑造形象,才符合戏曲表演艺术的要求。
既然说到程式的运用,那就首先要讲程式的规范化。如果身段动作不合规范,就失去昆曲表演艺术中舞蹈语言的基础。当然,生、旦、净、丑的程式规范是不同的。以旦角来说,昆曲的正旦、四旦(刺杀旦)、五旦(闺门旦)、六旦(贴旦),分行较细,程式也有差异。我们演小生的,小生分: 官生、巾生、鸡毛生、鞋皮生。官生之中,还要分大官生、小官生;大官生还有戴“口面”(京剧叫“髯口”)和不戴口面之别。他们的手法和步法,就有姿式和尺寸的差别。
除此之外,还有服装的运用,褶子、官衣、帔、蟒、靠等等的飘带、翎子、袖子、角带、帽翅、丝绦、鸾带等等;还有小道具的运用,扇子、书本、画轴、书信、状纸、拂尘、念珠、酒杯、烛台、瓷枕、马鞭等等,以及某些兵器,如剑、枪等。这里都有程式,也有规范。不合规范的话,就破坏了程式的美。
假如有人问: 戏曲表演的创作过程中有没有“体验”这一层次?我认为是有的,不过传统说法,不叫做“体验”,而唤作“设身处地,相情度理”。这是昆曲前辈沈月泉老师常说的。我在这里,可以引用明代两位昆曲艺人的故事,来作证明。
第一位名叫颜容,字可观,江苏镇江人。他演《赵氏孤儿》(昆曲名为《八义记》),扮以公孙杵臼。由于没有感动观众,效果不佳。回到家里,左手捋髯,右手打自己面颊,打得两颊都红。然后对着穿衣镜,抱一个木雕的赵氏孤儿,说一番、哭一番,把孤苦凄怆的感情,发挥得淋漓尽致。下一次再演这出戏,竟使千百观众看了,大为感动,有人失声痛哭。他回到家里,重又对着穿衣镜里自己的形象,深深作揖,说道:“颜容真可观矣。”他巧妙地借了自己的姓名(颜容)和表字(可观),意思说: 你今天表演中的颜容(面貌、形象)才真正可以一看了(可观)。这不是演员的内心体验和外部表现结合起来以后,才能塑造出精彩动人的舞台形象吗?
第二位,明末南京兴化班有一位艺人叫马锦,扮演《鸣凤记·河套》中的严嵩,演不过另一戏班华林班中姓李的艺人,非常失面子。他一气之下,离去戏班。听说当时的宰相某某人,跟严嵩的为人差不多,就跑到京里,在相府中当了三年佣人,天天侍候相爷,观察他的举止,倾听他的讲话,刻苦揣摩体会。三年以后,他回到南京,再和华林班李姓艺人比赛演技,演来得心应手,神情逼真,使华林的李姓演员跪在地上,请求收做徒弟,认真学习。这位马锦先生真是深入到生活中去,才能大大提高其表演艺术;也说明古代的戏曲演员,并非不懂“体验”,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效果。
但是,正像唱曲艺术中“字、音、气、节”和“曲情”的关系一样,在表演艺术中,“手、眼、身、步”的程式是基础,是手段。如果没有这个手段,或者基础不扎实,那就不可能把塑造人物形象的任务完成得好。请问: 演员只重视体验,而不重视表演的话,人物的内心活动再复杂,感情再丰富,而在外形动作一无表示,或者表示得不准确,不恰当,怎么能使观众看得懂?特别是戏曲并不像话剧、电影那样单有念白,而是念白之外,还有歌唱。如果不用形体动作配合一起,这些长长的唱段就很容易把观众唱跑了。所以“载歌载舞”应当是各种戏曲共有的特点,不过轻重分量有所不同,而昆曲的这一特色则更为鲜明。梅兰芳的体系,表现和体验相结合的创作道路,追根溯源,还是以昆曲传统为其前导的。梅家是著名世家,但在梅巧玲的时代,北京还有昆剧班,而且高手不少。比如产生所谓“同光十三绝”的时候,前后有王桂官(小生)、汪桂林(旦)、钱阿四(正旦,陈金爵之婿)、曹春山(老生、曹心泉之父,曹二庚之祖)、徐小香(小生)、朱莲芬(旦)、杨鸣玉(丑)、乔蕙兰(旦)等人,都是名噪一时的好角。过去北京京剧科班学生,都要先学若干昆剧,奠定基本功夫。所以杨小楼、余叔岩等,皆能演几出昆曲。梅兰芳先生也曾请乔蕙兰和南方的丁兰荪教过昆剧,我和他合作多年,就从《游园惊梦》开始的,中间又演过《断桥》《贩马记》等戏,最后以合演《牡丹亭》电影结束。他在中年到过美国、日本、苏联演出。在苏联演出了好多场《刺虎》,有一位老太太问他: 我看了几场《刺虎》,为什么每一场都有所不同?斯坦尼先生在梅先生身旁,就给这位老太太解释: 这就叫做“有规则的自由活动”。斯坦尼的这句话,说出了一切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质,当然包括中国戏曲,也包括昆曲在内。我理解到,昆曲的歌唱、昆曲的表演,都应当遵守规范,运用程式,而在程式的规范的范围以内,容许演唱者根据人物特点和演员本身条件,灵活处理,程式和规范只有处理和运用的高低之别,不存在“有”和“无”的问题。换句话说,程式和规范可能变化、发展,但没有程式、规范的文学艺术恐怕是不可思议的。那种废弃程式的主张,实际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七、 结束语
上面扼要介绍了昆曲的剧目、格律、歌唱和表演的源流和变革的部分情况,当然很不完备。如果要求全面和详细,非但不是一两次讲演所能完成的任务,就是写成文字,恐怕上百万字也解决不了。这是因为昆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太悠久了,剧作家太众多了,剧目太丰富了,而歌唱和表演的技艺法则和艺术手段又那样优美、那样深邃。坦白地说,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讲得完整、讲得清楚的。应当把昆曲看成是足以代表中国戏曲艺术的典型之一,而加以深入研究,升华为理论,以指导艺术创作的实践,很有必要独立建成一门“昆曲学”,作为中国戏剧艺术学的分支之一。我设想: 昆曲学的研究意义、学术地位和审美价值,将不低于“红学”“三国学”等等的。这是我在结束讲演时需要提出的第一点建议。
其次,自从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香港也有同胞爱好昆曲,唱昆曲;当然据我所知,在此以前,也有不少老曲友居住香港,并且有唱曲活动。在美国同样如此。我的老朋友项馨吾先生是昆曲专家,久住美国,可惜前几年已经去世了。但是还有不少老朋友,像李方桂伉俪,张元和、张充和两位姐妹,以及罗锦堂教授等,都对昆曲深有研究,造诣很高,还有我的昆曲学生杨世澎、孙天申也在美国。特别值得提一下,据知,有几位美国朋友也能演唱昆曲,真是令人兴奋的事!因此我感到,不论中国和友好国家的昆曲爱好者(包括专业和业余),应当团结一致,通力合作,把振兴昆剧的工作共同担当起来!我们要有艺术实践活动,写昆曲、唱昆曲、演昆曲;也要宣传昆曲,研究昆曲。我们可以先在各国、各地分别成立相应的群众性组织,然后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实行“横向联系”,把国际性的昆曲艺术联合组织建立起来,使昆曲的兰花芳香播到全世界去!这是我结束讲演时的第二个建议。
我年岁老了,今年八十五岁,可我为昆曲事业的进取之心还没有老。倘有客观需要的话,我愿意再以主观努力来适应这个需要,为昆曲而呼喊!为昆曲而奔走!
我的讲演,暂时到此结束。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