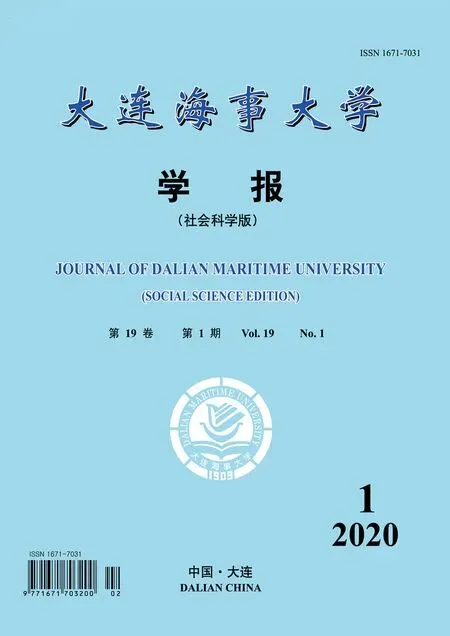新文化人胡适的儒士本色
2020-12-05马越
马 越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在一般的思想史论述中,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其形象主要是高唱西化、打倒传统的“斗士”。然而随着近年来海内外胡适研究的推进,尤其是对于其英文文稿和演讲的重新发现,使人们得以认识到真正的胡适的多重面相。他不仅仅是一个“斗士”,在思想更深层依然是一介“儒士”。他深深浸润于儒家文化之中,时时事事体现出“修身行道”的鸿儒本色。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集中于,作为“斗士”的胡适与作为“儒士”的胡适是如何统一于一人身上?以上看似矛盾的面相的深层原因何在?其中哪个面相才是胡适人格的最终归宿?
一、“斗士”的面相:胡适对儒学及传统文化之批评
儒学在两千余年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它深入士人与一般民众的心理结构,是传统社会思维模式的主要诠释者。儒学作为一种系统的思想体系,不仅包含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且落实为大一统王朝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结构,并与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互为表里。但随着19世纪末传统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的瓦解,固有的儒家文化在时代激变之中显得进退失据。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自幼深深浸润于儒学传统之中,自然对儒学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对儒学系统评价的首次出现,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他说:“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耀眼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1]从以上这段话中,可以得出几个重要信息。
第一,胡适认为儒学对于压抑人的精神和理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胡适曾这样写道:“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2]351胡适先生列举了许多令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其中尤其突出了女性地位问题。在儒家思想里,注重尊卑等级,强调三纲五常。在“夫为妻纲”一条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渐演变出女性应严格遵守的三从四德要求,致使中国女性的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抑与桎梏,裹小脚的行为更是历史悠久且愈演愈盛。至宋明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之时,妇女的名节又被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出现了甚多“以礼杀人”之事。胡适对于传统文化中此等毒瘤引以为羞,认为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孽障、病根。
第二,胡适认为儒学独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荼毒至深。儒学的独尊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被政权奴役、利用的现象。为了统治的巩固,丰富的学术思想被改造为单一呆板的正统学说。八股取士表面看只是一种文章格式的固定,实际上是将举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心力全部集中在文法辞章上。这种行为对民众精神禁锢之深可以想见,且儒学独尊使传统文化养成了一种骄傲自大、不尚反省接纳的坏习气。在胡适看来,国人在潜意识中总是唯我独尊,自诩为天朝上国,对外来之事向来呈一种排斥态度,没有足够的勇气反视自身,缺乏一定的决心去虚心学习,以至于闭关锁国,自欺欺人。所以对于西方优秀的近代文明、科学文化,我们竟始终不曾学到什么,只是守着自身文化的一丝优点乐不思蜀。所以对于那些“一面学科学,一面回复我们固有的文化”的声音,胡适一律斥为陈词滥调,对其大为光火。他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永远存在书本子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只会把这些好听的名词都写作八股文章,画作太极图,编作理学语录,所以那些好听的名词都不能变成有作法有热心的事实。”[2]356鉴于中国文化中的种种糟粕,胡适认为如果传统文化值得恢复弘扬,我们今天不至糟到这步田地了。他甚至说过“中国不亡是天无理”[3]的痛语。
胡适对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其对国民个人精神理性的禁锢与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掣肘这两方面。而这些批评的主要听众指向,则是国内的有识之士及普通民众。
二、“儒士”的面相:胡适对儒学及传统文化之弘扬
胡适一生推崇孔子及孔子所代表的儒道,认为他以非凡的魄力开启了儒学的中兴时代。孔子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抛弃了狭窄的畛域观念,将柔弱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起,促成新的弘毅的“君子儒”的形成,而他本人也有着“温而厉”、“与人恭而有礼”的人格。胡适不喜处处妥协柔弱的旧儒,而对于孔子改造过的有担当有品格的弘毅的新儒颇感自豪。他欣赏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淑世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承当意识、“知之为知之”的求真精神、“有教无类”的平等观念以及“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
胡适对待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观点,一直是反省和改造,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一片斥责声中,胡适对于传统文化,也有难得的温存。在《三论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胡适曾写道:“依我的愚见,我们的固有文化有三点是可以在世界上占数一数二的地位的:第一是我们的语言的‘文法’是全世界最容易最合理的。第二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因为脱离封建时代最早,所以比较的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第三是我们的先民,在印度宗教输入以前,他们的宗教比较的是最简单的,最近人情的;就在印度宗教势力盛行之后,还能勉力从中古宗教之下爬出来,勉强建立一个入世的文化:这样的宗教迷信的比较薄弱,也可算是世界稀有的。”[2]362
但是,即使是难得的夸奖,胡适也一定要说,“这三项优点中实在夹杂着不少有害的成分”[2]362。可说其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十分苛刻严厉了。然而翻看胡适的英文演讲稿,却不难发现当其对外国人言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时,态度言辞自是另一番景象。
胡适有着百余篇未收入任何文集的英文论著和演讲。其中一部分是他的手稿,分别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胡适纪念馆;一部分是他在世界各地的英文报刊上发表,但一直未能被搜集出版的散佚文章。[4]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资料得以被人们所认识。从诸多英文论著和演讲稿中可以发现,胡适对于中国文化,少了许多批评与苛责,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多的同情和维护:中国本就包含自由与人权,民主与科学;中国的妇女生活幸福,社会地位丝毫不亚于男子;中国的许多伟大历史人物出身平民,依靠公平合理的各类社会制度走向成功;中国儿童的学费低廉,人人都可受教育;中国的婚制合情合理,人性化且高效率……他从先秦哲学中,找到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根;从有教无类和科举制度中,找到了中国平等思想的根;从谏官制度中,找到了中国言论自由的根;从清代朴学中,找到了中国学术严谨、方法科学的根。胡适对外强调不仅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暗含近代科学与民主的种子,甚至连妇女在中国都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他举吕太后、窦太后、武则天的事迹,来说明中国女人的政治地位有多么的不同凡响。单看胡适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论述,甚至会觉得中国的妇女简直是世界上最受尊重、最有地位的女人了。胡适除了为中国的女权有过一番解释之外,在英文文章中,对中国的婚制也做过热烈的辩护。他说中国人由父母主持的早婚有两大好处:这可以保证男女青年的终身伴侣,因此,他们就不必为了寻找配偶这样重大的问题而焦虑,而这也正是西方年轻人所经常面对的难题。早订婚也可以给年轻人以一种责任感,要他们经常保持忠实而且纯洁。[5]至于说到中国的改变,他也强调中国是在进步的,不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人是充满上进之心和令人欣慰的实干精神的。
此时,即发声的受众群体指向国外知识分子与民众之时,在胡适的眼中,以儒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历史悠久且令人向往的,稍有不足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身为一个中国人,理应为其过去之辉煌与未来不可限量之前景倍感骄傲与憧憬。
三、双重面相之深层原因
一向择善固执的胡适,缘何在对待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呢?
首先,关于胡适以斗士姿态对内所展现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批评,稍做思考便不难发现,在表面的剑拔弩张背后,隐藏的其实是胡适的拳拳爱国之心与一种煞费苦心的文化策略。对于五四时期领导新文化运动之时坚定不移地捍卫近代科学与民主、反对向传统文化地位的恢复做一丝一毫之妥协的胡适,大有人斥之为不顾传统的全盘西化论者。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失之武断,在胡适的思想中包含了更为复杂且更为深刻的思考。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在这些苛责的背后,胡适的真实内心是由对这文化爱之深沉,转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进而急切地希望其快速获得新生法门。胡适曾说过,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尤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故坚持全面西化,最后自然可以得到一种折中的结果。所以他对一切提倡恢复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声音都斥为陈词滥调,认为其大可不必。知识分子是文化变革的领导者,如果知识领袖坚持“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态度,那么由于保守力量的抗拒作用,也就只能达到“有选择性吸收”的效果。而如果知识领袖从一开始就秉持“有选择性的吸收”的态度,那么得到的仍将是保守力量的抵抗,根本无现代化可言。[6]这样看来,大肆批评胡适全盘西化论的人,实在是太有负于胡适的良苦用心了。他只是在清醒而讲求方法地谋求中国文化的长期生存发展之道而已。胡适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文明选择的问题,谋虑自是比一般人要深远许多。但由于他未重视西化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关系且缺乏应有的辨析与说明,因此受到了诸多误解与批评。
其次,对外,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的大力赞美与弘扬,原因约有二端。一是出于游子在外对于祖国文化的天然依赖维护之情。这就好比家长在自己家中对子女不论怎样责罚打骂,但出了家门,却一定是一致对外,能对着他人说出自家孩子的诸多感人优点来的。这也正是我们对至亲至爱才会有的特别表现。回想幼时要强的胡母教育胡适:“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2]49而胡适对传统文化的内责外扬,又何尝不是如此?矛盾的言辞正是其深刻爱国内心的行为外化。二是缘于胡适对于名声的看重。胡适向来“爱惜羽毛”,幼时由于酷爱读书不喜玩耍得了个“先生”的诨名,偶然同一班孩子掷铜钱被大人看见,便羞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自己“先生”身份;年岁稍长,便开始不断地为自己取笔名、化名。[7]唐德刚先生曾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而唐本人也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这样一位爱惜名声之人,自是不愿意与自己有着血脉之亲的祖国的文化在外人面前有任何不好的印象,所以他在外时时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做辩护,不露出丝毫的不满之意。
最后,这种矛盾面相的呈现其实也是由于胡适本人思想的日臻成熟。在谈到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时,胡适曾提到布尔先生一句令他印象深刻的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令胡适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2]762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沉淀,胡适的思想也变得更加包容、成熟。从年轻时的意气风发,昂扬激进,主张“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绝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冲击一切保守势力与传统,到年长后的越发看中容忍的重要性,胡适言辞的包容性也自然强了许多。因此在外出演讲时,常常会温存地提起他所认为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优越性。只有放宽心胸,承认传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获得更多人的同情和理解,才能更好地修正其不足之处,获得长久的生存发展之道。这与其讲是矛盾之点,不如说是代表了胡适思想的成熟完善以及对“容忍”与“自由”之关系理解上的深化与提高。
以爱国情愫为主导,综合胡适本人文化观念策略、性格特征、思想复杂性等因素,在面对传统文化问题之时,其呈现出一种对内对外侧重各异的双重面相。
四、胡适一生矛盾表象背后的内在同一与儒士本色
胡适是一个精神信仰上的转变者,他自幼接受传统经学训练,思维意识与行为方式上都不可避免地承接着传统的血脉;成年后又积极执着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并力图将其先进性嵌入自己脑海的同时也嫁接在饱受苦难的中国大地上。然而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与信仰内核存于一人之身时,便显示出难以调和的矛盾表象。这种进退两难的徘徊也注定了胡适被新旧双方误解与批判的命运。
中国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是由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我们建构的一整套关于宇宙自然、生命来源、人生意义的架构所构成的。当外部世界形势与内部社会建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时,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是一场深刻的意义危机、精神信仰危机。就连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身,也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虚空之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试图用科学这一“万能的方法”为中国建立起一套新信仰,但自由主义者所建构的现代世界,却是一个恰如实证主义者所构想的“事实与价值、应然与实然二分”的机械论宇宙观下的世界。这种毫无价值超越性的理论根本无力解决20世纪中国普遍的信仰危机。
胡适是一个信奉科学自由的人道主义者,但他的人道主义信仰却并非来自于他毕生高唱的实验主义哲学——这一只能提供方法却无法确定价值信仰的哲学体系。胡适提倡自由主义,但他的自由主义却是建立在其强烈的社会群体意识之上的,而这种社会群体意识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老人文精神传统有着极深的联系。胡适在《不朽——我的信仰》一文中反复提到“大我的不朽”,这所谓的大我不朽不是指个人灵魂的不灭,而是社会的永续。这种论断显然是基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念之上,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神超越性的核心展现。
每个人的一生都时时刻刻受到环境的熏陶影响,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就在于孩童时期。这是人形成自我语言系统与思维意识最为关键的阶段,也是人格养成的重要时期。此时外在环境的熏陶影响会最大限度地内化于心灵之中,为日后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埋下种子。
概观胡适的一生,其幼时接受到严格正规的传统经学训练,承续着儒学的精神内核。他日后所有的道德操守、人格品行、价值倾向都在表象的矛盾背后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
作为一位深受传统经世之学影响的学者,胡适对于空洞无物、故弄玄虚的学问从来不屑一顾,但对与改良社会密切相关的学问,他却一直抱以积极关注的态度。这一点也表现出胡适心灵中“择善固执”、“淑世济民”的儒者气象。他从海外学成归国后致力于领导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的普及奔走呼吁,利用自己的学识能力为古老中国的文明转型寻求出路,为富国强民的美好愿景做身体力行的最大努力。他曾要求《新青年》同人们“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只致力于做思想文化上的变革。但不到五年,胡适就改变了初衷,站出来高谈政治。他沉默得越久就越发觉得自己有站出来说话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胡适任驻美大使四年(1938—1942年),正是中国抗战处在异常艰难的阶段,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支持,是胡适的外交使命。胡适为此不辞辛苦,奔走全美,上下活动,到处演讲。[8]他倡导好政府主义,主张通过一点一点解决问题获得社会进步,他坚决捍卫自己自由说话针砭时弊的权利,不为任何政党压力所笼络与胁迫。一言以蔽之:对于胡适这位注重力行的行动主义思想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骨子里的执着追求。
认识胡适的人,都会讲起他对于晚辈后进的无私援助,他的温润谦和。“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一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交场所极流行的口头禅。[9]文学家梁实秋曾讲道:“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时,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10]
这位具有忧国忧民之胸怀的儒者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深重苦难的解脱和社会的实质性进步。他的一生甚为跌宕,早年声名鹊起,晚年又归于寂寥。他的主张表面上矛盾重重,而其精神血脉则又始终如一。胡适虽接受西式教育,应时扛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但其内心仍是一身儒气,位列儒林。在现今时代国民亟须重塑文化自信之时,深入挖掘反思儒者胡适的思想理念之宝贵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深入中华民族杰出知识分子思想观念,深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代表的儒家传统,找寻我们自己的根基、自信和生存发展之道,刻不容缓且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