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他者的文化
2020-12-04徐谨
徐谨
人类学家是什么人 在很多人第一印象中是这样一群人:前半辈子躲在非洲深处或者南太平洋上的偏僻小岛,埋头融入某个部落族群的生活,体察当地风俗与宗教仪式,从日常田猎婚丧到比较奇异的“割礼”之类;然后,用下半生写出一本书——这类书往往在专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却很少受到大众关注。
当然,这只是关于人类学家的刻板印象。人类学家有不同的定位,并不是所有人类学家都需要进行这样长期的人类学实验。尤其,当都市生活成为人类生活的重心之后,人类学家的视野也在发生改变。张经纬,就是一名博物馆里的青年人类学者,普及人类学是他这些年的一大标签,新书《与人类学家同行》就是其人类学书评成果。
人类学的官方定义,就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之所以公众对他们存在刻板印象,其实也因为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很依赖田野调查,也就是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一般人會好奇,人类学家为什么这样喜欢折腾,上天入地满世界搞调研 受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的启发,张经纬提出了一个新视角:因为伦理。社会科学不能如同自然科学那样随时随地做实验,这种情况下,生活在海岛丛林、与外界联系较少的各类人群,就天然地成为人类学家的替代性观察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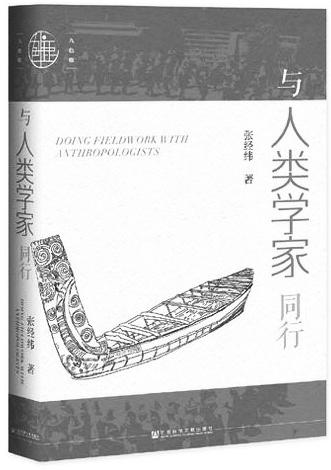
可以说,人类学家都有一颗好奇心,或者就像一本书的名字所说,是“天真的人类学家”。某种意义上,好奇心是驱动所有研究的动力,提供了想象力的可能,也是分享的来源。张经纬认为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能否理解他者的文化”——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根本前提:“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是源自同一祖先,因而天然具有平等的地位,以及对人类文化共有的理解方式(我们之所以拥有如此众多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只因我们身处地表不同的生态环境)。”
这些年,张经纬一方面自己做了很多田野调查,写出《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这样的专著,另一方面则一直在为公众普及各类人类学知识,书评就是其中的主要途径。在《与人类学家同行》《从考古发现中国》等书中,他不仅梳理了马林诺夫斯基、马塞尔·莫斯、列维·斯特劳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费孝通等学术大家的方方面面,也介绍了不少相对前沿的研究,甚至不乏立足中国视野的思考。他强调,人类学作为一门闻者甚少的学科,书评更是肩负向公众普及学科知识的重任。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更多是作者作为人类学书评者的告别。也就是说,经过了十年的人类学书评生涯,作者觉得可以开启自己学术生涯的下一段了——可以猜想必然是更大的学术规划。
张经纬写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接近十年,八易其稿,在这样漫长的写作岁月中,书评的写作与反馈显然给予他不少安慰——甚至,如果说专著是研究者一刀刀苦心雕塑出来的,那书评可能就是雕塑成型过程中零落的石屑碎块。
那么,作为读者,可以从作者的告别或者这些“碎屑”中看到什么 我想,是人类学的脉络。张经纬的专业训练、文章的深入浅出,可以让门外汉路过人类学大门时至少停下片刻,张望一下。这对于知识普及而言,显然利大于弊,毕竟,这是一个知识也不得不为自身吆喝的时代。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张经纬的阅读与思考始终围绕着人类学而展开,但是因为书中涉及不少历史问题,他也不时被误认为历史学者。我曾经请教他,人类学和历史学有什么区别 他认为,人类学和历史学都需要处理大量数据,但是历史学要面对过去,人类学则需要直面当下不断变化的文化。
这背后体现了深刻的观察。有人曾说,我们去看历史,应该当做去异国,因为历史已经变化太多,今天很多我们视为定见的,在过去完全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人类学的启发超出了人类学范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方法论,那就是抛弃先入为主的成见,不戴有色眼镜去观察不同人群、国家以及事件——他们或者他们的文化,必然存在与我们不同的面相,同时也必定有我们经过努力可以理解的一面。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