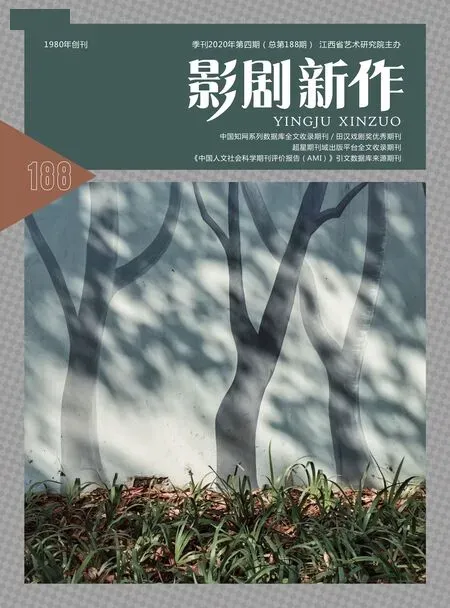君心似我心,不负相思意――读电影剧本《红杜鹃》有感
2020-12-04童孟遥
童孟遥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分界线,物质条件、情感理念、事业追求、文化需求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因时代的变革发生了许多转变和提升。当时的年轻人思想开始不再受到束缚,他们追求梦想与信仰,憧憬自由与爱情,但在面对现实生活时又往往并不知道如何去掌握自己的自由、理想与爱情,一旦遭遇到挫折时,就开始变得莫名的纠结与挣扎。
电影剧本《红杜鹃》的故事背景即设定在这个充满新鲜与矛盾氛围的80年代,主题是关于爱情和信仰,采用双线并行的故事结构,以爱情线为主,事业线为辅。不同于一般的爱情故事,编剧选择的是以一群防化工程从业者的角度,表现了科研工作者的生活、事业、爱情、亲情和友情,有血有肉,有泪有痛,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而不再是冷冰冰的、寡言少语的科学工作者的刻板印象。男女主人公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愿、共同的语言,歌颂了爱情的纯真与无私,颂扬了主人公们对事业的真挚和执着,对于现代青年人的爱情、事业的选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剧本情节结构紧凑、集中,故事性强。艺术结构上,采取了以主人公石峰、杜鹃的事业和爱情活动为线索,按照时间顺序发展,适当地插入回忆叙述的写法;人物塑造上,描写了石峰与杜鹃这一对灵魂爱人,二人之间相互“爱之深、望之切”,彼此相信,彼此成全,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和信仰。而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主要采取了对比式、对照式写法,将他们在面临重大抉择时表现出的行为和品行与主要角色、正面角色进行对比,没有脸谱化或漫画式刻画,而是真实细致地根据事件发展去深入形容和描绘,各具特性,让读者印象深刻。
全剧将80年代那段清纯时代的爱情用一种清新而深情的笔墨娓娓道出,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80年代的爱情,和现在的爱情可谓大相径庭。那是一种发自内心、不以占有为目的的爱,是一种愿意奉献、不求索取的爱。剧中的诸多情感表现和行为细节符合80年代的特征,男女主人公表述爱的方式大多是同理想、共患难,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来加深互相了解。编剧通过精心设置的那些爱情中的坎坷与复合,再现了80年代爱情中人性的纯真与美好,但又能极尽克制地保持着距离,有父母辈年轻时爱情的影子,如同电影《最爱》《我的父亲母亲》中描写的爱情那般纯洁无暇,同时对于理解父母那代人的事业和生活也大有裨益。
“杜鹃”一词是剧本中的核心意象,美好而坚定,悲伤又凄美,具有多重象征意味,兼具悲喜剧的双重象征。“杜鹃”是花亦是鸟,是爱情的象征,也有友情的暗喻,同时还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杜鹃花花朵繁密,花期长,是热情纯真、吉祥美好的象征,也是剧中情感属意的象征。如刘新将一束杜鹃花一分为二,其实也是隐喻着他情感的分流——对于石峰和杜鹃他同样看重,所以“杜鹃”在刘新心里的寓意是二重的:一半代表友情,一半代表爱情。而杜鹃鸟则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文化意蕴丰富,但多与悲苦、凄凉之意相关,运用在本剧中也就暗含了悲剧意味,而这与剧中石峰和杜鹃的爱情磨难相关联。
全剧的前两章多次运用闪回的艺术手法,故意将叙事顺序打乱,在故事结构中产生了特殊的悬念作用。在传统电影手法中,往往用短暂的闪回来表现人物精神活动、心理状态和情感起伏。闪回的主要作用,在于表现人物在某一个瞬间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用观众看得见的画面来表现人物角色看不见的内心发展和变化。但它必须与人物当下的行为、感受以及固有的性格、思想、感情相联系,符合人物或情节的逻辑,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特定性。闪回可以表现人物性格,窥视人物的心灵奥秘,相比一般的回忆,能更直接地揭示人物的内心动态。本剧共68场,总体按照起承转合的叙事节奏去进行,通过闪回补述,完整讲述了石峰、杜鹃二人的爱情起源、发展,呈现出情绪、情感和环境氛围的两相对比状态,悲与喜,乐与哀,更衬托出故事背景的落寞与感伤。在符合人物思想情感和思绪的发展前提下,剧中闪回的运用能够调节叙事节奏,活跃文本结构,保持一种顺序节奏下的不断插叙,既插叙故事前情,也补叙故事后续。镜头不断在过去、现在之间跳转,生动讲述了主人公爱情和事业上的矛盾,展现了女主杜鹃对于爱情及事业的坚定不悔以及男主石峰因身体残缺导致对爱情的失望和自卑,愿意牺牲自我成全爱人,塑造了主人公们坚韧的品质和美好的德行。
剧中闪回手法的运用灵活多样,根据不同媒介或介质,可分为多种闪回方式:一是藉角色言语直接过渡至回忆的场景,如第9场中“杜鹃长叹一声:‘我真后悔,我们是那样不愉快的分别……’”时间便由此回溯至当年二人争强好胜且不欢而散的场景;二是借特定物品牵动思绪,如第11场中杜鹃看到手上的手镯联想到手镯的由来,于是便回想起二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三是通过编剧叙述的角度直接入题,切入回忆等,如第6场中“杜鹃不语,沉默了。她在回想……”根据编剧直接的舞台提示,镜头便切换回过往,进行了一次不动声色的衔接。
该剧还巧妙使用对比手法,包括正侧相映,正反对比等,通过正侧面角度结合、正反面角色对比来讲述80年代年轻人的爱情和事业之争。剧中的对比是全方位、多层面的,不仅从外部、外人角度来谈论防化学科科研工作的意义,比如杜鹃之妹杜玲对科研工作的不理解;还从内部角色的对比来探讨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品质,如王哲对科研工作具有功利性,藏有自己成名立业的私心,而石峰和杜鹃对待科研工作、科研事业是无私奉献的,发自内心的热爱,有创造性,同时敢于质疑,展现了科研工作者所需的职业品质和高尚情操。除却事业模式的对比,还展现了两类爱情模式的探究对照。一类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共同理想追求基础上的感情,以石峰、杜鹃为主,二人互相体谅,虽分离却依旧有情;另一类则是属于物质享受上的感情,以王浩、杜玲为主,俩人虽未分离却并未有真情。所以经历过时间的考验后,石峰和杜鹃终于有情相守,而王浩、杜玲必定分道扬镳。
作为剧里主要反面角色的王哲是一位双重意义上的失败者,他对于事业、爱情都是抱着一种势利、世俗的眼光去争取,缺乏尊重,他的表现与刘新截然相反。同是爱情里的局外人,刘新的表现和王哲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表现出二人的心性和品格的不同。刘新作为石峰和杜鹃二人爱情的见证者和成全者,始终是真心真意地护持着他们二人,将自己牢牢放置在朋友的位置上,不越界不逾矩,在得知二人分手后极力重新撮合他们,是个心地坦荡、正直的人。面对石峰绝望自卑的时刻,甚至请他代替自己去使杜鹃幸福时,刘新愤怒了,为曾经朋友的荒唐言行而怒,为深爱的女孩痴心错付而怒,更为自身人格受损而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再这样下去,你对得起谁?”人生能得一如此干净纯粹的诤友,何其有幸!而如同跳梁小丑般的王哲却趁着石峰出事受伤的契机,多次搬弄是非,打击石峰自信心,为了自己情感需求的满足而毫无底线。
编剧在进行人物塑造的对白描写中,同时兼顾了抒情笔法的使用,通过环境描写的烘托、渲染以及情景交融的写法,或以美景衬哀情,或以冷景写伤情,或以胜景述衷情。景物、环境的描写始终与人物的心境是有所呼应的,“雨声淅沥”“细雨濛濛”是人物悲伤落泪的时刻,“浮云遮月”“自弹自唱”是人物情绪压抑、不得不黯然分别的时分,“白雪茫茫”是人物陷入低谷、消沉痛苦的时节,“冰凌迎着阳光透明发亮”是人物感情迎来新转机的时候,而“山花烂漫,绿树滴翠”则是人物情感和事业柳暗花明重现光明的时期。一切景语皆情语,文中的景物形象都是情中景,应和着角色的情绪特征。除了呼应角色的情感变迁外,剧本的镜头语言也极具象征性、隐喻性,有效暗指了人物角色的命运和前景、结局,如描写王哲、王浩兄弟俩的“他俩走着,胡同越走越狭小”,这就暗示了这对心胸狭隘、心思不正的兄弟俩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作茧自缚,咎由自取。剧中很少有直白的人物失控和情绪崩溃的场景描写,而是通过景语与情语的相互铺垫和交融、渗透去表达人物心境心绪,推进故事前行发展,往往在静默的影像中爆发出冲击力很强的情感张力,富有影像美感。
此外,编剧精巧运用了非言语行为来传达人物角色的真心。为了成全所爱之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情,于是受伤后的男主人公石峰多次口是心非,口不应心,甚至口出恶言,只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往往因为非言语行为包括表情神态、语音语调、眼神、身体动作等而暴露了真心,让观众在同情之余又给予了理解:因为爱,所以非自愿地伤害。剧中非言语行为传递的信息与言语信息是矛盾的,声调、眼神与面部表情表达了相反信息,如石峰在与基地党委书记邓瑾谈及与杜鹃的感情问题时多次否认自己对杜鹃的爱意“不,现在不爱”“不,是这样的(我是薄情的)”。但在邓瑾的目光直视下,石峰的表情和神态给出了真正的答案──渐渐低下头。这个低头的动作无疑才是未说出口的真心话:我爱她,“我只希望她幸福”。此刻人物角色的非言语行为起到了否定言语信息的作用,使主人公言语的伪装被揭穿,流露出真实的内心情感,也让观众更加深刻体会到人物角色的矛盾和纠结。
通观全剧,其实我们还能够看到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对本剧的影响,包括男女主人公的设定、个性、故事走向、主题表达等都隐隐带有《牛虻》的影子。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类似《牛虻》中牛虻和琼玛的爱情,包括暗恋、相恋、误会、重逢等桥段和设计,都印证了男女主爱情的遭际,但他们同时也都是升级版的。男主角石峰是一个“牛虻”式的、具备传统思维的男性。坎坷的家庭背景造成其忧郁沉默的性格,内心敏感,对人充满了友善和信任,而且也遭受了身体的磨难,姣好外貌受损,这些都与牛虻相似。但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毫无瑕疵的道德模板,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包括感人肺腑的爱情、矢志不渝的信念追求等。而女主角杜鹃也是一位更加积极主动的“琼玛”,她没有听凭恋人间的误会丛生,而是主动去探知真相,破除误解,百折不回,百挫不悔,最终也成功挽回了二人的爱情。两人优秀的品行和能力再现了我国科学工作者群体的良好形象,展示了科学工作者对待爱情生活和科学工作的挚爱与冀望,突出了信仰、奉献、牺牲等主题。可惜本剧故事以爱情线为主,因而思想深度和力度较《牛虻》相比弱了许多。
《红杜鹃》的编剧张音阶用富于个性化的语言通过人物的神态、行动等表现人物的性格、气质和思想,在“言”中表达人,在“动”中塑造人,注重对人性和人心的挖掘。如石峰既期望又害怕所爱之人真的如己所愿接受了别人,百感交集,内心满是冲突与痛苦,这些细节增加了作品人性把握的精细度。而且编剧尤其擅长在平静的文本叙述下隐藏着丰富的艺术张力,包括进与退、坚持与放弃、爱与不爱等,展示了科学工作者们的母子关系、恋人关系、事业信仰和追求等等,抓住了细腻可感的人物表情、情态,具有生活感、生活气息。情节一波三折,好不容易雨过天晴,转眼又再生波折和误会,真实表达了在爱情面前的怯步、徘徊、复杂的青年人的心态和表现。作品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和时代感,是一曲积极奋进的、时代调性明显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