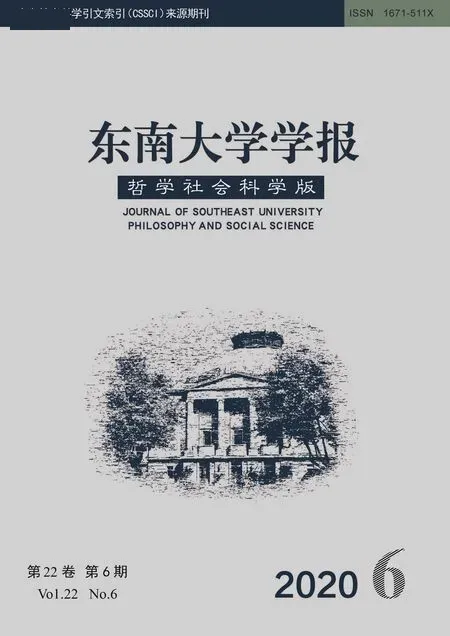易道的显现与感通:以“象”为枢机的分析
2020-12-04董春
董 春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
《系辞传》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四者之中,“象”乃是《周易》区别于其他经典的根本所在,《周易》通过独有的象数语言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精微而广大的意义世界。因此,在易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何去认知和诠释《周易》中的“象”一直是历代易学家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的传入和发展,人们开始借鉴西学特别是现象学的理论对《周易》中的象思维进行研究和解读,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1)何丽野《〈周易〉象思维在现代哲学范式中的解读及意义》(《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张祥龙《“美在其中”的时—间性——〈尧典〉和〈周易〉中的哲理之“观”及与他者哲学的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黄玉顺《中国哲学的“现象”观念——〈周易〉“见象”与“观”之考察》(《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等文皆从不同角度对易学之“象”进行了现象学的解读。。但是就对“象”的理解而言,易学理论亦有与现象学不同的独特之处,故本文试从易学中的“见象”“观象”“忘象”三个层面出发去理解易学的“现象”(2)本文所用的“现象”与西方现象学中“现象”(phenomenon)以及与本质相对的“现象”均不同,而是由“见象”“观象”“忘象”构成的道向我展现,我经由象体认道体的过程。观念。
一、见乃谓之象
不同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方式,“在西方思想的长期发展中,已经与概念理性和形而上学的探索方式结下了不解之缘”(3)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91页。。西方思想以概念理性作为探索世界的主要方式,故其建构哲学体系的根本在于抽象思维。而在中国思想当中存在一种与概念理性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象思维,这一思维方式对《周易》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象思维”为基础的易学哲学,其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不同,不再从现象世界中分离出一个抽象的概念世界,而是强调器依道而存,道依器而显现,二者有分别而不相离。正如朱熹在回答周谟关于《系辞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的“‘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的疑问时所答:“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所以谓‘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35页。道与器之分别就在“形”上。“形”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将……表现”或“让……显现”,故形著之前为道,形著之后为器,形著这个过程便是“象”。《系辞传》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乾坤之阖辟的过程属于形而上之道的层面,而“制而用之”“利用出入”则是属于我们可观的器的层面。而见之、形之便是道由隐而显、由“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到“感而遂通”的过程。这一道落实到器的过程,即形著的过程被称之为“见(xiàn)象”。以此观之,这个“见象”不是“从抽象到具体”,而是“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过程。
在《周易》中,圣人通过卦象的变化为我们展现了这个“见象”的过程。正如《系辞传》所言:“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通过仰观俯察,以阴和阳两种基本元素为基础,创造出了乾、坤、坎、离、艮、兑、震、巽八经卦去“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值得注意的是,此三画卦将“人”纳入到道落实于器的过程中,从天地人一体的角度去阐明道下贯于器的问题。如孔颖达所言:“二画之体,虽象阴阳之气,未成万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画以象三才,写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5)[晋]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至文王之际,八卦衍生为六十四卦,三画卦发展成了“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六位而成章”的易象体系。在六画卦当中三才之道进一步成熟,它以乾坤阖辟、阴阳消长之象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以此观之,《周易》之“见象”特别强调人之生存体验的重要作用。
在人的体验当中,《周易》尤其重视圣人的体验,因为“天道是一生道,这一生道之内在于人即为人道,圣人是能把这一生道在他的生命之中充分发挥出来的人,所以可以作为众人的楷模”(6)刘述先:《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1页。,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圣人与道同体,如《文言传》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也因此,圣人能够体会到种种复杂物象背后的阴阳生化流行之理,能够与天地相参。亦才能通过“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去建立这一整套卦象系统,以阴阳符号去“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通过卦象的变化将此“见象”的过程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圣人又具有“人”的最普遍的本质。正如王弼所言,“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95页。虽然圣人之神明茂,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不溺于物,不陷于情,但就此情、此神明而言圣人与普通人是相同的。故其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以及对阴阳之道的体悟所建构起来的这套“见象”的体系方能被一般人所理解。故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系辞传》)圣人通过六十四卦的阴阳消长展现出了事物的吉凶、悔吝、变化、刚柔等,为我们展现了人生存的失得、忧虞、进退、昼夜之象。通过这套卦爻符号和卦爻辞,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故由圣人所建构的这套体系将宇宙的生化流行都涵摄其中,从而“如一个镜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8)[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647页。。
以此观之,《周易》所讲的“见象”是道之显现的过程。圣人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见(jiàn),以阴阳符号为基础,通过六十四卦建构了一个天地人融而为一的体系。“这套象数体系集中于对宇宙生化之妙的探索,认为人生存于天地自然之间,生命的价值植根于此生生不息的天地造化之中,故而只要了悟此天地的生化之妙,即可对人生价值之应然有一透彻的理解。”(9)董春:《王弼易学的经学前见与义理新意》,《周易研究》2019年第5期。这套理论的最终目的乃是在宇宙的生化流行过程中寻求人如何“继善成性”的智慧。如《坤·初六》“履霜,坚冰至”,《文言传》注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便是通过人踩着霜,便预感将要迎来坚冰的自然现象,体悟到积恶成祸、积善得福的道理。故《周易》的这种“见象”思想,通过对外在自然现象的观察,落实到如何通过提升人的德性,从而达到与天地相参的境界。
因此,易学中的“见象”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是人生哲学的问题。正如孔颖达所言:“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10)[晋]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32页。《周易》“见象”的重点不在于对“象”的知识性认知,而在于如何通过“象”去展现天地人一体之境;强调人只有融入到“阴阳之道”的生化流行当中,才能理解这个“象”。故这个“象”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的对象,而是一个通过展现道显现为器的过程而成就人生的智慧。而要进入到《周易》通过“卦象”为我们建构的这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就需要我们去“观”。
二、观象察变而成己化物
所谓“观”者,《说文解字》曰:“观,谛视也。”(1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08页。在许慎看来观与普通的看不同,“观”有谛视的含义在内。而“谛”者“审也”,谛视就是审视,仔细地看,其中蕴含着一种严肃、庄重的内涵。故段玉裁亦注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1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408页。这种非常规的“观”乃是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对待外界事物不同的方法和态度。在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当中,本质源于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反思。到近代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那里,本质不再需要依靠反思而获得,它就在现象之中,通过对现象的“观”我们就能够获得本质。这种思维方式打破了西方哲学传统主客二分的结构,解决了一直困扰西方认识论的难题。也因此在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周易》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有学者特别重视这种“观”,如黄玉顺教授认为《周易》当中的那个“前存在者性的、非存在者化的‘见’,其实在‘观’的观念之中”(13)黄玉顺:《中国哲学的“现象”观念——〈周易〉“见象”与“观”之考察》,《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张祥龙教授亦认为在中国哲学当中的“观法与西方人似乎是头尾颠倒的”,先有非对象的直观,到宋明之后方才有了对象式的观,而这种非对象化的维度的观首先出现在《周易》当中,在易学当中观所凭借的并非是主客二分的对立关系,而是“《易》所呈现的能‘与天地准’的阴阳象数结构,即阴阳对补交生和再生的机理”(14)参见张祥龙《“美在其中”的时—间性——〈尧典〉和〈周易〉中的哲理之“观”及与他者哲学的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两位学者均试图通过在易学之《观》卦当中寻求那个未有主客二分的本源状态。诚然,《周易》通过《观》卦叙述了其特有的观看之道,但在易学中存在着比《观》卦更为基本的“观”,那就是“观象”。
《周易》的“观象”不是将“象”作为对象去观看、观察,而是试图通过“观象”这一活动去“成己”“成物”。“在早期思想人物的心目中,物不是纯粹的自然对象,而是人生命世界中不可分割的要素。”(15)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30页。这样人在观象的过程当中与物不再是分裂的、二元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人们在成物的过程中亦不断成己。因此,“观象”不再是我们对事物存在合理性的追问,相较于“观什么”这一行为更侧重于“如何观”。另一方面,在这个“象”当中还蕴含着圣人对生命的体悟。正如《系辞传》传所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我们通过“观象”而去体悟圣人之意,如此方能融入到道的境域当中。故《系辞传》曰: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圣人用以表征这个道的、以阴阳变易为核心的“卦象”体系,不是一个静态的、僵化的系统,而是一个有人参与其中的“唯变所适”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正如《系传》所言:“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静态之象只能展示对象的一个角度、一个侧面的僵滞状态,不可能具有无限的包容性。相反,只有活生生的动态之象,才能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展示对象的变化与发展,从而具有无限的包容性。”(16)王树人、喻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79-80页。故君子或居或动,最终是要通过“观”而融入到这个动态系统当中。这个观不仅注重外观于物,更重内观于心。“由于‘心藏神’,故观心即观神,亦即用心来观。内观其心可得其本体,外观万物可明其化育。一体一用,浑然如一;天人相孚,化育无穷。”(17)张文智:《从观卦看〈周易〉中的‘神道设教’观——兼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故君子无论是“观其象”还是“观其变”,最终都要通过“观”融入到道体当中成就自身。“易文本不仅形式上效法世界和谐结构、表达世界全部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是世界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方式。”(18)林忠军:《论〈易传〉的解释学:交感与会通——兼论〈易传〉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之异同》,《周易研究》2008年第5期。这就意味着观象之“观”成为一种不同于认识论的,具有特殊性质的观看之道。例如在《乾》卦当中,从初九爻的“潜龙勿用”到上九爻的“亢龙有悔”,均以龙为象。对此龙象的观,不是对龙的形状、颜色、大小、姿态进行研究,而是通过“观象”了悟《周易》在不同情景当中所呈现出的吉凶进退之方,如《杂卦传》所言:“《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通过“观”,我们对自身的生存境遇和生活经验进行审视,进而对自我的本性有一清晰的洞见。
因此,《周易》之“观象”不仅要研究其所观的象,更要对观之本身的意义进行探寻,强调对观象主体的理想品格和应然性质的“观”。这就赋予了“观象”以如何“成人”的价值论意义。故无论是圣人的“观象系辞”还是君子的“观其象而玩其辞”,均未将“象”看作一个客观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思考。正如《说卦传》所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在“观”之中蕴含着“工夫论”的内涵,强调通过“观象”而体悟其中的“德”。如《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周易》哲学尤其重视以人类之精神、人类之生命去“观”外在的世界。它所“观”的对象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自然界,而是具有真、善、美的价值世界。其最终目的就在于提升个体的精神修养,强调以道德之人格去适应道德之世界。故《周易》对这个世界的“观”的落脚处就在于人的道德生命和道德实践当中。
综上,“观”贯穿整个进入“易道”的过程,或者说在进入“易道”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观”。“观”始于直观的“看”,但并不停留于“看”,还必须超越于“看”,才能进入“易道”(19)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页。。《周易》的“观象”并非将“卦象”作为一个认知对象去观察,对象性的关系不仅不能使得《周易》所强调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为我敞开,反而会遮蔽了事物的本真,使得事物不能以“是其所是”的方式向人们显现自身。这种“观”的核心在于探寻人如何生存的智慧,是以“融入”为核心的动态的“观”。在此生生不息的世界当中,我们去观象,不是对这个世界进行对象式的研究和反思,而是要融入到此生活之流当中进行体验。“引领人们圣眼、经眼、易眼观世界,察天下,了人生,遵循阴阳消息之道,深切观照、理解由活生生的阴阳消息之象、消息生化着的万象所构成的人所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这一生动鲜活现实的《易》之文本,作出价值应然的选择。”(20)王新春:《汉易的〈周易〉诠释视域与方法——以〈周易集解〉所集升卦诠释为例》,《周易研究》2019年第2期。这就意味着《周易》真正地将“观象”这一活动纳入到了存在论的维度当中。我们通过“观象”融入到《周易》六十四卦所为我们建构的人与道、事圆融而无碍的“境域”当中,探寻人的生命价值,领悟《周易》“兼三才而两之”“分阴分阳,迭用柔刚”的精韵所在。故“观象”的最高境界为“观德”,正如孔子所言:“《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存〕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帛书·要》)而由“观象”到“观德”的关键环节就在于“忘象”。领悟了这一圣人通过“象”所展示的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将《周易》中所蕴含的开物成务、进德修业的精神真正内化于心,让天地之大德充满于自己的内心,最终进入到天理流行的生生之境当中,从而体悟生存的意义,成就自身,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忘象以见道
在《周易》当中,道通过“象”而显,圣人以阴阳消长之卦爻符号展现了这个过程。故“易象”乃是道由隐而显、由“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到“感而遂通”的重要环节。而这个象又能够被人所把握,故我们可经由“观象”去理解这个世界进而体悟道体。在《周易》的理论体系当中,象乃是上通于道、下及于物的中间环节。故这个“象”蕴含着两层含义,一个是“未见之象”,亦即是“大象”。所谓“大象”者,乃是“至大无外之象,总体普遍浑合为一之象,就是大象之道。至大无外之象就是道,所以‘道显为象’,这个‘象’还没进入‘形’以前的境域,其实很接近于道”(21)林安梧:《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5页。。另一个就是“已见之象”,即具象。具象通过我们意识的活动,将此天地万物显现出来。象一旦成为“已见之象”,就会进入到心灵当中成为有形质之物。对这些“已见之象”的“观”就成为我们体悟道体的一种方式,这种“观”乃是透过对“象”的省察而向道体的一种回归,而非以“象”为对象的观察。如果局限于象,那么“观象”就会沦为一种认知活动,象会逐渐脱离道,沦为一种对象化、外在化的物,人的认知也会产生异化和扭曲。如汉代之“象数”派醉心于象数体系的建构,无论是西汉象数易学的“卦气”“纳甲”之说,还是东汉易学的“卦变”“爻辰”“互体”“升降”等象数体例,都过于注重对卦象所象征的物、卦爻符号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以象数体例替代了易学之道。故无论这套理论多么精致,都无法揭示象的本来面貌。道被遮蔽在繁杂的象数体例之中,最终陷入“案文责卦,有马无乾”的困境。只有在道的层面中,才能避免这套“象数”符号陷入被对象化的泥淖之中。因此,对“象”的体悟必须要经由体道,让道去照亮这个象,如此才能融入道体之生化流行中,重新回到天地人不可分割的那个整体中。“道”作为形而上者,体现了整体性、全面性;“器”相对于道而言,则主要是指一个一个特定的对象、具体的事物。区分“道”与“器”的内在旨趣,在于扬弃“器”的限定性、由“器”走向“道”(22)杨国荣:《哲学的视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58-159页。。这就需要我们对“象”不断进行“解构”,因为一旦“象”被我们所观,它就成了一个已论之物,那么它就是有局限、有限定的。故我们需要通过“损之又损”的活动对其进行还原,回到那个道的境界当中,而这个过程就是“忘象”。
之所以将“忘象”作为人融入到天地人整体境域中的最后一环,乃是因为道彰显为象,象乃是道的体现。但道一旦以象的形式显现,它就成为已见之象而有了阴阳之别,这个象就已经被建构了,其无限性和本真性就会被遮蔽。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领悟道之“大象”,即阴阳未分之象。要对此有所领悟就必须要从“已显之象”向“大象”回归从而上通于道,而这就需要我们去忘象。忘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已见之象”的瓦解,这种瓦解不是通过让心直契道体而否定“象”的存在,这样就会使得易学对道的体认陷入对心的重视,成为有心无物的理论。这种理论会强调只要将心照顾好,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而《周易》之“忘象”并非如此,它认为此象、此心都是真实存在的,心与象乃是息息相关的,“忘象”乃是要打通二者的界限,让此心此象融而为一。这个“象”就如同庖丁解牛之刃,海德格尔之处于“上手状态”的锤子一般,它不再是一个对象,而是融入到我的生命当中,获得了最本真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本真的存在状态中,“我”与道体通而为一,天地人一体之总体通过我的存在而展现。故通过“忘象”方能追寻“人”最本真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本真的状态中天地人通而为一。也只有在这种境界当中人才能克服自身的有限性从而化去对“象”的执迷。
因此,只有“忘象”方能“见道”。而要达到“忘象”的境界不是对“象”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人对自身本真状态的追寻。人只有充分发挥天地所赋予个体的性命,挺立自身的德性,方能融入到道体的生化流行当中成就自身。如《系辞传》所言:“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所谓“穷神知化”者不是向宗教中的那个“人格神”皈依,而是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德性而呈现出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真正地融入宇宙中,打破了我与象的界限,达到了天地人一体的境界。而只有进入“德之盛”的境界,才能达到这种状态。这是因为“儒家发展到了《中庸》《易传》,它一定是‘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Cosmic order is moral order),它这两个一定是合一的,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23)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5页。。宇宙的生化流行对人的生存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消极的否定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单向的,不可改变的,作为主体的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尤其是通过提升自身内在的德性修养将个体的生命融入到这一大化流行之中,在“道”的境域中能够获得生命的本真。
通过“忘象”而进入道体之后,再去观照万物万象时,这些物和象就会被赋予了德性的含义,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言:
由此而人在观自然界之物之相感,或想像自然物可能有之相感时,皆可一面见自然物之德之凝聚,一面自求有其德行,与之相应;而后一切自然界之事,无不启示人一当有之德行,而亦无不显为一有德行意义之自然,亦无无德行意义之纯粹之自然矣(24)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21页。。
故而通过“忘象”我与道成为了共属的存在,道体直接下贯于我的生命,我亦能够直契天道。在此种境界中天地人真正融为一体,人通过提升德性修养,方能对此道、此象有一通透的体悟。故在《左传》的记载当中,无论是穆姜占筮所得的《艮》之《随》的“元、亨、利、贞”,还是南蒯占筮所得的《坤》之《比》的“黄裳,元吉”(25)详见《左传·襄公九年》与《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所记载的关于穆姜和南蒯的筮例。,均透过象而将目光聚焦于德。“德性”成为沟通天地人的重要依据,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就需要透过象而进入到德当中,以德性去感通天地,将极天地渊蕴与尽人事之始终相连,最终达到“与天地合德”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四、结语
《周易》围绕“象”思维所建构的“现象学”与西方通过对传统形上学中现象和本质二分的反思所建构的“现象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就其产生根源来讲,西方现象学源于对形上学的反思,而这种形上学产生的思维方式与西方语言的叙述方式相关,中国之形上学则与其“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体用论相关。西方现象学注重“面向事情本身”,寻求存在者是其所是的根本,而易学现象学则从中国特有的道不离器、器不离道的体用论出发,阐发“象”所象征的事物之“几”。故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辞传》)通过“知几”,我们“能够提前辨别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落实到人事,就是明察事物的吉凶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以做到见几而动,扬善抑恶,趋利避害,就吉化凶”(26)林忠军:《中国早期解释学:〈易传〉解释学的三个转向》,《学术月刊》2007年第7期。,从而将那种成而未成的状态展现出来。故易学现象学与Phenomenology不同,以“见象”展现道之形著的过程,以“观象”和“忘象”去寻求使得天地人这个整体得以存在的根本,即易学当中作为存在的存在。这个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象就成为我们建构易学现象学的基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