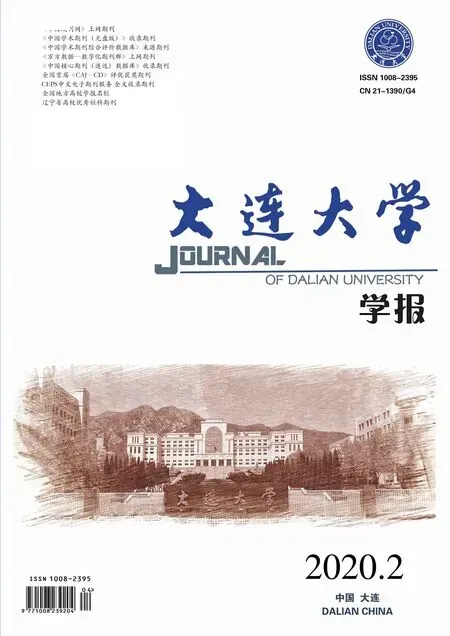论《中庸》的天地精神
2020-12-04张红翠
张红翠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经典之一的《中庸》,被誉为子思传授儒家思想心法之作。《中庸》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君子人格的构建及其内涵。然而,君子的人格德行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一套依据,即以天地精神为根本依据。对天地精神的引入并以之为参照,深藏着中国古人的哲学体验和世界信念。可以说,天地精神是《中庸》精神的内在蕴养,失此根基,则《中庸》精神以及君子人格无以立。因此,体会《中庸》的思想精神,厘清其中的天地观念和天地精神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中庸》中的天地含义
“天”“地”是《中庸》文本的重要概念,是其人格建构与精神显现的世界基础。在《中庸》不足4000字的文本中,“天”出现了21处,“地”出现了16处,可见二者之于《中庸》的重要性。在《中庸》中,“天”与“地”究竟有怎样的内涵,又具有怎样的品质,其之于圣人君子的意义是什么?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中庸》中的“天”与“地”是自然性的,而不是人格性的、神秘化的天与地。自然性的天与地是《中庸》中天地内涵的第一个层次。自然性的天与地指的是自然界存在的朴素的自然现象,是一种客观的世界存现。自然性的天与地的存在,向中国古人提示了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秩序”的价值,并且,这种秩序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先在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这种“秩序”显现为自然界中的“高下相形”、“高卑之别”,这种秩序是天地自然秩序的纯粹显现,这种显现显示了天地万物的自然应在的位置。正如《中庸》所说:“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则是古人从社会生活角度对世界秩序的强调和命名,这种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在许多地方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思想的存在,我们可以在《乐记》中找到鲜明的例证,《乐记》开篇即有:“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1]可见,正是在自然世界中,中国古人体会到了秩序:天地、阴阳、日月、雷霆风雨、动静、大小、上下、高远深厚等等……。进而,中国古人以此为参照,对应出了社会的结构秩序:君臣、礼乐、男女……。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因为,社会的等级秩序是以天地自然的秩序为依据和参照的,因而,最初本无贵贱的价值区分和赋予,这些价值区分只是后来社会附加上去的。儒家宗师孔子终生克己复礼,其目的就是构建和谐的礼乐秩序、社会秩序。
《中庸》用大量的章节论述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陵上”,“大德必得其位”“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2]31在这里,秩序首先是礼的内容和表现,秩序其次是有作用的,作用就是世界万物得以长养、孕育和存续,因为,万物安住自己的本然秩序才会成就生命,世界才能够流通运转。需要强调的是,《中庸》对天地自然秩序的看中,除了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存仰赖自然条件的客观原因之外,更有古人对自然天地的理性观察和深刻领悟。这种观察与体悟开拓了古人生存世界的空间,确认了人在天地间的共同体秩序。也正因为这个秩序的存在,我们才能够理解《中庸》“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以及“可以与天地并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伦理结构,才能够理解古人的世界观念和生态伦理。并且,《中庸》对自然性天地的引入,以及对自然秩序的强调,最终落实到了社会秩序以及政治的平衡。这是《中庸》哲学与伦理思想建构的基础,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它的在场奠定了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格局。
其次,《中庸》中的天与地不仅是自然性的,更是精神性的。《中庸》中精神性的天与地是哲学性的,而非宗教性的,是哲学道体的显现和存在,是人的世界法则所依循的根本。精神性的天与地提示了一种与秩序性价值相对应的更深一层的价值,即德行的价值。因而,《中庸》尤其注重对天地所具有的高尚品质的认定。《中庸》第二十六章集中论述了天与地的核心品质与特征:“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2]39在《中庸》中,天地的浩瀚精神就是,至诚无息、悠久博厚、为物不二、生物不测、博厚高明、广厚载物。这些精神以博大深厚的涵养万物的德性为主要核心,以化生万物为品德。对这种精神与德性的把握使中国古人的思想中有着深厚的尊重自然和生存宇宙的精神厚度,也有着高度的理性和神明感性。正是天地的深厚精神与品德支撑起了《中庸》的世界结构与生命视野,为《中庸》作构建的人道秩序提供了主要的背景和直接参照,为人类生活法则提供来源和依据。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理解和认定,《中庸》精神与天地精神以及君子的人格精神取得了内在的一致。
二、《中庸》的天地精神
(一)天人合一的世界原则。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哲学情怀,更是一种世界精神,这意味着《中庸》以及中国古人的世界是有机的、关系性的结构状态。天与地始终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与情感域限之内,这使得古人的视野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包容性,始终将人类的生命与天地间万物的生命保持一种关联与关怀的状态。这种世界精神孕育着无限的可能——理解的可能、万事万物之间辅助共生的可能。这个世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不是单一人类生命感知系统的,而是聚合了多样异质生命的“大全”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天人感应在:“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2]38通过对天地精神的对接和领会,人将自己的生命维系在天地的维度之上,从而也将自身镶嵌包围在天地宇宙之间,人在呈现生存实践同时也呈现其自身。人在这个系统中呈现而不是隐匿,迎向而不是逃避或者屏蔽世界图景以及宇宙系统。这种呈现和迎向的过程,显示了人类灵魂的参与而不是单纯的理性建构。人类的存在意图与贯穿于大自然中的世界意图永不冲突。基于这种精神意识,世间任何事物都具有生命的意义,因而具有灵性与精神的意义。
在经历漫长的哲学追寻之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中叶获得的哲学领悟似乎逼近了中国古人的哲学源头。在《生存哲学》中雅思贝尔斯说过:生存哲学“强调指出了长期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哲学任务:从本原上去观察现实,并且通过我在思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以及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3]3因为,“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3]3这是一种自我的理性,是主体意识的展现。但是这个自我得以成立的依据又是对一个更中级的生命的回归。所以,“他们愿意严肃认真地生活,他们寻找与隐藏含蓄着的现实,他们盼望认知可以认知的东西,他们试图通过他们对自己的了解达到他们的根源。”[3]4若此,每个人能够成为他们自己,也就是成为他们的世界本身。这显然是对“人”(我)与“天地”(大我)相融合的一种哲学追寻。之于这一点,《中庸》甚至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早有明确的表达:我不仅是我自身,我还是宇宙天地。如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还有庄子,以及后来的王阳明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都在阐扬这种道理。
(二)行动的理性原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被一般地认为缺乏理性特质,但是《中庸》精神却呈现了严肃而鲜明的理性原则,这种精神原则主要表现在《中庸》所倡导的“理性近乎仁”的行动原则。也就是说,“中庸”精神的实现需要在现实的行动中体现出来,对于行动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作为。因为,对现实行动的分寸拿捏正是对“中庸”精神的理性把握,绝不是感性的一时兴起。所以,《中庸》的理性精神是行动的理性,其中颜回的“择而能守”正是这种理性的典范,也是行动的典范。这意味着,《中庸》的天地精神具有高度的意志性,显示了一种本体的行动意愿和意志。这种行动的理性强调了中庸思想的实践性,没有不通过实践就能理解和获得的中庸精神,这是《中庸》天地精神内涵的理性精神。
(三)主体精神的内敛自谦原则。《中庸》的天地精神内涵着内敛自谦的主体品格。如朱熹先生在《中庸章句》第一章注释时指出的那样:“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反求诸身”、“正己化人”等精神旨趣是一种自约性的主体精神,而不是扩张性的主体精神,又与孔子“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的精神相一致。《中庸》所构建的主体,具有明显的主体限度和内敛的自谦精神,这些与古人思想格局中天地结构的超越性存在直接相关。因为,天地结构的存在为中国古人的主体人格规定了内部的精神秩序和自我发生的限度。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参照系统,古人在评判事物和自身的思想行动时就不是以自身体验为依据,而始终保持主体的限度,实现外视角与内视角的一致。
(四)仁爱的及物原则。当古人的生命世界扩大到世界万有,古人的生命情绪与感知便自然通向非人类的其他生命与存在。这种生命意识建构的其实是仁爱的及物原则。《中庸》中“赞天地之化育”以及“尽天之性,尽物之性”与孔子之“将仁爱施及于万物”的思想是一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贵的及物精神的体现,是与“他者”共在的平等精神和尊重意识的体现。“他者”的意义在于对“自我”的提醒,对自我与他人之间生存共同体关系保持清晰的认知。这种认知与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原子化个人主义的、只见“人的利益”和“自我”以及“欲望”的价值信念迥异。判断社会以及个体的道德指向,主要看它/他如何对待他人以及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对待他人/他者是《中庸》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讨论和构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孔子的“忠恕”到《中庸》的“隐恶扬善”,都在回答这一问题并且同时提出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这一理想建构的核心便是对社会共同伦理的参与性、群体性和公共性的强调。
最后,在《中庸》所呈现的这几种天地精神的含义中,理性精神是核心。因为:1.能够将自身的生存与宇宙世界镶嵌在一起,对宇宙的生命系统保持高度的关注和尊敬,这本身是一种朴素的理性,是人类应该有的、保持认知限度的自知之明和基本的生存之道;2.意志和行动同样需要理性的参与才能成为自明自觉的行动和意志,行动才具有合法性;3.如何对待人以及世间的万物是《中庸》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这是及物及人的道德精神。只有在真正理解了人与他人以及万事万物之间的有机性关系时,道德精神的建立才有可能。
三、《中庸》天地精神的当代价值
《中庸》中,天地的在场对于古人的生存、乃至古人的精神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向我们呈现了《中庸》的基本世界格局,即天地人共在的大格局,这种格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生态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人确立了基本的生存价值关系,即人是宇宙中的人、人是世界精神(道)的体现。因而,人的价值以及德行的法则与依据都在于人所生存于其中的天地宇宙。《中庸》的世界具体呈现为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之性、物性以及人性一体同观的大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因为超越于单纯的利益共同体而具有更高的哲学价值和意义。这种世界格局和人文生态对今天的人文生态思想也是一种参照也是一种启示,它反衬出“人为万物立法”的现代思想所孕生出来的、愈演愈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念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中国古人的公理在于顺从天地自然方能存活,但是今人的公理是征服方能存活。今人思想中的天与地,是纯粹的自然物体,是可以被征服的对象,以及可利用的资源,并仅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类有价值和意义。人与天地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分离对立的关系,是主客体二分的关系。自然被缩减为物质对象的同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体关系也随之解散。随之,人类文化的参照系中缺少了超越性的力量纬度,人类活动也基本只与自身发生关系,只以自身的利益为基调和标准。这种改变的直接后果是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以及道德的危机。因而,《中庸》的天地精神为现代思想命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方案,回到古人以及《中庸》,是我们获得检省现代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