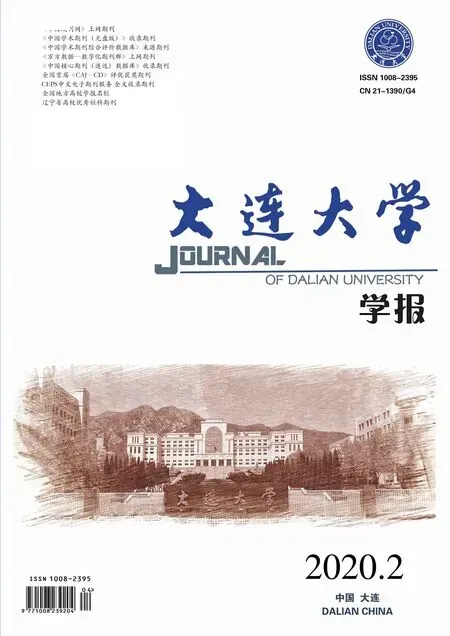朝鲜儒学巨匠柳麟锡的《宇宙问答》探析
2020-12-04崔峰龙苗倩倩
崔峰龙 ,苗倩倩
(大连大学 东北历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一、柳麟锡生平及《宇宙问答》著述背景
(一)柳麟锡的生平
柳麟锡(1842年—1915年),字汝圣,号毅菴,是朝鲜王朝末期最有影响力的卫正斥邪派代表学者和最有名望的反日义兵运动领袖,也是典范的“守华终身”之儒学巨匠,更是矢志不渝地追求“尊华事大”的爱国文人。他出生于朝鲜江原道春川府柯亭里世尊儒学的文人家庭。幼年时受教于叔父柳重教和学者金平默,14岁起拜华西学派奠基人李恒老为师,学习儒学经典,深受其爱国思想熏陶,并继承李恒老遗志,主张斥倭斥洋。
李恒老主张对内维系儒家道统,坚持春秋大义,对外“尊华攘夷”,要求“北伐满清,恢复明朝”。李恒老及其门人弟子更是以“卫正斥邪”为口号,坚决反对西教及当时朝鲜社会流行的开化思潮,发起一系列轰动朝野的“上疏运动”,故而被称之为“卫正斥邪派”。另外,其叔父柳重教也是华西学派的重要人物。因此,柳麟锡自幼在华西学派的熏陶下成长,后来逐渐成为“卫正斥邪派”的领军人物之一。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日本陆续侵犯中国和朝鲜的主权,并企图通过对朝鲜王朝施压,使其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王朝通过《马关条约》与清朝终止宗藩关系,开始走上谋求独立自主之路。但是日本浪人制造刺杀闵妃的“乙未事变”和高宗国王为摆脱日本控制而躲入俄国使馆的“俄馆播迁”等事件,更加突显出朝鲜王朝很难维持独立自主地位的危机。为了真正实现独立自主,朝鲜王朝试图寻求清朝的支持,以解除日本和俄国嵌入朝鲜半岛的阴谋。于是,多次遣使到清朝磋商建交之事。与此同时,朝鲜独立协会主张国王高宗改国号称帝、“设门立馆”,并且批判朝鲜传统的“尊华事大”思想,积极开展反对“事大主义”的万人集会。由此,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转变为平等外交关系,朝鲜国王称帝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于是,朝鲜人的对华观也从“慕华事大”急剧转向为 “脱华开化”和“排华独立”,且逐渐成为朝鲜社会主流思潮,而以华西学派为代表的朝鲜儒林人士则仍然坚守传统华夷观念,极力主张“尊华事大”。
柳麟锡作为华西学派传承者,为了挽救民危国难,竭力维护儒家程朱理学,举起“卫正斥邪”的旗帜,主张“尊华攘夷”,把朱子学以外的一切学说都以“邪说”加以排斥。在学问上“崇正学、辟异端”,即以孔孟、朱子、宋子(指朝鲜实学者宋时烈)学说为正统,将西方文明和国内诸多思潮视为邪说排斥。他在对外关系上“尊华攘夷”,即尊崇中国。他主张用坚守儒学正统的方式来抵抗外来侵略,进而“救国保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朝鲜李氏王朝日趋没落,政治腐败, 经济衰弱,社会矛盾加剧,国防力量不堪一击,因而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武装侵略被迫开港到亡国的时期。面对这一国家危难和民族危机,柳麟锡高举“卫斥尊攘”“尊华事大”的旗帜,倡导和领导反日义兵运动。在反日义兵运动初期,他的“卫正斥邪”思想达到高潮,后因随着儒生在义兵队伍中领导权受限和义兵运动的失败,这些政治主张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而淡出历史舞台。
早在1866年“丙寅洋扰”发生之际,他随李恒老赴京上疏,主张“内修自强,抗击外洋”。对于西方列强的武装挑衅和吏治混乱的局面,腐败的朝廷无法应对。他目睹这一朝野混乱局面,深感盲目接受“西学”的弊端,从而更加坚定了“卫正斥邪”的决心,并作《江华洋乱》[1]55一诗。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之际,柳麟锡与其门人共同呈上《伏阁儒生斥和疏》,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坚决反对与日本修好通商,主张“卫正斥邪”以救国难。此后,他带领华西学派进行“卫正斥邪”运动,积极宣扬“尊华事大”主张。1895年,日本制造“乙未事变”,杀害明成皇后,并强行颁布“断发令”。于是全国各地儒生纷纷举义,他被门人推举为江原道堤川义兵队长, 率门下举起反日义旗,拉开武装反日义兵运动序幕,史称“乙未义兵”。他向全国发表《檄告八道列邑》檄文,揭露日本的侵略蛮行,号召“为国母报仇”、“驱逐日寇,恢复国权”,并率先指挥其三千多人义兵队伍,转战于忠清、江原、京畿、庆尚等道,重创日军和卖国逆贼,带动了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反日义兵斗争。由于受到日军和官军的合力镇压,其义兵队伍连遭挫折,因寡不敌众、义兵队伍发生分裂,失败而终。此时,他提出“北迁”之策, 率领残部队伍240余人转移到中国辽东。但在辽东桓仁县又遭到地方官吏的阻拦,不得不解散其队伍,只带领24人到通化县五道沟。他在吉林省通化县五道沟定居时,设立“乡约”,坚持讲学,以图再起,并继续和国内门人士友取得联系,推动其“卫正斥邪”的乡约活动。
1897年,高宗派人前去招抚柳麟锡,表示亲日派已被击退,“断发令”已经废除,希望他回国。但他回国后,对高宗改国号“大韩帝国”不满,翌年春再次移居中国辽东。1905年11月,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外交权和警察权被剥夺,事实上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义兵运动再起,史称“乙巳义兵”。1907年,日本逼迫高宗皇帝退位,解散军队,朝鲜国内再度掀起反日义兵高潮,史称“丁未义兵”。他再度潜回国内参加义兵运动,但影响大不如前,很快被日军镇压,1908年7月,他亡命于俄国海参崴,欲求组建统一的义兵部队。1910年他被推举为“十三道义军”都总裁,统一领导国内和俄领及中国东北地区分散的义兵队伍,积极开展反日义兵斗争,且等待进军国内的机会。但反日义兵领袖人物先后遭到日俄当局的联合检举,又一次失败。日本吞并朝鲜后,他流亡到中国辽东,继续从事培养反日人才及著述活动,1915年3月14日卒于辽东(今辽宁省宽甸县芳萃沟),享年74岁。他一生留有大量诗歌、散文,并著有《宇宙问答》《尼峰稿小抄》《昭义新编》《道冒篇》《洛书大衍局图》等,均阐述了其“尊华事大”的主张。
(二)《宇宙问答》的著述背景
柳麟锡从1911年春到去世为止,为整理自己思想的著述活动倾注了心血,先后编撰《散言》《宇宙问答》《行状》《道冒篇》等。其中最能集中反映他的思想之书则是《宇宙问答》。
《宇宙问答》是以问答形式概括其政治思想和中华观及时局观的代表著述,1913年著于云岘(俄罗斯沿海州境内)。该书详细反映了1910年代因日本吞并韩国和中国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儒学知识分子对“国道双亡”的时代认识和反开化论,同时集中反映出他为维护东洋文化而主张排斥西方文明的“东方文化保存论”和“西方文明批评论”。这本书是韩末代表性的朱子学民族主义者综合地提出为保存东方文化而排斥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唯一之书。
《宇宙问答》是朝鲜被日本吞并和中国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柳麟锡为世人解释导致这一时局的原因和提出解决方策而著的。1911年秋,他听到中国发生革命,满人退去,实行共和政体的消息。他起初认为“华人打败清朝是件快事,但追随西方是比追随清朝更丑陋的事情,像正在参加革命的袁世凯这样的‘英雄’所做的事情可能和圣贤不同,只能观察今后发展,别无他法”[2]178。为此,他彻夜难眠,并且同年秋开始把自己的思索执笔著书。其后,他敏锐地观察中国辛亥革命的进展趋势。1912年3月,他听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他认为中韩两国是命运共同体,革命现在已到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的时期。于是他写出《与中华国政府》、《与中国诸省士君子》等意见书,让门第白三奎、张基正、金基汉等为总统袁世凯和中国政府及各省人士传信。这些信件的内容是只有恢复中华旧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强盛和自立[3]232-234。同时,他不顾老躯病缠,倾注心血,昼夜著述,终于1913年3月完成《宇宙问答》。这本书是为了给参加辛亥革命的袁世凯和他的表弟袁世勋等人看而写的。其内容涉及天理、人心、中外政治制度、东西方学术得失等问题。1913年6月,他让弟子金基汉等人在天津印刷800册《宇宙问答》,传给袁世凯等人,但是被中国警察没收。第二版由他的门人白三圭、金基汉于1914年冬天, 在中国东北奉天省暖泉山(今辽宁省宽甸县)刊行。柳麟锡逝世后,其弟子金基汉又去中国(关内)分发该书。
柳麟锡晚年著述、发行和分发《宇宙问答》的最终动机可以概括为主张君主制、反对共和制,进而维护儒家大道。第一,据《年谱》记载,柳麟锡在辛亥革命时听说中国将采用共和制,于是著述本书。这是由采用共和制与否将决定中国和韩国命运的现实认识而做出的决定。因此,柳麟锡为劝说自己认为是“英雄”的袁世凯废除共和制,实行君主制而写了这本书。第二,柳麟锡一直支持性理学的世界观和专制君主制,他担心大韩帝国的灭亡会导致“小中华”的灭亡。所以,他认为如果中国选择西方共和制作为统治方案,中华政治传统的帝王大统将被中断,文化传统的文物典章和衣钵制度将被废除,最终断定东方将会陷入文化黑暗期。因此,他极力反对引进共和制。第三,柳麟锡认为实行共和制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对韩国产生影响的国际问题。因为在中国实行共和政体的话,韩国(人)也必将议论共和政体的实施。从世袭君主制拥护论者柳麟锡的立场来看,这是难以接受的现实问题。但1910年代初期,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地区活跃的大部分独立运动家们就已经接受了共和制。即使如此,他仍为了反对在中国和韩国实行共和制撰写《宇宙问答》。
他反对共和制,支持君主制,其根本意图是排斥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保存儒教圣人大道。他一生所盼望的性理学社会结构包括专制君主制、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立足于农本政策的自给自足经济体制、儒教文化体系和价值规范。其中,柳麟锡欲求拼命守护的正是儒教文化体系和价值规范。即比专制君主制更上位的是孔子、孟子等中国圣贤的教诲,三纲五常等儒教伦理,用发髻、宽袖等文化体系表现的儒教大道。柳麟锡撰写《宇宙问答》的最终动机就在于此。
柳麟锡倡导和终身展开的抗日义兵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保存非实际存在的儒教大道,而非实际存在的王朝或国家的存亡。在朝鲜发布“断发令”之际,他提出作为儒林行动方案的“处变三事”即“去之守旧,举义扫清,致命自靖”。当义兵队伍失败而解散后,他欲求自杀之际弟子李正圭进言道:“现在先生担负着大道的责任,和那些与国家命运与共的人不同”[2]182。1910年韩日合并后,他又提出“处义三事”[4]261,充分表现出终身“遵华”“保华”“守华”之意念。即他认为“尊华”是儒学文明之天经地义;“保华”是保持君主之必然途径;“守华”是自己终身之信仰意念。这些都表明其根本宗旨是比起王朝(或国家)的保存,更重视儒教大道的保存。因此,对于他来说,无论是袁世凯、专制君主制,还是大韩帝国等现实的人物、制度、国家都是次要的。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保存儒家文化体系和价值规范。
二、《宇宙问答》的主要内容
(一)帝王大统论
柳麟锡反对西方共和制,主张君主制。他认为“帝王继天而立极,御万方,莅万民,万机之所总,万化之根本,惟其如是,称之曰大一统”[5]173,只有设立国君,实行君主制,国家才能统一强盛,社会才会安定,这是天理所在。正如他在辛亥革命后,听闻中国采取西洋共和制度,给中国政府的书信中所说“鸿雁有帝,蜂蚁有君,此天然不易之理也,可以人而不如微物乎”[3]232。且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的共和制弊端丛生,总统无实权又受制于臣下,而臣下各自为私,致使民众愈发困顿,最终引发动乱。鉴于此,柳麟锡主张“惟立君,立必推有德,一天下之公心,合天下之公议而已”[5]174。但是君主制也存在一些弊病。古往今来,帝王之争致使无数无辜生灵惨遭杀害,柳麟锡提出“以一姓相传为定势,而不改变,则无可虑”[5]178,不过他忽视了同姓之间还是会有争夺,依然会有帝王之争;他认为王位世袭是天理,如果遇到暴君,“臣当用伊尹周公之忠”[5]208,这样就可以国泰民安。当西学冲击朝鲜王朝立国之根儒学,而民族和国家犹如处于风前灯火之际,他坚信只有君主制才能挽救国难和国民。
“尊华攘夷”也是柳麟锡帝王大统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守华终身”。他的主张跟宋时烈以来的朝鲜历代朱子学者的“尊周大义”一脉相承,都是奉明朝为正朔,否定满清,并认为朝鲜为“小中华”,延续着明亡以后“中华”之血脉。他对中国极度推崇,说:“盖中国,世界之一大宗,天地之一中心也。中国立则世界定而天地成,中国跌则世界乱而天地毁”[5]208。他声称他所保之国不是朝鲜,而是“中华一脉”,救国之道也就是“保华之道”。
(二)宗教圣贤论
柳麟锡所说的宗教圣贤论,实际就是尊孔,只有这样才能保国保人类。他认为“孔子天纵之大圣,道继往圣,学启后贤,立为天下万世之教宗,出百代王,作一太极,中国人类可以有不宗乎”[5]174,中国乃至全人类都应该推崇孔教,尊孔子为圣人。1914年,柳麟锡在《书孔社会杂志》中说,他听闻中国毁道叛教、废孔庙祭祀,怒气冲天又伤泪溅地,高度赞扬孔子为“天地也日月也”[6]204。且“道”、“化”皆由“教”决定,三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才能使国家安定。面对国家民族危机,事大主义的“小中华”思想使柳麟锡对尊孔救国深信不疑。诚然,孔子的尊周正统思想确实有利于号召当时的朝鲜民众起来反抗侵略,维护正统。但是这种救国之策实行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而且当时受西学冲击,各派思想纷呈,并非所有人都信奉孔子。甚至有人提出废孔教的主张,柳麟锡坚决反对说“今废孔子之教则失其所有之正性情也”[5]221。
除了尊孔,柳麟锡还提倡文教兴国。“文,国之所以成化而为光华也”[5]177,文治对教化民众、国家繁荣昌盛起着促进作用。国家的治乱盛衰都和文教密切相关,文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柳麟锡在《国病说》中提到养育人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更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主张用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圣贤之学来培育人才,作为国家发展的永续力量,即“养育人才,国之大务也长计也。道之以礼义廉耻,申之以孝悌忠信,尽资以圣贤之学,各修其纲常之道,成德达材。大小各就,以为国家无限之需用,是则保国之基也”[4]224。在日本对朝鲜进行文化愚民政策时,意识到文化教育对于救国极为重要,不得不说他对时局有着独立的思考。
(三)伦常正道论
“中华之为中华,非以其地而已,为以其道也。革其道而永无,亦难其地之永有也”[3]234。柳麟锡认为道创造世界万物、五常五伦以及国家制度,决定人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他所说的“道”就是“伦常大道”或“伦常正道”,是“维持宇宙之栋梁,奠安生民之柱石,一日不道乎,此则国不国,而人不人矣”[5]174。他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李氏王朝,将“道”与“伦常道德”相结合,竭力维护儒教性理学,举起“斥正卫邪”的旗帜,把朱子学以外的一切学说都以邪说加以排斥。他在《西行时在旌善上疏》中说道:“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三纲……不可容于万世”、“天下之为国,各有长技……而我国以礼义制度为长技……岂有不敬惮而加慢侮哉”[1]605,极力主张践行儒教的三纲五常,注重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讲求以礼仪制度治天下,如此便可克敌制胜。
但是,他面临国家民族危机,积极投身反日义兵运动实践之后,他开始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认为道德是关系到反对外来侵略胜败和国家兴亡盛衰的基本因素。这恰恰和以往儒家脱离实际而空谈道德修养相反。他认为只有道德得到充实,才能战胜外来侵略,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反之亦然。柳麟锡反对儒学者空谈道德修养,强调道德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他主张道德因素决定国家兴亡夸大了道德的作用。
“道举其要,则仁义也”[5]176。在他看来,实践的道德不是孤立的,而是兼备“智、仁、勇”即文武双全。只有这种道德才是不空虚、内容充实的真正的道德,才符合“五常五伦”,通于万事万物。可是“有夫妇,不可以不有别”、“夫死死从”[5]189,他的伦理道德观并没有摆脱儒教封建伦理道德。
(四)衣发重制论
柳麟锡认为重视衣发且世代传承,才是顺天敬祖守孝保国之举。在他看来“发,与生俱生也。衣,人以而物不以也。宜其重之,而不可不之重也”[5]191。“衣是身之所威仪,而古之圣人法而作之,万世传之”[5]174,上天让人穿衣而不是羽毛,所以人区别于万物而威仪。古代圣贤做法服,从天子到庶人着装皆有规定,在中国已有千年,朝鲜也已经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从人类始祖开始,上天便把头发依附于人的头上,历经千百代。古代圣贤认为,头发得于天,受于父母,是与生俱来的,其重要性已成为定法,在中国世代相传上千年,在朝鲜也存在千年之久。头发法服,和天地相关,与万物区别,代表一个人的德性、伦理和礼仪,严肃庄重。
面对“断发易服令”,柳麟锡在长潭聚集几百名门人士友,举行了大规模的讲习礼和乡饮礼,并发表《乙未毁服时立言》。在其文中主张若断发易服,就失去士人坚守之道,从而得罪于天地、圣贤、先王、父祖,即“守先王之道而死,士之义也”[4]216,倡导儒学救国之道。在《宇宙问答》中,他认为外国人不知头发重要而削发,是对天的大不敬。中国、朝鲜人学习西方削发,是不可取的。何况家中微小的旧物都要珍惜爱护,而衣发有千年之久,不是一般旧物,却不珍惜爱护,有违人之常情且不合道理。断发易服,就会失去上天眷顾和为人之重,并且有违孝道。中国、朝鲜人应该遵守衣发重制,才对得起皇天、先祖、古圣贤,国家才能得以保全。这对于激发民众抗日救国加入义兵队伍起到了号召和推动作用。
(五)为政以德论
柳麟锡的为政以德不同于孔子,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君主有德,国家强盛;臣下有德,互相敬让;民众有德,忠和一气。上下同心同德,天下太平。但是只有德,并不能完全治理国家,还需要刑法来辅助治理。刑法能禁止民众为非作歹,鞭策民众向善。惩罚是出于爱护,死刑是创造生存机会,都是仁的表现。如果政刑相辅相成,大国一定会有所畏惧,不会轻易入侵。但是也要法随世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照搬古法。只有以德为主、以刑为辅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此外,孔子的为政以德主要用于统内,柳麟锡则在于御外。他认为如果朝鲜能早日以德为主,就能抵挡外来侵略。“朝鲜二千万人,恨不早力主道德,而今后且当另注意于主道德也”[5]206,可见柳麟锡想以德为主来抗敌救国。《国病说》中道“民惟国本,保国在保民”[4]223。他认为君主当爱民如子,人民视君如父,君臣亲如一家则可保国。同时也要注重道德教化,使得民心所向,内无乱贼,共御外敌。
“不论贵族贱族,用其贤,不用其不贤”[5]208,任人唯贤是为政以德的另一层含义。选官用人要选国人都认为贤德的人,并且在考察以后才能任用。既然任用就要对其尊重、信任,不听信谗言,以宾客之礼相待。这对于国家政治是有利的,也是动乱之中萌生的强国应敌之策。
三、“尊华事大”思想的特点及影响
(一)“尊华事大”思想的特点
柳麟锡于乱世之中,坚持维护儒学正统,提出儒学救国之策,继而参与并领导“卫正斥邪”运动。其“尊华事大”思想与“卫正斥邪”思想相辅相成,贯穿始终,且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极度推崇儒家文化和盲目排他。
“盖自天地肇判,人类生焉。皇王作极,人道立焉。爰有君臣父子彝伦之大,衣冠文物制度之盛,建诸天地而作经义,垂之百世而为程法。是则人道之所以至重,中华之所以至尊也”[6]212。柳麟锡在进行反侵略斗争过程中,宣扬儒学救国主张,表达了为固守儒家文化中的礼乐典章、圣贤学说、纲常伦理和冠裳法度而斗争到底的决心。他推崇孔孟、程朱思想,认为孔子是天地、日月。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三纲五常、礼义制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民本思想等在柳麟锡尊华事大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推崇儒家学说,作为正统的儒学国家,君主是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臣民必须忠于君主。为此,柳麟锡的尊华事大思想断然拒绝了西学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设备,从而排斥西学整体。另外,由于极度推崇儒学,也排斥国内涌现出的其他思想,具有盲目排他性。
第二,区域性合作共赢观念,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作为华西学派的传承者,柳麟锡深受朝鲜朱子学“尊周大义”思想影响,尊明朝为正统,否定满清,且将朝鲜以“小中华”自居,以延续明亡后“中华”血脉。他在《处义有三》中提到“处义有三:一曰保华于国,二曰守华于身,三曰以身殉于华。盖复国然后可以保华。虽复国,至不保华有守于殉耳”[4]261,主张国人应该共同努力保华,同道中人一起守华,殉华则在于个人选择。柳麟锡认为“保华”胜于“救国”,而“救国”是“保华之道”,所以“尊华事大”救国思想的实质就是“保华”。对他来说,儒家大道比国家的存亡、民族的仇恨更为重要,所以为了保存儒家大道,他主张暂时摒弃国仇家恨,与日本联合,从而建立东洋三国连带合作,共同应对西方入侵,其视角由单一的国家发展转变为多国区域性合作,无疑是进步的卓见,对当今构建东亚共同体具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第三,柳麟锡的“尊华事大”思想具有辩证色彩。
柳麟锡在谈及“救国保华”时称“盖复国然后可以保华”,又在1912年致书中国诸省士君子时说“而贱品粗闻尊攘义理,慕向中华。殆近血诚,痛敝邦之倾覆,望中国之兴立,有赖而扶持”[3]234,强调“救国”可以“保华”,而“保华”亦可以“救国”,“救国”与“保华”紧密联系,相辅相成。
柳麟锡对为政以德思想进行深化与补充,强调德主刑辅,并且把德治的范围由原来的君主施行仁政扩大到臣子和人民。“杀之出于生道也”[5]177,他认为死刑可以创造生存机会,因为死刑的威慑,臣民奉公守法,进而安居乐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死和生是对立统一的,具有辩证法思想。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坚持的儒学是注重道德实践的儒学,而非空谈道德。他在领导义兵运动之际,重新意识到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他在领导沿海州义兵运动时亲自制定《义兵规则》和《贯一约》,加强义兵军律。和以往儒家不求实际,空谈道德不同的是,他认为只有用“智、仁、勇”充实道德,才能战胜外敌以救国家。另外,他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主张因时因势“取西之兵技兵器,及他所长”[5]187,可见,他在晚年过去盲目“斥邪”态度也有所转变。
(二)“尊华事大”思想的影响
柳麟锡“尊华事大”思想在当时的朝鲜社会产生了迥乎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作为“卫正斥邪派”的领军者,儒林普遍对他持赞赏态度,高度肯定他对儒家思想、士人精神的贯彻和坚持,为挽救国家和儒教大道而积极抗日,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被尊为“斯文宗匠”。但另一方面,他也蒙受了开化派的诘责。当时,他并不被社会主流认可,被冠以“匪徒”之名。著名开化派官员金允植认为,柳麟锡领导义兵运动失败后入辽东,诱引朝鲜和清朝百姓斥洋排外,并且与义和团勾结,将有贻害本国之举。可见,开化派对柳麟锡非常反感。此外,儒界部分学者批判他固守事大主义和“小中华”思想。柳寅植认为他崇华庙,导致士气萎靡不振,民风懦弱。“乙未事变”后,他曾说“国母遇害是朝廷之臣,非在野之民之事”。因此他受到当代人“不以国母家祸为契机举义,而只是等待断发令而举义”的批评。尽管柳麟锡博闻多识、赤心报国,但在他生活的年代却是极具争议的人物。
柳麟锡“尊华事大”思想受到儒林推崇,衣发重制论激发士兵斗志,鼓舞士气,推动了抗日义兵运动。但是却不被朝廷采纳,原因大体如下。首先,他坚决反对高宗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并且部分儒学者对他的“小中华”思想也是批判的,可见,他的“尊华事大”思想已经与迈入近代的朝鲜社会过时不适。其次,朝鲜国内学派林立,主张各不相同。而他所坚持的“卫正斥邪”思想与已占政坛的开化派针锋相对,故而其一些主张被认为是保守的,遭到社会主流思想的抨击。再次,他的一些主张更注重的是内在性,没有实效性,并且实践起来需要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无法解决燃眉之急。最后,他领导反日义兵运动,又以中国为宗,对抗侵略朝鲜的日本。后来义兵运动也是在国内外势力的联合打压下,告以失败。
四、结 语
如上所述,柳麟锡的《宇宙问答》一书,主要从帝王大统、宗教圣贤、伦理道德、衣发重制、为政以德五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尊华事大”思想和中华观及时局观。他提出了文教兴国、政刑相辅、为政以德、任人唯贤等不同观点,这些积极合理的观点说明他过去盲目的“反开化论”相比有所变化和进步。君主制、衣发重制观念虽然没有摆脱儒家传统观念的局限,面对近代化进程过分强调“尊华攘夷”,但是也有一些合理内核,对于调动民众抗日积极性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尊华攘夷”则不符合当时朝鲜社会的主流思想,颇受抨击。另外,主张道德因素决定国家兴亡夸大了道德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柳麟锡反对儒学者空谈道德修养,强调道德实践,并认为士农工商兵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这表明以“三纲五常”为准绳的封建宗法等级伦理道德根基开始瓦解。
柳麟锡的“尊华事大”思想极度推崇儒家文化,全面排斥国内其他思想以及西方文化,显然具有盲目的排他性特点。但是,他将“保华”与“救国”紧密联系,又赋予“尊华事大”思想辩证色彩。这就意味着“救国”实为“保华”,具有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历史观,其眼界已超越时代局限。
华西学派主张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或王朝,但不能没有儒教大道。因此,柳麟锡比起恢复国权和确立民权的问题,更重视儒教文化体系的保存。在《宇宙问答》一书中,柳麟锡强烈批判导致朝鲜灭亡的主犯是比日本更被仇视的“开化者中的顽固者”。因为他认为开化者是破坏东洋儒教传统且最终导致朝鲜人民心向西洋化发展的罪魁祸首。而他著《宇宙问答》的终极目标也是维护儒教大道。总之,柳麟锡一生的反开化上疏活动,在堤川、沿海州的义兵活动,平安道的讲学活动等,都具有保卫东方文化的朱子学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进而言之,柳麟锡《宇宙问答》的著述、刊行、分发活动也正是这种朱子学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
总之,柳麟锡“尊华事大”思想有合理的因素,也有其局限性。虽然他尊华事大、固守封建文化制度,对文化的交流发展和国家的近代化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这一思想指引下的“卫正斥邪”运动和反日义兵运动,不仅唤醒和鼓舞国民的爱国热情,而且沉重打击日寇侵略,为东方精神文化的保存、延续和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