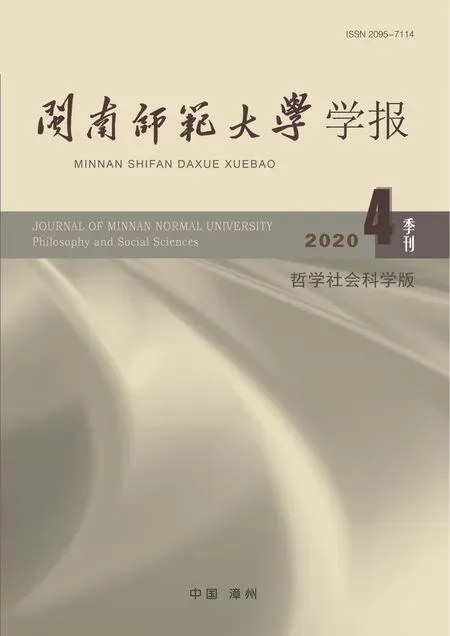《丁晋公谈录》作者考辨
2020-12-03杨娟娟刘子轩
杨娟娟,刘子轩
(1.闽南师范大学教务处,福建 漳州 363000;2.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自南宋以来的各类文献记载中,《丁晋公谈录》一书的作者归属问题就一直存疑,主要有潘延之“润益”或“所作”之说、“不知何人作”之说、丁谓“余党”之说等差异较大的说法。现为了厘清事实、还原真相,将逐一考辨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较早的潘延之“润益”或“所作”之说
持此说者乃两宋之际的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晁公武(1105—1180年)。在其《郡斋读书志》解题中,原本就经历了一个从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起先是在晁氏《郡斋读书志》较早的版本中,出现重复著录《丁晋公谈录》的情况,不仅将其学术性质归属为两个不同的门类,而且彼此的解题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是在晁氏之书的最终修定本中,不再重出,遂成定论。
如《郡斋读书志》袁本①袁本,是由《前志》《附志》《后志》三部分合为七卷,其中《前志》源于晁公武门人杜鹏举于宋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间(1180—1184年)刊刻行世的蜀刻四卷本,今已佚,传世的是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年),由黎安朝在袁州(江西宜春)重刻的四卷本,即所称袁本。在黎安朝重刻之时,还一并刊刻了由赵希弁依据自家藏书续撰的蜀刻四卷本《附志》一卷,又在次年刊刻了同为赵希弁据衢本摘编而成的《后志》,合于前后所刻形成了《郡斋读书志校证》的袁本系统。详见(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前志》卷二上《杂史类》第三十一“晋公谈录三卷”的解题曰:
右皇朝丁谓撰。多皇宋事。每章之首,皆称“晋公言”,不知何人为润益。初,董志彦得之于洪洲潘延之家。延之,晋公甥,疑延之所为。[1](P254)
由此载可知:晁氏在认为《丁晋公谈录》一书的作者为北宋丁谓的同时,又依据该书记载内容“多皇宋事”,且因“每章之首皆称晋公言”的缘故,提出了“不知何人为润益”的质疑。接着晁氏按照该书最早出现在丁谓外甥潘延之家的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推断:该书初成于丁谓之手,终则由潘延之“润益”而成。概而言之,晁氏所谓“润益”之说的关键在于:确认该书的原作者应当是丁谓,潘延之只不过是进行加工润色的整理者而已。
可是,同在袁本《前志》卷三下《小说类》第五十五“晋公谈录一卷”的解题中,却是差异很大的另一种说辞:
右皇朝丁谓封晋公,不知何人记其所谈。此书襄阳董识得之于洪洲潘延之,晋公甥也,疑延之所作。[1](P254)
由此载可知,在晁氏看来,丁谓应当不是《丁晋公谈录》一书的作者,而是一个追述当朝历史故事与自身经历的人,至于听故事、作记录并整理成书的人,其实“不知何人”,照理应该不会是丁谓本人。接着依旧按照该书最早出现在丁谓外甥潘延之家的实际情况,做出推断为:该书可能是由潘延之“所作”。简而言之,晁氏所谓潘延之“所作”之说的精要在于:丁谓最多只是一个成书素材的讲述者或提供者,潘延之才是真正修撰成书的原作者。于是,同在袁本中就出现了前后大相庭径的两说,对后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不过,仅以晁氏潘延之“所作”之说的推断而言,应当是不可能的事(详参下文辨析)。因此,该说在晁氏后来的修订中已经自行做出了修正,最终被摒弃了。
再据《郡斋读书志》衢本著录《丁晋公谈录》一书不再重出,且与袁本《前志》卷二上《杂史类》基本保持一致的情况来看,晁氏见到的应是《丁晋公谈录》的三卷本,并依据其学术性质准确归属为史部杂史类。至于该书的作者,晁氏虽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很明确的肯定,但最终还是倾向于坚持《丁晋公谈录》一书的原作者是丁谓,潘延之只是对该书进行过加工润色的整理者。若将此作为晁氏最终坚持的定论来看,应当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所以学界对此一向予以充分的尊重。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因晁氏生长于北宋时期著名的官宦之家,自然谙熟上层官僚之间的逸闻轶事,故所言较为可靠。二是因晁氏书中著录的均为其所拥有的家藏之书,也是经过晁氏“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1](P17)之后的相对较为完善的精校精刊本,故晁氏最终得出的定论,确实具备较高的可信度。三是现存于晁氏衢本所载的可靠程度更高,这是因为衢本是在蜀刻四卷本刻行后,晁氏又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修订和补充,最终形成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的蜀刻十二卷本,这也是较早由晁氏的另一门人姚应绩编辑刊行的本子;尽管蜀刻十二卷本的原本今已佚,但是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年)由“游钧在衢州(今浙江衢江区)重刊蜀刻十二卷本”[1](P2)传之后世,实可据之;尤其是在晁氏历经反复修订并得以刊刻的衢本中,之所以能够最终自行删除了早期著录于《前志》卷三下《小说类》第五十五中的“晋公谈录一卷”条目及其解题,而保留了早期著录于《前志》卷二上《杂史类》第三十一中的“晋公谈录三卷”条目及其解题,这应是晁氏修订过程中经过认真考订后做出的、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判断,也是长期以来学界认同度相对较高的结论。
二、受晁公武“不知何人作”之说影响下的作者归属
从衢本的角度来看,晁公武袁本中存在的前后冲突之说最终是得以自行解决了,可是晁氏之书一向有不同的两个版本系统流布于世,这影响到后世的各种目录书在著录《丁晋公谈录》一书时,始终还是存在着三类具有明显差异的记载。
第一类是受晁氏之书影响而保持存疑的“不知何人作”之说。诸如,在编纂体例、图书分类等诸多方面直接承袭晁氏之书的宋人陈振孙(1179-约1261年),在其《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丁晋公谈录一卷”条的解题中,仅有一句曰:“不知何人作。”[2](P206)显然,按照此载只为“一卷”而不计为“三卷”的实情来看,陈氏同晁氏一样,对《丁晋公谈录》一书的作者持怀疑态度,于是在最终难以得出定论时,只好参照了晁氏之书袁本《前志》卷三下《小说类》第五十五“晋公谈录一卷”的解题中“不知何人记其所谈”的记载,既没有采纳晁氏之书《前志》卷二上《杂史类》第三十一“晋公谈录三卷”的解题所载,也没有沿袭袁本前后任何一种推断,只是得出一个继续存疑的结果。尤其是陈氏判定《丁晋公谈录》一书的学术性质为史书,故采纳晁氏袁本中将其准确地归入史部的做法,而并没有沿袭晁氏早期归入子部“小说类”的做法。不过在史部之下,陈氏之书的进一步归属又与晁氏有所不同:陈氏在史部之下虽设“杂史类”,但将《丁晋公谈录》归于“传记类”中,而不是沿袭晁氏的做法将其继续保留在同样设置的“杂史类”中。足见,陈氏对晁氏之书既有承袭,也有摒弃,更有谨慎的判定与严谨的做法。也正是由于陈氏持有这一判定和做法,影响元代修《宋史·艺文志》时,将史部传记类中李昉之子李宗谔所撰《李昉谈录》之下的、包括“《丁晋公谈录》一卷”在内的八部著作,统一归结为“并不知作者”[3](P5119)的情况。再至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孙星衍在其《孙氏祠堂书目外编》卷四著录“《丁晋公谈录》一卷”,并在此条下存小字注文曰:“不著撰人名氏。”[4](P177)及至今日,处于存疑依旧未决的前提下,自然就会出现整理者认为《丁晋公谈录》“传为丁谓撰”①如据大象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收入虞云国、吴爱芬整理的《丁晋公谈录》,署名情况即是如此。的作者不确定现象。
第二类是受晁氏之书影响认定该书为丁谓所作,即间接倾向于潘延之“润益”之说。如明代李栻辑录历代野史而成丛书《历代小史》,该书收录《丁晋公谈录》一书时直接署名为“宋丁谓编”[5](P408);清初钱谦益在其《绛云楼书目》中先著录“丁晋公谈录”,然后在此条之下存小字注文曰:“三卷。丁谓。”[6](P51)显然李、钱二人已是毫无疑问地认定该书作者是丁谓,几乎不顾及晁氏所持潘延之“润益”之说原本存在着的质疑的一面。诸如此类确定作者的情况,在宋代以来的公私目录书著录中相对比较常见,看似明确承袭着晁氏袁本与衢本记载一致的结果,实际上是在逐渐忽略了晁氏存疑的情况下,最终将丁谓理所当然地视为《丁晋公谈录》的作者,且因持是说者日众,自然也就成为较为通行的结论,以至于成为现今该书作者认定的主要导向。
第三类是受晁氏之书影响而倾向于潘延之“所作”之说。此说虽早已被晁氏自我修正,但其影响一直存在。特别是此说的关要之处正在于:认定丁谓不是《丁晋公谈录》的作者。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考订和论证,并最终得出该书作者是潘汝士的结论。如:
《丁晋公谈录》到底是潘延之还是潘汝士所记,这里须作一简要的考证说明。潘延之名兴嗣,“自幼得官,高蹈不仕”。宋廷曾发表他为试将作监主簿,但他却“抗志不就”。“嘉佑间,宰相韩琦等奏,乞加拔擢。凡所旌宠,每至辄辞”。因而他的朋友杨杰也说:“延之,有道之士也。得官不赴,退居钟陵三十年。”潘延之的妻子钱氏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终年四十七岁。潘延之即便比他的妻子钱氏大十岁,其生年也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到丁谓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时,潘延之年仅七岁。到丁谓死时,潘延之也才过弱冠。而《丁晋公谈录》的内容涉及到不少宋真宗朝的典章制度和掌故,非与丁谓过从甚密、且熟悉朝廷典章及掌故者所不能记。因此,《丁晋公谈录》不可能出于潘延之之手。潘汝士系潘慎修之子。潘慎修字成德,祖籍泉州莆田,其父潘承佑始定居洪州。潘慎修仕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累官至右谏议大夫、翰林侍读学士,于宋真宗景德二年去世。潘汝士时为太庙斋郎,被宋真宗特擢为大理评事。天禧五年,潘汝士又以太常博士直集贤院,与潘洞、萧贯等人并直史馆。其后,仕至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潘汝士在以太常博士直集贤院、直史馆期间,正是丁谓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因此,《丁晋公谈录》出自潘汝士之手当为可信。[7](P4-5)
目前学界的这一考定结果,确实令人信服,不仅最终纠正了长久以来影响力较大的晁氏所持潘延之“润益”之说,即认定了作者不会是潘延之;也彻底否定了晁氏曾认为有可能是潘延之“所作”之说,即肯定了作者不可能是丁谓。据实而论,《丁晋公谈录》一书虽出自潘延之洪州家藏,但能够真正确定潘延之“润益”或“所作”该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丁谓在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被封为晋国公、当年七月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的事实来看,《丁晋公谈录》一书的创作时间,一般不会早于1022年之前;再从该书中所载“晋公被谪之初”“冯侍中拯薨背”“王相公钦若薨背”[7](P13)之类发生在1022年之后的史实判断,也是如此。然而,潘延之②延之,是潘兴嗣(约1023—1100年)的表字。潘兴嗣,南昌新建(今江西南昌)人,潘慎修之孙,潘汝士之子,丁谓之甥。通经史,工诗文,与曾巩等时当世著名文士相友善,《宋史》无传。其人,据宋人曾巩于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奏章中称:“潘兴嗣五岁以父任得官,二十二岁授江州德化县尉,不行。熙宁二年,朝廷察其高,以为筠州军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岁,安于静退三十余年。”[8](P1802)由此可推知:潘延之的生年应该不会早于1022年。也就是说,在丁谓被贬期间,潘延之至多是个刚刚出世的孩子,肯定不会有作此书的可能性。二是从《丁晋公谈录》记载的主体内容来看,均以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事及朝廷制度为主,内容多涉权臣逸闻轶事与朝廷典章制度之类。然而,据《万历新修南昌府志》记载的潘延之其人,则是“少孤笃学,与王安石、曾巩善”“仕为德化县尉,因刺史许诚不为礼,径归筑居豫章城南,自号清逸居士”[9](P374)之类的情形。由此可推知:生平专心向学、为人清高自傲的潘延之,,既不热心于仕途,又无丰富的仕宦经历,在志趣、情性完全不同于丁谓。也就是说,若无必要需求与特别兴趣,处在正常情况下的潘延之是不可能花时间和精力来撰写或整理这样一部作品的。三是从出自潘延之家中的藏书情况来看,应是其祖父与父辈的遗迹居多,即据《全唐文纪事》载:“豫章潘兴嗣家,有李后主归朝后乞潘慎修掌记事手表。慎修,李氏之旧臣,而兴嗣之祖也。”[10](P495)也就是说,《丁晋公谈录》一书出自潘延之父辈所作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其父潘汝士在朝为官时期与丁谓交往过密,官职一连升迁,及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十月四日,潘汝士已由殿中丞升任为“太常博士、直集贤院”[11](P4736)。同时,潘汝士也是丁谓被贬之后,深受牵连的主要亲属之一,即“降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权判盐铁勾院潘汝士知处州。汝士,谨修子,丁谓女壻也①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十三载,“降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权判盐铁勾院潘汝士知处州,汝士,谨修子,丁谓壻也。”且《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十七载,潘汝士于太平兴国四年解试,而丁谓于淳化三年登进士甲科,则潘汝士与丁谓二人理应年龄相仿。晁氏《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等均记潘延之为晋公甥。《宋史·潘慎修传》中记潘慎修有二子,即潘汝士、潘汝砺。故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潘汝士为丁谓女婿一说存疑,笔者认为,潘汝士可能为丁谓妹婿,而潘延之即为潘汝士之子。”[12](P2293)。足证潘汝士为该书作者的可能性确实最大。
三、四库馆臣的丁谓“余党”之说与潘汝士为作者的最早记载
在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根据《丁晋公谈录》“不著撰人名氏”,且所载内容“皆述丁谓所谈当代故事”,尤其是所记丁谓之事“皆溢美”而着力攻击其政敌寇准等状况,断定该书“即未必延之所作,其出于谓之余党,更无疑义也”[13](P1216-1217)②该书记述“澶渊之事,归之天象,一字不及寇准”;记载寇准“挟嫌私改冯拯转官文字事,皆颠倒是非,有乖公论”;称赞丁谓“筹划军粮,决真宗东封之行,以为美谈,则欲誉其才适彰其附合时局,小人之情状,终有不能自掩者矣”等。。四库馆臣所持论断的紧要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否定了晁氏之说最终倾向于《丁晋公谈录》先由丁谓所作,后由潘延之进行加工润色的结论;二是秉持了晁氏之说中一直存在的怀疑态度,进而断定作者是不确定的丁谓“余党”。应该说,四库馆臣做出的这一论断是有价值的,对于我们确认潘延之之父潘汝士为《丁晋公谈录》的作者有着很大的帮助。
其实,早在南宋时就有关于潘汝士为《丁晋公谈录》作者的记载。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李焘(1115—1184年),在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真宗》的“景德元年”十二月条中曾引《丁晋公谈录》为例证,并明确称“此事见潘汝士《晋公谈录》”。所谓“此事”的历史背景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南下攻宋,一路势如破竹,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引起宋廷震动,先是王钦若、丁谓、陈尧叟等重臣建议宋真宗南迁金陵或西迁成都以避其锋芒,最后是在寇准的极力主张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于是宋辽双方在澶州西南的澶渊隔河对峙至当年十二月,签订澶渊之盟而结束战争。所谓“此事”的引证情况是在这次结盟前夕,先出现“日有食之”的天象,接着处出现“德、博州并言契丹已移寨由东北去”的奏报,于是李焘在此下引《丁晋公谈录》记载以证其事,故存双行小注曰:
晋公言:“景德中,契丹寇澶渊,在河北,圣驾在河南,阵次,忽日食尽,真宗见之忧惧。司天监官奏云:‘按《星经》云主两军和解’。真宗不之信,复检《晋书天文志》,亦云‘和解’。寻时,契丹兵果自退,而续驰书至,求通好。”时晋公为紫微舍人,知郓州。此事见潘汝士《晋公谈录》。按是日敌使韩杞已入对行营矣,《谈录》妄也,今不取。[12](P1289)
鉴于潘汝士的仕途沉浮与丁谓在朝中的升迁休憩相关,且与丁谓又属亲戚关系,所以视其为丁谓“余党”,自当毫无疑问。再者潘汝士在仕途上一贯追随丁谓并与之结党,肯定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更适合的机会听取并记录丁谓的言行,为之刻意誉美亦实属理所当然。至于《丁晋公谈录》一书所载以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故事为主,则最适合的创作人选也非潘汝士莫属:一方面是因为其父潘慎修与其本人相继的仕宦经历经正是处在这一时期,故对宋初三朝诸多逸闻轶事了如指掌;另一方面是因为潘汝士曾任职直集贤院,完全具备查阅和了解当朝实录、会要等机密档案资料的条件,故对朝廷历史掌故相当熟知。所以,后来《丁晋公谈录》一书出自潘汝士之子潘延之家藏书中,也正是确定该书理应出自潘汝士之手的最为直接的证据。
总之,《丁晋公谈录》一书的作者归属问题中,潘延之“润益”或“所作”之说肯定是与事实不符,故早在晁氏之书修订到后期就已经做出了自我否定,即为盖棺定论,则后世沿之者显然是被误导所致;“不知何人作”之说的关键在于保持质疑态度,有益于后世继续探明真相;丁谓“余党”所作之说应是最具有可能性的定论,且诸多证据指向潘汝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