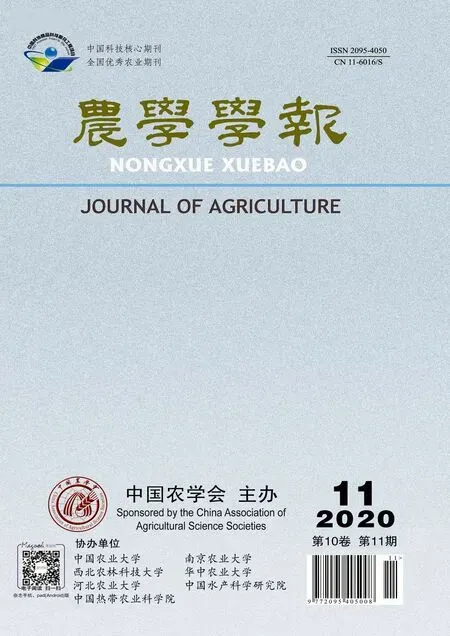降雨对不同坡比边坡产流产沙过程的影响
2020-12-02杨庆楠徐金忠李志飞侯淑艳
杨庆楠,徐金忠,李志飞,侯淑艳
(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土保持研究所,黑龙江省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哈尔滨 150070)
0 引言
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侵占土地面积大,侵蚀类型多样且相互作用。根据2012年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仅黑龙江省长度在100~5000 m的侵蚀沟有11.55 万条[1],沟道总面积928.99 km2,总长度45244.34 km,沟道密度0.10 km/km2。受植被覆盖度低、土壤抗冲性差、降雨相对集中[2]及人为因素等影响,侵蚀沟发展迅速[3],水土流失形势严峻[4],造成耕地、道路被吞噬,土地生产力下降等诸多不利后果。侵蚀沟是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问题的集中表现,是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5]。侵蚀沟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发展沟、稳定沟和半稳定沟[6],其中半稳定沟和稳定沟的沟道两侧边坡相对平缓,植被能稳定的生长,而发展沟的沟道坡面坡度较大,沟岸及沟坡经常发生崩塌[7]、滑坡等现象,鲜有植被生长。发展沟的沟岸扩张、沟底下切,发展迅速,是侵蚀沟治理中的重中之重。
目前,边坡植被防护措施研究主要集中于高速公路、道路、填埋场、排土场等特定边坡[8-11],鲜有针对侵蚀沟边坡植被防护措施的研究。在实际侵蚀沟治理中以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为主,陡峭边坡需削坡至稳定边坡比后进行植被措施的配置,削坡会侵占一定面积的耕地,由于尚无补偿政策,往往难以实施。目前侵蚀沟边坡以栽植乔灌木为主,如杨树、樟子松、灌木柳、沙棘等,根系深、分布范围广,固土作用强,优于草本植被。但在侵蚀沟恢复前期乔灌木生长缓慢、地表裸露面积大,防止雨滴击溅的能力弱,而草本具有生长速度快、迅速覆盖地表等优点,在侵蚀沟边坡前期防护中应用前景广阔。
因此,本研究以无芒雀麦(Bromus inermisLeyss.)、早熟禾(Poa annuaL.)、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L.)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径流小区的观测,了解分析在植被覆盖下次降雨对产流产沙过程的贡献,以期为侵蚀沟植被边坡防护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径流小区布设
在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科技园区一自然坡面上进行人工削坡,设计坡度为1:1.2(39.81°)和1:1.5(33.69°),坡向为南北向,削坡后坡面回填2~3 cm表土。在1:1.2和1:1.5 坡上分别设置A 组、B 组试验区,每个试验区又分为8 个微型径流小区,小区间隔为0.3 m,边界由铁板构成,铁板高40 cm,地下埋深20 cm。径流小区由坡面区、集流区、导流区组成,如图1 所示。通过导流区的径流泥沙直接流入集流桶(上口直径28.5 cm,下口直径25.5 cm,高34 cm)中进行收集。
1.2 试验设计
选取适合在当地生长,且生长迅速、固土能力强的无芒雀麦、早熟禾、紫花苜蓿3种草种。播种前进行室内发芽试验。2018 年5 月3 日,人工清理、平整坡面,充分浇水灌溉后将3 种草种按照表1 配置分别按照50 g/m2等重量比例撒播在各相应的小区坡面。播种后覆0.5~1.0 cm表土,轻轻镇压,苫盖遮阳网。出苗前定期灌溉,出苗后无需管理,定期拍摄照片。
1.3 径流泥沙测定
每次降雨产流后,将集流桶内径流泥沙充分搅拌均匀,取出500 mL浑水样品(不足500 mL全部取出),标记好带回实验室滤纸过滤、烘干,测定泥沙量,剩余浑水全部倒入量杯中测定体积,做好径流量的记录。

表1 径流小区植被配置
1.4 试验仪器
降雨因子采用SL-2 型虹吸式雨量器(长春,0.1 mm精度)测量;泥沙样品采用鼓风恒温烘干箱(中国大陆,1℃)烘干,称重采用天美JA2603D 电子天平(上海,1 mg)测定。
1.5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与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6—9月采集有效径流泥沙样23次,对应的降雨历时、平均雨强、最大30 min雨强(I30)、降雨总动能(E)、降雨侵蚀力(EI30)情况,见表2。
2.1 1:1.5和1:1.2坡比边坡降雨产流情况
2.1.1 1:1.5 坡比边坡降雨产流由图2 可知,总体上次降雨产流量随雨量大小的变化而变化。0~5 mm 次降雨量,径流小区平均产流2.4 L,5~10 mm次降雨量,径流小区平均产流4.4 L,大于10 mm 次降雨量,径流小区平均产流7.4 L。同等次降雨量对6月和7月产流的影响大于8月和9月,主要是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和径流小区建设土层稳定性受干预造成的,贺小容等研究表明土层紧实度直接影响坡面产流结果[12],同时径流对降雨量的敏感性随植被盖度的提高而降低。但也存在特殊情况,如7月15日和8月30日的降雨量相对较低,但产流量却较高,是因为7月15日降雨的历时短,平均雨强、E 和EI30较大,对坡面的侵蚀能力强,产流量大。8 月30 日虽雨强和土壤侵蚀力较低,但之前发生连续降雨,土壤含水量高,土壤下渗能力差,进而形成较多地表径流。7 月15 日与7 月16 日的降雨量相差悬殊,产流量却相近均较高,与7月12日降雨量大、历时长,土壤有足够时间入渗,土壤含水量高有关,影响7月15日的降雨入渗量。8月前,不同降雨量下,B1~B8产流量差距较小,8月及以后B1~B8产流量差距变大,且降雨量越高,差距越显著,这是由于前期植被覆盖率均很低,受植被影响较小,雨热同期后不同草种植被覆盖率有显著差异,导致植被截流降雨作用的差距,产流量不同。7—9月,各次降雨B8产流量都高于植草各径流小区,且随时间推进差距逐渐增大,可见植被减流作用的重要性。6月中旬—7月,除B1和B2的其他植被配置小区各次降雨下产流量相差不大,8—9月,5 mm降雨量左右时各径流小区产流差别不显著,10 mm 左右降雨量时B7减流作用非常显著。前期B3减流作用明显优于B1和B2,后期B1和B2减流作用反超B3。

表2 次降雨各因子情况
2.1.2 1:1.2 坡比边坡降雨产流由图3 可知,A 组次降雨产流随雨量大小的变化而变化,与B组趋势一致,0~5 mm降雨量,径流小区平均产流2.4 L,5~10 mm降雨量,径流小区平均产流4.9 L,大于10 mm降雨量,径流小区平均产流8.4 L。坡度增大,次降雨量愈大,A 组产流量愈高于B 组,但增量很小。肖登攀等研究也表明坡度增大后,增大产流增加的可能性[13]。整体上看A7、A6、A5和A3产流量较小,但不同时间段优势植被配置不同,6月A3和A7产流少,7月A6和A7产流少,8 月A3 和A7 产流少,9 月A7、A3、A5 产流均低。6 月和7月A组和B组各次降雨产流量相近,虽坡度变大,但同样降雨量和较低植被盖度情况下,产流量相近。8月除4日和27日A组产流量明显高于B组,其他次产流A组和B组相差不大,与降雨量大小和土壤条件密切相关。9月各次降雨产流量A组显著高于B组。即坡度变陡后,植被生长前期产流量大小较为一致,8月雨量较小时A组和B组产流差距不大,当雨量较大时,差距明显变大,9月无论降雨量大小A组产流大于B组。
2.2 1:1.5和1:1.2坡比边坡降雨产沙情况
2.2.1 1:1.5 坡比边坡降雨产沙由图4 可知,整体上产沙量不随降雨量大小的变化而变化,各次降雨下产沙量差距悬殊,存在阈值。降雨量小于15 mm,产沙量较少,降雨量大于15 mm,产沙量明显升高,且B8产沙量比其他植被配置径流小区增长量更大。王蕙[14]、黄俊[15]、钟壬琳等[16]试验表明坡面产沙随雨强增大产沙量也增大。6月和7月次降雨下的产沙量较高,一方面由于径流小区建成初始,土壤容重、紧实度、稳定性等变化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由植被根系发育不完全,固土能力弱导致的,占海歌研究表明植物根系能提高土壤的抗蚀性,降低产沙量[17]。产沙量主要集中在6 月20 日和7 月16 日两次降雨,是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平均雨强、I30、E、EI30高造成的。同时6 月5 日、7 月19 日和8 月30 日产沙量也较多,其他次降雨产沙量则极小。6 月5 日,径流小区土壤稳定性没有恢复,土壤颗粒随径流极易被带走导致产沙量大。7月19日产沙量较高由平均雨强、I30、E、EI30较高形成的。8 月30 日降雨量较小产沙量却较高,是因为8 月24—27 日有连续降雨,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地表产流量大带走泥沙量大。相同降雨量下,6 月和7 月产沙量高于8 月和9月。6月植被混播配置B6、B7、B3产沙较少,随着时间推移,不同时间段优势植被配置不同,7 月B3、B4、B5减沙效果较好。8月B1和B2相比其他植被配置,由前期产沙量高变为明显下降,甚至超过混播配置及紫花苜蓿。9月产沙量均极少。
2.2.2 1:1.2 坡比边坡降雨产沙由图5 可知,A 组在各次降雨下产沙走势与B 组基本一致,次降雨产沙主要集中在6月20日、7月16日和7月19日,同样的次降雨量,坡度变大后,坡面抗侵蚀能力降低,产沙量明显增加,特别是7月19日A组产沙急剧增长,与赵龙山等[18]研究表示坡面产沙量随坡度增大而增加相同。6 月5日和7 月20 日产沙量也较高,其他次降雨产沙量极小。6—9 月0~5 mm 降雨下A 组与B 组产沙量相近,6月和7 月大于5 mm 次降雨A 组产流显著高于B 组同期产沙量,8月和9月则差距不大。8月24—27日连续降雨时均有产沙,略高于B 组同期产沙。侯沛轩[19]研究表明,除去降雨、坡度、坡向、土壤等相同因素,产沙量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径流量大小和植被种类的不同。但8月30日次降雨下,A组产沙量低于B组,是因为坡度变大后,坡面入渗能力降低,8月24—8月27日产流量相对较多,土壤入渗量并未达到饱和,8月30日降雨土壤入渗增加,地表径流减少,产沙减少。初期A3产沙量较少,后期A5 和A7 产沙量少。因为各径流小区播种重量一致,A3紫花苜蓿播种量大,快速出苗,根系发挥作用和降低击溅作用较早,与艾宁研究植被改土可减沙结果一致[20],与孙婷婷等[21]研究认为紫花苜蓿混合生态护坡保土效果好一致。
3 结论
(1)产流量与降雨量密切正相关,产沙量并未随降雨量紧密变化,不同次降雨范围产沙量差距悬殊,15 mm 雨量是产沙量的阈值,产流能力随植被生长有所降低,但与主要受降雨影响,产沙能力受植被生长影响相对较大。
(2)不同时间段次降雨减流减沙优势植被配置不同,紫花苜蓿草种前期减流减沙效果好,无芒雀麦和早熟禾草种后期减流减沙效果好。
(3)坡度变大后6月和7月次降雨产流量大小较为一致,8月次降雨量较小时产流量也相近,当次降雨量较大时,差距变大,9月无论次降雨量大小1:1.2坡比产流都明显高于1:1.5坡比。
(4)产沙量主要集中在6月和7月的几次降雨中,1:1.2 坡比边坡产沙高于1:1.5 坡比边坡,8 月和9 月产沙量较少,1:1.2坡比边坡产沙量略高。
4 讨论
1:1.2坡比边坡植被生长后期产流量稍高,前期产沙量较高,在植被配置时要充分考虑前期水热条件不足情况下仍能较早出苗且植被覆盖有优势的紫花苜蓿,并需提高混播比例,但紫花苜蓿后期保水保土效果变弱,搭配后期体现保水保土优势的无芒雀麦或早熟禾,陡坡边坡防护将达到较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