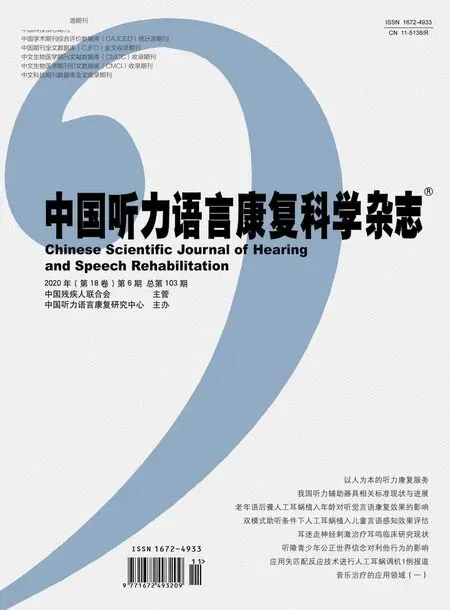OTOF基因突变听神经病听障儿童人工耳蜗植入康复效果分析
2020-12-02邱素梅邹雨滴张颖文谢薇
邱素梅 邹雨滴 张颖文 谢薇
听神经病是一组具有特殊听力学及临床表现的感音神经性聋,其听力学表现是ABR严重异常或缺失,耳声发射(OAE)正常或耳蜗微音电位(CM)引出,纯音测听与言语识别率不成比例下降[1]。随着电生理技术及基因学的深入研究和高通量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听神经病的鉴别诊断、病变部位及病理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2003年Kelly等在4个非综合征型隐性听神经病家系中鉴定出OTOF基因是这4个家系的致病基因[1],从而确定了OTOF基因是第一个与非综合征型隐形遗传性听神经病相关的基因[1]。OTOF基因突变为婴幼儿听神经病的主要致病基因之一,在我国患儿其突变率高达41.2%[2]。OTOF基因是耳蜗内毛细胞的基因表达,该基因表达异常者,植入人工耳蜗可取得较好的效果[2~4]。本文3例听障儿童确诊为听神经病,配戴助听器效果不佳,基因检测均携带OTOF突变,于2018年初行人工耳蜗植入,通过术前术后对声音感知、言语识别率和语言能力等评估进行比较,探讨术后康复效果。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病例1:女,5岁5个月,双耳极重度听力损失,双耳ABR 100 dB nHL未引出相关波形,双耳OAE引出,排除中耳病变,耳部CT平扫及MRI内耳未见异常,基因检测①OTOF(2p23/NM_194248.2),位点c.5098G>C纯合突变;②SLC26A4(chr7/NM_000441.1),位点c.919-2A>G杂合突变,耳部CT平扫及MRI内耳未见异常,学习能力测试及精神智力发育正常,有助听器配戴史,单侧植入人工耳蜗,植入年龄4岁,对侧耳配戴助听器,术后一直在定点机构康复训练,因家庭问题曾中断康复,家长效能欠高。病史采集其弟为双侧极重度听力损失,基因检测OTOF(2p23/NM_194248.2),位点c.5098G>C纯合突变,2018年9月单侧植入人工耳蜗,学习能力测试及精神智力发育正常,目前在康复机构训练,康复效果比术前有明显进步;其父亲基因检测①OTOF(2p23/NM_194248.2),位点c.5098G>C杂合突变;②SLC26A4(chr7/NM_000441.1),位点c.919-2A>G杂合突变;其母亲基因检测OTOF(2p23/NM_194248.2),位点c.5098G>C杂合突变。
病例2:男,4岁9个月,双耳极重度听力损失,残余听力少,双耳ABR 100 dB nHL未引出相关波形,OAE引出,排除中耳病变,病史采集无明确病因,基因检测:①OTOF(2p23/NM_194248.2),位点c.5098G>C纯合突变;②U S H I C(1 1 P 1 4/N M_0 0 5 7 0 9.3,位点c.1 6 3 0 G >T 杂合突变;其父携带O T O F(2 p 2 3/NM_194248.2,位点c.5098G>C杂合突变;其母携带OTOF(2p23/NM_194248.2,位点c.5098G>C杂合突变)、USHIC(11P14/NM_005709.3,位点c.1630G>T杂合突变)。患儿学习能力测试及精神智力发育正常,有助听器配戴史,单侧耳植入人工耳蜗,植入年龄为3岁9月,对侧配戴助听器,目前在定点机构康复训练。
病例3:女,5岁11个月,双耳极重度听力损失,双耳ABR 100 dB nHL未引出相关波形,OAE引出,病史排除中耳病变,CT耳部平扫内耳结构未见异常,学习能力测试及精神智力发育正常,有助听器配戴史,基因检测OTOF为c.3674A>G(p.K 1225R)杂合突变,双耳植入人工耳蜗,植入年龄4岁7月,术后在定点机构康复训练,目前已上普通幼儿园。
1.2 方法
1.2.1 助听听阈测试 助听听阈测试是功能增益评估。在符合GB16296标准隔声室下,建立标准声场并校准,即两侧扬声器与参考点等高、入射角为45°、距离为1 m,用啭音作为刺激声,测试频率为0.25、0.5、1、2、3、4 kHz共6个频率,评估标准采用正常人言语香蕉图,测得的助听听阈结果与正常人言语语音香蕉图比较,音频感受补偿范围0.25~4 kHz进入言语香蕉图为最适合范围;0.25~3 kHz进入言语香蕉图为适合范围;0.25~2 kHz能进入言语香蕉图为较适合范围;0.25~1 kHz进入言语香蕉图为看话范围,平均助听听阈采用0.5、1、2、4 kHz 4个频率的均值,评估时间为术前、术后4个月和术后1年。
1.2.2 听觉功能评估 测试材料选用《听障儿童听觉、语言能力评估标准及方法》,包括自然声、韵母、声母、数字、声调、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三音节词、短句等10项内容。测试环境本底噪声≤45 dB(A)安静房间;测试者坐在受试者术耳侧(优势耳),距离50 cm并排坐;采用口述给声,强度为70~75 dB SPL;受试者双侧配戴助听设备,采用听话复述或听话识图指认,记录各项测试的正确识别率。术前评估韵母、声母、双音节词、短句等4个项目;术后4个月、12个月10项内容全部评估;为比较干预前后的效果,术后选择韵母、声母、双音节词,短句等4项与术前进行比较。
1.2.3 语言能力评估 测试材料选用《听障儿童听觉、语言能力评估标准及方法,包括语音清晰度、词汇量、模仿句长、听话识图、看图说话、主题对话6项内容,对听障儿童的发音、词汇、语法、理解、表达、交往能力进行测试。评估标准为正常幼儿各年龄段语言发育指标——语言年龄,通过测试可以获知患儿语言发展水平及与正常幼儿相当语言年龄。测试环境为≤45 dB(A)的安静房间内,测试者与患儿面对面坐,给声强度70~75 dB SPL,每项测试内容有相应的测试方法和要求,术前评估听话识图、主题对话等2项,术后4个月、12个月6项内容全部评估,选择术后听话识图、主题对话2项与术前进行比较。

表1 3 例患者术前、术后不同时间助听听阈 (dB HL)

表2 3 例患者术前、术后4 个月、1 年听觉能力(%)

表3 3 例患者术前、术后不同时间语言能力评估(岁)
2 结果
2.1 助听听阈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病例1术前补偿效果以1 kHz以下和4 kHz补偿不足;病例2术前平均助听听阈≥85 dB HL,提示助听效果差;病例3术前高频补偿缺损。3例患者术后4个月全频听力提高,听力重建后平均助听听阈在43 dB HL以内;术后1年平均阈值35 dB HL内,重建听力曲线较术后4个月平坦。
2.2 听觉能力评估结果
从表2得知,3例患者术前、术后4个月和1年平均言语识别率情况。病例1术后1年韵母、声母、双音节词、短句识别评估得分比术前有明显提高;病例2术后1年在韵母、声母、短句识别评估得分与术后4个月和术前比较,提高不明显且双音节词得分比术前、术后4个月下降。病例3分术后1年在韵母、声母、双音节词、短句识别评估得分比术后4个月和术前明显提高,康复效果明显。
2.3 语言能力评估结果
表3表明,3例患者术前、术后4个月和1年语言能力情况。病例1理解能力术后1年比4个月、术前明显提高;交往能力术后1年比术后4个月、术前提高,术后4个月与术前比较无变化。病例2理解能力术后1年比术后4个月、术前明显提高,但交往能力术后1年、4个月与术前无变化。病例3理解能力、交往能力术后1年与术前有明显提高,术后4个月比术前变差。
3 讨论
3.1 听神经病的干预没有金标准
听障患者可以通过助听器及人工耳蜗获得不同程度受益,有学者认为人工耳蜗植入由于电刺激可引起听神经的同步化,但植入后效果存在多样性,个体差异较大,除了自身影响因素外,关键取决于病变部位能否精确判断。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及不断深入研究,目前发现与听神经病遗传有关的基因至少有17个,OTOF基因突变在我国婴幼儿听神经病中有较高突变率,携带该基因突变的患者植入人工耳蜗可获得较好效果[5],因为人工耳蜗植入术绕过耳蜗受损的毛细胞直接刺激螺旋神经节、听神经并传到大脑产生听觉[6]。本文3例被试为听神经病,基因检测都有OTOF突变。病例1携带了OTOF(2p23/NM_194248.2),位点c.5098G>C纯合突变,其弟弟也是该基因同个位点纯合突变,其父母携带同一基因同一位点的杂合突变;病例2携带了OTOF(2923/NM_194248.2),突变位点c.5098G>C纯合突变,其父母携带了同一基因同一位点的杂合突变,病例1及病例2的家人同样携带同一基因同一位点突变,虽然该基因提示突变临床意义未明,可能是无相关数据库表明其临床意义或到目前没有报道其致病性,但从以上2例患儿及家系基因突变位置、蛋白改变和病理有致病性的可能性。文献报道在听神经病患者中检测到该变异,千人基因组(1000 g 2015 aug-ALL)和dbSNP147数据库中有收录,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其有致病可能。病例3检测OTOF为 c.3674A>G(p.K 1225R)杂合突变,该位点导致听障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杂合突变临床不能明确致病性。以上基因结果虽不能作为明确听障的病因,但未来随着基因学的深入研究、数据积累可能在临床中有意义。
3.2 助听听阈是一项评估安静环境下听敏度的测试指标
助听听阈测试可以了解听障患者在听力补偿或重建后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听敏度,尤其是无言语能力的婴幼儿,可以作为助听设备调试、优化的参考依据。本研究采用游戏测听法,从表1获知,3例术前术耳(4耳)配戴助听器后在标准声场下平均助听听阈大于68 dB HL,其中1例在适合范围,2例(3耳)看话范围,提示高频补偿不足;术耳术后4个月声场测试平均助听听阈为37 dB HL,听力重建后各频率可进入正常言语香蕉图,术后12个月声场测试平均助听听阈为31 dB HL,重建后各频率的阈值较均衡,为聆听和感知不同频率的声音奠定了良好的聆听条件和基础[7]。术后在短时间内能较好配合测听,这与术前配戴助听器并参与康复训练有很大关系,术前助听器配戴史和康复训练有利于缩短人工耳蜗术后适应时间和重新建立聆听意识。
3.3 言语识别率(听觉能力)是听功能最直接的判断标准
助听听阈只反映声音察知敏感度,不能真实反映患者对言语声的分辨和识别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3例患者平均言语识别率术前、术后4个月、1年分别为22.2%、40.2%、62.3%,随着训练时间延长总体得分有所提高,但从个体得分上分析,病例1和病例3随着术后康复时间延长听觉能力呈明显上升,各项测试得分不同程度提高;特别病例3术前平均言语识别率为25.8%,术后1年为87.5%,比术前提高61.7%,取得明显康复效果,该患儿已进入普通幼儿园。例2术后1年与术前、术后4个月比较无明显提高,且双音节词得分反而下降,说明听觉能力不稳定,听能发展非常缓慢。
3.4 干预后效果存在个体差异性
听神经病患者植入人工耳蜗后效果具有多样性。人工耳蜗植入的最终目的是使患者听懂言语、发展言语及提高语言表达能力[7],并融入主流社会。语言能力评估可以分析听障儿童通过康复训练获得阶段性语言发展的水平[8]。研究表明语前聋患儿植入人工耳蜗后3年内闭合式言语理解能力明显提高,开放式言语理解能力在前2年发展有限[9]。人工耳蜗术后在语言发展、表达能力及言语清晰度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影响因素较多,如植入年龄、术前配戴助听器史、手术方法、听神经纤维数量、耳蜗损害和发育情况、螺旋神经节数量、期望值、父母或监护人的效能、康复方法[10~14]等。从表3获知,病例1植入后虽在机构康复训练,但因家庭问题中断训练,家长积极性不够,效能不高,从而影响康复效果。病例2术前残余听力少,助听效果差,术后的康复效果与术前比较提高不明显,听觉语言发展缓慢,干预后效果不佳。病例3术后12月为3岁水平,无论从理解能力还是交往能力术后1年比术前提高明显,与双侧同时植入人工耳蜗提供听觉生理优势有一定关系。表3显示病例1和病例3术后4个月理解能力、交往能力得分反而比术前差,分析原因可能为①人工耳蜗植入后开机一般是术后1个月,初次刺激的电流较小,开机首要工作是习惯佩戴及逐步适应环境声音,对人工耳蜗设备的适应时间不一,存在个体差异,特别强调跟踪随访。②提供足够的声音灵敏度需要循序渐进的优化调试。③助听器与人工耳蜗工作原理从声学方面有本质的区别,助听器是利用患儿的残余听力进行声放大,是一种补偿手段,而人工耳蜗绕过耳蜗毛细胞直接刺激听神经,是一种听力重建手段,虽然患儿术前有助听器配戴史,但植入人工耳蜗术后需要重新认识、熟悉声音和建立聆听意识。④适应期重点是培养聆听意识和发展听能,可能导致语言能力暂时性退步。
4 小结
OTOF突变听神经病患儿植入人工耳蜗术后随着康复时间的延长可获得不同程度的康复效果,但存在个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