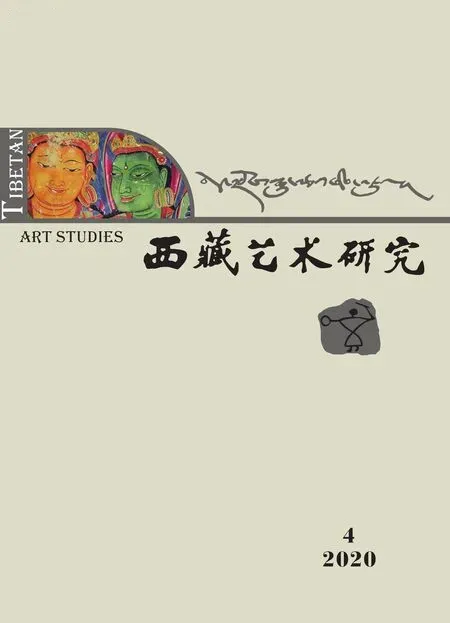以世界文化遗产罗布林卡为例浅谈汉藏文化交流
2020-12-02普智
普智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不仅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展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独特的作用,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深刻地影响着高原的经济生产活动和居民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它的文化具有许多与高原以外的其他地域明显不同的特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考古学证明西藏从史前时期开始与外部世界已经有了交流,以物品交流命名的如麝香之路,食盐之路、还有地域之间的交流,如唐蕃古道、蕃尼古道,以及唐宋以后的茶马古道①霍巍,讲座2019年7月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考古发现与高原丝绸之路》.。
一、汉藏融合的建筑风格与园林意境
罗布林卡从建筑外观透露着浓郁的藏式建筑风格与寺观景象,汉藏交融的建筑与造园意境亦是其一大特点。罗布林卡的总体布局与中国皇家园林十分相似,在持续的营造过程中,各院落风格虽有别,但从平面布局,到意境构造,从具体手法,到细部装饰充满着汉地造园艺术的特点。
1、园景按自然区域分区,使各区各具其特色。罗布林卡建筑采取园中园格局,以墙垣、植物、楼阁为分割空间手段,悠然使人产生深不见底的错觉,营造了咫尺山林的园林意境。还以措吉颇章宫殿建筑群水池为主题,以路径环绕,水池中置三岛,湖心宫和西龙王宫、门亭以石桥相连,两岸果林夹道,花草相间,可谓“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宫殿与园苑可谓水乳交融,每一处都呈现着不同的景观,达到了移步换景效果。
依罗布林卡需求及条件突出了三个主区,使其成为全园之重心,并因而造成各区之主次关系。在宫殿建筑群中布置单独和分散的小园,如主宫:达旦明久颇章、格桑颇章、坚赛颇章的格局功能基本相同,而其他的殿则有为藏经阁、鲁神庙、祈福殿、观戏楼等分布于主殿的周围。
3、汉藏融合的屋顶装饰。罗布林卡主要采用中国建筑屋顶歇山式,屋顶在建筑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藏式建筑因西藏材料、气候、日照等自然地理因素,多采用铜鎏金、琉璃瓦。格桑颇章、达旦明久颇章等大多数建筑屋顶采用了铜鎏金歇山顶,湖心宫的屋顶采用了黄琉璃瓦歇山式。建筑细部如青灰大理石雕刻的栏板、望柱、木雕的门窗、隔扇、以及彩绘几乎都使用了汉族的传统营造手法。湖心宫背面的鲁神西殿是汉藏风格的混合结构,在攒尖屋顶的下部采用了汉式的斗拱结构,屋顶飞檐翘角,汉藏建筑艺术在此结合的巧妙自然。
4、运用对比、掩映、借景、错觉艺术手法。利用措吉颇章宫的一池湖水倒映着岸上林木、建筑、景物、山水;四时花木和天空变幻景色,如朝霞落日、星月银河;俯览桥下流水,水里游鱼。待冬日树叶凋零,拉萨哲蚌寺上方神山便清晰的倒映于湖水中,以及宫殿的翘首飞檐、黄墙、白宫与苍翠林木,就如同宫殿
所蕴含的意思一样,“虽由人做,宛若天开”。
5、运用动、植物的生态环境艺术。罗布林卡是把宫殿、水、植物、动物集聚一起,这也是中国园林重要的造园艺术。拉萨虽地处高原,海拔高、气候干燥,生态亦十分的脆弱,罗布林卡却有自己小气候,这里地处拉萨河流经之处,地下水十分的丰富,在历经200余年人工的雕琢后,渐渐褪去了灌木野林。几辈的达赖喇嘛在这里广植了各方奇花异草、高林巨树,尤其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植花木、育禽兽,从锡金、以及西藏热振、林芝、亚东、错那等地引进和栽种了大量的植物、花草。其中较为常见花是被人们叫做“张大人”花的波斯菊,据说,驻藏帮办大臣张荫堂“张大人”带去了一包的“扫帚梅”种子,这种花生命力极强,迅速传遍西藏各地,人们不知花名,只知是张大人带来的,故一律称他带来的花为“张大人”。如今园林植物的品种已是十分丰富,植物品种达到200 余种,树木的数量达到3 万余株,花卉更是数不胜数,在园丁的精心培育和呵护下满园恣意怒放。
罗布林卡措吉颇章院内的一排兽房①洛桑土登:《罗布林卡志》(藏),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内部资料),1983年.,曾喂养有大象、虎、豹、鹿、熊、孔雀、狼等近20 种动物。对虎、豹等凶猛的野兽采取圈养,对孔雀、梅花鹿、獐子、大象等温驯的动物采取放养。湖中放养斑头雁、黄鸭等水禽,水中的蛙、鱼、龟、蟹,据说均被认为龙族的眷众。唯此番美景,龙神才肯栖息。林中的果实吸引了鹦鹉、麻雀、猫头鹰、喜鹊、戴胜鸟、斑鸠、画眉、和诸多鸟类嬉戏争食,发出各种清脆悦耳的啼声,争相吐蕊的花卉散发着满园的芬香,招蜂引蝶,让原本静的罗布林卡平添了许多天然野趣。
二、壁画艺术突出汉藏关系及文化交流
罗布林卡的壁画以勉唐画派为主,内容十分丰富,尤其以汉地题材绘制的壁画更是比比皆是。
1、达旦明久颇章宫殿的历史壁画②洛桑土登:《罗布林卡志》(藏),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内部资料),1983年;《拉萨文物志》1985年8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68 页.。在达旦明久颇章宫殿的斯喜堆古齐殿堂的墙面绘制的约29 平方米的壁面中,有两百余幅画面和三百零一段文字,壁画以连环画形式收录了西藏古往今来的重大事件,汉藏情谊的内容贯穿始终,忠实客观地展现了这一历史事实。在西墙上约占三分之二的二十余幅画面,描绘了迎请文成公主的经过,唐朝太宗皇帝“六试婚史”,吐蕃请婚使者大臣噶尔·东赞以智取胜,早已成为藏族人民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幅文成公主进藏图,场面十分壮观,描绘了公主携十二岁释迦牟尼等身像、珍宝、经书、典籍等策马入藏的重大历史事件。文成公主进藏,是藏汉关系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成公主是为发展藏汉友好关系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她所携带的释迦牟尼像迄今仍供奉于拉萨的大昭寺,仍被千万佛教信众所膜拜。西北墙面还记录了公元710年唐中宗将金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的故事。金成公主携带了各种工艺典籍,随同她入藏的还有乐工杂技人等,唐蕃之间友好往来不但得以加强,中原的文化也更加广泛地传播到了吐蕃。有关金成公主的事迹,一幅“宴前认舅”图更是形象地描绘出金成公主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联姻,生下王子后,被赞普的另一个王妃抢走,当时公主十分悲伤。次年,在举行王子的“迈步”庆宴时,赞普邀请公主和大唐使者、王妃和大臣贵戚参加,分列两旁就座。赞普将斟满酒的金杯递给王子,让他将酒献给舅舅。王妃的亲友,拿出各种玩物呼唤王子,而王子却将酒献给唐朝使者,投入汉族舅舅怀里说:我是汉人的好外甥,母子重聚,情景感人。赤德祖赞上书唐玄宗时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成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唐蕃之间近二百年的甥舅情谊,记载这段历史的唐蕃会盟碑现仍然耸立于大昭寺前,反映了唐蕃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历久不衰,世代保持下来。
东墙上一幅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皇帝图,再现了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受到顺治皇帝隆重接待的情景。翌年,五世达赖喇嘛返藏,顺治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确定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壁画还绘有1908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情景,记录这段历史的壁画在罗布林卡其他殿堂里也多有展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壁画还绘制了1954年,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三位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中南海亲切接见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场景。壁画生动地记录了自公元七世纪以来的一千三百年间,藏民族和其他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的历史,表现了西藏与祖国内地水乳交融的血肉情谊。
2、坚塞颇章宫殿内的汉地壁画。在罗布林卡的坚塞颇章宫殿二楼的廊壁上绘有一幅颐和园全景图。这幅画反映了公元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随从的画师带回颐和园素描全景,坚赛颇章宫殿建成后,便绘制于此。画面描绘了颐和园内各处的景观及众多人物形象,在绘制颐和园佛香阁处,还有一些藏地僧人的形象,记录了这段历史,反映了藏民族据史作画、以画言史的绘画传统,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晕染,均采用藏民族传统的绘制方法,颐和园上空凌云中,示现佛祖与十六罗汉、四大天王、飞翔的比丘僧人,远处万寿山、白塔寺等景观依稀可见,描绘了一处人间仙境。
藏族画师们还在罗布林卡内创作了许许多多汉地题材的壁画,如道教八仙人物,福禄寿喜,关公、婴戏图、长寿老人比比皆是,穿行于罗布林卡各宫殿就如同在壁画中畅游。
三、宫藏文物中的汉藏情谊
藏传佛像艺术在千百年发展历史中,通过不断吸收和融合印度、尼泊尔、中原内地等艺术风格和手法,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藏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体系。其珍藏文物品类,一应俱有,有佛教造像、唐卡、经书文献、玉器、瓷器、印玺、漆器、珐琅、竹木牙骨雕刻、金属器皿、文房珍玩等,可谓一座巨大的文化艺术宝库。这些珍藏中还有历朝中央赏赐给的各类物品,有的则是历代朝廷为西藏特制。
1、佛教造像
罗布林卡藏有西藏本地产的各种质地,风格各异的佛教造像外,也有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和中原内地等造像。据文献记载,汉地造像分为早期汉地造像和晚期汉地造像①德达·久美林巴的《造像鉴定的渊源分类及特点考略》。罗布林卡现藏有部分明永宣德和清代佛像较多,多用青铜和黄铜制作。如宫藏一尊鎏金铜金刚持佛像,造像妩媚、装饰繁缛、气质高雅,座底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六字,可谓造像之上品。在藏传佛像艺术中,明朝宫廷制作的佛像十分引人注目。由于明朝宫廷造像制作主要集中于永乐和宣德两朝,所以通称为“永宣宫廷造像”,或简称“永宣造像”。这些专门制作的佛像往往兼有中原、西藏、尼泊尔等地风格,表现出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罗布林卡旧藏中,最重要最多的部分是清代西藏官办作坊“雪堆白”工院的造像。当代著名的扎雅活佛指出,“雪堆白”造像总体风格比较明显的东印度即帕拉遗风,酷似永宣佛像,“酷似永宣造像”充分说明汉藏文化的交融,这些造像的风格和特点,充分体现西藏制佛工艺此时达到了巅峰阶段和文化交融。
2、唐卡艺术中的汉藏情谊。
西藏绘画艺术通过吸收、借鉴印度、尼泊尔和中原内地等地的绘画技艺而逐渐形成自己地方特色的画风,有齐岗画派、勉唐画派、钦则画派、噶赤画派、尼泊尔画派等。罗布林卡旧藏唐卡的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唐卡从工艺上分为两类,绘画类和织绣类,从绘画类来说西藏勉唐画和噶赤画派发展历史使得其绘画颇具汉风,在吸收了汉地明代绘画中的山、云、水、石、花、树、建筑等画法,噶赤画派的作品,画面构图简洁、色彩淡雅鲜活,所绘人物形神兼备、特征鲜明、衣纹用笔潇洒自然,陪衬的山石、瀑布、树木花草、灵禽瑞兽有机结合了主题,可谓情景交融,使画面产生一种美丽神奇的艺术境域。
在织绣类唐卡刺绣、织锦、缂丝几乎都出自汉地工匠,大多是在明清时期由宫廷为西藏特制,如所藏一幅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缂丝唐卡是罗布林卡旧藏的一件珍品。大慈法王本名释迦也失(1355—1435年),宗喀巴大师称为“辩才无碍”的八大弟子之一,曾多次应召进京。明成祖封他为“妙觉圆通慧慈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印及金边黑色僧帽一顶。永乐十七年(1419年),他回藏后在拉萨北郊主持修建了著名的色拉寺。宣德九年(1434年)应宣宗皇帝之召,再次进京觐见,被留于京师。在此期间,明宣宗颁赐御制法轮金印,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次年十月二十四日,卒于返藏途中,明廷下令在其卒地青海卓摩喀尔建弘化寺,以示纪念。寺内修建至善大慈法王塔院,收藏其舍利①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第1 版,第559—562 页。。这幅缂织唐卡是明朝赐给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画心人物就是他本人,虽历经五百余年,仍色泽鲜艳,他为发展西藏地方同明朝中央的关系,为促进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做了毕生的努力。这
幅缂丝唐卡不仅工艺价值十分珍贵,也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对研究明代时期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和绘画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再比如一幅刺绣香巴拉法王像唐卡,描绘了香巴拉法王月贤接受时轮双身灌顶,众臣、信众听法的场景,以色泽丰富明亮的丝线为材料,采用平绣、散套绣,钉线,缠针以及平金与穿针线相结合的刺绣技法。画面色彩明快鲜艳,织物立体质感强,纹样虽然细小繁缛,却都绣制得精细,是内地传统织绣手工艺与西藏绘画艺术的完美结合。
3、宫藏瓷器
瓷器具有耐腐蚀、洁净美观、卫生实用等特点,是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内地工艺品,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瓷器易碎,古代内地与西藏交通不便,能够安全运到西藏的瓷器就显得非常珍贵。罗布林卡收藏有瓷器数千件,多为明清时期历朝中央赏赐给西藏地方上层,以盘、碗、杯、碟、瓶为主,也有历代朝廷为西藏特制,很多器物造型和纹饰明显带有藏传佛教特点,如明宣德青花梵文僧帽壶,清代官窑瓷器中常见诸如“贲巴瓶”、“多穆壶”“酥油灯”等等具有西藏特点的器物,数量可观、品种全、质量高、真实可靠,体现了明清时期文化交往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贡施关系。如:明洪武釉里红牡丹纹执壶,造型端庄、美观大方、布局严谨,绘工精细,为洪武瓷器中的精品,且保存完好,更属罕见。据文献记载,洪武一朝三十五年中,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官员、使者往来见于记载的就有四十六次。其中重要的如洪武五年十二月“乌斯藏摄帝喃加巴藏卜遣使来供方物,诏踢红绮禅衣及鞋帽、钱物有差”,还有洪武九年起“自是赐予多用瓷器铁釜”②《西藏博物馆藏明清瓷器精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22 页.,因此可以考证明代时期赏赐瓷器的先例。
另外,一件瓷器是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僧帽壶,内口沿绘缠枝莲纹,外口沿绘串枝灵芝纹,颈部莲纹托八宝纹,肩部如意头内绘折枝莲纹,腹部书藏文一周,意为“昼吉祥,夜吉祥,正午吉祥,昼夜吉祥,三宝吉祥”融入了藏民族文化的元素,铭文中的个别藏文字母及分隔符有误,显系不通藏文的汉族工匠仿书。器底双圈书六字二行楷书款“大明宣德年制”①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文物精粹》第139 页.。
所藏民国时期的一批瓷雕像也是宫藏文物的亮点之一,数量多达60 余件,个个都是民国期间名家的作品,有曾龙升的十八罗汉像、茂记生的水月观音坐像、游隆盛造的福、禄、寿三星、万顺同的“粉彩寿星”,还有一些没有款识的西游记人物形象,这些瓷雕像瓷质光滑细腻,形象极为写实,面部表情生动传神,表现了景德镇窑工高超的烧瓷技艺,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此外,从罗布林卡无处不展示了汉藏文化交融,其内的诸多家具,无论是其形制的变化,还是在雕饰、图案上内容上,融藏汉一体。如一件大理石花卉纹圆桌,其圆桌周围绘有寓意多子多福的佛手、仙桃、石榴等祝福吉祥的图案,造型简洁明亮,寓意吉祥。另一件嵌珐琅八仙人物的藏式立柜也颇具特色,八仙属道教之神,但早已渗入了佛教的色彩,成为一种民间的普遍信仰。藏民族对锦缎的喜爱也可谓情有独钟,精美的锦缎还用来装裱唐卡,装饰和供养的经幡寺院、宫殿的梁柱,制成袍服、鞋帽,经书的包面,这些锦缎和丝绸大多来自汉地。还有专门为宗教活动时使用的各种法器和生活用具,这些器物带有明显的西藏特色,反映了当时中央王朝与西藏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反映了西藏文化对内地制造技术的影响。如大清乾隆年制的珐琅葫芦瓶,瓶身嵌满白色小葫芦,寓意吉祥子孙满堂、万代相传、万事如意、万寿无疆。寓意国泰民安的各类珐琅彩香炉、如意等,也都是稀罕之物,还有很多诏书、印玺、服装饰物以及等等未及介绍。
罗布林卡是中华园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颗璀璨明珠。行走藏地,就会发现,上述这些造园艺术,并非罗布林卡所独有,而是随处可见的特有景象,它是汉藏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