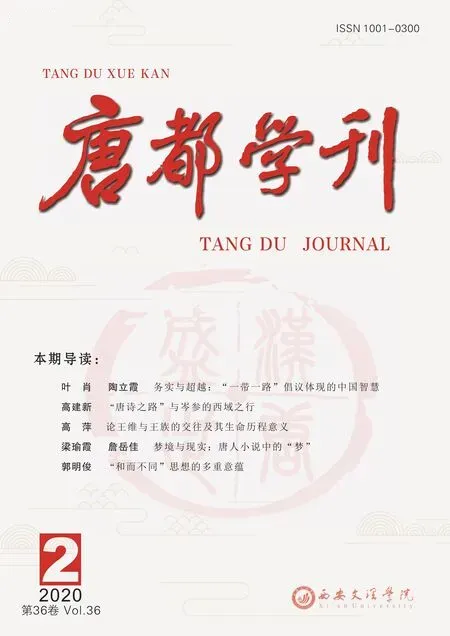青年周恩来的儒家文化观及其现代启示
2020-12-02李富强
李富强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自汉代尊崇儒学以来,儒家文化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长期处于独尊的地位,儒家思想渗透到古代中国的制度、法律与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周恩来(1898—1976)出生于清朝末年,自幼年起便受过传统私塾教育,熟读儒家主要典籍。在全面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之前,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儒家思想一直支配着他的精神与思想生活。本文力图通过对周恩来早期相关文献的梳理,勾勒出青年周恩来的儒家文化观,并立足当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以阐明青年周恩来的儒家文化观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一、青年周恩来的儒家文化观
吴国桢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的挚友,据吴国桢回忆,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中文水平在校中名列前茅。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成绩从南开学校顺利毕业,据《周恩来传》记载,他以“国文最佳者”获得特别奖[1]。就思想而言,周恩来信奉孔子的学说,“他是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2],但吴国桢并没有详细解释那时的周恩来为何是一个儒家信徒。翻阅周恩来早期的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在南开学校读书前后期的周恩来是儒家信徒说是可信的。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记载,周恩来自幼年起就交由嗣母陈氏抚养,陈氏出身于贫寒的书香门第之家,能诗文,会作画,颇有才学。在陈氏的教育下,周恩来进私塾读书,初步接触了一些儒家文化典籍,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少年时期的周恩来濡染儒家典籍,对儒家思想有浅显的认知。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既重视“西学”,也重视“经学”,认为“求西学者须有经学之根柢,读经学者当有西学之法眼”[3]。在校长的推动下,南开学校一直保持着“读经”的教育传统。青年时期正是思想活跃求知心旺盛的阶段,也是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儒家思想已经有了深入的理解与领悟,形成了其具有个人特色与时代印记的儒家文化观。概而言之,周恩来的儒家文化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严于修身的伦理道德精神、治国平天下的忧患意识、向往大同的社会理想、尚中贵和的中道和谐精神、慎终追远的家庭孝道观。
(一)严于修身的伦理道德精神
儒学是“为己之学”,是严于修身的君子之学,以自我完善和成就君子式的道德人格为第一要务。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1913—1917),发起组织了一个团体“敬业乐群会”,在《敬业乐群会简章》中规定组织的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4]13。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华大地上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在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先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特点是偏重于理智层面的求知,而中国古代文化则偏重于道德层面的践履。所以,很多新式学校的教育都注重理智精神的培养,即便如此,这些新式学校也没有将道德教育弃之不顾,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使然。周恩来组织的“敬业乐群会”宗旨虽然以智育为主体,但最后还是要归宿于道德,伦理道德问题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周恩来在谈论名誉问题时指出:“然德之不修,礼之不讲,尤其于六朝五代,而毁誉之界限益淆。”[5]47在周恩来看来,东汉的士人阶层是最看重个人名节与操守的,而到了六朝五代,熟读儒家典籍的士人阶层不讲道德修养,不谈克己复礼,毫无珍惜名誉之心。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谈到道德人格的养成问题。他说:“夫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5]181孔子在《论语》中没有提及“良心”,良心概念最早出自《孟子》一书。孟子说过:“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良心实质上就是人的仁义之心,它标识着人是区别于动物的道德存在,道德人格的养成全在于良心,但凡人去做一件事情,如果违背正理,人就会感受到良心的自我谴责,内心会有焦虑的不安感。良心没有纷扰,保持宁静的状态,正是道德人格养成的明证。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是当时兴起的两种主要社会思潮,周恩来认为教育和实业可以并行不悖,根本则在于教育。教育的重心必须放在国民的思想上,尤其是放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周恩来留学海外的时候,也保持着修身的习惯,他在1918年所写的《旅日日记》中,专门列出“修学”一栏,以格言警句作为修身原则,以期达到自我激励与磨练意志的效果。
(二)治国平天下的忧患意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修身是基础和根本,治国、平天下是最终的社会理想。儒家经邦济世的入世精神深深植根于青年周恩来的心灵世界,使他既注重“内圣”层面的个人修身问题,也重视“外王”层面的治国、平天下问题。1911年,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小学时,修身课上,老师提问“读书为了什么?”他回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4]10。又在另一篇获奖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说:“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5]2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生发了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他在《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申述说:“盖子舆氏有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彼富贵利达之徒,值上下相安之日,以为国家无事,遂泄泄沓沓,耽于宴乐,百政不举,田亩荒芜,终至盗贼蜂起,弊害丛生。内患既开,外辱斯乘。”[5]71周恩来认为当时的中国有两个危机,一个是事实上的危机,即在西方列强的瓜分与步步紧逼下,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亡国境地;另一个是精神上的危机,即国民道德的沦丧,已经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周恩来在旅欧勤工俭学期间,目睹英法等国工业、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对中国百弊丛生的现实所产生的忧患意识更为深刻。他在1921年写给同学陈式周的信中说:“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6]在某种程度上,忧患意识是圣人、君子阶层所具有的精神品性,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与完成历史使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精英意识,促使具有此意识者所忧之对象不再是个人的死生荣辱,而是关涉百姓福祉的天下兴亡,这也是中国人文精神所具有的重要特质之一。中华民族历经患难、历经千载,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忧患意识。
(三)向往大同的社会理想
“大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首见于《礼记·礼运》,儒家在本篇中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对这种理想社会的追求鞭策着历代儒家知识分子不畏艰难,力图将理想化为现实。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著有《大同书》,该书出版后,对动荡中寻求安定的读书人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青年时期的周恩来也受到康有为的影响,痴迷于《大同书》中所描绘的人人都自由而幸福的生活,并实现人的本性的理想境界。周恩来将大同视为一种最高的政体,描绘了政体的进化规律,他说:“酋长也、君主也、民主也、大同也,为政体必经之阶段,人们应渡之时期,循序而进,非一朝一夕之所可立而待也。”[5]86在青年周恩来看来,“大同”不仅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更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那么,人类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大同的理想境界呢?周恩来又回到了儒家的立场上,他在《诚能动物论》中认为儒家的诚与仁是人类的天性,即人生而固有的,没有丝毫假借,自然而然地就表现在每个人的言语与行动上。周恩来坚信:“人类之产生,距今亦千万年矣。仁灵之具无或差异,其达于大同之境、和平之途,宜矣。”[5]150人类只要将自己固有的天性,展现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上,天下为公、至善至美的大同理想就可以变为现实。即便在旅日期间,周恩来也一直对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充满向往之情,他说:“要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5]334。
(四)尚中贵和的中道和谐精神
儒家经典《中庸》说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和的状态中,天地才能形成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和谐秩序,万物才能自然地生长发育。周恩来曾说他的性格富有调和性,这显然也是他青年时期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后来,周恩来将儒家尚中贵和的理念运用到外交事务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1953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7]118。这五项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周恩来相信各个国家只要秉持这种尚中贵和的中道和谐精神,坚持这五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实现睦邻友好的邦国关系。1963年,周恩来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8]民族传统中的文化与哲学思想对民族的整体性格具有塑造作用,这是民族文化的社会学意义。就个体行为方式而言,民族文化与哲学思想可以为个体提供行动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恩来深知中国人的行动哲学与处事智慧不全是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结果,而是来自于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
(五)慎终追远的家庭孝道观
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其最高的价值理念是仁义,但最具有现实的生活实践意义的是家庭关系中的孝道。孔子将孝道视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天性之爱,对父母尽孝道是个人的天性,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极为寻常的行为。《论语·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先祖,人民的道德才能归于敦厚。周恩来在和睦友爱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使他对友爱兄弟、孝顺父母的人伦孝悌之道有直接而切实的人生体验。周恩来的生母和嗣母在他10岁之前就已经离世,但他对父母的教养之恩却是永志难忘。以至于10年后,青年周恩来对两位母亲的去世仍感到极为悲痛,读到嗣母遗墨“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5]308,然后含泪焚香静坐,来表达自己对嗣母的眷念之情。1949年后,周恩来也谈过儒家孝道的问题:“说到赡养老人,我们有些青年团员也许会问:‘难道现在还要我们讲孝道?’‘孝道’要作分析,要辩证地看。……封建统治已经被推翻了,我们就不能笼统地说‘非孝’了。”[9]面对青年团员对孝道的质疑,周恩来认为孝道在封建社会是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现在封建统治被推翻了,孝道也获得了解放,对父母尽孝、赡养老人是人的天性。孝道是顺乎人情的,它是道德实践中最基本的德行,是每个有道德良知的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
二、由“尊孔”到“排孔”:青年周恩来思想转变释疑
由前文可知,青年周恩来是个地地道道的儒家信徒,尊崇孔子。但到“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之后,“打倒孔家店”的反传统思潮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想动态,周恩来也未能置身事外,他改变原来的“尊孔”立场转而赞成《新青年》提出的“排孔”主张。青年周恩来在儒家信仰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思想转变的实质是什么?他真的排斥孔子本人的学说,抑或出于反对袁世凯等人复辟帝制的政治闹剧而排斥被符号化的“孔教”?这是我们要探寻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1917年6月,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毕业,9月即东渡日本留学。此时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引领社会思潮,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是其舆论阵地。其实,《新青年》杂志创刊号在1915年9月已经出版,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并没有对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在留日期间,《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新思想却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这一点在他的《旅日日记》中得到了确证,周恩来在1918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加着我那时候正犯着研究‘汉学’兼‘模仿古文’的两个大毛病,没有心肠去用在这些改革的想头上呢。”[5]334旅日期间,周恩来抽出大量时间认真阅读了《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原先“尊孔”的主张受到了影响,他说:“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5]334此时的周恩来不仅认同《新青年》所提倡的独身与文学革命主张,而且赞同“排孔”。
“排孔”给人的首要印象是排斥孔子,周恩来真的排斥孔子本人的学说吗?他对儒家文化是否持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呢?其实不然,周恩来排斥与否定的只是为帝王专制摇旗呐喊的“孔教”运动。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是“孔教”运动的推动者,1912—1918年间是“孔教”运动的活跃期,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其实质是为了配合袁世凯“尊孔复辟”的政治图谋。《新青年》杂志所提出的“排孔”主张并非反对孔子本人的学说,其批判矛头直指袁世凯等人的“尊孔复辟”活动。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其日记中有所记述,他在1918年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有的人说,袁世凯要不是因为日本反对他,他的事业早成功了。这句话说得很没有道理。要是中国人个个赞成他的主义:‘复古’‘君宪’‘孔教’‘军国’这四种主义早已实行了,又何必要日本许可呢?”[5]337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也有类似的认识,李大钊视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的护身符,已经不适用于时代精神生活的需要。他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说:“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0]青年周恩来对《新青年》杂志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持一种激赏的态度,新文化运动不仅批判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闹剧,而且使人们开始正视儒家文化中的僵化以及束缚个性发展的部分,为儒家文化的新发展提供了机遇。所以,现代新儒家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11]青年周恩来对待孔孟儒家的态度并未有大的变化,他还是同李大钊、贺麟等人一样,相信儒家的真精神,所谓“排孔”只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袁世凯“尊孔复辟”的政治企图。
新文化运动中各派人物批判的“孔教”,又被称为吃人的“礼教”,孔子等原始儒家主张礼乐教化,原始儒家的“礼教”本来是富于宗教的仪式与精神内涵的,它基于人的自然情感,以人伦道德为中心,以如何成人为教旨。孔子本人并不认为礼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主张“礼有损益”,“礼教”的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新变化的。但原始儒家的“礼教”被后来的专制君主利用,变成了僵化的束缚人性的教条。被袁世凯等权势者吹捧塑造的孔子并非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孔子本人,孔子被用来当做复辟帝制的护身符,使孔子受到大批判。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批判袁世凯时说:“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12]孔子是儒家文化的象征性符号,青年周恩来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孔子的儒家精神,但他由“尊孔”到“排孔”的思想转变,则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时代问题,即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问题。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危机,根本上是文化危机,儒家文化在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上丧失了自主权,没有新的生命活力,不能应对新的世界格局。危机中孕育着机遇,从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反保守、反儒家文化的思想文化运动。反而观之,却促进了儒家文化的新开展,涌现了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群体,延续并激活了儒家文化的生命。
三、青年周恩来的儒家文化观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启示
青年周恩来处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代表西方文化、制度、科技的“西学”,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而得以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中华民族固有的“国学”受到冷遇和批判,青年周恩来在《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中表达了自己对“西学”与“国学”关系的看法:“且学校潮流,多趋重于西学,故吾言国学之当视为要图。西学非可卑也,兼而学之,要不失将来实用之旨。以国学役西学,吾主之,切勿使西学役吾,而国学转置之无用之地也。……今吾学者,止知惟西学是求,视国学无所用而不重也,遂卑之。殊不知国魂国魂,惟斯是附。今吾弃之,国何以立?”[5]64在周恩来看来,国学与西学都很重要,西学的价值在实用层面,国学是“国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周恩来所谓国学,即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儒家文化又是传统文化的主干,重视国学的地位就是重视儒家文化的地位。青年周恩来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与重视,也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遗产与创造问题上的看法。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7]343周恩来进而认为中华民族的特点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将其融合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液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在确立“以我为主”的原则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彻底研究明白,并将其中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青年周恩来的儒家文化观及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正面评价,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现代启示:
其一,儒家文化中的一些核心观念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如青年周恩来的儒家文化观所体现出来的五种内涵:注重道德人格教育的修身理念、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意识、向往大同的社会理想、尚中贵和的中道和谐精神、慎终追远的家庭孝道观。儒家文化中的这些核心思想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价值,反而可以对当下青年人的某些问题起到矫正作用,如部分个体道德感衰落的道德滑坡现象,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而导致的社会责任感不强,不求中和的暴戾之气,不知孝顺父母而只知啃老的自私风气等。
其二,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可以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不可能完全抛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与传统不可完全脱节。基督教新教伦理孕育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儒家文化推动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现代化进程,儒家文化也应该参与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现代社会的一大疾病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历史虚无主义实质上是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正如青年周恩来所言:民族传统文化是国魂,是民族的根,现代社会的发展并非是与传统完全断裂开来的,在坚固的传统文化之根上才能生长出丰硕的现代成果。
其三,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从本质上看,民族复兴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复兴的主流当然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强盛了,儒家文化也必然迎来起死回生的良好机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在文化层面提出的重要方针政策,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9年,教育部表态,从2020年开始,教育部将在高校本科专业增设“国学专业”,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的精神是永存的,它并没有成为只供人们用来观赏的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也没有像西方汉学家列文森所预示的,“纪念孔子诞辰的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在为孔子唱葬歌,将他送入历史的坟墓而已”[13]。儒家文化的命运在经过短暂的曲折动荡之后,在当代中国社会愈发显现出它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