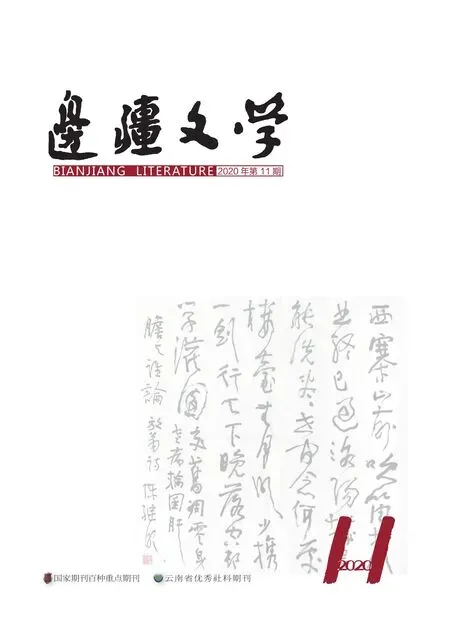老王的一米阳光
2020-12-01孙云
孙云
“老王,开工啦!”
今天是正月初八,这个年过得我腰酸背痛的,于是在上班第一天的午休时间溜达到了公司对面那家“欣欣盲人按摩”去做推拿。
从一间小小的休息室应声走出了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五十来岁的男人。花白的毛寸、瘦消的脸和一双干枯的眼睛。他熟练地蹭到了前台,问:“哪间屋?”“一号,门边靠墙的床。”
这家盲人按摩房不大,统共就一号、二号、三号三间供推拿使用的所谓治疗室,每个治疗室里有三到四张专用推拿床。除此之处还有一间公共卫生间和推拿师的休息室。
一缕阳光刚好从对面两栋办公楼之间的缝隙射进了一号治疗室。我趴在离墙最近的那张推拿床上听见“噌噌噌……”,是鞋底与水泥地面的摩擦声。老王蹭了进来,他伸手够到了我趴的那张床,手指轻轻地在床边点了两下,问:“哪儿不舒服呀,有什么重点吗?”我回答说:“哪儿都不太舒服,尤其是脖子和腰。”老王“哦”了一声,站到了我头顶的位置用两个大巴掌按了按我的脊背,然后把一块白毛巾铺在了我的肩劲上,开始从头按摩。我眯着眼趴着,享受着。但没过一会儿,我就觉得老王的手法很一般。
记得有一次去长沙出差,那儿的同事请我做过一回盲人按摩。那手法真是精湛,感觉是“一针见血”,每按一处都在点儿上,而且力道也很合适。回北京后在一些价格不菲的连锁按摩院也陆陆续续地做过几次但总也没找到感觉。春节前我就发现在公司的对面也新搬来了一家盲人按摩,所以刚一上班我就迫不及待地过来了。但是,老王有些令我失望。
他总是按不到我的“点儿”上,所以我老想挪动一下身体,好配合他的手法,但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不过力道倒还令我满意,算是弥补了一下手法的不足。
我一言不发地趴着,老王也一句话没有。不像在那些连锁的按摩院,按摩师会不断地和你说话,不是这儿不好就是那儿不好,不是该如何如何就是不该如何如何,接着就会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离这儿近不近呀,然后就该问是否办卡呀,办卡有优惠等等等等。总之去按摩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斗智斗勇的战场。因此,我轻易是不敢去的。这次一是因为太难受,二是想图个新鲜,三是盲人按摩总体比较便宜。但也是报着斗智斗勇的心理来的。可老王不仅眼盲,更像个哑巴,要不是刚进来时听见他说了几句话,还真以为他是个又盲又哑的人呢。
我实在憋不住了,先开了口:“您是姓王?”
“对。”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
“嗯,东北的,吉林。”
真是言简意赅呀,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说。
于是,我接着问:“我冒犯问您一下,您不会生气吧?”
“没啥,你问吧。”
老王似乎知道我要问他什么似的,“没啥,你问吧。”让我听起来有些心酸,有些委婉,更像是一个无底深渊。
我便问了:“您是全盲吗?”
“不是,还能看见一点光。”
“那您是从小就这样了?”
老王轻咳了一下说:“不是,是生了一场病,突然就看不见了。”
“没办法了吗?”
老王又轻了轻嗓子:“没办法了,都这么多年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似乎问到了老王的痛点。因为我能感觉到老王的手颤抖了一下。
“本来就一只眼看不见了,没一年另一只也看不见了。”老王主动和我说了一句话,而我却只“哦”了一声,不知该怎么往下说。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这样了,几十年了,就这样吧!”老王的口气让我感到了他的无奈和委屈。几十年的光阴也没把这种委屈抒发殆尽,反而更加深厚和浓重了。
我又“哦”了一声。此时我的心情倒是有些复杂了。随意而无心的几句问,似乎惊动了老王记忆深处的封印,让他有了些异动。
片刻之后,好奇心又驱使我问了一句:“那这推拿是您后来学的?”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不是废话吗,当然是后来学的。要是眼盲之前学的就叫中医了。
老王并不怎么介意,“是呀,不学这个还能学什么?干什么?总得养活自己呀。”
此时老王站到了我的左侧,开始按摩我的脊柱和左肩。
“你有点儿驼背呀。”
我一听立马抬起了头。“啊?严重吗?”
“不严重,还有点脊椎侧弯。”
我的耳朵简直都要竖起来了。“什么?严重吗?”
“不严重,以后一定要注意了,不要总是坐着,要经常扩扩胸。看,你的肩也很硬。”
我心想,完了,我的毛病被我一点一点地给挤出来了,接下来就该让我办卡了,又要开始套路了,原来老王也不过如此。但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发问,老王就又变成了一个哑巴。
总得说点儿什么,不然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因为春节刚过,除了老王和前台那位眼神也不太好的大爷外就是我了。其他的推拿师还都没上岗,更别说来按摩的客人了。按摩房虽然不大,但架不住人也少呀!我虽不喜热闹,但过于安静时,我也是要弄出点儿动静的。于是,还是我又先开了口。
“那您后来学盲文了吗?”又是一句听似废话的话。
“没有,那玩意儿不好学,而且太麻烦。”
我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应合地说了一句:“是呀!字书都那么厚,要是翻译成盲文,还不得成山啦!”话一出口又是一阵的后悔,心想,我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句句都能说在点儿上?
老王倒是笑了,“是呀,眼盲之后就没想过看书的事,其实也没什么书能让我们看,但我们可以听书。”
“听书?什么都能听吗?”
“基本上吧,现在有一种阅读软件,装到手机上就可以听,其实也不是什么都能听,但总比以前强多了。”老王的语气轻松了很多,这也让我放松下来,有点儿昏昏欲睡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老王拍了我一下,叫我侧个身。我按照他的指示侧身背对着他。直到我坐起来让他做最后的放松,接着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两巴掌后,我们都没再说话。但我总是觉得老王的心似乎很沉,沉得他都直不起腰。按摩结束,老王微低着头,面带着那种服务型的微笑说:“好了,别忘带上随身物品。欢迎下次再来。”然后把那块小白毛巾往床沿上一搭,又“噌噌噌”地蹭出了一号治疗室。
走出“欣欣盲人按摩”我扩了扩胸,虽然感觉老王并没全按到点儿上,但确实是轻松了许多。
过了正月十五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整天忙忙碌碌,每每从欣欣盲人按摩门前经过,但没再踏进半步。转眼就进入了四月,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
刚从上海出差回来的我正从北京南站乘地铁回家。四号线地铁缓慢地进站了,我顺着车的方向看去,好像有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手持盲杖也在等着上车。我脑子忽然一闪“那是老王吗?”,他跟我隔着一个车箱。此时车门开了,我被上车的人流推着进了车箱,人头攒动实在看不清旁边车箱的那个手持盲杖的人倒底是不是老王。但我仍不死心,推着一个小箱子还是挤了过去。原来不是。我暗笑自己,“真是的,认识了一个盲人老王,难道这世上的盲人就都是老王了吗?”
那个盲人个不高但比老王胖,还有些秃顶,带着一副歪歪扭扭的墨镜,那根盲杖已被他折叠起来攥在手中,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车门旁的那个扶手。并没有人注意到他,更没人给他让座。
门边座位上的一个小伙子突然站了起来,面对着那个盲人说:“您坐这儿吧。”并且用身体挡住了一个从他侧后方想要抢座的中年妇女。那个盲人开始并没意识到是在和他说话,接着,那个小伙子用手碰了他一下又说了一遍“您坐这儿吧。”那个盲人才忙不迭地说了声“谢谢”。此时大家似乎才注意到他,并为他让出了一条路,但谁也没注意,在他的正前方有一根供乘客扶握的竖杆。那个盲人一头撞了上去,幸好旁边有人一把抓住了他,然后搀扶着将他送向了那个座位。
这完全引不起什么骚动,却让我心中一惊。那位盲人真的什么也看不见,一根就那么立在眼前的竖杆,连小孩子都会很自然地绕过去,而他却毫无防备地撞了上去。我忽然又想起了老王。他平时不工作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呢?他出门吗?他怎么买东西?在这儿人流似洪水般湍急的北京城他是如何往来的?对,有盲道,在有些红绿灯路口还有发声器,快的“嘟嘟”声是可以通过,慢的是等待。但也只是有些红绿灯路口,而不是全部,但也只是红绿灯路口才会有,那些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他是怎么过的……我似乎看到了老王,一个人手持盲杖站在十字路口中央,四周车声人声聒噪一片,而老王手忙脚乱完全失去了方向,就那么在原地打着转儿。
忽然车门开了,我猛地睁开了眼睛,一只手抓着箱子,一只手紧握着吊环,被上下车的人流挤得前仰后合。
很快我就到家了,老公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我和他聊着出差的趣闻,和江南如烟的春色,早把在车上看见的那个盲人的囧态和我心中老王的“苦恼”丢到了脑后。
“五一”刚过,夏天的感觉就来了。这天下班我一个人在公司边的“小馆儿一条街”上闲逛。老公晚上有应酬,所以我就在这“小馆儿一条街”上解决晚餐问题。
一个慢吞吞的身影从地下通道口晃出来,我定睛一看,是老王,他左手抓着盲杖不断地敲击着地面,右手弯曲微微向前伸着。老王一身灰暗,裤腿有些长,感觉马上就要拖到地面了,脚上穿了一双同样是灰色的旧旅游鞋。
他也是来吃饭的吗?我默默地跟在他身后,想知道他倒底要去哪。在一个小路口他停住了,用盲杖仔细地四处探查了一番便向左拐进了家街边的小超市。原来他是来买东西的。我迟疑了一下还是继续向前走去。
走出一段距离后,我忍不住还是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老王已经从小超市里出来,向回寻找着那个地下通道口。在街灯下他的背影暗淡无光,本就不高大的身材因为要小心翼翼地行走就更加显得干枯瘦弱。很快他就被湮没在了都市繁忙的光影里。
天气越来越热,今年北京的夏天还是那么不好过。办公楼里的中央空调“呼呼呼”地从来就没停下来过,冻得我手脚发紫,一走出办公楼就是一股股的热浪迎面扑来。再加上我不是敲键盘就是摆弄手机,似乎天天都没有抬头的工夫。脖子、肩膀、腰和腿没有一处是舒服的。不由得我又想起了欣欣盲人按摩。
这天还是午休的时间,我未经预约就走进了“欣欣盲人按摩”。里面还挺热闹的,三间治疗室几乎都满了,只剩下两个床位,一个在有空调的房间里,一个在没空调的房间里。这时跟在我后面进来的一位五十来岁的女人抢先我一步,要了那张不在空调房的按摩床。我自庆幸,我可受不了在汗流浃背的情况下被按来按去的。推拿师也只剩下了一位,我偷眼一看是老王。我本就不想让老王再帮我按了,就故意又谦让了一把。
我指着挂在墙上的那张照片对前台的大爷说:“大爷,这位年轻的师傅还多长时间做完呀?”大爷瞟了眼便喊到:“小王,你还多长时间?”屋里传来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两分钟。”我心想,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大爷又冲我说了一句:“小王可比其他人都贵呀,你看清了?”“嗯,我看见了,没事,就他吧。”心想就是因为他贵一些我才点他的,贵总有贵的理由吧。
确实如此,小王的手法要比老王好许多,次次都按在了点儿上。除此之外小王也比老王要善谈很多。他告诉我,他是从小就盲的,虽不是生下来就这样,但小时候眼睛就有毛病,上小学前他就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应该算是先天的。小王说起这些似乎很轻松,还有些调侃的味道,不象老王还是有些心存不甘。
他懂一些盲文,但是能用盲文读的书实在是太少了,幸亏科技发展的速度快,有各种阅读软件,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或是自己喜欢的装在手机里,就可以听书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书都能听。说着说着就又说到了老王。
“我和老王都姓王,他岁数大所以是老王,我是小王,呵呵!天儿这么热,他还得在没空调的房间推拿可真够一呛呀!”
我说:“可不,还真有人能待得住。”
“嗯,有的客人就是怕空调,所以我们特意有一间屋没装空调。可这天儿也太热了。”
我趴在床上想着老王汗流浃背地忙活着的样子。在又闷又热的房间里什么也看不见,摸索着床上那个蒸腾着热气的潮乎乎的身体是一种什么感觉?虽然有一块小小的白色毛巾将客人的身体与推拿师的手指隔开,但此时,也许那块毛巾也已经湿透了。老王真是一个可怜人呐。我开始后悔起来,真不应该因为他的手法稍差一些就把他放弃了。
小王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他跟老王真是两个鲜明的对比,一会说我肩膀太硬,一会说我腰椎弯度过大,总之一直在说,我简直都插不进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从小眼睛就看不见所以才这么能说的。那老王呢?他现在惜字如金,那在眼盲前他是不是也是个话唠?
“我听说老王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小王神神秘秘地蹦出这么句话来,我一听就来了精神,马上“八卦”了起来。我旁边床的客人也把头扭了过来,轻轻地说了一句:“真的?说说。”他的那位推拿师“噗嗤”地笑了一声。
“我也只知道一点儿,老王从来也不说。”
“那你怎么知道的?”另一位推拿师问。
“我是从别人那听的,那人和老王算是好朋友吧,也是个盲的。以前他们在一起干过。”
小王接着说:“好像是在东北……”
“对,老王是东北人。”我迫不及待地插了一嘴。
小王又说:“是在老王眼盲前好上的,那个女的是城里人,家里条件还不错,听说那女的爸爸是个老板,但老王是农村的呀。那女的看上老王人好、厚道又能干,老王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呐!
别看老王是农村的,可在城里打工,追他的女孩子也不少。老王是正经八百的高中毕业,听说高考也就差几分。那女的不知给老王下了什么迷魂药,把老王给迷的呀,别提了。那女的也特别喜欢老王,非他不嫁的。
可好景不长,女方家不同意,但那女的坚持。最后听说还是要谈婚论嫁了,但天有不测风云,
老王盲了。那女的还是想和老王好,海誓山盟的,家里人不同意。生生给拆了。

陈继明 书法
老王就一直四处漂泊再也没找,这不现在漂北京来了。”
我好奇地插了一句:“老王是生了一场病才盲的吗?”
“不是,听说是事故,一场很严重的事故。”小王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地说:“老王从来不跟别人聊这事儿,我上次开玩笑似的问过他,他差点儿跟我急了。”
“我想肯定跟他女朋友家有关。”小王又补了一句,然后接着说:“我都能当侦探了,唉!可惜了!”
我又插了一句:“老王刚来北京吗?”
“哪能呀,他来了好几年了,一直就在欣欣干。老板挺信任他的,他颇有些管理才能,这不欣欣开分店就让他过来啦!他现在也算是个管理者了。但价钱还是没我高。呵呵!”
原来老王还有这么一段罗曼史,是呀,谁会把自家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一个乡下的盲人呢?想想当年的老王,四肢健全、体魄健壮、能说会道,但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摸不准,一步也不敢往前走,能感觉到阳光的明媚,眼前却没有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才二十多岁的老王就将注定在没有星星和月亮的黑夜里度过余生。阳光、色彩、星光和明月只能是他的记忆了,而这些记忆老王又能保存多久呢?
老王的眼倒底是怎么盲的?什么事情让老王一提到那个“她”就心情大变呢?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小时很快就在小王的唠叨中过去了。他用他的大巴掌同样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两下,然后说了声:“OK。”第二次按摩圆满结束。我自信地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出“欣欣盲人按摩”一股热浪直扑而来。
秋风未起秋老虎却势头不减,马上“十一”了可热度犹在。这天在网上闲逛的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助盲的志愿者组织。点开网站仔细阅读着简介,原来这是一个帮助有需求的盲人把纸制的书籍转换成可使用阅读软件阅读的数字文件的组织。我毫不犹豫地提交了资料并申请加入。
三个工作日过去了,我每天都关注着这个网站,终于在第四天下班前我再一次打开网站时,发现我的申请已被通过。点击“下一步”出来了一个二维码。手机微信扫码后,我进入了“盲读志愿服务微信群”。“哒哒哒、哒哒哒……”群主给我发过来两个压缩文件,最后是一段说明文字“您好,欢迎您加入盲读志愿服务,请按照第二个说明文件进行操作,如有问题请@群主。我代表所有盲人朋友感谢您的爱心!谢谢!”
我按照说明、步骤依次办妥,并又仔细阅读了群主随后发来的第三个“软件使用说明”文件,@了群主,告之一切妥当,时刻准备着。群主礼貌地发来了一个笑脸后又过了一个来星期。
这个星期我既兴奋又焦躁,天天手机不离身,时不时地就打开看两眼,就连开会的时候也得摆弄几下。整个办公室的同事似乎都已感觉到我的反常,从不八卦的办公室主任马叔那天也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儿过了头,就这么点儿事怎么一点子城府都没有。
在焦急的等待中我迎来了“十一”长假。就在第二天,群里终于有了动静,是一个招募启示。要招募十二名志愿者进行一本中医文献的转换工作,我立马报了名。很快十二个名额就满了。接着,我收到了一份压缩文件,马上上传至电脑,开始了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的志愿服务。
假期后几天我一直都在电脑前忙碌着感觉比上班还累,第一次操作这个软件也十分的不熟练,并且中医文献真不好懂,本想着一边学学中医一边转换文件,可以一举两得,但还真不是这么回事。不说文中引用了很多晦涩难懂的古文,关键是有很多字我都不认识。不过还好规定的期限为十天,这对我来说还是绰绰有余的。随着假期的结束,我的第一次志愿服务也告罄。
秋日的凉风慢慢地推走了最后一点暑热,终于凉快了。工作却仍如夏日般的火热,再加上我又多了一个盲读志愿者的身份,几乎所有的转换文件工作我都报名,所以更加的繁忙,但我却乐此不疲。我又一次次地从“欣欣盲人按摩”的门口走过,甚至连扭头瞟它一眼的工夫都没有。
转眼进入腊月,在妈妈家喝完热腾腾的腊八粥后全身的寒气都被挤了出去。过了腊八就是年,心情似乎一下欢愉了起来。这天还是午休的时间,我兴冲冲地进了欣欣盲人按摩。屋里很暖和也很热闹,好像人们都想在这一天把这一年的不舒适全推拿挤按出去。我扫视了一圈,三间屋子都满满当当的,好像没地儿了。扭头问了一下前台的大爷:“大爷,什么情况?没地儿了吗?”“嗯,等一会儿吧,快了。”大爷也没抬头,一双朦朦胧胧的眼睛盯着部手机,正在听着广播。
就在这时,老王从卫生间里蹭了出来,甩着两只湿漉漉的手,显然是刚做完一个,笑滋滋地冲着前台说:“李老头儿,还有客人吗?”我立马举起了手,喊了一声:“有!”前台的大爷虚着眼说:“刚进来一位,老王你不用歇歇?”“不用,这点儿活儿,不累。来吧,李老头儿你帮着收拾一下,我去喝点儿水。”一分钟后李大爷把二号屋的那张刚用过的床收拾停当,我便脱了羽绒服趴了上去。
“小孙,是你吗?”“嗯,是我,马主任,您今天也来按啦!”我旁边的那张床上趴着的是我们办公室主任马叔,他可是个一丝不苟,并且从不乱花一分钱的人,今天却也来了这个消遣的地方。他旁边床上的是谢姐,我们财务科的会计。“谢姐,我刚进来时就看见您和马主任了。”谢姐趴在那儿向我挥了挥手,说:“唉!年底了,事儿太多,加了好几天的班,今天实在太难受了,本来想约老王,可他正好没时间,只好让这个小欧帮我按了,还不错,跟老王的力道差不多。唉!真累死了!”
“小孙,你年纪轻轻的也来做推拿?”马叔强扭过头冲我笑了笑。
“我都奔四啦,哪儿还年轻?”
正说着老王扶着墙蹭了过来。搓了搓手,按了按我的脊背说:“哪不舒服?”
“还是脖子和腰。”
“听你的声音很耳熟呀,我给你按过吧。”
“对,今年我是您的第一个客人,正月初八。”
“哦!我想起来了。一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今天老王的声音洪亮,音调上扬,并底气十足。
“嘿!是呀!”马主任接过话:“现在岁数大了,感觉时间越来越快了。小孙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嗯,当然有。哪像小时候,天天盼放学,天天盼天黑。”
谢姐马上接了过去:“现在,天说黑就黑,连个喘气的工夫都没有。累死了。啥时候才能退休呀!”
老王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按着,没有一点要插话的意思。他还真是个闷葫芦。不知道小王现在在哪间屋,若是他在肯定连珠炮似的开始轰了。
我感觉老王一直是笑滋滋的,便问:“老王,您今天好像特别高兴。有什么喜事吗?”
“我一个孤老头子能有什么喜事,今天客人多所以高兴。”
我心想,才不是呢,肯定有什么事发生。上次我来的时候人也挺多的,也没见他这么开心。
“老王,你每按一个客人提多少钱呀,这年底了,要发年终奖了吧?”谢姐一边说一边哼呀哈呀的,好像按到了她的痛点上。
马主任又开腔了:“老谢你一说就是钱,真是天生的会计,这可是人家老王的隐私,不好问的。还是眯瞪一会儿吧,下午还有好多事呐!”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谁也没再说什么。可我一直想把参加助盲志愿服务的事情告诉老王。
终于,机会来了,马主任和谢姐一前一后推拿完毕出了屋,只剩下我和老王。我赶紧打破沉默:“老王,您知道吗?我参加了一个助盲志愿者组织。”
“哦!是做什么的?”
“帮助盲人把想读的字书转换成可以用阅读软件读出来的数字文件。”
“哦!很麻烦吧?”
“不麻烦,有一个应用软件,挺简单的。嗨,我也不跟你说细节了,您有什么想看的书吗,我帮您弄。”
“嗯——谢谢啦!还真没有什么想看的。说实话,眼盲前我还真是个书虫,可这都几十年了,再没想过看书的事。一时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说完老王竟“嘿嘿”地笑了两声。
我沉默了,真是想像不出老王眼盲后都能做些什么。眼盲同聋哑、同肢体残疾都不一样。在盲人这一生的记忆里会留下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树有多高,枝叶有多茂盛,不知道草有多绿,草原有多大,不知道花香也是有色彩的,不知道海的辽阔天的无边,更无法被那高山之巅,云海滂沱所震撼。这些语言文字在他们面前显得那么的平淡无味。他们的脑子里倒底存放了些什么?
上个周末阳光明媚,我闭着眼在楼下的小公园里寻着盲道一点点地向蹭前着。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用脚底感受着盲道的凹凸,双手向前伸着,老公在一旁看护。突然老公一把把我拉向一边,我猛地睁开了眼睛,原来一个石凳赫然地拦在盲道上。绕过石凳,盲道消失在了一片小树林里,即没拐弯也没停顿,就那么直直地进了泥土里。
“快过年了,该办年货了吧!”老王首先打破了沉默。将我的思绪拽了回来。
我随口应合着,心想老王肯定有什么喜事,今天可真不对劲儿。我努力地把头扭过来面对着老王,说:“老王,您肯定有喜事,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快过年了,您哪天回老家过年呀!”
“我原想早点回家,可一直也没买到票,但无论如何我腊月二十七也得走,我今年要在三十前到家。”
“哦,谁不想回家过三十呀,您怎么买票呀?车站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有什么特殊政策吗?”
“有没有政策我不知道,每年都是托一个明眼的朋友帮忙抢。”
原来是这样。“那您那位朋友能抢到票吗?”我掠过了一丝丝的担心。对于我们这些明眼人来说春运抢票都似恶梦一般,老王,能抢到吗,他的那个明眼的朋友有那么神通吗,也许只是个票贩子吧!
“唉!我也不知道,我真是无能为力,只能期盼着老天爷啦!呵呵!”
“老王,您肯定有喜事,跟我讲讲呗!我都是助盲志愿者了,我们也算是朋友啦!”
老王还是架不住了,便说:“春节一个朋友要带着孙子去乡下看看我,在农村过个年。”
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住了,一下想到,那个带着孙子的朋友一定是老王的前女友。我还是没敢多嘴,只是应合着说:“这就让您这么开心呀?一定是个老朋友吧!”
“开心,孩子总会给人带来快乐,我只想摸摸那个小孙子。”
不会吧?我又搭上了一根筋,该不会是老王的孙子吧?我紧紧地闭着嘴,生怕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是吗?”就再也没开口。
最后老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两下说:“好了,今天你的话不多呀!”
……
我走出了欣欣盲人按摩,这一次真是神清气爽呀!腊月的寒风吹在脸上干巴巴的,又有十好几天没有有效降水了。但空气清爽,天蓝无云,明晃晃的到处都是那么的亮堂。
老王腊月二十七回家,他的那个朋友和他朋友的小孙子倒底和老王是什么关系?唉,我为什么会对老王的事情这么好奇?对,是因为他的脸,他的神情。都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可老王的眼睛已经有些干瘪变形了,但似乎还能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他很忧伤,而且这忧伤一直挥之不去,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印在了他每一声叹息和话语中,他的动作,他的触摸都笼罩在他的忧伤之中。而那一天,一缕阳光穿透了他忧伤的雾霾,他干瘪变形的眼睛好像有了一些灵动和跳跃。那一缕温暖的阳光慢慢的蒸发掉了他心灵深处那挥之不去的忧伤。那一缕阳光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他的那个朋友,和他朋友的孙子那儿来的吗?
腊月二十八,已经没什么要紧的工作要做了。我趴在办公室的窗前正好可以看到欣欣盲人按摩,心想,老王应该已经到家了吧,他的那个朋友是什么样子呢?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蹭进了我的视线——老王!他,他怎么还在北京?是没买到票还是其他的什么事?就在这时办公室主任马叔笑呵呵地进来了,说:“下午没什么事儿啦,可以早点儿回家。明天上午十点钟都到单位来,打扫一下卫生,然后封门、过年!”
我赶紧收拾东西,披上羽绒服冲了出去。守不住秘密、憋不住事的我可不想再错过这个满足好奇心的机会了。
“老王!”还没到跟前我就冲他喊了一嗓子,倒把老王吓了一跳。
“是我,小孙,前几天您还帮我推拿来着,记得吗?”
“记得,你的声音我听得出来。”
“您不是昨儿就回家了吗,怎么,没买到票吗?”
“我那朋友骗了我,收了好多钱但没办事。”
“啊?那不回去啦?”
“回,一定得回,再赌一把,明天,明天是最后的希望。一定要回去。”
“哦,那一定行,好人是有福气的。”
“是呀!好人有福气呀!”
说话间老王转身蹭进欣欣盲人按摩扭头对我说:“今天你不再按按啦!”
“不了,前几天不是刚按完吗,我可不那么勤。”
“嗯,是不应该那么勤,还是应该好好锻炼身体,推拿按摩只是辅助性的。真安静呀,大家都回家过年了。”
“我这不还陪着你呢吗!”前台的李大爷从台子后面转了出来一把扶住老王,“有我陪着你,你就不孤单啦,赶紧买票,赶紧回家,我也好回家亲我那外孙子去。”李大爷家就在北京,所以他可以陪着老王直到他买到回家的票。
老王和李大爷刚要坐在前台边的小沙发上,忽然进来了一个人,一看是谢姐。她一见着老王便说:“哎呦!老王,你还没走,太好了,快帮我按按,这颈椎又犯毛病了——”老王赶紧直起身摸索着蹭进了一号屋。
我的好奇心又落空了,干巴巴地立在那儿,和李大爷干聊了几句,就跟老王和谢姐道了声:“先给您拜早年啦!”便离开了欣欣盲人按摩。
春节总是那么忙,七天的假期一晃就过去了。还是正月初八,我仍旧腰酸背痛地踏进了“欣欣盲人按摩”。
一进门我就一边四处寻摸一边问:“李大爷,老王回来了吗?”
“回来了,你又是第一个呀。”李大爷虚着眼瞟了我一下。
“老王,开工啦!”
老王还是那样从休息室里蹭了出来,我还是趴在一号屋,靠门的那张床上。
“哪不舒服呀,还是脖子和腰?”
“老王,您太了解我了,没错,还是脖子和腰。”
老王的大巴掌还是在我的脊背上按了按,然后开始从头按摩。
“老王,去年腊月二十九抢到票了吗?”
“没有。”
“啊?那您没回老家?”
“回了,是正月初二回去的。”
“那看见那个小孙子了吗?”
“没看见。”
“什么?她们没等您吗?”
“我初二走的,初三晚上才折腾到家,她们初四中午就要出国了。所以没法等我。唉!没事,以后还有的是时间呢!”
“出国,她们去旅游吗?”
“不。她老伴前年走了,孩子的爸妈担心她一个人带着孙子,就特意请了假回来过年,顺便接他们去法国。”
“那孙子是您的?”我还是没管住这张嘴。
老王没说话,手突然颤抖了一下,轻叹了一声,似乎咽下了什么。
我们一直沉默着,直到他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两下,说:“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明年春节她们还回来。”说完便蹭出了一号屋。
当我磨磨蹭蹭地整理好衣服走出来的时候,正看见老王坐在前台边的小沙发上,慢慢地撩起白大褂,又翻开了上身穿着的驼色毛衣,从贴身的那件灰色衬衫的兜里掏出了一个小金锁。他用他那粗壮的手指不断地搓摸着那个小玩意儿,还不时地放在自己已干枯的眼前晃来晃去,好像能看清似的。在老王的搓摸下小金锁不时地发出“哗啦啦”的响动。
我心里突然一紧,这一定是老王送给小孙子的压岁礼物,可惜他们没见到面。老王听见我出来了,突然向我仰起头,看着我,说:“你说,她们明年真的能回来过年吗?能回来吗?”
我的鼻子酸了,不加思索地说:“能,当然能。中国人都是要回家过年的。”
我走出“欣欣盲人按摩”,这次我没有匆匆离开,而是站在门口。正月里的天还是那么的晴朗无云,午后阳光显得有些慵懒,风好像也没腊月里那么辣了。我看着脚下的盲道向两侧延伸着,在路口拐了一个直角,一根标示杆紧贴着拐弯后的盲道。我回头看着“欣欣盲人按摩”的牌子,心想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又要来了。看着老王坐在前台边的小沙发上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个小金锁,老王抿着嘴好像是在笑,但有一颗晶莹的泪珠从他干瘪的眼眶中闪出,迅速的滑过脸颊,落在了那个小金锁上,办公楼夹缝间的一缕阳光慢慢地移动到了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那颗泪珠在这阳光下映射着七彩的光芒。
一个想法突然在脑子里一闪,我一路小跑着回了办公室,迎面正好撞见办公室主任马叔。他瞪了我一眼说:“怎么啦这是,急什么?”
“马叔,咱们单位今年不是要搞个志愿服务吗?有个现成的就在眼前,您干不干?”
“好啊,已经有几个把设想交上来啦,你先说说看”
“助盲呀,对面欣欣按摩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呢,年底帮他们买车票,平时带他们去超市,嗯——还可以帮他们转换图书——”最后一句“帮他们转换图书”几乎是马叔和我同声说出来的,我好奇地看着他。
马叔哈哈地笑了一笑,说:“我知道你在盲读志愿服务,我也在上面,你这个马大哈,没看见每次招募的时候还有我的名字吗?”马叔走到办公桌前,放下手里的文案,接着说:“你的想法不错,其实我们身边就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但很多都被我们视而不见了,或是怕麻烦,志愿服务是长期的、持续的,不是一次性的,你有决心把他一直做下去吗?”
我还真没想得那么长远,在停顿片刻之后,我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马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那好,你写个小方案,你来发起,我来协助,咱们一起把这个小小的志愿推广起来。”
坐在电脑前,我开始进行规划。首先要有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好呢?对了,一缕阳光就叫“一缕阳光志愿服务”……这时我似乎看到了老王在隆冬的腊月喜气洋洋地坐在回家的火车上,他终于可以把那个小金锁戴在小孙子的脖子上了,他终于可以去摸一摸那个小孙子的脸了,也许那个孩子的脸真的可以成为一缕温暖的阳光蒸发掉老王心中的所有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