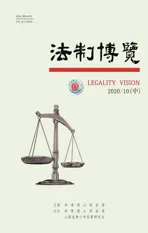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问题研究
2020-11-30穆潇
穆 潇
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山东 泰安 271000
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任何以刑法进行规制的问题均应以其合理为前提,同时如若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其范围的确定以及救助义务人的保护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对见危不救行为的犯罪化进行研究,期望可以为见危不救的刑事立法贡献微薄力量。
一、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合理性分析
任何问题的合理性不在于其本身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是与特定的时空背景相吻合。同样地,刑法规制见危不救行为的合理性,也不在于行为本身在初始状态下就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应是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刑法将其纳入规制范围是必要的。因此,如果当前社会需要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那么刑法规制见危不救行为就是合理的。我们可以从社会需求及司法实践角度对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分析。
(一)群众的呼吁是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客观基础
“法律或是由于物理之必然,或是由于人事之命令。”在刑事法领域,物理之必然可以理解为自然犯的规定,而人事之命令则可以理解为法定犯的规定。尽管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标准有很多,但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标准区分二者”[1]。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来看,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在于,行为被规定为犯罪是否以违反伦理道德为基础。自然犯是因为违反了伦理道德,且刑法认为有必要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由于社会民众的认识存在差异,自然犯的范围也会有所变化。也就是说,见危不救是否属于自然犯,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民众的认识。
(二)见危不救犯罪化是解决司法困境的需要
让我们先从一个司法案例说起。2007年5月25日,周某因盗窃自行车被失主颜某等人抓获,颜某等人为让周某吃点苦头遂对其进行殴打,周某为躲避殴打,情急之下跳河欲游到对岸,但因体力不支溺死。颜某等人见状未予救助,各自离去。该地法院认为颜某等人负有救助义务而不救助,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三人归案后如实供述可酌情从轻处罚,遂对三人判处了不同期限的有期徒刑。
在见危不救非犯罪化的情况下,对于上述案件仅能从传统的不作为犯角度进行分析,那么行为人的不作为义务出于何处将成为案件的关键。从形式义务说角度出发,我们只能从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来寻找出路。[2]在本案中,韩某等人殴打周某的行为能否产生他们对周某溺水的救助义务是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殴打行为所能产生危险仅是基于殴打而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并不包括溺死。当然,有学者会认为如果没有殴打行为,周某就不会跳水,如果不跳水就不会有溺水的危险,所以韩某等人有救助义务。以此方式解释,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周某没盗车,韩某等人就不会殴打周某,周某之所以盗车是因为生活所迫……那么任何事物之间都会有联系,由此得出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再者,跳水也并非周某当时的唯一选择,尽管溺水与殴打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但并非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因此,将殴打行为作为产生溺水救助义务的先行行为是不合理的,如此解释将导致刑事责任的泛滥。
因此,无论是从形式义务说还是从实质义务说的立场来看,司法机关对于上述案例的裁判似乎都是欠妥的,从现有的刑法理论中我们也很难找到其他能支撑判决的理由。然而,法官作出此种裁判并非盲目的,说明类似的行为的确有社会危害性。但法律应具有明确性,尤其是涉及人身自由的刑法。人们要通过刑法的规定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人们就不能判断其行为的合法性,如果此时仍处罚其行为,那么必将造成草木皆兵的状况,不利于社会的自由发展。暂且不论上述案例判决是否妥当的问题,但其至少说明了部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是司法实务的需要。因此,为了避免难以找到判决依据的情形,将部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是合理的选择。
二、见危不救行为的确定
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并不是将所有的见危不救行为均作为犯罪处理。如果不予区别地将所有的见危不救行为完全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那么每个公民都可能在无意识间触犯了刑法,这种人人自危的后果显然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见危不救犯罪化的难题并非行为需要犯罪化的问题,而是何为刑法意思上的见危不救行为。
(一)“危”的范围问题
见危不救,从字面上看就是见到危险不予救助,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见危不救行为,如果没有一定的客观标准,那么法律规制见危不救行为将毫无道理可言。基于法的安定性,法律所规制的行为必须是能基于一定客观标准而形成的类型化行为。当然,客观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内容也是有所差异的。刑法作为维护社会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其所规制的见危不救行为应当是范围最小的,判断标准也就应当是最高的。对“危”的理解将直接影响见危不救的范围。因此,我们所称“危”应当仅限于严重危及人生命安全或国家及社会稳定的危险。
(二)见危不救主体范围的确定
将见危不救犯罪化,就意味着刑法将给一定的群体设定了新的法定义务,那么这个群体到底应当包括哪些人的问题将成为焦点。对见危不救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主体范围也存在差异。如果从广义上理解见危不救,那么所有知道上述利益面临危险的人均应履行救助义务,否则将因不作为而触犯刑法。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具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都有可能成为见危不救的主体。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考虑,这样的规定似乎是合理的,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强制要求每个公民履行道德义务似乎是不现实的,正如学者所言,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规定严格的法律制裁是过于超前和缺乏法律依据的[3]。因此,有必要从狭义上理解见危不救,将其主体范围划定在合理的限度之内。
我们认为,见危不救的主体应当是与面临危险的法益之间有基于事实或法律原因而产生实质性关系或基于场地支配建立密切联系的人。有人会拿社会学中的“六度分离”理论提出质疑,但我们所称的关系并非任意的关联。一方面,主体可以是基于事实或法律原因与面临危险的法益间产生实质性关系的人。另一方面,主体还可以是基于其所支配的场地与面临危险法益间建立密切联系的人。这里的实质性关系是很好理解的,但何种联系才是密切联系的问题是值得探讨的。事实上,联系是否密切可以由案件发生的场地所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应当排除目前刑法理论已经存在的关系。将部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那么其应当属于不作为犯。目前不作为的义务来源,根据我国刑法通说可以分为四类,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业或业务上要求的业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及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4]。因此,我们所称的关系还应当是排除由上述四类义务所产生的关系。
(三)见危不救的期待可能性
将见危不救犯罪化,其本身是将道德义务法定化,因此应注意法律不应对其设定过高的要求。因为如果法律要求不顾自身安危去履行本属于道德层面的义务是极其不合理的,挺身而出的英雄主义并非刑法所鼓励的。所以,此时的期待性低于其他不作为行为的期待性是合理的。
因此,需犯罪化的见危不救行为应是指人的生命或国家及社会的稳定面临紧迫性的威胁时,基于事实或法律原因与上述法益所面临的危险具有实质性关系或基于场地支配建立密切联系的人,能救助而没有救助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应满足三个基本的条件,即特定法益面临紧迫性危险,具有救助义务的人故意不救助,救助具有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