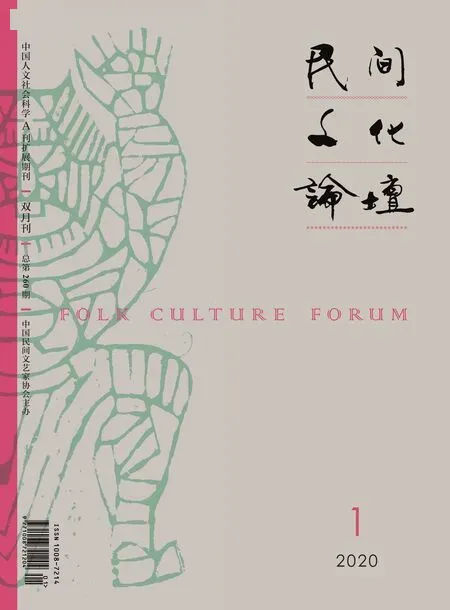《马可·波罗游记》真伪的民俗学立场
2020-11-30向云驹
向云驹
2019年3月23日,中国和意大利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罗马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并出席备忘录签署仪式。习近平在会谈时指出:中意关系植根于双方千年交往的历史积淀中,拥有深厚民意基础。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两端,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天经地义。西方媒体报道指出,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希腊、马耳他、波兰、葡萄牙等欧盟国家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此次签署该备忘录,使其成为七国集团(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中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将产生超出两国合作范围的更广大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共同铭记的重要时刻。
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的两端,代表了这条伟大的历史道路的双向起点与终点,也代表和象征着东西方文明互相往来、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镜鉴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地理。回望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正是中国与意大利的一次重要的相遇相见,记录和见证了东西方的一次历史性遇见,这次遇见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改变了历史的面貌;也彰显出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伟大价值和意义。
一、质疑的产生与事实的传奇性
恺撒开启和巩固了以西方为终点的丝绸之路的终点、目的地,历史以终端打通中端,贯通了整个丝绸之路。中国到罗马的丝绸之路及其贯通,实现了欧亚大陆时代已知陆地世界的“全球化”。同样缘自于将地球另一端作为目的地进行探险、不惜身家性命也欲到达的历史,再一次在古代希腊罗马千余年之后,又得以轰轰烈烈地上演。只不过这一次的历史不是帝王的推动而是一介平民,目的地也不是丝绸之路终点的西方而是遥远的东方。起点成为终点,终点成为起点,事件发生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此一历史事件仍然发生在同一个国度——意大利。这就是伟大的马可·波罗和他不朽的传奇。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先生在其1931年出版的著作《马哥孛罗》中指出,马可·波罗是在极东的中国和极西的罗马之间在长期的遥远的时间和空间阻隔后,第一位实现了将两国直接交通的人,并且从此开启了新的世界交通史。他指出:
当今世界大通,历史家眼光扩大,知悉古代世界上最大文明国有二:极东为中国,极西为罗马,中间有数万里山河沙漠之隔,自汉武帝以后,中国极力向西扩张势力,经汉唐两代,兵威所布,声望所及,不过至里海滨而止。罗马人亦极力向东开拓领土,最东亦未过油付莱梯斯河及梯格莱斯河。中国史书上空闻极西大秦国文物昌明,土宇广阔,人皆长大平正,土多金银奇宝。罗马人白里内(Pliny)、梅拉(Mela)等书中,盛称中国之丝,远贩罗马,为彼邦贵族妇女之华服。席摩喀塔(Simocata)记中国法律严明,持正不阿,人性温和,技巧异常。《汉书》记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于桓帝延熹九年来献。《唐书》记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献。以后历高宗、武后、玄宗诸朝,皆有使来献。罗马史家佛罗鲁斯(Florus)记奥古斯都皇帝时(西汉末时)中国有使臣朝贺帝之威德远被。以上记载皆模糊影响,片断之辞。而所谓使臣,或为商贩冒充,回国以后,毫无记载。所传口碑,大约即上方各书所留之记载也。即为真使,而古代航海学未精,船舶不坚,或为海洋中风涛所破,葬身鱼腹,或旅行沙漠,中道渴死也。以此各种原因,故自古以来,迄于元初,东西皆无直接交通,真确详细记载。其情形犹之今代天文家,以望远镜窥测火星中有黑影线,而揣测其中人文明程度若何之高,使人欣羡,恨不能亲往一游也。设有人能造一飞行机,其速率千万倍于今之飞行机,游客乘之飞达火星,归报其中真况若何,详言空中航路若何,可作后人航空之指南,为探险各星球之导引线,则其人必名传全球,受全人类之顶礼膜拜,可断然也。马哥孛罗犹之飞机中之乘客。乘客得达火星,而享盛名,岂可忘其飞机,及造飞机之人乎?马哥孛罗不过商人之子,非有过人之才,及超人之智,而得享盛名者,完全风云际会使之也。① 张星烺《马哥孛罗》,系张著《欧化东渐史》附录,第106、107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据旧版编订重印)出版。
这段论述强调指出马可·波罗的平民商人身份及其意义,强调了他东行并著述的首创性,随后还指出他之所以成行是由于出现了蒙古大帝国创造的广大地理,以及帝国为商人横贯东西提供的便利。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9.15—1324.1.8),生长于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都是威尼斯商人。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约四年,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梯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出《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
《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16世纪,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说,马可·波罗在1299年写完《游记》,“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有数十种版本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已达143种各种文字的版本(据杨志玖先生《马可·波罗在中国》统计)。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意义。
大概由于马可·波罗第一次基于自己近二十年的经历和父亲、叔叔此前亲历中国的经历,他才能首次这样全面、这样细节、这样丰富、这样传奇地讲述遥远富有的中国。他不无夸耀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他讲述的目的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盛赞给予他此次旅行、此番经历创造条件、提供便利、给予信赖、委以重任的中国皇帝忽必烈。他明确表示:“请为君等叙述‘诸汗之大汗’之伟迹异事,是为鞑靼人之大君,其名曰忽必烈,极尊极强之君主也。”①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页。正是这位帝王对马可·波罗一行颇为信任,赐予金牌可用驿站,受沿途供应,可驶驰驿道,还让他奉使办理公务乃至担当地方长官数年,最后托付远嫁公主让他们护送随行。在马可·波罗眼里,忽必烈的历史地位是这样的:
第一君主成吉思汗之后,首先继承大位者,是贵由汗。第三君主是拔都汗。第四君主是阿剌忽汗。第五君主是蒙哥汗。第六君主是忽必烈汗,即现时(1298年)在位之君主也。其权较强于前此之五君,盖合此五人之权,尚不足与之抗衡。更有进者,虽将全世界之基督教同回教帝王联合,其力量及其事业亦不及此忽必烈汗之大。此汗为世界一切鞑靼之君主,统治东方西方之鞑靼。缘鞑靼皆是其臣民。② 同上,第52页。
二是炫耀他在商旅之中所见到的东方的富庶和巨大的财富。全书有大量的篇幅讲述中国的地大物博,城市的繁华,金银珠宝香料触目即见,商业繁荣、贸易发达、港口繁忙。
三是作为一个西方人在东方的见闻,东方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地理等等。其中又有三点:1.从陆路由西向东,沿途所到所见国家、城市、地方;从中国的西域、北方到中国的西南、南方、东南沿海诸地诸城;从中国南海及海路返回西方途经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等诸岛、国、港、地方、城市等等。2. 在中国西部、北部,京城、小市,西南、东南,港口、大城等种种地方数十个大小城市所见到的中国样貌。对中国重要区域和主要城市叙述得如此完整、如此具有整体性,如果不是亲历亲见,仅凭道听途说和发挥想象,是很难做得到的。3. 中国所见到的奇风异俗、西方未有未见的事物、迥异于西方的风物风俗风景,是一个外来的他者对异域最直观、最敏感、最特别的事物。这三个目的都使他的讲述必然具有传奇性,也使讲述中的中国具有整体性和丰富性。这使其成为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国讲述,是一次有来有回、路线清晰、目的合理、经历真实的传奇游历,也是东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相遇和交流。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后,曾经有很多人质疑其真实性。这种质疑其实主要来自于他叙述的中国太伟大、太传奇、太陌生、太遥远。但是,正如他在生前就坦然面对这些质疑,并且在临逝世时有人希望他赶紧澄清并忏悔他的讲述都是虚构和欺骗,而他最后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他说,我还没有说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半。
二、马可·波罗的讲述能力及其游记的风俗志特征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有一些民俗事象作为局外人的视点被聚焦,并且呈现其准确的细节,如果没有到达现场并亲自观察亲身体验,就不可能被描写。风俗的被描写程度和其中的深广度,是亲历与否的一个重要试金石。马可·波罗在观察、记录、讲述风俗方面是有天才般能力的,他自己似乎也对此做过刻意的训练。他自述在大汗麾下任职外务,回大汗帐下述职时,其他官员的讲述寡淡无味,而他的讲述则使大汗听得津津有味,尤其喜欢听他讲各地奇风异俗。这也使他强化了自己对风俗的捜集和观察能力。《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有两节专门叙述了这个情况:
尼古剌君之子马可,嗣后熟习鞑靼的风俗语言,以及他们的书法,同他们的战术,精练至不可思议。他人甚聪明,凡事皆能理会,大汗欲重用之。所以大汗见他学问精进、仪态端方之时,命他奉使至一程途距离有六个月之地。马可慎重执行他的使命,因为他从前屡见使臣出使世界各地,归时仅知报告其奉使之事,大汗常责他们说:我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乃汝辈皆一无所知。大汗既喜闻异事,所以马可在往来途中注意各地之事,以便好归向大汗言之。
在随后讲述中,马可·波罗不无骄傲自己的此种才能:
马可奉使归来,谒见大汗,详细报告其奉使之事。言其如何处理一切,复次详述其奉使中之见闻。大汗及其左右闻之咸惊异不已,皆说此青年人将必为博识大才之人。自是以后,人遂称“马可·波罗阁下”,故嗣后在本书中常以此号名之。其后马可·波罗仕于大汗所垂十七年,常奉使往来于各地。他人既聪明,又能揣知大汗之一切嗜好,于是他颇习知大汗乐闻之事。每次奉使归来,报告详明。所以大汗颇宠爱之。凡有大命,常派之前往远地,他每次皆能尽职。所以大汗尤宠之,待遇优渥,置之左右,致有侍臣数人颇妒其宠。马可·波罗阁下因是习知世界各地之事尤力。尤专事访询,以备向大汗陈述。
可见马可·波罗在风俗方面是很用心用功的,“专事访询”做的就是民俗调查了。
由此之故,马可·波罗于风俗志方面,在其游记中对当时的中国是有深度观察的。他大概是随手将当年向忽必烈展示的讲俗能力拿来向家乡的意大利人略加表现而已。以下试举若干例子:
1.关于纸币。这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早在宋代中国就广泛推广使用纸币,元朝继承金、宋体制,继续使用之。马可·波罗作为商人对此十分敏感。他在叙述多个城市时,都不会忘了根据所见,注上“使用纸币”字样。他记录的使用纸币的城市有:泰州、南京、强安、襄阳、镇巢军城、新州、临州、邳州、西州、镇江、行在、刺桐、高邮、宝应等。这说明纸币使用的广泛性和全国性,说明这种独特的便捷的货币及其货币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其中具体结构模式。他说:
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用。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他为此还记述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和过程:“此薄树皮用水浸之成泥,制以为纸,与棉纸无异,惟其色纯黑。君主造纸既成,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
2.关于丝绸。中国是丝绸故乡,马可·波罗对此也多次述及。在南京、苏州、涿州、太原、土番州、镇江、福州、行在等地,他都有“织罗甚多”“织造金锦丝绢及最美之罗”“产丝甚饶”等等字样。对南京的丝绸他用“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表述。至今南京云绵技艺被确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可见当年风釆。可见他的描述不虚。
3.关于陶瓷。陶瓷也是中国极具东方个性的特产。马可·波罗对此种器物印象极深,观察也细。他的陶瓷记述成为西方文献对中国陶瓷的首次记载。马可·波罗到达一座叫做Tinju(泰州)的城市,这里:
人们制作瓷碗,这些碗大小不等,美轮美奂。瓷碗只在这座城市制作,别处没有;它们从这里出口到全世界。在这座城市,瓷碗到处都是,且价格低廉,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三只精美的瓷碗,其玲珑可爱,简直无法想象。这里的杯盘碗盏用易碎的泥土或者黏土制成。土块似乎釆自矿山,被堆成高高的土丘,三四十年间听凭雨打风吹,日晒雨淋。此后,灰土变得如此细腻,用它做成的杯盘呈天蓝色,表层晶莹剔透。你们要明白,当一个人把这种土堆积成山时,他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风化成熟需要漫长的等待,他本人无法从中获取利润,也不可能把它派上用处,但他的儿子将继承它得到酬报。① 转引自[英]埃德蒙·德瓦尔:《白瓷之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页。
当代英国陶瓷史家埃德蒙·德瓦尔说:“这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瓷器。”②同上,第10页。马可·波罗关于陶瓷材料用土需囤积、老土化,在今天中国诸多制陶地方如景德镇、宜兴、无锡、德化等地,依然如故。八九百年前能描写出这样的细节,令人叹服。
4.关于中国的桥。游记对中国的桥梁印象深刻。在北方,他记述了著名的卢沟桥,称它是普里桑干河上的美丽石桥,桥两旁皆有大理石栏、石柱,柱顶别有一狮。“此种石狮巨丽,雕刻甚精。每隔一步有一石柱,其状皆同。”卢沟桥和桥上狮子给马可·波罗留下深刻印象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这座石桥石狮在中国人眼里也是别具一格的。民间有很多关于这座桥的建桥传说和狮子传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句北京人妇孺皆知的俗语,明代就见于典籍,说的就是桥上的狮子大大小小,造型各异又复杂万状,狮子数量之多竟达数百,使这座桥无与伦比。南方是水乡,诸多水上人家和水上城镇,大概堪比威尼斯,所以马可·波罗多次述及。他说行在城(杭州)有石桥12000座。大的桥桥拱甚高,大船不放桅杆也可通行。因为这个城市是完全建筑在水上的。苏州也是如此,有石桥6000,“桥甚高,其下可行船,甚至两船可以并行。”
5.关于若干生活习俗。在大量风俗描写记录中,有一些非常中国化,是观察者细心体味过的。比如中国人的“生辰八字”和运用于占卜。马可·波罗说:
此地(杭州)之人有下述风习,若有胎儿产生,即志其出生之日时生肖,由是每人知其生辰。如有一人欲旅行时,则往询星者,告以生辰,卜其是否利于出行,星者偶若答以不宜,则罢其行,待至适宜之日。"这种情状,对旧时中国人来说是一点都不虚的日常生活。比如中国人的生死轮回观。"彼等信灵魂不死。以为某人死后,其魂即转入别一体中。视死者生前之善恶,其转生有优劣。
此外还有蒙古包的形制和建造,哈密的歌舞,沙州及多地的葬礼,驿站的运行模式,十二生肖和纪年,元朝的节日、逆水行舟的拉纤和竹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巫师施法治病,以及云南地区所见到的产翁制。在云南大理往西骑行五日后,马可·波罗在金齿州(此地之人皆用金饰齿,至今云南多地有染齿、黑齿、凿齿习俗,如壮族、布朗族等)的永昌,发现一种产翁制:“妇女产子,洗后裹以襁褓,产妇立起工作,产妇之夫则抱子卧床四十日。卧床期间,受诸亲友贺。其行为如此者,据云妻任大劳,夫当代其受苦也。”产翁制作为一种奇风异俗,据人类学家报告,早在罗马时代、罗马地区有过遗存。拉法格在其所著《母权制:家庭探源》中描写道:
生于纪元前两世纪的亚波罗尼就有一个居住在黑海沿岸的民族,曾经说道:在女人们生孩子的时候,丈夫们也参与其事。他们躺在床上,蒙头盖脸,呻吟哭叫,妻子们则给他们喂饭,喂水,替他们洗浴。① 拉法格著:《母权制:家庭探源》,刘魁立译,见《民间文艺集刊》第6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48页。
法国巴斯克人也有过此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印第安人有过此俗。印度南部也有类似习俗。世界各地一直以来都有发现和报告。“法国巴斯克人有一种产翁的习俗。当妻子要生产的时候,丈夫就躺到床上,盖了被,开始呻吟喊叫。干亲和邻居到来,纷纷向他道喜,恭贺他生产顺利。”②同上。当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时,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同样的习俗。在南美阿比朋人中,“当你看见新生儿的时候,你会同时看到一个丈夫躺在床上,严严地盖着被衾和皮衣,不让一点凉风吹着。他守持斋戒,躺在一个封得很严实的房间,自愿地许多天不进肉食,这样就可以发誓赌咒地说,是他生了孩子。”③同上,第249页。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也有此俗。中国壮族、傣族、仡佬族、藏族都曾保留过这种古老习俗。宋代《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录《南楚新闻》记载,“南方有僚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裖,饮食皆如乳妇。”这被认为是对仡佬族此一风俗的记录。该书对壮族先民越族人的风俗记载有:“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明代《百夷传》、清代《顺宁府记》都记述有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流行产翁制。《云南志略》载:“妇女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所以,中国学界大多都认为马可·波罗的记述讲的是云南傣族的产翁习俗。方国瑜、林超民两先生著述有《〈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详细论证了马可·波罗云南之行的具体事实,很有说服力。
产翁制是人类早期社会婚姻制度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产物。瑞士著名人类学家巴霍芬在其名作《母权论》中指出:“人类从母系观念发展到父系观念,构成了男女两性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④巴霍芬:《母权论》,孜子译,三联书店,2018年,第60页。恩格斯更是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这一转变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的革命。“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2页。拉法格在其著作《母权制:家庭探源》中结合评价马可·波罗的记述指出:
在欧洲,在非洲,在旧大陆和新大陆,也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种风习几乎到处可见。十八世纪,马可·波罗在云南(位于中国西南部,在西藏和缅甸以东)也见到过这种风习。……产翁习俗——这就是男人为了取缔妇女的地位和财产而釆用的花招之一。生育活动曾经宣告妇女在家庭中应有很高的权力。男人把这桩事体也拿来表演一番,正是为了使人承认孩子获得生命主要应归功于父亲。我们看到,父权制家庭——是一种比较新兴的制度。伴随着它的出现曾经演出了多少争讧、犯罪和荒诞不经的闹剧啊。① 拉法格著:《母权制:家庭探源》,刘魁立译,见《民间文艺集刊》第六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49页。
作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特殊产物出现的“产翁制”,是在用象征的方法把父亲同化于母亲,以确立社会性的父权,它不仅适应着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而且对这一过渡起到了促进作用。我国历史记载和后来的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调查证明,古代和现代中国一直存在着大量原始民族和原始婚俗。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转型变革的婚俗大量存在。除了产翁制多有流行外,还有痛哭母权丧失的“哭嫁”习俗在多地民族中保留。不落夫家、游方、跳月、浪哨、放牛出栏、串故娘、行歌坐月、放寮、抢婚、走婚、从妻居等等此类过渡期婚俗更是随处都有。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表示遇见过很多的女性习俗和特殊的两性习俗、接待和对待外来男性的习俗,大多也都属于这一类被后世归为人类学范畴的民族志现象。真正的民族志和人类学是大航海之后才逐渐兴起的。马可·波罗是启发、启动这个学科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很多记录我们必须从人类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其中意义、价值。在人类学未能展开和充分发展的马可·波罗时代,他的被误解和被质疑也就不可避免。这也是个中原因之一。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可·波罗讲述的中国包括了大元帝国时代的蒙古统治阶级层次,也讲述了元帝国统治下的南方汉人社会,以及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和东南沿海商业通向海外的港口城市,最后还包括处于相对原始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风俗状貌。这种中国描述空前绝后,不仅完全符合中国人文地理历史史实,具有丰富的历史层次性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也使后世所有描写中国样貌的亲历者的图书都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许多西方的研究者喜欢拿500年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和他们对中国的记录与马可·波罗相比,认为前者(真实到达中国)有许多中国奇风异俗和独特事象物象的记录,可是在后者(是否到达中国存疑)所述中却付之阙如,因此可能是他没有到达并且虚构了中国。这些事象主要有:长城、妇女缠足、鸬鹚捕鱼、筷子、中医、茶叶等。具体辨析这一质疑,我们就不展开了。可以肯定,马可·波罗的讲述有很多方面比马戛尔尼一个团队按科学调查方法开展的记录还要真实、准确、丰富,他们团队遗漏的中国独特文化要多得多,因为马可·波罗曾在中国生活了17年,而且他到过的中国地方比马戛尔尼他们多得多。既使如此,以中国历史之久、风俗之富、思想之深、现象之杂,任何记录者都会挂一漏万。我们不能以事象的无一遗漏来判断真伪,而应以其描写的真切度、不可虚构性的内容来作判断。
三、东方的现实打开西方的空间想象力
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元帝国的铁蹄横跨欧亚,使整个欧洲震惊与恐怖。他们一方面根本不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巨变,一方面也根本不知道东方和中国为什么会带来这种铁血历史。所以,马可·波罗竟然与忽必烈汗为伍,发生亲密关系,这是不可想象的。原因之二在于马可·波罗讲述的中国太富有、太有商机了,这个世界的东方还有这样一个世界,而在此以前的历史中几乎闻所未闻,这太出乎想象了,这让西方人实在难以置信。原因之三是中国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他们的历史太独特、太悠久了,这样特异的生活方式,怎么也会来自人类的创造,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他们的质疑从马可·波罗在世时就层出不穷。他们不是质疑他的道听途说、转述他人见闻。他们质疑的是中国强大、富庶、独特的真实性(这正如数百年后中国人知道强大的西方,见识西方城市与繁荣时目瞪口呆是一样的)。
实际上,西方一直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
怀疑部分。他们把马可·波罗的讲述文本归于传奇文学,把它推向虚构文学,从文学归属上否定其写实性纪实性。后来也有人指出,此游记严重缺乏文学性,只是一种平铺直叙。它的文学性来自内容的超常性,所谓现实比文学更具想象力,此之谓也。所以,在当时浪漫传奇小说都弥漫着这种东方式的浪漫精神,许多小说还直接取材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比如14世纪的《耶路撒冷的第三王》,就是当时受其影响最深的文学作品。乔叟、但丁、弥尔顿等文学大家也都是参与这种影响的文学人物。马可·波罗讲述的文学性(在这里这是贬意词,与指认他说谎骗人、非真实是同义词),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笔录者鲁斯梯谦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通俗小说家。后者按通俗文学的传奇叙事格式给游记穿靴带帽,造成了“虚构”假象。有些版本的开场白就是当时许多浪漫传奇小说的同一模式的翻版。美国学者史景迁说:“鲁思梯谦在记叙时,经常恪守宫廷传奇应有的格式,而不是我们认为像马可这种老练的旅行家所惯用的语汇。”①[美]史景迁著:《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阮叔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页。此外,游记中还结合所到之地和所见之人、物、事,附会编创了一些民间传说,记录重述了一些民间宗教神话,讲述描绘了一些虚幻的民间故事。比如,他用最新的历史史实对传说了很长历史的西方想象东方的著名的长老约翰故事,附会到与成吉思汗的经历中,为这则古老传说增添最新的解读,也使长老约翰传说再添新的谜团。比如,他讲的“巴格达之移山灵迹”,是一个圣迹显灵的神话,让山移动的情节颇与我国古代神话愚公移山类似。这种超自然现象也是很难让人置身真实历史。比如,他讲的波斯三王的传奇,极富民间文学特色,应该是对波斯民间文学的转述,但却变成了历史人物讲述,让虚事变实有,其中超现实的神话传奇内容就很难让人信服。
信以为真部分。从一开始许多人便因此游记开始向往、憧憬、梦想到达中国,激发了许多人再去探险的雄心壮志和野心勃勃。陆路抵达已经失去元帝国贯通东西的条件,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以此互为因果,终于促成历史复活与重现。这就是哥伦布登上历史舞台。
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早期的读者中,最著名的就是哥伦布。我以为,他也具备与马可·波罗相似的三个条件:一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帝国的崛起和称雄世界的野心和科技、军事能力;二是他强烈地感受到了《马可·波罗游记》中隐藏的巨大商机和财富诱惑;三是对中国风俗有强烈的感同身受、亲历探险的冲动。美国学者史景迁在他的著作《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考据和介绍了哥伦布大航海的此一动机:
哥伦布展开1492年的探险前,想必已熟知该书内容。他1496年返乡后,订购了该书,并且或在当时或日后,于书页空白处写下了近百个眉批。这些眉批主要以拉丁文写成,间杂以西班牙文,显示了最吸引哥伦布注意的段落。……虽然哥伦布对这些感官描述、奇闻捜秘深表兴趣,我们却不难发现,他真正的意图还是在贸易经商,以及其中隐藏的危险和机会。因此只要波罗提到黄金、白银、纯丝买卖、香料、瓷器、红蓝黄宝石、硫璃、醇酒、釆珠人等事,哥伦布就会做记号。同样深受哥伦布注目的内容,包括季风期来临时船队航行的方向及时间、海盗或食人部落猖獗的情形以及类似食物及其他物资可能的位置。哥伦布特别对几个看来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做了记号,其中包括扬州和杭州,并对它们的通商机会做了些评论,不过他只对一个城市写下了,'商机无限'这几个字,这个城市正是'汗八里'(CambaIu),也就是忽必烈汗在中国的新都,波罗对北京的称呼。为了强调他的兴奋,哥伦布在眉批旁加了一个图案,那是歇息在云端或浪涛上的一只手,所有手指紧握,只有顶端的食指直伸,指向撩动它的那段文字。① [美]史景迁著:《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阮叔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1492年8月,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大汗的国书开始了他以中国为目的地的远航。
意大利威尼斯的弗拉·毛拉修士也是对游记坚定的“信以为真”者。他受游记影响,于1460年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呈现给葡萄牙国王。该图依据游记补充了过去的欠缺,完善了世界地图,同时根据游记在地图中标示了一些中国地理元素,地图中最繁华的地方是最靠近伊甸园的中国与大都,其中还有游记特别叙述到的卢沟桥。地图的东部海域,游弋着高大威猛的中国式帆船;西部世界则是体型较小、单桅双帆的西方帆船;可见游记对毛拉影响至深。②地图原件藏于意大利威尼斯马尔恰那国家图书馆。2018年6月9日至8月19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多国国家博物馆在北京举办“无问东西——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出了此一地图的图片。这幅地图表达的意图就是:葡萄牙人应该绕过非洲,与中国人的世界相融合。30年后,迪亚士(好望角发现者)完成了这一“葡萄牙人的使命”,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
无论对马可·波罗是质疑怀疑还是信以为真,它们的客观效果却是相辅相成,形成合力的。以游记文学、传奇体式展现中国,开启西方的东方想象,打开西方思想的空间想象力。文学的浪漫主义为资本主义时代初期的创业雄心和探险精神添加了动力和想象力,设立了一个瑰丽的远方和诱惑的目的地。而坚定地确信东方黄金遍地从而付诸行动奋力前往,则开辟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以东方为目的地和终点的大航海,导致新大陆的发现,进而实现环球航行。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气象和世界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