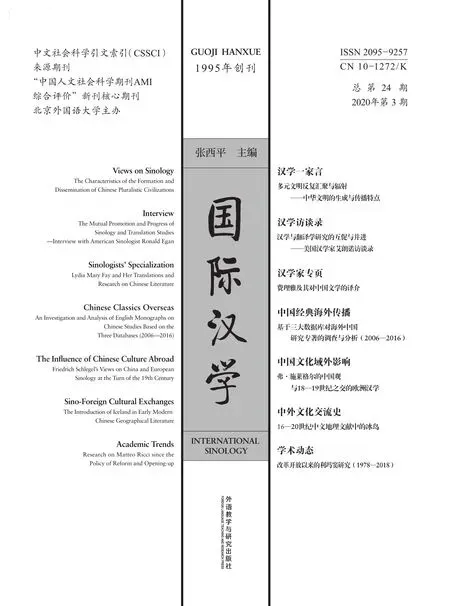从传教士汉学到“新汉学”
——西班牙汉学发展与流变述略*
2020-11-30管永前
□ 管永前
一、西班牙汉学的创立:16 世纪中叶
西班牙汉学最初是伊比利亚民族传播天主教以及贸易和军事扩张主义的产物,传教士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班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为了在中国传播“福音”,首先要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进而需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由此开始了西班牙汉学的发展历程。
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是西班牙汉学的创始人,被天主教会奉为圣人。1541 年,沙勿略受罗马教廷的派遣前往东方传教。由于他在日本和印度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华夏文明的认知,沙勿略总结出以文化调和主义为核心的传教士“适应”策略。1552 年,沙勿略踏上中国的上川岛(今广东省台山市),由此拉开了基督教继唐朝与元朝后第三次传入中国的序幕。为了向中国民众宣传“福音”,沙勿略开始学习中文,编写《教义问答》,并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作积极的准备。然而不幸的是,在等待获得进入中国内地许可的时候,沙勿略因患重病于1552 年12 月3 日在上川岛去世。尽管他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但沙勿略提出的“适应”策略成为此后天主教东方传教运动的主导方针,影响广泛而深远。可以说,沙勿略从客观上开启了西班牙的汉学研究。②张铠:《西班牙的汉学研究(1552—201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9 页。
奥古斯丁会修士马力陈( Martin de Rada,1535—1578)是一位博学之士,曾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和巴黎的大学学习数学、地理、天文学和语言。1565 年他来到菲律宾后,喜获中国明末刊刻的《古今形胜之图》,由此西方人第一次通过中国的地理图像来认知中国。后在旅菲华人的帮助下,马力陈将该地图上5 000 余字的中文说明译成了西班牙文。马力陈对《古今形胜之图》的研究可以视为西班牙汉学研究的正式起步。
1574 年,马力陈曾花两个月的时间在福建旅行,并得到上百本中国古籍。他第一个指出,马可·波罗笔下的“Cathay”就是中国。回到菲律宾后,他利用中国典籍,著成《菲律宾群岛奥古斯丁会神甫马力陈与其同伴赫罗尼莫·马林以及与他们随行的士兵在中国观察与体验到的事物》(Las cosas que los padres Fr. Martm de Rada,provincial Orden de S. Agustin en las islas Feiiipnas,su companeros Fr. Jeronimo Marin y otros soldados que fueron con ellos vieron y entendieron en aquel reino,简称《中国纪行》)。马力陈由此成为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现实社会概貌较为真实地展示给欧洲的第一位西方人。他的这部《中国纪行》也成为其后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个起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力陈被称作“西方第一位汉学家”①《西班牙的汉学研究(1552—2016)》,第10 页。。
二、西班牙汉学的黄金时代:16 世纪中叶至17 世纪
在沙勿略榜样力量的鼓舞下,前来东方的西班牙传教士刻苦学习中文,亲身体察中国的国情,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迎来了西班牙汉学的黄金时代。
(一)门多萨与《中华大帝国史》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1545—1618)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后来成为波帕扬(Po Dayan)地区的主教。他是“征服中国”论的支持者之一,曾觐见菲利普二世,劝说其进行这项军事冒险。1581 年,当西班牙王室决定向中国派出使团时,他被委任为团长,并率团来到通往中国的中转站——墨西哥。由于至今未明的原因,门多萨的中国之行受阻,但他利用在墨西哥期间收集到的有关中国的大量资料,写出了《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1585 年,《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在罗马一经问世,便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实际上,这本书是16世纪有关中国地缘环境、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等领域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百科全书,形成了欧洲对中国的基本概念,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到1700 年,这本著作已经有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及拉丁文等几十个版本,堪称盛况空前,“代表着16 世纪西班牙汉学的最高成就”②同上,第11 页。。
(二)高母羨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高母羨(Juan Cobo,1546—1592)是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于1588 年抵达菲律宾,并在旅菲华人聚居的“涧内”(Parian)一带传教。1590年,他将范立本编于1393 年的《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成为第一位把中文文本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人,也是第一位把汉字“拉丁字母化”或“罗马字母化”的人。
为了使中国人了解基督教教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高母羡用中文写出《天主教教义》一书,这是继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S. J., 1543—1607)于1584 年用中文写出《圣教实录》后第二部由西方人写出的中文著作,同时也是在中国境外第一部用中文刊刻的宣教之作。为了让中国人了解到基督教文明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上,高母羡又用中文写出一部《辩正教真传实录》(又作《无极天主教真传实录》),该书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用中文写作的介绍西方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著作。高母羡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促进东西方两种异质文明的交流上。③同上,第12 页。
(三)庞迪我:融入中国社会的“西儒”
在晚明来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当中,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并被中国知识界以“西儒”相称的只有耶稣会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一人。庞迪我于1597 年来华,1601 年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抵达北京,将西方新奇物品呈献给万历皇帝,从而获得在京居留权,成为那个时代仅有的能出入紫禁城的西方人。1602 年,庞迪我致托莱多主教古斯曼(Luys de Guzman,生卒年不详)的长信则让欧洲首次对中国有了较为完整、客观的认识。
在最近关于西班牙和中国关系的研究中,庞迪我被重新提起并得到肯定,因其代表了西方的“儒家文化”。庞迪我来华后始终坚持沙勿略倡导、利玛窦身体力行的“适应策略”,并在中国知识界上层做着“合儒”“补儒”的工作,以期实现“超儒”的目的。因此,庞迪我和利玛窦也是将方济各·沙勿略的“适应策略”运用得最好的两位。庞迪我用中文写成的《庞子遗诠》《七克》《天主实义续篇》《具揭》等著作为中国士大夫所喜读,一时被称作“庞子”“庞公”。庞迪我也是将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人物之一,比如测量广州和北京的纬度,继续利玛窦对历法的研究,帮助徐光启等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医学等。尤其是在世界地理学的研究中,庞迪我还写出一部世界地理概述,后经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整理刊刻,这就是著名的《职方外纪》。庞迪我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庞迪我还是利玛窦著作的遗产受赠人。他于1604 年完成的利玛窦书信、文书和日记整理,是当时欧洲有关中国现实的最出色的记载。可以说,庞迪我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也是造诣很高的汉学家,标志着西班牙早期汉学研究进入了成熟期。①张铠:《庞迪我与中国(1597—1618)》,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
(四)黎玉范和利安当的汉学贡献
多明我会的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1597—1664)和方济各会的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o de Santa Maria,1602—1669) 是 反 对“适应”策略的代表性人物,正是他们拉开了“礼仪之争”的序幕。黎玉范也是一位多产的汉学家。在他的著述中,一部分是具有论战性质的专著,诸如《中国传教史》(Historia Evengeliga de China)以及与他人合作写成的《中国礼仪研究》(Estudios sobre los Ritos Chinos)等。他用中文写的《圣教孝亲解》手稿8 页,现藏梵蒂冈档案馆。他曾编写过一部《西班牙–汉语官话语法》(Gramatica Espanola mandalina)和几种汉语–西班牙语双解合璧字典。在中国方言的研究方面,黎玉范是一位先行者。
利安当则以极大的热情学习汉语,专门研究中国儒家典籍。《天儒印》是其代表作。他从“四书”中摘出一些儒家先贤的名言、名句,然后与所谓“天学”中的类似名言、名句相对照,再从中找出二者的相似之处。他实际上是在暗示,在整个儒家学说中,暗含着基督教的天启真理。利安当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哲学体系和中国文化基本特征的深入研究上。以利安当为标志,西班牙汉学有了进一步深化。
(五)万济国及其《华语官话语法》
万济国(Francisco Varo,1627—1687)是多明我会修士,曾热心投入“礼仪之争”的辩论,写出大量论辩性文章和著作。除了与黎玉范等合作写成《中国礼仪研究》一书外,他还用中文写下了四卷本的《主教明证》。万济国的贡献在于,在汉语语言学的具体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他编写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语法结构和规律的专著,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不衰。他还编写了《汉语官话辞典》(Vocabulario de lingua mandarina)、《西班牙语与汉语官话双解语法》(Gramatica Espanola mandarina)和《通俗汉语官话辞典》(Vob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 con el estilo y vocablos con que se habla sin elegance)。如果说利安当在汉学整体研究上有了较大超越,那么万济国则在中国语言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六)闵明我:西班牙汉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闵明我(Domingo Fernandez Navarrete,1618— 1686)为西班牙来华多明我会修士,也是“适应”策略的最大反对者之一。他最主要的著作是1676 年发表的《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Tratados historicos,politicos,ef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该书对中国国情作了全面介绍,试图为衰落中的西班牙帝国提供可借鉴的榜样。这本著作对中国的认识,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前述西班牙传教士所无法企及的:马力陈在福建仅待过两个多月,门多萨从未到过中国,庞迪我虽然在中国度过21个春秋,但主要是在北京传教,而闵明我在中国省城长期生活和宣教,对中国社会了解得更加深入和全面。此外,马力陈、门多萨和庞迪我等论述的多是晚明时代的中国概况,闵明我则详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清朝的早期概貌。因此,该著为西方国家提供了一幅更为完整、叙事年代更长的中华帝国的历史画卷。
《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发表后,引起欧洲知识界对“礼仪之争”的极大关注,很快被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出版。在闵明我及其他西方来华传教士相关著作的激发下,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出现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研究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化的热潮,即历史上“中国热”,从而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该书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部杰作,而且对欧洲一代启蒙大师产生过重要影响。可以说,闵明我是17 世纪西班牙汉学研究的一代宗师,达到了18 世纪以前西班牙汉学研究的顶峰。①《西班牙的汉学研究(1552—2016)》,第17 页。
在16 世纪、17 世纪,除上述以传教士为核心的领军人物外,还有许多人关注汉学。比如安德雷斯·德米兰多拉(Andres de Mirandola)于1569 年写的《致菲利普二世的信:关于中国的伟大和习俗以及葡萄牙发生了什么》(“Letter to Philip Ⅱ from Andres Mirandola Telling Him What Happened to the Portuguese,with News from China of Her Greatness and Customs”)以及马尼拉第三任总督桑德(Francisco de Sande)于1576 年写的《致菲律宾统治者菲利普二世陛下的信》(Letter to H. M. Philip Ⅱ,the Governor of the Philippines,Dr. Francisco de Sande)。其他著作有关于中国自然的百科全书,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另有关于征服菲律宾、马鲁古群岛(Maluku)和其他西班牙殖民地的情况,如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1480—1521)首次环游地球中的中国部分等。简言之,这些书都是为国家或者传教士而写,并不是给普通民众阅读的。②王圣佳编译:《西班牙汉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年,第84—98 页。原文载于《西班牙汉学》(Spanish Sinology),作者为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历史学教授劳尔·鲁伊斯。
三、西班牙汉学的衰退与停滞:18—19 世纪
在18—19 世纪,西班牙汉学受到消极的历史环境影响。一方面,1640—1713 年,西班牙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衰落,国王由向外扩张转为守势。1805 年起西班牙陷入一系列战争,先是卷入拿破仑战争,而后又为争夺大西洋的控制权与英国开战,并以战败告终。1808—1839 年西班牙内部又陷入长达30 年的内战,使得自1500 年来称霸世界的西班牙势力一落千丈。另一方面,在罗马教廷的权利斗争中,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为了抑制耶稣会势力的膨胀,于1773 年取缔了耶稣会,使西班牙耶稣会士难有作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晚明时期发生的“南京教案”使在华天主教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在后来的“礼仪之争”中,西班牙传教士对儒家学说的批判,遭到中国社会的抵制,清王朝与罗马教廷之间出现了严重冲突。“礼仪之争”最终使清朝下决心驱逐天主教传教士,严禁传教土再进入中国(1724)。如此以来,西班牙来华传教士,无论是方济各会修士还是多明我会修士,大多被迫转移到福建边远地区传教,失去了接触中国主流社会的机遇和深入研究汉学的条件。
从整体上看,18—19 世纪西班牙汉学陷入了衰退与停滞时期。在这个阶段,西班牙汉学由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主导,出现了一些具有传教士特色的语言类著作。与以前为了政治和文化目的编写的著作不同,这些关于语法、词典、词汇、教义问答等的著作是为了教育和传教的需要而写。如弗朗西斯科·古来乐(Francisco varo y Guerrero,1627—1687)的《中国语言的艺术》(Art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一书,第一次研究了中国官话的所有音调。另外还有卡斯塔内拉(B. Castaneda)的《中文广州方言基本语法》(The Basic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Cantonese Dialect)、曼努尔·德尔·萨克拉门托(Manuel del Sacramento)的《汉语语法》(Arte de lengua China)。圣托·米格尔·卡尔德隆(Santo Miguel Carderon)、克里斯托瓦尔·普拉(Cristobal Pla)、胡安·克罗木(Juan Colon)、多明格·巴劳(Domingo Palau)和圣地亚哥·加西亚(Santiago Garcia)等人都曾编撰过福建方言字典。
由于西班牙来华传教士大多深入民间传教,他们用中文写下了相当一部分宣教著作,比较有影响的如《圣体要理》《圣经直解》《圣母行实》《圣母行实目录》《默想神功》《圣教明征》《形神实义》《人类道安》《圣教切要》《天主教入门问答》《罗洒行实》等。这类中文著作以在民间宣教为目的,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为地区性方言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①《西班牙的汉学研究(1552—2016)》,第30—31 页。
除此以外,1847 年派驻中国的第一任西班牙使臣玛斯(Sinalbo Mas y Sanz)是继法国、英国和美国之后第四位获清朝皇帝承认的西方使臣。他的著作包括1857 年在巴黎出版的《英国、中国和印度》(England, China and India)和1861 年同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和基督教势力》(China and the Christian Powers)。他的朋友、西班牙驻香港办事处的何塞·德·阿吉拉尔(Jose de Aguilar)撰写了《理解中国官话:为中文译者准备的简单句型分析集》(The Chinese Interpreter: Collection of Analyzed Simple Sentences to Understand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China),于1861 年在马德里出版,为中文向现代拼音转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②同上,第84—98 页。
四、西班牙汉学的复苏:20 世纪
尽管18 世纪初至19 世纪末这200 年间西班牙汉学一度消沉,但进入20 世纪后西班牙汉学出现了复苏。
在汉语研究方面,20 世纪初一批新的汉语语言学著作相继问世,如拉蒙·克搂美尔(Ramon Colomer)的《汉西注音辞典》(Diccionario tonico Sinico-espanol)和路易斯·玛利亚·尼埃托(Luis Maria Nieto)按“国语拼音字母”排序编写的《中西实用辞典》(Diccionario manual Chino Castellano)等。20 世纪上半叶,在福建一带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格外重视当地方言研究。如孟塞诺尔·特奥多罗·拉布拉多尔(Monsenor Teodoro Labrador) 与 拉 伊 蒙 多· 吉 哈 诺(Raimundo Quiano)出版了《西中福州方言辞典》(Diccionario espanol-chino del dialecto de fuchou)。皮袅尔·安德来武(Piñol y Andreu)发表了其名著《华班辞典》,即《中西厦门方言辞典》(Diccionario chino-esparol del Dialecto de Amoy,1937)。布拉斯·克尔内霍(Blas Cornejo)编写了《西中福安方言辞典》(Diccionario espanolchino, dialecto Fogan, 1941—1943)。
在中国典籍研究与翻译方面,西班牙汉学家杜善牧(Carmelo Erolduy,1901—1989)的汉学研究最受推崇。他于1961 年翻译完成《道德经》;1967 年发表《庄子:道家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Chuang teu: Literate, filosofo y mistico taoist);1968 年出版《东方政治中的人道主义》(Humannismo politico oriental);1972年发表《道家思想中的六十四个概念》(Sesenta y cuatro conceptos de la ideologia taoist);1974年翻译出版《中国浪漫诗歌中颂歌选萃》(Odas selectas romancero chino),这是中国《诗经》的选译本。埃洛杜伊对《易经》和《墨子》进行了多年研究,先后于1983 年和1987 年出版了《 易 经》(El Libro de los cambios) 和《 墨翟:具有普遍之爱的政治家》(Mo Zi: Politico del Amor Universal)两本专著。另一位颇有声望的西班牙汉学家是安东尼奥·多明格斯(Antonio Dominguez,1915—1991),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将西班牙汉学研究先驱高母羡于1593 年用中文撰写的《辩正教真传实录》译成了西班牙文,并于1953 年出版(1986 年再版),此外他还于1978年出版了《中国文化中的孝道》(Filial Piety in Chinese Culture)一书。③雷孟笃(José Ramón Álvarez):《西班牙汉学研究的现况》,《汉学研究通讯》总第101 期,2007 年,第36—47 页。
1973 年中国与西班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西班牙汉学日趋活跃,不断取得新进展。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的翻译上,比如《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聊斋》《四书》《汉书》《孙子兵法》以及中国部分古典诗词等均已有了西班牙文译本。其中,劳雷亚诺·拉米莱斯(Laurenao Ramirez)的《儒林外史》西班牙文译本曾荣获西班牙国家翻译奖。刘勰的《文心雕龙》已由格拉纳达大学(University de Granada)中国语言与文学系教授阿雷王林克(Alicia Relinque Eleta)译为西班牙文并加以注释;2002 年她又翻译出版了《中国戏曲三种》(Tres Dramas Chinos),即《窦娥冤》《赵氏孤儿》《西厢记》。从事中国诗词翻译的西班牙汉学家主要有艾莲(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的代表性译著《李白50 首诗选》(Cincuenta poemas de Li Bo,1988)、《苏东坡——赤壁怀古及其他诗作》(Recordando el pasado en el Acantilado rojo y otros poemas de Su Dongpo,1992)、《王 维99 首绝句及同时期风格相仿的诗人》(99 cuartetos de Wang Wei y su círculo,2000)、《白居易111 首绝句》(111 cuartetos de Bai Juyi,2003) 等 多 部。还有卡洛斯·德尔·萨斯–奥罗斯科(Carlos del Saz-Orozco)的《唐朝诗人》(Poetas de la dinastía T’ang,1983)、戈麦兹·吉尔(A. Gomez Gil)和陈光孚合译的《中国诗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唐朝诗选》(Antologia Poetica de La Dinastia Tang,1999),等等。
与此同时,西班牙汉学界还扩大了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译介,如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东方研究中心的塔西亚娜·非撒克(Taciana Fisac)已将巴金的《家》(1985)、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1989)和钱锺书的《围城》(1992)等相继译为西班牙文。
在20 世纪西班牙汉学家中,还有两位女性不得不提。一位是偏重跨文化研究和翻译的女性黄玛赛(Marcela de Juan,1905—1981)。她是一位中国驻西班牙外交官的女儿,曾随父亲来到中国。她致力于把中国文学介绍到西班牙,主要作品有《中国古代的传统故事》(Cuentos chinos de tradición antigua)、《东方幽默故事》(Cuentos humoristicos orientales)、《中国说书人选集》(Antologia de cuentistas chinos)和《昨日中国与今日中国》(La China que ayer vivi y la China que hoy entrevi)等。①《西班牙汉学研究的现况》,第36—47 页。另一位跨文化女性学者是易玛(Inma Gonzalez Puy),曾任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和中国西班牙文化中心主任。她是中西建交后最早来华的留学生之一,曾在西班牙使馆任文化专员,期间创办过“学术论坛”性质的期刊——《西班牙》(Espana)。易玛曾将中国广为人知的《红灯记》译为西班牙文。
五、西班牙“新汉学”的兴起:21 世纪至今
从20 世纪末至21 世纪初,在西班牙出现了一种“新汉学”,它与16 世纪至20 世纪的汉学研究有着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研究主体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这种被称为“中国学”的研究思潮发轫于西班牙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出现了一些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人员,将考察中国社会经济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合了当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研究、哲学与政治研究、经济与社会研究等诸多领域。“新汉学”的阵营由学术团体组成并不断发展壮大,他们正在努力创建一个稳固的学术体系,其首要目标是让“中国研究”进入西方公众视野。这种“新汉学”与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同欧洲其他国家保持相同的研究水准,并出版了大量论文和专著。
在中国历史文化综合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的劳尔·米雷斯·鲁伊斯与路易斯·帕拉西奥斯(Luis Palacios)合写的《中国:历史、思想、艺术与文 化》(China: Historia, Pensamiento, Arte y Cultura, Cordoba, 2011)一书。②朱政惠:《西班牙汉学研究的新成果》,《文汇报》2012 年7 月23 日,第00C 版。该著旨在向西班牙语世界介绍中国4 000 多年来不曾间断的恢宏历史和文明以及儒家文化对华夏民族的长远影响。
在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研究方面,近年已涌现出许多佼佼者。如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Universitat Pompeu Fabra,Barcelona)的欧阳安(Manél Ollé Rodríguez)③欧阳安,西班牙汉学家,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终身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常年从事16 世纪、17 世纪中国海洋史研究,西班牙、葡萄牙东亚扩张史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史研究以及现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等。曾合作翻译《唐诗选》、蒲松龄《聊斋志异》选集,出版专著数部。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魏京翔博士提供以上材料。写出了《想象中国》(La invencion de China, 2000)和《中国事业:从无敌舰队到马尼拉大帆船》(La empresa de China: De la Armada Invencible al Galeón de Manila,2002);胡安·吉尔(Juan Gil)著有《马尼拉华人(16—17 世纪)》(Los Chinos en Mannila, Siglos 16—17, 2011);科尔多瓦大学的安东尼奥·加西亚–巴索罗(Antonio Garcia Abase)著有《砖石城墙与丝绸大炮:在西班牙帝国的中国人(16—18 世纪)》(Murallas de piedra y Cañones de Seda: Chinos en el imperio español, siglos XVI—XVIII,2012)。 现 在台湾大学任教的鲍晓鸥(Z. E. Borao)曾于1994年写出《西班牙与中国(1927—1967)》(Espana y China, 1927—1967)一书,目前正致力于西班牙占领台湾史的研究,尤其是台湾早期原住民的历史,这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课题。
在西班牙来华传教士研究方面,萨拉戈萨大学(Universidad de Zaragoza)的何塞·安东尼奥·塞维拉(Jose Antonio Cervera)曾对高母羡的《辩正教真传实录》进行过深入研究,并于2001 年完成了《东方的传教士科学》(Ciencia Misionera en Oriente)一书,从中可以看到在大航海时代西方传教士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有关庞迪我的专题研究也有新进展,由马德里南部历史研究所(Instituto de Estudios Historicos del Sur de Madrid)贝亚特里斯·蒙科(Beatriz Monco)整理的庞迪我致托莱多大主教古斯曼的长信《关于几位耶稣会神父进入中国后在该国所见所闻纪要》已经于2011 年出版。加泰罗尼亚欧佩塔大学(Universitat Oberta de Catalunya)的萨尔瓦多·梅迪纳·拜纳(Salvador Medina Baena)所撰的《十七世纪的文化融合与有关中国的记述——以庞迪我为例》是一篇通过对16 世纪和17 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回顾来评述庞迪我历史地位和影响的长篇论文。此外,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罗慧玲和伦敦大学英国皇家学院的蒋薇已将《关于几位耶稣会神父进入中国后在该国所见所闻纪要》这封致古斯曼主教的长信全部译成了中文,经金国平审校后已收入《耶稣会士庞迪我文集》中,为深入研究庞迪我这位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在当代西班牙有关中国政治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西班牙前驻华大使欧亨尼奥·布雷 戈 拉 特(Eugenio Bregolat I Obiols) 所 著 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La Segunda Revolucion China)。该书详尽记述并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并深刻阐释了中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引起了国际上渴望解读中国伟大复兴之“谜”的政治家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4 年布雷戈拉特又出版了论文集《中国的复兴》,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西班牙的汉语教学也在快速发展之中。目前,西班牙约有14 所大学开设汉语专业,它们是阿利坎特大学(Universidad de Alicante)、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巴塞罗那大学(Universidad de Barcelona)、马德里自治大学、格拉纳达大学、马拉加大学(Universidad de Malaga)、塞维利亚大学(Universidad de Sevilla)、庞培乌·法布拉大学、加泰罗尼亚欧佩塔大学,布尔戈斯大学(Universidad de Burgos)、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巴亚多利德大学(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和拉里奥哈大学。此外,西班牙还开设八所孔子学院,分别是马德里孔子学院、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瓦伦西亚大学孔子学院、巴塞罗那孔子学院、大加纳利斯拉斯帕尔玛斯大学孔子学院、莱昂大学孔子学院、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孔子学院以及萨拉戈萨大学孔子学院①详见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网站: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9 月2 日。,它们对于推动西班牙的汉语教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上述大学和孔子学院外,还有许多机构提供亚洲课程,并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比如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简 称CSIC)下 辖的历史研究所、西班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HSS)、巴塞罗那国际事务研究中心 (Barcelo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简称BCIA)基金会以及西班牙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简称IAS),还有华金·贝尔特兰(Joaquin Beltran)负责的“当代中国图书馆”。
21 世纪伊始,西班牙汉学研究机构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合作,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由格拉纳达大学发起的“西班牙亚太研究论坛”(Spanish Forum of Asia Pacific Research)。2002 年“亚 洲 之家”(Casa Asia)成立,旨在推动各种项目和活动,以加强西班牙对亚太地区的认识。2007 年,在西班牙政府支持下创立了“拉丁美洲东亚研究网”(REDIAO),成员包括30 多个拉美国家机构,目的是促进伊比利亚语世界对东亚的研究合作。由拉里奥哈大学(Universidad de la Rioja)开发的网络统计引擎Dialnet,则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书目门户网站之一,为西班牙“新汉学”注入了新的动力。①劳尔·拉米雷斯·鲁伊斯著,魏京翔译:《2010—2015 年西班牙“中国学”研究现状与趋势》,《国际汉学》2016 年第3 期,第186—192 页。
综上所述,西班牙的“新汉学”是建立在大学的汉语教学研究机构和学术论坛的设置以及互联网引擎的开发和利用这三根柱石之上,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稳固的学术体系。②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关于西班牙的汉学研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持续关注,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以下仅选取近五年来的重要成果。其中著作类主要有:叶农整理:《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张铠:《西班牙的汉学研究(1552—201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学术论文类主要有:(1)关于高母羨:张西平《儒家思想早期在欧洲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16 年第3 期,第160—170 页。(2)关于庞迪我:高胜兵:《述译:〈庞子遗铨〉中圣经的“名”与“实”》,《圣经文学研究》2016 年第1 期,第223—239 页;叶农、罗诗雅:《与巨人同行者——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及其中文著作》,《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6 期,第131—142 页;李奭学:《中西会通新探:明末耶稣会著译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国际汉学》2015 年第1 期,第127—141、第205 页。(3)关于黎玉范和利安当:纪建勋:《明末清初“礼仪之争难题”与“中国礼仪之争”第一人——兼论“礼仪之争”还是“利益之争”》,《基督教学术》2018 年第2 期,第297—309、第459 页;杨慧玲:《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文献——对梵蒂冈图书馆藏稿抄本Borg.cin.503 的初步研究》,《史学史研究》2016 年第2 期,第93—98 页。(4)关于闵明我:李亮:《以方求圜:闵明我《方星图》的绘制与传播》,《科学文化评论》2019 年第5 期),第56—67 页;罗莹:《中国“礼仪之争”中反对“文化适应政策”的声音——以〈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论〉一书为中心》,《国际汉学》2016 年第2 期,第44—51、第202 页等。这些论文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关于西班牙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此外,2018 年9 月5—6 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西班牙驻华使馆主办的“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之思考——纪念庞迪我逝世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本次会议重新审视庞迪我的历史贡献,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结 语
通过对450 多年来西班牙汉学发展和变化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班牙已经逐步完成了从传统意义上的传教士汉学向当代“新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转变。西班牙汉学在世界上起步最早,16—17 世纪形成了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早期的西班牙汉学由传教士所书写,他们大多数是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修士。其中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汉学巨著,对西方汉学影响深远;闵明我和其他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则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西班牙汉学的发展与西班牙的政治兴衰紧密相联。16—17 世纪的西班牙是全球性大国,西班牙汉学缘起于帝国全球扩张的雄心,可以说是宗教狂热和军事扩张主义的产物,因而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及至18—19 世纪,当西班牙军事力量崩溃,政治力量衰落时,汉学成为传播“福音”的工具,汉学研究也日渐衰颓,曾经独领风骚的西班牙汉学逐渐衰弱至被人遗忘的境地。自20 世纪开始,西班牙汉学出现复苏。特别是中国与西班牙正式建交后,西班牙汉学日趋活跃。至21 世纪,一股新型的学术力量开始涌现,西班牙“新汉学”从大学和研究机构起步,开创了新的道路,逐步转向专业化的“中国学”研究。目前,西班牙汉学正处于复兴之中,必将推动中西两国的理解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