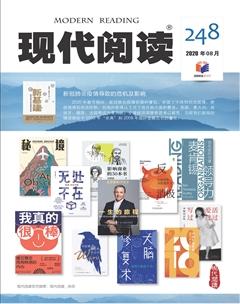法庭科学实验室文化:痕迹证据与观察者偏见
2020-11-28

当我们谈到犯罪现场调查这个话题时,近年来流行的“CSI效应”一定无法回避。它源自2001年以来持续播出的3部美剧。然而,电视剧《犯罪现场调査》每周都必须限定在1小时内完整讲述一起案件的侦破过程。要做到这些就不得不走一些“捷径”,如时间上的压缩、夸大了的设备分析数据及其转化为证据的能力、实际不可能得出的结论,以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犯罪现场调查员——他们不但收集证据、分析证据、询问证人,甚至连抓捕嫌疑人也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事实上,现在许多法庭科学实验室确实都在与警方合作,参与到犯罪现场调查中,幫助警方技术人员寻找、收集和保存物证,也有助于他们随后的分析研究及得出结论。但不得不说,法庭科学家前往现场协助调查同样也会增加“确认偏误”的可能。
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几件震惊世人的刑事案件,已使公众对法庭科学家的客观性疑虑重重。“马德里爆炸案”就是明证之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偏见会存在于许多法庭科学家的思维和工作中。它现已成为一些研究的关键词,如“观察者偏见”。
当法庭科学家在科学证据的分析鉴定中,结果或结论受到无关知识或信息的影响时,就会出现观察者偏见,即使这些知识或信息并没有直接应用于正在进行的科学分析。观察者偏见可能不仅仅是无关知识的影响,还可能是法庭科学家的潜意识期望或主观渴望得到的预想:这种偏见可能潜移默化、如影随形,出现在法庭科学的各个领域——从法庭科学证据分析结论的措辞变更,到以微妙的方式支持公诉人或辩护人。甚至在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法庭科学家编造证据和提供虚假证词的极端情况。
观察者偏见较易在痕迹证据分析鉴定方面产生,指纹、枪械和工具痕迹、笔迹、毛发、咬痕、血痕及其他类似的痕迹证据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特征:法庭科学家需要将待检材料(或称未知检材)与已知样本进行比较并发现其中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科学仪器提供可备份数据,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分类法用以确定特征的普遍性或稀缺性,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关联性结论的基础。法庭科学家只能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得出结论。任何微妙或显性的偏见都有可能在无意中(尽管也有可能不会)影响在特殊情况下得出的结论。
其实,在认知心理学看来,观察者偏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它几乎影响到所有类别的科学研究。大多数负责任的科学家普遍认为观察者偏见广泛存在,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家们会采取一些措施,如双盲测试和完全独立的重新测试等,来消除或者至少弱化此类偏见。不过,即便如此,部分法庭科学家仍坚持认为他们没有这种偏见。他们声称自己已意识到观察者偏见的可能,并因此自我警告,且已将它们清除出头脑。他们还声称,自己的个人信仰以及关于案件的知识,与最终结论的产生无关。事实上,免于偏见影响正是法庭科学家的必备素质之一。然而,尽管有这些信念,来自真实案例的充分证据以及一些针对法庭科学的研究已经表明,观察者偏见在法庭科学中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否定偏见存在的集体心理状态,也抑制了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和影响:虽然认知心理学的一般实验可以并确实揭示了科学界存在的观察者偏见问题,但法庭科学仍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也就是通过实际的研究分析,发现偏见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影响法庭科学家的日常工作。
以一个典型的法庭科学实验室工作为例,法庭科学家对收集自犯罪现场的证据进行分析鉴定,以确定嫌疑人或受害人的身份,另外,他们还需要收集一方或双方的样本,并与现场证据进行比对。这就是案件的全部。我们有时会问他们,“这个犯罪现场证据的来源是什么或是谁”,抑或“犯罪现场证据是来自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害者”。虽然都是询问,但它们产生的效果迥异: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已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不同询问方式得到的答案可能大相径庭。
通常,当实验室的法庭科学家收到来自犯罪现场的证据时,他们还会获知其他相关信息,如犯罪类型、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姓名、犯罪细节及某些适用于该案的特殊证据。其中大部分信息可能与科学鉴定分析并无直接关联。例如,在欺诈案中,证据仅是一张支票上的签名,法庭科学家获得的比对样本仅为某人提供的类似于兑现支票的签名。此时,这个信息对笔迹鉴定的特征分析其实并无直接关联,但该信息可能会对法庭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又可以说,案件信息类型不同,对法庭科学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又如,对法医病理学家而言,越多的信息越能帮助确定死亡的原因和方式,而相反地,枪械分析员则仅仅需要判断子弹是否从某把枪支中击发即可。
通常,尽管法庭科学家要对某个证据进行全面分析,但他们往往仅被要求提供部分鉴定结果,其余的则被认为不重要,甚至不需要。有时,那些无法得出结论或无法起到证明效果的证据又被重新送回实验室进行复检,而那些对侦破案件明明有利的证据却被弃置一旁。这些也都算是具有明显偏见的普遍现象,对它们也要有防范意识。
法庭科学实验室应该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或消除某些类型的观察者偏见。这些措施可能是昂贵的、烦琐的,甚至是官僚的,并且有时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即使每个科学研究领域都有内部规范程序和措施预防偏见,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仍然要坚持依靠客观的试验分析和研究得出结论:一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或许就决定于法庭科学家一个寥寥数语的结论,因此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不容懈怠。
当目击证人在辨认犯罪嫌疑人时,六七名外表相似的犯罪嫌疑人会在现场从一个单向透视镜后列队向证人展示。这就是所谓的“列队辨认”。喜好罪案题材影视剧的读者朋友一定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在大多数法庭科学家协助的案件中,分析员也同样需要面对类似的“列队辨认”挑战,也就是将一个已知样本与诸多未知样本进行比较。这种辨认方法要求聚焦于辨认某一个犯罪嫌疑人或受害人。将若干相似且已知的物证“列队辨认”,能够帮助分析员排除观察者偏见,“强迫”他们必须根据科学数据分析得出鉴定结论。例如,在涉及指纹识别的案件中,当指纹从犯罪现场提取并送往实验室时,分析员不但会获得犯罪嫌疑人的指纹,还会一并获得其他相关、相似的指纹。此时的焦点就在于分离、识别并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指纹,并提供已知指纹与未知指纹各自的细节特征,保证指纹比对更加客观公正。
“无关范围”的信息较易使分析员产生偏见,这基本已成共识。虽然只为分析员提供分析证据所必需的信息是最为理想的操作,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很难实现。由于案件类型的差异,法庭科学对所谓的“无关范围”信息的定义难以统一。我们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类型,来确定信息的有关和无关。若某个次要信息被分析员排除,必须有其他方式最终能将所有分析鉴定结果联结起来。若所有的相关信息均能为分析员所用,证据构建的案情也就愈加清楚。因此,在法庭科学的分析及鉴定实践中,通常会安排案件主管,专门负责收集报告并将各类信息汇总,对各种证据进行联结。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案件主管接收证据后,决定每个分析员需要何种必要信息,然后将必要信息及证据同时分配给每位分析员。
这一措施保证了分析员免受无关信息的污染而产生偏见,同时也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完成分析鉴定。若实验室安排另一位分析员重新检验证据以进行确证,则他将不能获得前一位所得出的任何结论和信息。“马德里爆炸案”就是一个分析员结论互相“污染”的典型案例。尽管法庭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DNA分型技术在内,都有可能受到观察者偏见的影响,但无疑痕迹证据是各领域中最易受到影响的。此类分析鉴定几乎完全取决于分析员的个人观察和意见。因此,对法庭科学家而言,了解观察者偏见及其负面影响,同时制定消除或降低其影响的科学操作程序至关重要。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人人都该懂的法庭科学》 作者:[美]杰伊·西格尔 译者:孟超 任鹏宇 王刘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