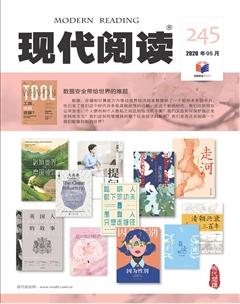出没在《诗经》里的植物
2020-11-28
近日顿顿大鱼大肉,肠胃不堪其苦,中午的时候突然很想吃蔬菜,痴痴地想了一下午,设计了N多蔬菜方案。想做个火龙果爆干贝,周围嵌一圈西兰花,又觉得不够朴素,不够直奔蔬菜。回来时绕到久违的菜场,找了采光效果好的摊位,一个个梭巡过去。“要空心菜?”“有净菜吗?”“有啊,你看看,刚摘的。”指甲掐上去,哇,一掐掐出纤维来,“小姐的指甲好漂亮。”是啊,就是留着掐菜的,你没看我就蓄了这一只手指吗?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哈哈,小姑娘很会做生意,“那看看苋菜吧,快下市了。”“多少钱一斤?”“不多卖你,三块。”“妈呀,我总不能用吃肉的价吃菜吧。”最后斟酌再三,买了两斤物美价廉、宜家宜室的木耳菜。
一路想着回家第一件事就得洗菜,菜的水汽滤干了,加了蒜泥,热锅热油,爆炒,出锅以后还是虎虎有生气的,要是带着水汽,就趴了。有一次读植物谱,才发现原来木耳菜就是“采葵持作羹”的葵的一种。过去在《诗经》里读到葵,都以为是向日葵的葵,毛茸茸的叶背,触感粗粝可怕,想来即使把它切碎了,用油炖了,加盐和香料,味道也够困难的,想着就觉得古人居大不易,心生敬畏,最后知道自己又滥情了一把,原来葵就是木耳菜(木耳菜别名落葵)啊。如果油够辣,火够爆,菜够水嫩——上次在安徽,是直接在地里摘了吃的,真是肥美得很。很多素菜要借势荤菜或荤油,才能把清鲜味逼出来,或析出味道的浑厚,木耳菜却必须素油素炒,可见它天生不近权贵,是民间食物。“采葵持作羹”亦是民间生活的素笔写照,夯实、清减、微苦的民间生活,就是把素心、素性子、素长相的一盘子木耳菜,盛在家常的白陶盘子里端上来。“采葵持作羹”是可以入画的,为什么有人画大白菜、红萝卜,就没有人画这个呢?
常吃的复古食物还有它——莼菜。它在《诗经》里叫作茆,“思乐泮水,薄采其茆”,下一句,步不扬尘,穿着绣鞋紧跟上来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先是采了水生植物做羹,然后就着水景喝酒,水波微兴,清风拂袖,菜的美往往得靠软环境的烘托,这个,古人早知道了。其实古时吃的更多的是它的双胞胎兄弟——荇菜。春夏之交,路过荷塘,或是有水泽处,常见着它,枝叶都漂在水面上,密布着细碎的小黄花,逆着光看过去,金光蹀躞,烁彩翩跹,妩媚的水生植物。如果没有花的旁注,则它的叶很容易和莼菜弄混,它们都是荷钱状的,滴溜溜的圆。“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水波滟滟,荇菜随水而动,采摘的动作也有种水性的流动和美。荇菜古时是贵族专享,这个采荇的女人应是贵族少女,难怪是君子好逑了。
莼菜盛产于太湖,上半年去三山时吃过一次,可能是季节过了,莼菜的边缘有点儿僵硬,口感粗粝起来,吃得我张口结舌,哪里是记忆中的莼菜,高汤一煮,就渗出黏液,口感中那种调皮的滑,瞬间即逝的滑,让人缅怀。莼菜胜在口感的圆融而不在味道。吴人嗜莼菜,自古“莼鲈”并肩为江南美食的意象载体,进而引发怀乡之幽思。吴人张翰在洛阳为官,见秋风起而思莼鲈,不惜辞官回乡尝鲜——多半是家里还有二亩薄田,基本物质资料不至于匮乏。莼较之于糊口的“葵”“茆”,是有贵族气息的。“双桨莼波,一蓑松雨,暮愁渐满空阔”,连莼菜引发的愁怀,都有奢侈的气息。
木兰——这种花现多栽于道路两侧,做观景植物,它的花瓣大而邋遢,不结实,尤其不经雨,一场秋雨则满地狼藉。
“朝饮木兰之坠露”,可见它花面大,所以承水,就好比比喻人生苦短说“譬如薤露”一样,薤的叶面窄,落在上面的露水很容易就蒸发了。古人的比喻都很老实,但木兰可以制舟,这就使它笨重的意象轻盈起来,想想“兰舟桂桨”,召伎携酒,溪水流香,是多么美的意境。
留夷,今称芍药,红的为“红药”,白芍药则直称“药”。
一直想写篇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就叫何红药,实在是香艳热辣的名字,芍药的花形类牡丹而微,但芍药是草本,而牡丹是木本,也难怪芍药开不出牡丹的气势与王气。这个药我也常常吃,有时是赤芍,有时是白芍,主补血,在药袋子里翻出几片干燥失色的根的碎片,但如果是用玫瑰入药则可见全尸。
楸——此树逢秋落叶,所以名之楸……这我就不懂了,树之枯荣,尤其是北半球的树,不都这个规律么,我一直以为小时候我家门口种的是榆树,如今看了图片才知道是楸。
到春末它会悬坠一串串线状物,小时候我以为是榆钱,现在知道那是楸线,古代灾民常用它熬饥荒,可见其味不如榆钱,在盛世自然被遗忘了。屈原被逐出“郢都”的时候,回首 “望长楸而太息”,可知楸是宫廷的夹道树,后来才被生命力更泼辣的梧桐取代。
桃李——桃李常常被并提,一是因为它们花期接近,二是桃花艳红李花素白,古人为求色彩对比的观赏效果,喜欢将它们并植。“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开起来阵势很大,且花期又短,生得热烈,死得惨烈。“夹路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殘红”,就像青春期一样。摔着,痛着,被践踏着,就这么过去了。桃花灼目,是日光下的花,李花淡泊洁密,更宜月夜。宋代大概是崇尚理学的缘故,重花格而轻花色,梅花清骨傲节,正是精神化的美,桃花直白肉感的艳丽被斥为“妖客”,明代以后更沦落成妓女的代言花,为什么《桃花扇》是桃花扇而不是梅花扇、月季花扇?这个心机也太露骨了。这让我怀恋《诗经》,《诗经》里的植物心态,要平和得多,它关注植物本身的功用,而不会带着人类的阶级色彩,强行把它们分为香草、恶草什么的,再附会在君子、小人身上,褒贬人事。生活在《诗经》里的植物,是幸福的,安详的,让我们隔着几千年,亦觉得亲。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读Reading第一辑典藏版》 本文作者:黎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