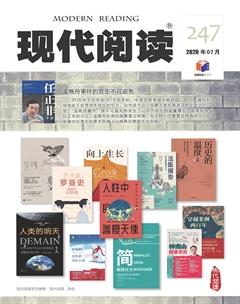你需要知道的关于爱的哲学
2020-11-28阿兰斯蒂芬王亚庆
阿兰?斯蒂芬 王亚庆
从哲学上来说,爱的本质从古希腊开始,就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哲学探究对象了,由此还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从与生理欲望和基因驱动密切相关的爱的物质概念,到作为个体间联结纽带的爱的精神观念——譬如人们的美德、友谊和幸福。
苏格拉底:狄奥提玛之“爱的阶梯”
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苏格拉底概述了一种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爱是物质的,那么它就由某种东西组成,如果它是由某种东西组成的,那么它就是一个被渴望的对象,因此是某种可以拥有的东西。苏格拉底接着叙述了与曼提尼亚的女祭司狄奥提玛的对话,狄奥提玛被他称为爱情方面的专家。
狄奥提玛(名字意为“受到宙斯之神的尊敬”)指出,爱的第一种形式,是由对美丽和极好事物的渴望构成的,尤其是对智慧的渴望。狄奥提玛补充说,爱不能与爱的对象混淆,而爱的对象与厄洛斯(爱本身,感官的爱和欲望之神)相反,是完美和至善的。希腊人相信厄洛斯是精神驱动的人类之爱,但这只是一个起点而并非爱本身,这只是对爱的对象的一种肤浅的占有欲。在一个著名的章节中,狄奥提玛说爱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神,因为厄洛斯“实际上是贫穷和资源的孩子,总是不知满足,但总是有创造力”。
然后,狄奥提玛指导苏格拉底如何攀登“爱的阶梯”:第一步是确认并渴望一个美丽、完美的年轻人;其次,从爱一个人的身体转移到认识它与其他美丽身体所共有的品质;一个人要通过欣赏所有的美,学会欣赏灵魂的美大于身体的美,反过来学会爱那些灵魂美丽的人,无论他们的身体是否也美丽;意识到自己已经超越了爱的物质领域,就会理解存在于其他领域的美,理解和体验自身的美,而实践、习俗和各种形式的知识也共享同一种美。
简而言之,狄奥提玛的爱之阶梯是一段自我实现的旅程,其中包含了对美的各种形态的超越,以及对美德之美的各种显现形式的不拘泥。这表明,在这段爱与生命的旅程中,最终目的地是达到灵魂的不朽和对神的崇敬。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引入了一个“爱”的概念,这个概念以友谊和忠诚为核心,被他称之为“菲利亚”。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幸福或快乐或充实的生活的追求包括理性的实践,因为理性能力是人类特有的功能。但是人类的特有目标不仅是推理能力,还有形成有意义、友爱人际关系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认为,菲利亚通过实践平等、慷慨的精神和简单、善良等美德,将爱引导到家庭、朋友和社区之中。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菲利亚也能以抽象和感性的方式进行实践,来描述如何能够通过艺术、诗歌和音乐之美所激发的体验和情感或自然之爱对爱进行探索。柏拉图通过将欲望(厄洛斯)、友谊(菲利亚)和哲学(对智慧的爱)融合成一种超越和转变人类存在的、单一的、全面的体验,并将其与永恒、无限和不朽的普遍真理(希腊的概念,靈性之爱或超凡脱俗的爱)联系起来,从而调和了这些立场。对柏拉图来说,真理和真实比以它们为目标的理性和爱更有价值,甚至比仅仅表现它们存在的幸福更有价值。
让-保罗·萨特:爱是斗争和冲突
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支持者,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包括评论文章、小说和戏剧都概述了存在主义哲学学说。他的核心思想是,人拥有无本质的“本质”,人是生而存在的,但由于上帝不存在,人类生活也就没有本质;“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在他著名的文章《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中写道:“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人首先存在,面对自己,在世界的浪潮中翻滚,然后定义自己。如果存在主义者觉得自己是无法定义的,那是因为一开始他什么都不是。”
萨特认为:当人类分析他们自己的存在时,他们会发现只有“虚无”。然而这种“虚无”既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诅咒。一方面,人类可以完全自由地创造“自我”,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另一方面,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或者说是消极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限制我们自由。
因此,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断言,“被判自由的人肩负着整个世界的重担;他要对世界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意识的个体,但我们需要别人的认可来验证我们的本质,并“让我们是真实的”。简而言之,要创造我们的自我并感到完整,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虚无”与他人的“存在”连接起来。
在人际关系方面,萨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人如何在自我决定的自由与想要被“别人”需要以验证我们的存在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在试图将一个人作为物体占有时,人类必然会努力占有被爱者需要的意识自由,“给予爱的人想成为被爱者的‘全世界”。给予爱的人必须成为被爱者的“范围”,并向他们展现他们自由的最终边界,并希望他们能够自由地选择不再去感知。从给予爱的人的角度来看,萨特写道:“我肯定不再被视为世界上的‘这个——和其他的‘这个一样,而这个世界要以我的方式展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特认为在想要掌控被爱者的自由时,给予爱的人在要求自己是被爱者存在的中心的过程中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给予爱的人实际的困境出现了,因为他依赖于被爱者,而这种依赖使得他们与自己的本质自由疏远:“只有想要被爱的人才会仅仅因为想要别人爱‘他们而疏远‘他们的自由。”
对萨特来说浪漫关系的力量在于,将一个人的虚无状态和另一个人的存在融合在一起。虽然人类的“本质”依赖于来自“他者”的确认(否则,我们就是虚无的状态),但我们在爱情中永远没有安全感,因为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可能不是爱人世界的中心,而是众多事物中的一个——许多“这个”中的一个“这个”。
因此,由于无法真正拥有他人的意识,爱变成了一种斗争和冲突。萨特认为,给予爱的人感到有必要被爱,但这样做会使得他通过顺从和默认从一个自由的主体变成一个对象,并且被他们所爱的人的期望所约束。萨特说,这类似于受虐狂的一种形式。另一种选择是,给予爱的人可以通过限制被爱者的自由和本质来控制他们,从而使自己成为主体,萨特认为这相当于一种虐待狂。
客体性与主体性之间的斗争,是爱情中一切冲突和未决问题的核心。人际关系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战争,双方都需要感知对方的自由,并希望将对方作为一个物体拥有。如果剥夺了对方的自由,他们就不再有吸引力,爱情就“不真实”了。然而,如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物体,他们就不可能被拥有。萨特认为唯一的答案在于承认和接受他人的自由,因为这是我们能够“拥有”他们的唯一方式。
尼采论爱与女人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莱比锡附近的罗肯。尼采的父亲是路德教牧师,在他5岁时死于脑瘤,留下他和妹妹由母亲、祖母和两个未婚阿姨抚养。评论家们经常推测尼采对女性的复杂和矛盾的态度是受他由女性主导的成长环境的影响。
在他的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通过一系列格言,以及简短、不加限定的陈述和观察,阐述了他对人类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哲学观察,这种风格后来成为他作品的标志。《人性的,太人性的》收录了680多句格言,分为9个主题松散的部分,涵盖了形而上学、道德和宗教,包括了从友谊到性别研究的各种主题。尼采在他题为“女人和孩子”的章节中写道:“完美的女人是比完美男人更高层次的人,也更为罕见。动物的自然科学提供了方法来证明这一说法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奇怪的概念,让女权主义者感到困惑,因为尼采似乎在说,由于具有生育能力所以女性是一个优越的物种。
关于女性和养育孩子的心理学,尼采在第387条箴言中认为:“有些母亲需要快乐、受人尊敬的孩子;有的需要不快乐的孩子,否则她們无法表现出作为母亲的善良。”在这句话中尼采对立和矛盾的爱是显而易见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一切都好,都渴望为他们的成就和幸福而自豪,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正是在描述母爱时巧妙使用了“需要”一词,尼采揭示了这一矛盾。母亲真的会通过孩子来寻求自我肯定吗?为了证明自己的好而让孩子生病,这就像一种被称为“代理孟乔森症候群”的精神病,即父母故意串通一气让他们的孩子生病,这样孩子就需要他们的照顾和关注。
你可以在尼采的格言中发现他对母亲的自负的攻击,这看上去像是一种蔑视:“如果儿子的朋友特别成功,母亲很容易嫉妒他们。通常母亲爱自己胜过爱儿子本身。”因此,要看到尼采是如何论证“完美女人”是“更高层次的人类”就有问题了,除非他能够否认这种完美背后有“更加罕见”的愚蠢行径。
在男女关系这个话题上,尼采似乎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能够成为最好朋友的人可能会成为最好的妻子,因为美好的婚姻是建立在友谊的天赋之上的。”对尼采来说,友谊和经历的分享可以取代身体吸引力或浪漫迷恋的需要。在某一点上,他甚至建议,在身体吸引力被抑制或消失的情况下,男性/女性的关系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女性可以很好地与男性建立友谊,但为了保持友谊,一点点身体上的反感肯定会对此有所帮助。”
最终尼采对婚姻的看法是,如果把浪漫的田园牧歌作为基础,婚姻是注定要失败的:“为爱而生的婚姻(所谓的爱情配对)包含父亲的错误和母亲的需要。”这句格言说明了尼采许多箴言中的内在矛盾和对立。在上面的婚姻例子中,尼采到底是在暗示那些为了爱而结婚的女人满足了一种渴望的需要,还是说她们进入了一种悲惨的境地?
(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给快节奏时代的简单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