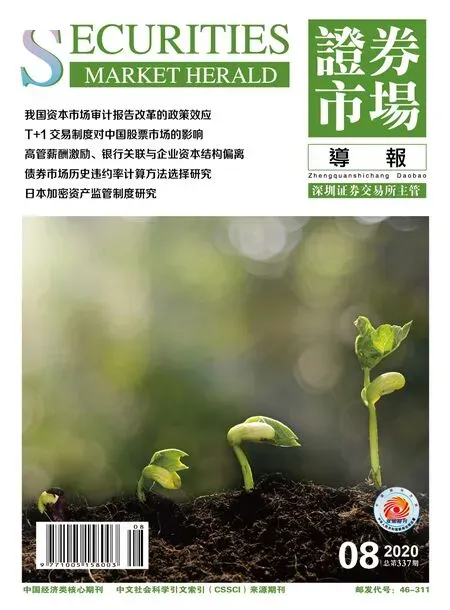日本加密资产监管制度研究
2020-11-25张伊丽皮六一薛中文
张伊丽 皮六一 薛中文
(1.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 200062;2.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一部,北京 100033;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 100033)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代币和分布式记账等新技术的发展,加密资产1交易在世界各国异军突起,已经逐步引起了各国监管层的关注,各监管辖区及相关国际组织也围绕加密资产交易进行了认真研究。22018年3月,20国集团(G20)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布公报认为,包括加密资产底层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有可能广泛提高金融体系和经济的效率和包容性3,加密资产对金融系统和整个宏观经济大有裨益。2019年6月在日本大阪召开的G20经济部长会议签署了《大阪数字经济宣言》,提出加快数字技术的发展,并使数字经济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金融制度一直给人留下过于保守的印象,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也远不及欧美金融市场,难以适应日本高度发达的经济增长需要。日本落后的金融制度严重束缚了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微观经济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近年来,加密资产交易的兴起助长了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行为,日本的监管机构收到了海量的投诉。为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同时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加密资产交易市场的健康运行,日本把加密资产交易市场作为一大突破口,致力于推进区块链技术在金融方面的应用,修订相关的金融法律制度,加强市场监管,以适应金融科技和新经济、金融业态的发展。42019年大阪会议后,日本即着手对《支付服务法》《金融工具交易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加强对加密资产交易商和相应业务的监管,在全球率先对加密资产交易进行法律规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监管框架,采取了针对性的监管举措。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全球加密资产交易较为发达的国家,加密资产监管制度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
二、日本加密资产监管制度的演变历程
加密资产的主要功能包括资金转移、交易结算、企业融资等。近年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资产作为支付手段或者投资工具受到一些投资者的追捧,重要原因之一是专门从事加密资产业务的中介服务机构逐步兴起,这些机构主要开展加密资产与法定货币之间的交易以及不同加密资产之间的兑换等业务,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消费者有机会接触到加密资产的相关交易。虽然加密资产最初被称为虚拟货币,但它并不是真正的货币,不属于货币的范畴,不是由中央银行或者其他的政府授权机构发行的,其内在价值没有国家信用作为保障,仅限于在认可该产品的投资者之间进行交易。加密资产的价格也主要受供需关系的影响,价格异动的风险较大。5因此,加密资产市场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而且,由于加密资产自身的特殊属性,加密资产交易中的各种投机性交易、洗钱、逃税、恐怖融资(AML/CFT)、遭遇黑客攻击等不良事件层出不穷,这也逐渐成为很多国家面临的法律监管难题。
2015年6月在德国召开的第41届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 Summit)提出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与加密资产交易相关的规章制度。近年来,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等也均开展了相关工作,防范由此引发的各类风险。拥有庞大的加密资产交易市场,同时又经常发生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破产倒闭事件的日本,为规范加密资产交易市场的发展,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等不法活动,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决定加大对加密资产买卖以及加密资产和法定货币交易平台的监管。2017年4月1日,日本颁布实施《支付服务法》,这是日本首次在法律上对加密资产交易商的经营行为和交易规则等相关事项进行规范,在全球来说也是首创。由此,日本不仅从法律上认可加密资产与法定货币之间的交易,允许不同的加密资产之间进行兑换,而且引入了加密资产交易平台(交易商)的注册登记制等相关制度。2017年4月,日本还颁布了《防止违法所得转移法》,旨在加大对加密资产交易商的监管力度。2018年1月,日本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Coin Check遭遇黑客攻击,价值580亿日元的加密资产被盗,这些被盗资金全部被存放在“热钱包”中。2018年9月,日本加密资产交易所Zaif的运营商Tech Bureau也被黑客攻击,“热钱包”中的比特币、Mona Coin等巨额资金被盗取,总价值约为70亿日元。日本多次发生的加密资产交易平台(商)遭遇黑客攻击的事件,导致大量客户的加密资产损失惨重。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利益,日本开始加大对加密资产交易商内部管理体制的监管,要求加密资产交易商(所)的股东与经营者分开,系统开发者和系统管理者分离,实行更加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多举措防止加密资产交易系统被恶意攻击。
2018年3月,日本设立了加密资产行业自律组织——加密资产交易商协会(Japan Virtual Currency Exchange Association,JVCEA),旨在加强加密资产交易商的自我管理,确保加密资产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2018年3月,日本金融厅还成立了“加密资产交易研究会”,成员主要由专家学者、加密资产交易商及金融实务部门的相关人员构成,针对与加密资产交易有关的保证金交易、权证交易、ICO(initial coin offering)等问题进行专门研究。2018年12月21日,该研究会公开发布了《加密资产交易研究报告》,主要总结和分析了日本加密资产监管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加密资产监管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62019年3月15日,日本金融厅提出了《为应对因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而出现的金融交易多样化部分修订支付服务法等相关法案的议案》(以下简称《修订案》),希望对《支付服务法》《金融工具交易法》和《金融工具销售法》等法案中的相关条例进行补充或修订,日本众议院于2019年5月31日通过该议案。2020年1月14日,日本金融厅公布了《令和元年关于修改支付服务法等相关法案的内阁府令》,该法令不仅包括《支付服务法》和《金融工具交易法》等相关内容的修订条款,还包含《加密资产交易商内阁府令》等,主要内容涉及加密资产交易商的注册资格、变更加密资产名称或更改加密资产交易类型的报备制度、加密资产管理业务7规则、加密资产信用交易规则、禁止虚假宣传和招揽客户、投资者保护等。
三、日本的加密资产监管框架
目前,日本是全球率先将加密资产业务纳入法律监管范畴的国家,从最初设立专门的监管法规《支付服务法》,到后来修订的《金融工具交易修正法》和《金融工具销售修正法》等法案的相关条款,以及针对金融机构特定金融交易的部分规定,从不同层面对加密资产的交易主体、业务类型、中介机构等都在法律上作出详尽规定,主要的监管机构包括日本金融厅、加密资产交易商协会(JVCEA)和国税局等。
(一)监管主体
日本对加密资产市场行使监管职责的主体机构包括两类,一是行政监管机构,例如日本金融厅、国税局等;二是自律监管组织,例如加密资产交易商协会(JVCEA)等。
1.行政监管机构
日本金融厅是日本最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其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应的金融监管法规,充分调动各类金融机构的市场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确保金融市场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提高金融效率,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方面,日本金融厅主要负责加密资产交易商的注册登记,制定或修改加密资产和ICO业务等方面的监管法规,加密资产的业务报告审核和相关法律条款的信息披露等;其明确规定信托银行和信托公司均不可以开展加密资产方面的信托业务,不得从事与加密资产相关的任何投资活动。日本国税局则负责制定加密资产方面的税收制度与执行细则。日本是全球首个在加密资产交易税收方面作出明确法律规定的国家,并将加密资产交易所得收益计入国税局的“其他收入”栏目中。
2.自律监管组织
日本《支付服务法》第87条将自律组织分为三类:预付类支付工具(prepaid payment instrument)发行方、资金划付方和加密资产交易兑换服务提供商,并统称为“支付服务提供商认证协会(Certified Association for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2018年,日本金融厅正式授予加密资产交易商协会自律监管的地位,该协会也是唯一被日本金融厅认定的加密资产交易兑换服务提供商行业的半官方行业自律组织。加密资产交易商协会的宗旨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加密资产交易行业的健康发展。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制定本行业的自律监管规则;明确相关业务的会计准则,对会员的经营活动进行相应的指导、劝告或处分;对申请加入的会员进行资格审查;处理加密资产交易纠纷事件;统计和公布加密资产交易情况;提供相应业务的洽谈或信息咨询服务等。其中,加密资产行业的自律监管规则主要涉及交易商或交易所的运营规则和内控体系、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消费者保护制度、系统性风险和网络安全;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制定加密资产交易新规;禁止虚假宣传和违规推销等。加密资产交易商协会的会员有三类:一是现存加密资产交易提供商;二是根据《支付服务法》的规定正在申请成为加密资产交易提供商的实体,三是其他类会员。截至2020年7月底,第一类会员有25家,第二类会员有8家。一类会员中,有3家位于大阪,1家位于横滨,其余的均在东京;二类会员则均位于东京。可见,从事加密资产交易的公司大多集中在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的东京。
(二)监管对象
日本不断扩大对加密资产的监管范围,监管对象的类型也日益增多,目前主要的监管对象包括加密资产交易商、加密资产投资基金公司和“云挖矿(cloud mining)”企业。
1.对加密资产交易商的监管
根据日本最新的《修订案》,加密资产交易商是指提供以下业务之一者:直接从事加密资产买卖或者不同加密资产之间的兑换;作为代理商或者中介机构帮助客户进行加密资产交易方面的相关业务;帮助客户管理加密资产或者为客户提供用于加密资产交易方面的资金管理。本次修订后,即使某机构不直接从事加密资产的买卖或者兑换,只是代理客户管理加密资产或者根据客户要求划付加密资产的,也将被视作加密资产交易商。
根据日本的《支付服务法》,加密资产交易商必须在日本金融厅和财政部注册后方可开展加密资产交易服务业务。申请注册国内加密资产交易业务的企业必须持有1千万日元以上的自有资本金,且净资产不能为负。从事加密资产交易业务的平台有义务向客户详细介绍交易规则和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说明加密资产的特性、交易金额、手续费、潜在风险等,并在金融厅网站公布其所从事的加密资产业务类型。如果加密资产交易商变更受理的加密资产的名称、种类、受理客户申请的方式或者管理办法等,须事先报备。禁止加密资产交易商哄抬价格、故意炒作或通过不当行为招揽客户。加密资产交易商进行广告宣传时必须公示所持牌照的信息,向客户说明加密资产的特性、强调加密资产不属于货币,还需说明加密资产的业务内容以及市场风险等,禁止进行虚假广告和夸大宣传。加密资产交易商不得通过电话劝诱投资者购买某类加密资产,不得通过座谈会、研讨会等方式强行推销加密资产,不得诱导客户进行“投机性投资”,不得使用诸如“该产品由金融厅推荐”“该产品一定会涨价”“本金肯定不会受损”等诱导性语言。在加密资产交易商与海外交易商业务情况发生变化,加密资产价格受大宗交易影响以及加密资产发行主体或交易商破产时,应就细节信息向投资者作充分的信息披露,并履行或有的追偿义务。
从事加密资产管理业务的交易商8应持有与代管的加密资产价值相等的本国货币。加密资产交易商应对自有资金和客户资金分开管理,客户的资金账户每年要接受一次以上的外部监督检查。加密资产交易商至少每三个月须向长期从事加密资产交易的客户进行一次信息通报,包括用户的交易记录、资产余额等,并请客户进行核对确认。针对日益频发的加密资产被盗事件,日本逐渐加大了对加密资产交易商的监管力度,要求95%以上的客户委托管理的加密资产应存放在未接入互联网的“冷钱包”中9,剩下的5%以下的加密资产存放在“热钱包”中,交易商自身的加密资产必须全部存放在“冷钱包”中,并规定加密资产交易商应拥有与“热钱包”中保管的加密资产币种相同、数量相等的偿还资本金。与此同时,日本进一步提高了加密资产交易商的准入门槛及申请牌照和注册审查的透明度,严格执行业务报告制度。
2.对加密资产投资基金公司的监管
加密资产投资基金以加密资产为投资对象,所得收益由基金公司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给投资者。该基金除了投资对象比较特殊以外,投资框架与一般的投资基金基本一致,因而该投资基金可以参照日本《金融工具交易法》的相关规定确定投资者权益。投资基金公司必须注册并取得“二类金融工具交易”从业者的牌照。而且,由于该基金的投资对象为加密资产,存在一定的特殊风险,如可能遭遇黑客攻击、硬分叉(hard fork)10风险等,故投资者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充分了解该类基金的投资风格和风险特性,相关监管制度也应在这方面作出相应规定。另外,日本的对加密资产指数基金的投资也被列入《金融工具交易法》的监管范畴。
3.对“云挖矿”企业的监管
一般来说,加密资产在进行交易之前,必须在区块链上进行相应的验证,这种验证交易的过程被称为“挖矿”。挖矿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等资源,成本比较昂贵,很难单独执行。为克服这类缺陷,市场上产生了“云挖矿”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租赁托管服务,通过网络远程使用别人的矿机挖矿,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挖矿方式。“云挖矿”由专门的服务商提供矿机、网络、运行维护等,用户只需要支付一定的租赁和托管服务费用,就可以进行挖矿,并由此获得相应的报酬。近年来,日本有意愿参与“云挖矿”的企业越来越多,模式趋于多样,日本正在考虑将“云挖矿”企业也纳入《金融工具交易法》的监管范畴。
四、日本对加密资产业务的监管举措
加密资产交易业务不仅包括交易商自身参与的加密资产交易,还包括交易商代理客户进行的买卖、兑换或者资产业务管理。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发展和加密资产交易环境的日益变化,加密资产的业务类型逐渐增多,为应对市场变化可能引发的新问题,日本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加密资产交易方面的监管制度。2019年5月31日,日本国会通过的《修订案》主要涉及《支付服务法》《金融工具交易法》《金融商品销售法》《加密资产交易商内阁府令》等。
(一)加密资产现货交易的监管措施
加密资产的现货交易既包括对加密资产的买卖,也包括不同加密资产之间的兑换,该类交易应遵照《支付服务法》的相关条款进行监管。为维护此类交易市场的安全稳定发展,日本金融厅要求现货交易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确保交易价格的公开、透明。相关机构不得夸大宣传或者通过不当手段进行交易,不得通过虚假交易或者散布不实信息等方式操纵市场价格,严厉打击各种不公平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加密资产交易商应按照要求提交相关业务的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由日本金融厅定期对加密资产交易商进行项目审查,禁止交易商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
(二)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的监管措施
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包括与加密资产有关的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和保证金交易等,此类交易均按照《金融工具交易法》的相关条例进行监管。加密资产的衍生品交易首先应遵照一般的衍生品交易规则,比如加密资产交易商须满足最低资本金、分账管理、杠杆率、止损点设置、禁止虚假广告和不当推销等条件要求。按照日本《金融工具交易法》的规定,日本提供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机构应满足以下条件:净资产不少于5000万日元,资本充足率应达120%以上,每个月末须上报资本充足率情况,或者月中资本充足率低于140%时也须及时上报相关情况。如果该类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低于120%,将会被勒令整改相关业务;如果资本充足率低于100%,将会被禁止从事该类业务,并被撤销相关资质。此外,考虑到加密资产的特殊性,交易商应适当提高客户参与门槛,例如规定交易账户的最低保证金、投资者的知识背景和收入水平等资格条件。
加密资产保证金交易是日本目前最主要的一类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品种。当前日本对加密资产保证金交易的监管主要参照外汇保证金交易的相关做法执行,严格禁止加密资产交易商的任何不当推销行为。另外,由于加密资产的价格波动远远大于法定货币,保证金交易的杠杆率不宜过高。目前有的日本加密资产交易商将最大杠杆倍数设置为25倍,但2018年10月24日加密资产交易商协会公布实施的自律监管规则规定,加密资产保证金交易的最大杠杆倍数原则上不能超过4倍,而且为进一步降低该类业务的投资风险,日本金融厅计划再度收紧加密资产保证金交易的杠杆率,拟将保证金交易的杠杆倍数限制在两倍以内。11
2020年1月,日本还推出了数字资产指数——“NRI/IU加密资产指数”12。为更好地规范加密资产交易市场,日本要求加密资产交易商应向客户详细说明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的特点,将加密资产和加密资产衍生品的风险权重设定为100%,针对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的不法行为制定了相应的监管规则。
(三)加密资产信用交易的监管措施
部分日本加密资产交易商还向客户提供加密资产信用交易13。由于日本现在还没有制定专门针对加密资产信用交易的监管法规,所以目前对于该类业务的监管是参照《支付服务法》《加密资产交易商内阁府令》的相关条例执行。根据相关规定,如果客户之间进行加密资产信用交易,加密资产交易商应以书面形式报备以下内容:加密资产信用交易的初始保证金金额及其计算方法;加密资产信用交易的类型;止损规则;投资亏损额可能大于保证金数额的原因;如果以代币缴纳保证金,当代币的市场价格下跌时,需补充缴纳的保证金数额;当触发止损点完成交易时,因信用交易产生的债务规模及还款期限、结算方式等。根据《加密资产交易商内阁府令》的规定,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参与加密资产信用交易的杠杆率都不能超过200%。另外,加密资产交易商应根据加密资产的价格波动和流动性等设置止损点,准确掌握客户账户的仓位情况,以便及时进行“止损”交易,并定期或者在必要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实际的“止损”交易情况。14
鉴于加密资产信用交易是由客户向加密资产交易商支付一定数额的法定货币或加密资产作为保证金,在加密资产交易过程中应付资金不足时,可先从加密资产交易商借入部分加密资产进行交易,因此,加密资产信用交易和保证金交易具有相同的投资特性,市场风险相近。所以,今后日本可以对这两类加密资产交易采取相同的监管措施。
(四)ICO业务的监管措施
ICO是指发行主体首次以发行代币15的方式募集资 金16。日本现在还没有专门针对ICO业务的监管法规,但相关部门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以期弥补监管制度的漏洞。本次修订前,日本主要依据《金融工具交易法》和《支付服务法》的相关法规对投资类ICO业务进行监管。本次修订后,日本则结合ICO业务的投资风格和风险特性,将ICO等同于可获取收益分配的投资,规定对ICO发行主体应采取与加密资产交易商同样的监管措施,列入《支付服务法》的监管范围,并明确将投资类ICO代币按照证券投资业务进行监管,具体监管措施参照《金融工具交易法》执行。
在日本,由于以ICO方式发行的代币等同于加密资产,所以日本在考虑今后代币的发行主体是否应该申请加密资产交易商的牌照,还是委托已取得牌照的加密资产交易商在相应的加密资产交易所内进行发行销售。加密资产交易商应向客户充分披露发行主体的资产状况、持有的加密资产类型及其规模、发行价格等相关信息,而且还需向客户充分说明发行主体通过ICO方式进行融资的发展规划,详尽介绍发行项目计划书以及项目的可行性,对于发行主体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如果ICO代币采用的是预付手段,代币发行就应该遵照《支付服务法》的相关要求;如果ICO通过证券化方式进行融资,即以证券型代币发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STO)的方式融资,则代币发行就应该被列入《金融工具交易法》的监管范畴,发行主体应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并规范发行主体的广告和销售行为,同时结合投资者的能力和投资经验等设定不同门槛的投资项目17。
五、日本加密资产监管的特点及问题
伴随日本加密资产监管体系的不断成熟与完善,目前日本已是全球加密资产交易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截至2019年12月底,日本已注册的加密资产交易商共有19家,另有7家机构正在申请或者计划申请注册成为加密资产交易商。根据日本加密资产交易商协会的相关数据,2019年12月,在日本与加密资产交易相关的开户总数已达321万,其中活跃账户约为201万,而且,加密资产保证金交易账户高达235万18,即保证金交易占日本加密资产交易总量的80%左右。另外,该数据显示,日本各类加密资产的现货交易额已达2794.96亿日元19,加密资产的保证金交易额更是高达3.83万亿日元20,保证金交易的总建仓数21达1.32亿个,有近一半的加密资产交易商提供加密资产保证金交易22。由此可见,日本已经拥有非常庞大的加密资产交易市场。2020年初,日本新经济联盟向日本政府提交《面向区块链国家战略的建议》,日本将打造世界领先的加密资产市场,不断创造新价值和新服务。日本监管机构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日本加密资产监管的特点
1.日本对加密资产进行分类监管、专门规制
加密资产性质的划分在全球范围饱受争议,有的监管辖区将加密资产认定为货币,有的则认定为商品或证券等。23加密资产性质边界的模糊直接导致上位监管法律不清晰,从而出现一定的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问题。在本次法律修订前,日本也没有明确的专门针对ICO和STO业务的监管法律,导致发行规模不断下降,相关的诉讼案件也不断增多。本次的法律修订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项空白。一方面,本次修订对加密资产进行分类监管,将加密资产分为“证券类”和“支付类”,分别受到《金融工具交易法》和《支付服务法》的监管,对加密资产的性质和上位法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法律监管权限的明确有利于形成清晰的监管框架,给市场参与者形成明确的市场预期,稽查执法也将更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对特定加密资产类别进行了专门规制。《金融工具交易法》的监管范围新增了一种新的资产类别——“电子化记录可转让权益”(electronically recorded transferrable rights,以下简称ERTRs),通常所说的在区块链上进行转让的证券类加密资产就属于此类别,《支付服务法案》也相应地从其监管的加密资产的范围里排除了“电子化记录可转让权益”,并明确“效用类加密资产”(utility token)仍然归《支付服务法案》监管。
2.日本加密资产监管形成完整且体系化的框架
总体来看,在本次法律修订后,日本基于现有的较为完备的法律框架,对加密资产作出了有针对性、完整的条款规定,而非零散的法律条文,使得加密资产监管的合法性得以落地,同时将关口前移,赋予个别自律监管组织一定权限,基本形成了“行政牌照+法定信息披露+行业自律”的全套监管模式。例如,在持牌经营方面,根据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从事“电子化记录可转让权益”交易或公开发行业务的机构需要注册为“一类金融工具业务运营商”(Type I financial instruments business operator)。在信息披露方面,规定“电子化记录可转让权益”转让需填写证券登记说明(securities registration statement)等文件,之后每一财年还需披露年度和半年度报告。在行业自律方面,修订后的《支付服务法案》规定,相关交易所申请注册时若不属于支付服务提供商认证协会会员,则需要有对标该协会自律规则的内控规定。日本加密资产监管有充足的立法供给,辅以行业自律安排,有利于加密资产行业的良性健康 发展。
3.日本加密资产监管设置了具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安排
创新和风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加密资产市场对金融、法律、治理带来正向作用,日益替代了传统投资。加密资产的发行去掉了金融中介,降低了交易费用,发行者可以为长期项目融资,也可以在项目初创阶段融资。加密资产种类的多样化给认购者和创始人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选择。24另一方面,加密资产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具有独特的技术特点,增加了认购风险,因此,在发挥加密资产市场优势的同时,日本也针对加密资产的重要风险点进行规范。具体内容如下:一是识别并从严应对运营商风险。本次《支付服务法案》修订后,加密资产的存管服务被认为与交易服务25具有类似的风险,将受到同等监管。此外,还需评估运营商初始、持续的运营能力等。二是前置必要的加密资产交易准入和市场参与人行为准则。本次《支付服务法案》修订后规定,在加密资产的名称、交易服务条目及服务的提供方式发生变化时,需要向金融厅进行事前报备。加密资产风险各不相同,不同的资产须披露的信息程度各异,平台应当做好交易信息的披露工作。此外,平台应该设置资产交易标准,该标准旨在防止欺诈和市场操纵行为,监管部门应对标准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三是设置安全有效的清算、交收、托管安排,促进市场公平、公正。从实践来看,虽然加密资产交易平台与传统交易场所相似,但由于加密资产交易平台持有投资者的资产,所以托管和结算安排也有所不同。本次《支付服务法案》特别规定:加密资产交易商应拥有与“热钱包”中保管的客户资产对等的偿还资本金,以确保客户的资产安全。此外,随着加密资产市场的发展,专业的第三方托管和专门针对“稳定币”储备的第三方审计也应运而生,日本在本次修订中均有涉及。
(二)日本加密资产监管的问题
第一,在信息披露内容上,加密资产的监管还需兼顾传统风险和加密资产特有风险,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日本本次法律修订明确规定,《支付服务法案》适用于支付型加密资产,《金融商品交易法》适用于证券型加密资产。将新兴的加密资产纳入既有的法律框架有利于对加密资产实行针对性的监管,但还应当看到传统的监管框架下存在对加密资产监管内容的某些缺失。例如,现有的证券“发售说明书”的披露要求中,需要对发行人的董监高情况进行披露,但是此举是否适合ICO仍然存疑,因为ICO项目背后的公司高管对项目发展的重要性未必很大,反而开发加密资产网络的技术专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股权类加密资产持有者未必与传统法律中的“股东”具有类似的法律地位,在传统企业里大股东享有企业剩余权利,对管理层具有任免权,但加密资产持有者未必享有类似的权利。因此,对于加密资产的投资者来说,需要有区别于传统金融工具的特殊的法律条款来保护其应有的合法权益。再如,传统的加密资产交易所均是中心化平台,采用连续竞价机制,有订单簿、订单匹配机制和各种订单类别等,投资者通过金融中介接入平台。虽然现在已有一些加密资产运营商采用了类似的运营模式,即平台负责资产的存管,掌握用户电子钱包的私钥,控制平台所有的交易,但是也存在部分去中心化的平台,通过开源的区块链技术运行,用户可以直接接入,交易直接发生在用户之间,平台不掌握用户电子钱包私钥,也无法干预交易,订单通过所有者授权执行的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匹配执行。这些交易所有着新的风险特点,应当在未来的监管中更加关注,予以明确。
第二,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是加密资产监管中的重要部分,应当探索关于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的更为全面的监管措施。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占2017年日本加密资产交易服务提供商交易的80%,远高于加密资产的现货交易。但在本次法律修订前,日本对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监管处于真空状态,市场操纵、欺诈等案件频发,金融厅收到了海量的客户投诉;本次《金融商品交易法》修订将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纳入监管,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但应该看到的是,加密资产衍生品交易仍然存在一定的盲区,比如由于加密资产独特的技术特点,很难清晰界定加密资产发行人和未公开披露的信息,所以相关立法中也没有涵盖内幕交易的规定。这些还有待于相关的监管科技发展来提供进一步的解决路径。
第三,加密资产监管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必要的国际合作,贯彻相对一致的国际标准和理念,预防监管套利活动。加密资产与其他传统金融工具最大的不同是其交易的全球性特点,监管者很难去识别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的精确地理位置和交易活动的发生位置。加密资产交易平台可以给包括那些明令禁止相关活动的监管辖区在内的任何辖区的参与者提供服务,且参与者接入受另一个监管辖区监管的交易平台时,将会存在更高风险。在不同辖区之间,还可能存在监管套利风险。一种在一个辖区内被认为是证券的加密资产,在另一个辖区内可能完全不受监管,投资者可能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框架和不同水平的争议追索权益,监管或执法活动可能因交易的跨境特征而面临挑战。目前,除日本外,在马耳他(Malta)、韩国、塞舌尔共和国(Seychelles)、伯利兹(Belize)等地注册的交易所的交易也极其活跃,而我国大陆、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地则明令禁止加密资产的相关交易。为吸引国际市场上的投机者入驻,个别国家间已展开了激烈的监管竞争,或导致“监管逐劣”(regulation to the worst)现象。加密资产的发行人、运营方、投资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规避日本现行监管要求。因此,与传统的金融工具监管不同,由于加密资产是跨资产、跨市场、跨国界的,因此监管重点还应更加关注跨境执法、监管合作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高效和透明的市场环境,防范系统性 风险。26
六、日本加密资产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2017年底,全球通过ICO方式筹措的资金规模已达55亿美元;2018年1月至10月,此类融资规模约为167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通过ICO方式不仅可以实现跨境融资,而且融资成本较低,有利于中小企业快速便捷低成本融资。加密资产的跨境属性给我国监管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有必要吸收借鉴境外经验应用于我国的监管实践 之中。
(一)跟踪国际市场动向,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面对加密资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国际标准制定组织也采取了诸多措施以防范风险,促进金融经济体系的稳定。2018年和2019年两届G20峰会的公报中,G20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表示,加密资产“引发了有关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市场诚信、逃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问题”。各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也根据机构宗旨监测加密资产及其风险。27目前,金融稳定委员会联合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已经在构建加密资产市场的金融稳定性标准体系;后者已经开展了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研究,且已在支付创新分析方面有了一定成果。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正在量化银行直接和间接的加密资产风险敞口,将对这些敞口实施审慎应对措施,监测加密资产,开展针对银行的金融科技监管。国际证监会组织二级市场监管委员会(Committee 2 on the Regulation of Secondary Markets)于2018年初开始审查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相关问题,并发布了政策研究报告。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发展加密资产是大势所趋。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重要产业转折点,我国需要把握和积极引领时代发展方向,按照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部署,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为中国加密资产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壮大数字经济。
(二)加强国际监管交流与合作,保护我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加密资产突破了特定的国界线,对监管执法提出了新挑战。在某些跨境交易执法实践中,监管机构需要从国外的经纪商或交易平台获取投资者身份信息,在涉案双方所在管辖区未签订谅解合作备忘录的情况下,获取信息存在很大障碍。因此,为防止监管套利、识别并处理潜在的市场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应促进信息分享,建立必要的跨境监管合作机制:一是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协调会议、签订多边和双边的监管合作备忘录,就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监管的临时性、重大监管协调等事宜达成一致。此外,还可通过定期召开高层级别或员工层面的协调会议、组织监管合作论坛等形式,促进非强制性的监管协同、监管哲学及观点共享。二是建立双边或多边强制安排,即建立对双边或多边均具备法律强制约束的监管合作安排,就加密资产交易的跨境监管常态化机制条款、是否存在可替代性的合规流程安排作出规定。28
注释
1. 加密资产即虚拟货币。2017年4月1日,日本颁布的《支付服务法》中使用的名称是“虚拟货币(仮想通貨)”,这是因为在日本制定《支付服务法》时,FATF(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律中对该产品的称谓均为“virtual currency”,即虚拟货币,但在2018年以后,在很多的国际场合中都将“virtual currency”改称为“crypto-asset”,即加密资产(暗号資産),由此,日本也相应地将交易商名称由原来的“虚拟货币交易商(仮想通貨交換業者)”改为“加密资产交易商(暗号資産交換業者)”。为避免名称上的混乱,本文将相关概念统一为“加密资产”和“加密资产交易商”。
2. 参见皮六一, 薛中文. 加密资产交易监管安排及国际实践[J]. 证券市场导报, 2019, (7): 4-12.
3. 参见米晓文. 全球数字加密货币反洗钱监管:经验与趋势[J].华北金融, 2018, (11): 62-67.
4. 参见証券取引における分散台帳技術の利用を巡る法律問題研究会. 証券決済制度と分散台帳技術[J]. 金融研究, 2018, (7).
5. 参见曾繁荣. 加密资产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分析[J]. 国际金融, 2019, (1): 70-75.
6. 参见宇根正志. 暗号資産における取引の追跡困難性と匿名性:研究動向と課題[J]. 金融研究, 2019, (7).
7.机构不进行加密资产的买卖,只是帮助客户保管加密资产,或者按照客户的要求将加密资产转移至指定的账户。
8. 即该交易商并不从事加密资产的买卖,只是帮助客户保管加密资产或者按照客户的要求将加密资产转移至指定账户。
9. 加密资产的私钥储存方式可以分为“冷钱包”和“热钱包”。“冷钱包”不接入网络,所以可以避免黑客盗取钱包私钥的风险,比“热钱包”更加安全。“热钱包”可以被网络访问,在联网状态下能够被随时用来交易,便于交易商进行快捷交易。
10. “硬分叉”是因为“共识”协议不同,旧节点不接受新区块,从而导致产生新旧两条链。具体来说,当加密区块的交易方式发生改变时,没有进行升级的节点会拒绝对已经升级的节点生产出的区块进行验证,双方各自沿着自己的链向前走,然后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链。
11. EUNEX欧联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设置的加密资产保证金交易的最大杠杆倍数均为两倍。
12. 该指数主要追踪比特币、比特币现金、以太坊、莱特币和XRP五种加密资产的价格。
13. 是指加密资产交易商通过加密资产交易向客户提供资金或者加密资产方面的贷款信用。
14. 参见河合健, 三宅章仁, 青木俊介, 田中智之等.「暗号資産·デジタル証券等に関する政府令案について」[J/OL]. [2020-02-03]. www.amt-law.com, アンダーソン·毛利·友常法律事務所.
15. 代币(token)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可以用来替代货币的一种凭证,也可以视为通过区块链技术发行和流通的加密股权(crypto equity),融资资金主要是比特币、以太币等。
16. 投资者可以使用指定的虚拟货币(比特币、以太币等)购买代币。
17.日本的《金融工具交易法修正案》中的“电子记录转移权”对此做了相关规定。
18. 其中的活跃账户为58万。
19. 各类加密资产的现货交易总量超过14亿个货币单位。
20. 各类加密资产的保证金交易总量超过8亿个货币单位。
21. 包括买进和卖出。
22. 即杠杆交易,是指投资者只要缴纳一部分的保证金就可以买到相应倍数的加密资产,可以做到以小博大,将资金的利用效率最大化。但是,该类投资既可能实现收益倍增,也可能放大亏损倍数。
23. 参见柯达. 加密资产分类监管研究——以英国、瑞士、新加坡三国为例[J]. 证券法律评论, 2019: 323-336.
24. 参见傅晓骏, 王瑞. 加密资产概念、现状及各国(地区)监管实践[J]. 金融会计, 2018, (5): 45-53.
25. 修订前《支付服务法案》规定,以下情形视为提供了加密资产交易服务:管理客户的交易资金或用于“币-币”交易的加密资产;为上述交易行为提供代理经纪和中介服务。因此,加密资产存管服务(指仅仅托管客户的加密资产且将该加密资产划转至客户指定地址的行为)由于不涉及上述行为,并不构成加密资产交易服务。
26. See Board of IOSCO. Issues, risks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relating to crypto-asset trading platforms[R]. Madrid: IOSCO, 2020.
27. 参见陈歆. 加密资产的监管方法及未来方向[J]. 金融发展研究, 2019, (9): 67-70.
28. 同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