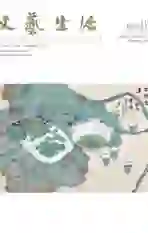《辽史?乐志》中的“四旦”之争论
2020-11-23李可童
摘要:关于唐俗二十八调是七宫四调还是四宫七调的争论已持续已久,这就归于人们对《辽史·音乐志》中的“四旦”的理解。这一理解一直以来都颇受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旦”就是“声”或“调”,因而“四旦”则是“四调”;有的学者则认为“旦”是调的集合,因而“四旦”则是何昌林的四纵均,更不能推出唐俗乐二十八调是七宫四调或是七调四宫。每种说法都各有千秋,因而,本文将仔细阅读这几篇文章,以求更好地理解这一理论。
关键词:《辽史·乐志》;“四旦”;争论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6-0004-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6.003
关于唐俗二十八调是七宫四调还是四宫七调的争论已持续已久,这就归于人们对《辽史·音乐志》中的“四旦”的理解。这一理解一直以来都颇受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旦”就是“声”或“调”,因而“四旦”则是“四调”;有的学者则认为“旦”是调的集合,因而“四旦”则是何昌林的四纵均,更不能推出唐俗乐二十八调是七宫四调或是七调四宫。每种说法都各有千秋,因而,本文将这几篇文章进行仔细阅读,以求更好地理解这一理论。
我们先来看《辽史·乐志》的原文:“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求合七声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大乐调雅乐有七音,大乐亦有七声,谓之七旦。一曰婆力,平声;二曰鸡识,长声;三曰沙识,质直声;四曰沙侯加滥声,五曰沙腊,皆应声;六曰般赡,五声;七曰俟利,斛先声。自隋以来,乐府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为大乐。”
从中可发现,《辽史》中的旦虽无明确的意思,但在第二段文字中笔者有将“声”称为“旦”的意思,那么这个理解又是否正确呢?因而,许多学者会将这其中的“旦”与《隋书·音乐志》中的“旦”的概念来相比较。“旦”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隋书·音乐志》中郑译转述他向苏祗婆学习的过程的一段话。那么,“旦”在《隋书·音乐志》中是怎么样的呢?《隋书》上对于旦是这么说的,“旦者则谓均也,其声亦应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所以,《隋书》中的“旦”是理解为“均”,那这和《辽史·音乐志》中的“旦”是否是一样的意思呢?这几位学者就对此产生了不一致的看法。
首先,刘勇在他的文章《《辽史·乐志》中的“四旦”是四宫吗?》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辽史》中的此“旦”非《隋书》中的彼“旦”,这理由是建立在他对文献有错误理解的背景基础上的。他认为编撰者对于音乐知识有着不足的认识,将苏祗婆的七声(七调)当成了七旦。而且加上《辽史》中除了音乐知识的欠缺、还有材料的轻率处理和妄改的做法都足以提醒我们《辽史》中的这些错误不容忽视,尤其是发生在问题关键所在的时候。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辽史·乐志》中的“四旦”是为四声(四调)之误,四旦二十八调应为七宫四调。
而孙新财先生却在他的文章《《辽史·乐志》中的“四旦”不是四宫吗?》中就“刘文”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反驳的观点有以下几点:
1.从形式错误来看,中国的宫调体系既有均/宫/调三层次,则二十八调之七律调×四声调应有六种可能,而刘勇只排除了其中两种可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二十八调是属于七宫四调这一可能。
2.从辩证逻辑来看,由现存古谱既已能得证知:“无论二十八调中之七律调或四声调,都与主音(调式)无关”,则无论四调(式)说或七调(式)说,就因都与事实真相不合之故,因而“刘文”在做出“二十八调是七种调高,四种调式”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3.就文献背景来看,孙先生认为“刘文”所说《辽史》“多误”这点是多余的。因为依形式逻辑上来论,只要既非“全误”,则应无任何“必误”、“亦误”的论证力,不能据此而论,有关其四旦之载也是错误的。
4.“孙文”认为“刘文”所说的“旦”谓之“均”用现代的话来理解成音阶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所熟知的“同均三宫”理解为一均可有三宫,也就有三个音阶。若旦相当于均,则旦就也有三个音阶!则均(及旦)就不可能是一个音阶。因而,基于以上几种理由,孙先生认为“旦”是一个多义字,而“旦”作为“调”的集合只是其中一个含义,故由此得出《辽史》中的“旦”与《隋书》中的“旦”是同一个概念,《辽史》中四旦就是何昌林的四纵均(七律调是七横均),都有“旦作七调”的原始定义。
颇为有趣的是,在比较了“刘文”和“孙文”两篇文章后,杨善武教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辽史·乐志》中的“四旦”不是四宫,肯定了刘勇的观点。对此,他针对“孙文”中反駁刘勇的观点为“刘文”进行了申辩,他认为对理论的探究是在文献理解的框架中的,因而文献错误的注释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
所以说,刘文的文献有错误的背景绝不是多余的,而是要足够引起我们重视的。不止如此,杨先生也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其一,他认为《辽史》与《隋书》对于旦、调概念的使用是相反的,而《辽史》所载二十八调则与《新唐书》一致。虽然《辽史》没有象《隋书》那样直接道出四旦是什么,但并不是说《辽史》中就没有这方面的表述。就看《辽史》中的四旦二十八调,从纵向来看,开始的“婆陇力”、“鸡识”、“沙识”、“般赡”,实际上是对七宫、七商、七角、七羽四个调类的一种归纳;从横向来看,每行七调,就是新唐书所说的七宫、七商、七羽、七角。其二,落实到具体的史料记载中,无论是《隋书》还是《辽史》,其中都只有两种层次,其均与宫是合一的,因而二十八调的组成就只有两种可能。因而,他认为“孙文”所说的六种可能是脱离了史料的实际情况的。其三,杨教授认为“孙文用“同均三宫”来解释是有偏差的,没有看到其真正的乐调本质。因而,在总结与比较分析前面两篇文章后,作者认为仅就《辽史·乐志》而言,依据史料来判断,即使“四旦”与调式无关,但也不会是四宫。
纵观这三篇文章,笔者发现深究到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学者们对于“同宫三均”的理解差异,因而导致了他们对《辽史》中的“旦”以及对《隋书》中的“均”理解不一致。“同均三宫”是由黄翔鹏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一种理论,指的是中國乐学的基本理论中,均、宫、调是三层概念。均是统帅宫的,三宫就是同属一均的三种音阶,而分属三种调高。而“均”则是这七个律高所构成的绝对音高位置与各律间相对的音程关系的总和。这一理论面世后,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但对其所持的态度却各有不同。笔者觉得这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蒲亨建的观点,他虽没有直接对同均三宫提出异议,但是否认三种音阶的存在,认为正声音阶和清商音阶应该是下徵音阶的上、下五度转调。这样就与同均三宫格格不入了。他的观点建立在童忠良的理解基础之上,即认为唯三宫可“保持完整的五正声”,因而他认为“均”或“调域”如果只定义为一种“律学规范”将其限定为“律学规范”,就会显得过于偏狭,而应当是更为规范的“乐学规范”。而回归到前文所提到的三个学者“,孙文”无疑对“同均三宫”是持赞同的观点的。他在文中提到,其次一均可有三宫,也就有三个音阶。若旦相当于均,则旦就也有三个音阶,则均(及旦))怎会是一个音阶呢?由此可见,他是认为“旦”是“调”的集合,“均”是“律”的集合,所以“孙文”是将“均”放在“律学规范”的角度去看待的。而“刘文”和“杨文”则相对保守很多“,刘文”认为用现代术语解释,均就是一个音阶,五旦即指这个音阶在五种调高上出现。“杨文”则认为均在实际中的存在又是具体的,我们所见到的均都是以一定高度的某律为宫的音阶所表现出来的。可见,二人都承认它有合理性,但确实有着很多的不解之处,因而就不会将“同均三宫”的理论列入考虑范围。
总的来说,目前对于《辽史·乐志》中的“四旦”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但这些不同的见解可以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古代乐调的本质,以取得一种更为准确的乐调认识。相信通过进一步讨论,情况会有所改观,何为“均、何为“旦”?“何为唐俗乐二十八调”?这些答案必将更加明晰。
参考文献:
[1]蒲亨建,“同均三宫”再辩[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1(03).
[2]孙新财,《辽史·乐志》中的“四旦”不是四宫吗?[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02).
[3]刘勇,《辽史·乐志》中的“四旦”是四宫吗?[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08).
[4]杨善武,《辽史·乐志》中的“四旦”不是四宫[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11)。
[5]刘勇,何为“同均三宫”——“同均三宫”研究综述[J],音乐研究,2000(09).
作者简介:李可童(1996-),女,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