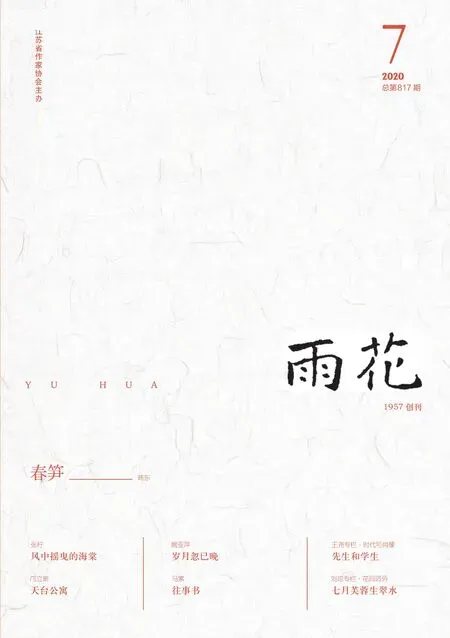七月芙蓉生翠水
2020-11-22
诵读古诗词,不能完全依据现代汉语,否则会发现韵辙平仄有时不是那么规范。同样,随着时易物替,解读古诗词也不能完全照搬字面意思。
最典型的是月份。古人的月份是按农历甚至夏历推算。比如《诗经·豳风》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说的其实是初秋和初冬的事。按夏历也即阴历推算,七月已至夏末,几近初秋,这样的夜晚,天蝎星西沉,天气转凉,所以被记录为“七月流火”,而不是后人误读的“七月热得冒火星”。九月已是初冬,让妇女们着手准备寒衣,故曰“九月授衣”。古人厉害,在没有现代工具和技术辅助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肉眼和体感,对天象岁时进行观察,形成记录。这是人类祖先的宇宙意识。江河奔流,物竞天择,藉由这些生动、可感、经验性的历朝历代的文字记录,历史的“自然性”有据可考了。
就说七月。阴历七月,娇艳欲滴的荷花早已盛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蓉”。“出水芙蓉”由此而来,并逐渐演化为对于女性清奇曼妙的赞美。看过三部以《出水芙蓉》为名的电影,两部是美国米高梅影业公司出品,一部是香港导演刘镇伟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米高梅影业公司1944年首映的那部喜剧,一个叫史蒂夫的流行音乐作曲家爱上了美丽的游泳课老师卡罗琳,闯进女子学院后各种歌曲、舞蹈、花样游泳以及男主花样百出的被虐情节,让整个电影院洋溢着快乐。翻译非常出色,电影看完了,“女人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你是最美的,世界上每个人都爱你”,这句经典台词陪伴了许多女性许多年,包括我。片名译得也好,是涵养了传统文化的意译。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的这句诗,用芙蓉的纯净天然形容文章写得自然质朴。“清如水”“清水出芙蓉”这类诗句,符合古典审美标准,也可以用来描绘女性的天生丽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到南宋无名氏撰写的宋传奇《李师师外传》《李师师外传》里,宋徽宗听闻李师师艳名后的第二天傍晚,就带着重金宝物,到镇安坊“驾幸”李师师。小说用的是欲扬先抑的对比法。老鸨先是送上果食,后又送上各种肉食,还要求这个重金恩主依例沐浴更衣。时间在延宕,恩主的心情更加急迫。“为徒倚几榻间又良久,见姥拥一姬姗姗而来,不施脂粉,衣绢素,无艳服。新浴方罢,娇艳如出水芙蓉。”李师师出场这段描写的最大特点是不正面写李师师如何“色绝”,只写其如何清婉、如何有个性、如何不慕钱财,最后写到如何“艺高”,“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轻拢漫然,流韵淡远”。李师师何许人也?北宋末年汴京名妓,相传与宋徽宗赵佶、著名词人周邦彦都传出绯闻。北宋开市后,教坊文化发达,又碰到风流倜傥的帝王一力提倡,自是产生了许多善才名曲。帝王以宋徽宗为最,与教坊青楼的关系非比寻常,留下了许多可猜想的绯闻空间。宋徽宗和李师师的关系,北宋末年已经或明或隐见诸某些文字。有意思的是,贵为帝王的徽宗似乎也不以为忤。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人情趣”。传八卦是世风,敢传当朝帝王的八卦,恐怕不是无风起浪。靖康之变后,徽宗、钦宗二帝被囚五国城,李师师也从公众视野里消失。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南宋初年,诗人刘子翚在《汴京纪事》的最后一首里写到李师师的一种“下落”。借李师师湖湘沦落,诗人抒发的是自己的故国之哀和古国之思。
美人迟暮本就令人伤感,何况“一曲当时动帝王”的李师师沦落至此,常人不免唏嘘。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李师师的忧伤,即便是在恩宠顶峰时期,也被《洛阳春》记录在案:“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倚栏愁,但问取亭前柳。”《洛阳春》的作者是周邦彦。周邦彦相传是李师师的另一个恩主。“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传说是这样甚嚣尘上,以至于连周才子未识李美人之前所写的这首广为流传的《少年游》,不仅被后世好事者传为因李师师而作,甚至还编出徽宗吃醋的桥段。书生人情一纸间,与美人好,得美人垂青,吟诗、作词、抚琴、唱曲,都是风雅留情之举。而李师师正当怀春之年,不重皇家重诗家,似乎顺理成章。一个是大内才子,一个是倾国佳人,人们愿意如此为他们编造故事。但这个顺理成章,顺的是老百姓自己的理儿,成的也不是一代名妓的故事。欢场总归是欢场,帝王也好,才子也好,喜欢归喜欢,娶不娶回家,能不能白头偕老,是另一说。青楼出身,即便“芙蓉如面柳如眉”,最后也是“零落成泥碾作尘”。或“缕衣檀板无颜色”,或“老大嫁作商人妇”,或“怒沉百宝箱”,岂止李师师,王师师,张师师,众多的师师,不都是如此不甘心地收了终场吗?
四十多年前,母亲开始恢复与娘家交往后的第一个春节,记得旧金山的舅舅那时还在国内,第一次来我们家,逛新华书店时抱回来一整套简体版的“三言二拍”。这套书,后来某种程度上成为我的文学启蒙。“三言二拍”都有涉爱涉性书写,严格来说,并不适合幼小学生阅读。记得是某个暑假,我躲在蚊帐里,几乎一气儿把两个“拍案惊奇”看完,这是通俗小说的好处,好读。“三言”就看得慢点,记住了个别细节。某年在浙江丽水碰到作家龙一,讨论起这个问题,他也主张“开架有益”,让家里的书架完全敞开,不开书单,不立任何规矩。许多阅读都是这样,起初并没有目标,所谓开卷有益。懵懂无知的阅读中,慢慢地也完成了一种自我教育。这种成长教育,包括性和爱的教育,传统的中国式的家长往往会有意忽略。
写作跟阅读一样,经验丰富,视野杂,写的东西才有可能好看。看过采访作家张爱玲的文字,张爱玲最爱看小报上的花边新闻和杀人越货的报道,每天都会买各种各样的上海滩小报。貌似高冷的女作家居然有这等不能告人却还要告人的偏好,当时年少,看到此处,忍不住大笑,但这个细节也记下来了。张爱玲在中国内地被一些研究者重新打捞出来后,有一阵子,许多青年作家纷纷学她的笔法写东西。学得像的,似乎没有几个。这一点不奇怪。笔法只是书写的外在风格,张爱玲的那种直接和间接的经验,是她的时代和她的生活给她的,这是旁人没有办法学的。
近年来,网络文学忽然成就了各种大IP,受到关注。各种议论中,也有人认为网络文学承继了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衣钵。是不是衣钵不好说,但古典小说,哪怕是志怪、传奇,表面怪力乱神,实质上写的依旧是现实。最典型的就是《西游记》和《聊斋志异》。阅读古典小说,无论有名还是无名,总还是能看到写作者鲜明的情趣和志向。从写作的动机看,纯粹消遣娱乐的古典小说倒真不多见,大概因为古典时期的写作者都是非职业写作的缘故。以“三言”为例,《警世通言》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一组白话短篇小说,现实指向性就很明显。《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中之一。这个故事被各种戏曲传唱,甚至被拍成电影。拍电影是当代的事了。上海姑娘潘虹那时候年轻,又美,杜十娘这个角色由她饰演。潘虹饰演的杜十娘是大女主,像反抗的李师师。“三言”里这类故事不少,对于女性个体意识的书写自觉,甚至超过今天一些网文。
“网红”这个词这两年红了。无意间翻看了一下短视频,许多女性网红开始用身体“带货”。“带货”也是刚刚红起来的新词。在女性就业有较大选择余地的今天,通过“身体”,原始化地谋生存、谋发展,如果不是被迫,而是出于女性自身的选择,我这个老古董看完之后,还是有些伤感。
好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难以阻挡的变化,形成了许多诗词伤感的来源。欧阳修的这首《渔家傲·七月芙蓉生翠水》写芙蓉盛开,也写人事兴替。“七月芙蓉生翠水。明霞拂脸新妆媚。疑是楚宫歌舞妓。争宠丽。临风起舞夸腰细。乌鹊桥边新雨霁。长河清水冰无地。此夕有人千里外。经年岁。犹嗟不及牵牛会。”一句“七月芙蓉生翠水”,写活和写足了芙蓉开放娇艳似霞的胜景,在芙蓉霞光的映照下,一池碧水生机盎然、生动活泼。词的上阕,除第一句外,其他各句似乎都着力写妙龄女子明艳生辉的姿容。七月芙蓉盛开,好似“新妆”。明霞,起舞,细腰,色、形、态宛然眼前。借写女性之美,喻指芙蓉也即荷花的错彩镂金,笔触大胆、细腻、清灵、可感。欧阳修终归是一代宗师,起笔只用一个“生”字,就能生出花来。越美好的事物,越经不起时间的磨损,整个下阕,宕开眼前景物,由荷花池写到更大更远的时空,这是抒情,在“物境”中引入了“情境”。借描物抒写胸中丘壑,本是诗的擅场,作为诗文改革先锋的欧阳修,在词的写作里,也有意无意融入了诗的追求。
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以倡导诗文改革而名。欧阳修诗文改革的具体表现是举韩愈柳宗元大旗,对抗五代以来盛行的西昆体和太学体,不仅有理论架构,文学实践同样丰富出色。《朋党论》《秋声赋》都是欧阳修的散文名篇。但今天的读者,可能更熟悉《醉翁亭记》。《醉翁亭记》也系欧阳修因范仲淹“乌诗台案”牵连贬官滁州后的“下沉”之作。“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气息贯通,末章显志,诗性和思辨性浑然一体。可以说,《醉翁亭记》作为实践文本,充分表达了欧阳修的文章主张,即文章要论事说理、抒情言志,言之有物,靶向性明确。欧阳修的这个改革主张,是改革五代以来盛行的华而不实的浮夸文风,不是不要文采,而是提倡文采文辞为内容服务。
有意思的是,在欧阳修自己的写作排序中,文章也即散文是第一重要,诗词是副业,是捎带手的事儿。或许是认为不那么重要的缘故,文章写作追求言之有物的欧阳修,对于词的写作,却要宽容得多。诗直抒胸臆,词婉转表情,欧阳修总体上遵循这一传统。这个态度的变化,也体现了欧阳修的实事求是。
文章大家的欧阳修也是词家,词的写作,深得“要眇宜修”之道。从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可以约略感受到这一妙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是欧阳修词的代表作之一。讲究而不艰涩,丰润而不铺张,让我喜欢。音韵优美,读起来可以说句句都好,比如“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比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各种意象令人意想不到,却又那么贴切传神。对于欧阳修这样阅历深厚、经验丰富的大家,写作是情感排遣,也是时局感怀,是兴发际会,也是更加博大深沉的生命忧患。表面上似乎写闺怨伤春,实质上,词也好,文也好,看任何事情,写任何东西,可能山都不是山、水都不是水了,景别都带着景深。景深也是眼力,决定了写作者的笔力。
刘熙载在《艺概》中写道:“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冯延巳的词有花间词的婉约,又广开题材,不拘“宴宾酬客”,被后学者传颂。其实,欧阳修最像冯延巳处,还是“因循出新”,因循词的传统的基础上,又开新面。有评论认为,欧阳修对于词的创新方面有两点贡献,一是沿着南唐李煜的方向,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二是朝着北宋柳永的方向,开拓了词的通俗化趣味。两首写“七月”的“渔家傲”,都体现了这种突破。以欧阳修的另一首写七月的“渔家傲”为例。这首《渔家傲·七月新秋风露早》写农家生活,朴实、有趣,用今天的话说是“接地气”,这使词从文人化趣味扩大到民众趣味。“七月新秋风露早。渚莲尚拆庭梧老。是处瓜华时节好。”欧阳修是造境高手,通俗不流俗,用词精巧,音韵晓畅。这是欧阳修的词的好处,得到传统和创新两派的认可。
“渚莲尚拆庭梧老”,在田园派诗词中,荷花或者莲花是常见的一种意象。莲的果实叫莲子,莲子居住的房子叫莲蓬。渚莲就是莲蓬。
人们对于荷花的感情,来自于美,来自于习俗,主要来自于实用。相传中国古人有春天折梅赠远、秋天采莲怀人的习俗。荷花或莲花有理由受到人们欢迎。花开可赏花,莲蓬结子可采莲,荷叶可煮粥熬汤。南方冬天,尤其临近春节时,壮汉们会光着脚,下到抽干水的荷塘里踩藕,间或还会捉上几条大鱼,为年夜饭配好佳肴,这是荷花在这一年最后的奉献。必须是壮汉,荷塘泥泞,再能干的主妇这时候也只能在岸上助兴。
至少我,对于荷花的喜爱,主要来自莲子,藕还在其次。
莲有诸般好处。不记得采莲是否用来怀人,但莲子鲜甜,喜食莲子确实是从小养成的习惯。生在水乡,“采莲南塘秋”是生活常景。我说的是四十年前。四十年前,长江中下游河汊密布,出门是水,需要摆渡、行船,沿途的池塘里和河湖里长满了荷花或莲花。荷花或莲花是多年生草本,生命力极强,又全身是宝,一年四季都可以当主角。八月初,菜市场里,就会有农人在地上铺张荷叶,荷叶上,莲蓬堆出了尖。不像其他摊贩,售卖莲蓬大多是临时活儿,大概持续半个月左右。喜欢吃生莲子的人得抓紧。莲子生吃,是比任何水果都要更接近“鲜”这一层滋味的。新鲜的莲子,带着湿气,鲜,甜,先鲜,后甜,因鲜而甜。莲子是河鲜的一种,不能脱水,所以买莲子是连着莲蓬一起买回家。把莲子从莲蓬里摘出来,不到半天,就会变硬变黑。莲子清火,又好吃,聪明的农人把莲子做成干货,过去是在南货店里卖,物流便捷后,东西南北各大超市都有售卖,煮汤,清蒸,红烧,都可。
荷花具有较强的适应力,种植普及度高。有水的池塘可以种植荷花,没有池塘,用瓦缸或者瓷盆接上水也能种,也会开花。我在北京的许多池塘里都看到荷花。最著名的是朱自清在散文《荷塘月色》里写到的清华园的荷塘。什刹海荷花市场直接以荷花为名,莲花池的荷花据说有三千年的种植历史,品种出色者当然还得数颐和园和圆明园。北京的超市里偶或也能见到新鲜莲子,可惜不但不甜,甚至还有点干涩。一方水土养一方植物,莲子还是南方的好。
莲子如此鲜美,从《诗经》开始,到汉乐府、唐诗宋词、南北朝民歌,围绕采莲,留下了许多浪漫优美的诗句,也让后人对先人的生活产生了兼具细节的想象。采莲看起来很美,其实是个技术活儿,长期生活在乡下的农人也未必能驾驭刁钻的腰子盆。芜湖话里,“腰子”是肾的意思。腰子盆是长江流域采莲和采菱角用的工具,形如腰子,两头尖,中间稍胖,也很浅,只能盛一人。有经验的人知道,这样的盆在荷花塘或者菱角塘里,很难保持平衡,也很难划动。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时,湖北黄梅有人,在长江上划着腰子盆,进入江西九江江面,被拦截下来。烟波浩淼的长江和娇小的腰子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个新闻报出来后,令我吃惊的不是此人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荆楚文化里这种自古以来似乎就层出不穷的“异想天开”。
夏天,去乡下过暑假是最期盼的事。采莲的经验没有,采菱角的经验有过一次。小姑妈自己划得好,鼓动我也试一试。七八岁的孩子懂什么,竟然就爬上盆,划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几个农人路过大叫起来,我这才意识到有多危险。菱角比莲子早,夏初上市。菱角开白色小花,持续不断地开,菱角也是采了又长,长了又采,持续不断地长,直到夏末。这时候,莲子上市了。我们也要收拾收拾书包,准备回城。
这是从前。可以行船的河道和荷花池、菱角塘,在各种工业园区和居民住宅的蚕食下,已经一个一个地从地图上消失了。去年夏天,一起长大的闺蜜从南方快递来一个大箱子,装满了莲蓬。鲜甜的莲子吃完,思恋像野草,更加疯长。
荷花与莲花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睡莲科。荷花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孕育和衍生了许多品种。如果硬要强调差别,莲叶要比荷叶更加阔大,荷花要比莲花更加出挑。荷花的叶和花会高出水面,所谓“亭亭玉立”“出水芙蓉”。而莲的叶和花大多齐着水面,或浮在水面。中国古人早就注意到这个差别,最典型的证据,便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诗人的观察力极强,看到莲和荷的区别,所以既写了莲,又写了荷,莲写叶,荷写花,各取其胜,各得其所。
全国不止一个净慈寺。杨万里写的净慈寺,位于杭州西湖南岸。西湖得名于北宋,也扬名于北宋。北宋时期,西湖总面积将近6.3 平方千米,与今天基本持平。“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南宋朝廷偏安临安后,文人墨客在此长期逗留,西湖的名声越来越大。净慈寺,今天的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净慈寺里的“南屏晚钟”作为西湖十景之一,是大名鼎鼎。净慈寺对面是雷峰塔,相传法海用来镇压白娘子。鲁迅的著名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写的就是这座雷峰塔。塔因文名,所以现当代以来,雷峰塔名声大噪。雷峰塔名声大是大,真没什么可看。比较起来,还是曲院风荷值得看。附近的北高山也不错。秋天的时候,当然是去满觉陇赏桂了,但我最爱去平湖秋月。西湖处处有荷花,夏天的早晨,从求是村出发,骑车到平湖秋月,只需半个小时。沿途都是新鲜的荷花,晨光中,新鲜饱满,美如处子。平湖秋月的人不多,坐下来,吃上一碗桂花藕粉。西湖的藕好,藕粉也与别处不同,糯,甜,一点点Q 弹,撒上一把满觉陇糖渍的丹桂,人间天堂也是美食天堂。
藕好,藕粉就好。湖北的藕也好。疫情后期,响应线上助农,购买了许多湖北洪湖出产的藕。打开快递,每节不仅裹着泥,还都精心地用保鲜膜包裹起来,像人参一样。这是卖家认真。把带着洪湖湿气的泥巴洗净,用筷子压一压,塞紧糯米,上锅蒸,大火,三十分钟。又甜又糯的糯米藕就可以出锅了。洪湖的九孔藕与别处不一样,轻轻地咬一口,可以拉出好长好长的丝。
口味是有记忆的。语言也是这样。我有一个男同事,早年留学英国,能说一口标准的京白,还能说相对标准的牛津英语,后来不幸罹患脑瘤,病至晚期时完全丧失认知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去世前一年,语言开始返祖,满口是苏北乡下方言。
语言会返祖,口味更如此。忘了是谁说的,说五岁以前的口味,往往会形成一个人的终身口味,或者说最执着的口味。这一点,许多成年以后四海为家的人可能体会更深刻。青年和中年时期,是一个人口味最开放的时期,也是身体最能承重的时期。到了老年,口味开始苏醒,开始返祖。我自己就是典型案例。十七岁离家到西北读书。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头两年,粮食市场没有放开,西北种植小麦、高粱、玉米,但不产大米。学校食堂里,馒头管够,米饭凭票供应。年轻的胃口开始学习接受面条、馒头、窝窝头以及辣椒、醋、孜然,还有一种叫“蓬灰”的由蓬柴草烧制的草灰,大街小巷的兰州牛肉面都靠它增加口感。四年后回到南方,重新巩固南方口味。之后,又北上北京近三十年。东南西北仿佛都待过,口味似乎更宽容才是。其实不然。记得某年出公差到呼和浩特,各种原因,一连去了五趟。这一年,从吃的角度,很惨。被草原民族优美深情的歌声打动,但面对丰盛的烤全羊,从舌头到胃都罢工。接待方单独炒了一盘青菜送上来,也难以下咽。草原民族的蔬菜是羊油炒的。我可能是“最汉”的汉人了。接待方很尴尬,顽固的口味,让我更尴尬。这种顽固的口味,过了四十,更加任性横泼。口味的变化,是生理的变化。从前一度酷爱的辣椒,几乎不能吃了,就连清淡的杭邦菜也被部分扬弃,几乎全方位地向淮扬菜回归。因为不能吃辣椒,连从前最爱去的巴蜀大地,已经将近五年都不敢涉足。淮扬菜在江淮之间,以河鲜和海鲜为主。河鲜和海鲜都讲究一个“鲜”字,对食材要求高,在江淮之外,吃到鲜美的淮扬菜自是不易。人老思还乡,恐怕也是这个原因。
荷花看起来娇艳,却没有这些顽固的口味,它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被子植物之一。对于荷花,大概可以用两个“既……又……”来概括。一个“既……又……”是,既拥有“活化石”的老资格,又拥有娇美的花容。金庸大侠笔下有个人物叫“天山童姥”,荷花是植物界的天山童姥。第二个是,美丽的东西往往无用,而荷花既美丽,又全身是宝。在栽种普及的亚洲东南部,印度和越南这两个中国的近邻,甚至以荷花为国花,而荷花几乎打通三界,从世俗世界到灵魂世界,都被高度认同。随和,适应能力强,使荷花早在十万年以前,就与恐龙和蕨类植物同期出现,并超越恐龙——存活至今,超越蕨类植物——栽种广泛。
如《周书》所记“薮泽已竭,既莲掘藕”,是距今五千年前的西周初期有关于荷花的人工栽培记录。其实,更早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也出土了荷花的花粉化石,这说明距今七千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采集和播种荷花的花粉。从野生状态进入人工栽培,荷花与人类的关系更加紧密。
中国人对于荷花的情感异常丰富。在诸多的民间或文人的文字中,我其实还是最喜欢王勃沿用乐府旧题书写的《采莲曲》,气如长虹,调韵悠扬,是初唐气象。“采莲归,绿水芙蓉衣。秋风起浪凫雁飞。桂棹兰桡下长浦,罗裙玉腕轻摇橹。叶屿花潭极望平,江讴越吹相思苦。”全诗很长,只读开头几句,便已知道它的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