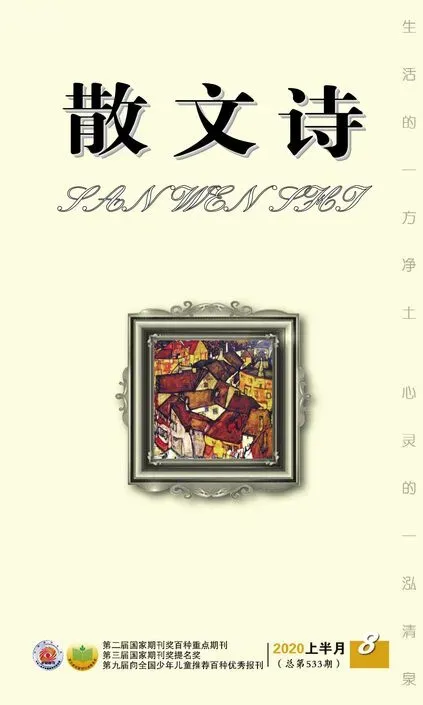钟的秘密心脏
2020-11-22方向荣
◎方向荣
塔楼
在塔楼上,你感觉到叶芝,那凝聚的目光像灯一样,照亮你面前黑漆漆的道路。
置身于黑暗中的耳朵,在谛听,在谛听那未亡大师的灵魂闪射的光芒——你不是翘望黎明,就是跃入更深的黑暗。激浪滚滚的时刻,词的喧嚣,猛烈的撞击使你心扉洞开,包围并容纳下整个的夜!
塔楼的光芒就是黑暗世界的光芒!
流亡者
一个流亡者的灵魂是深不可测的。正如布罗茨基,总是满含着低沉的抑郁伫立,呈现在世界面前。
当他脱下帽子向你致意时,你总能看到他稀疏干黄的头发,荒草般纠缠着死亡。死亡,那标点符号,向落日的深度延伸。帝国的大厦在他眼中倾斜、崩裂、土崩瓦解。事实上,他已成为一个掘墓者,挖掘着黑暗世界地底的宝藏,一个世界暴露在我们面前——我听到落日在他胸中惊叫,他的骨骼被罡风摇晃得如钢铁般嘎嘎作响!
文化
艾略特的眼里,呈现出一个荒芜的世界。在那令人恐惧的荒原上,女仆的灵魂正在生根、发芽。
不可摆脱的梦魇是:从伦敦到斯特斯加,章鱼们坠落于快餐的流行文化。我们如鱼得水,穿插其中,饱餐着使人类幸福的流行文化!
月光
月光摇曳的树影令人恐惧。荷尔德林,一个诗人中的诗人,一个精神失常的智者,他的灵魂正被月光的琴弦奏响——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
而沉沦的大地,马蹄声远去,琴声远去……忧郁的诗人,神的自喻者,走进幽深恐怖的世界。语言的毒液,鱼的唾沫,飞溅于泥泞的道路。自爱者的灵魂总是神圣的!
他抬头向高天仰望,无垠的月光,照在他忧伤圣洁的脸上,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像,凝视远方,谛听惊雷在心头轰响……
祖国
流亡的布罗茨基,他最终背弃了自己的母语,却不能背弃自己灰暗的祖国。
他的灰色、低垂抑郁的目光,总是在大洋彼岸,回头,再一次地回头,他凝望着风雨中飘摇的祖国,心,滴血般疼痛……
祖国,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个咒语,背负在他的灵魂之上,走向人生的漫漫长途……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使命是:挖掘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旧梦。他在少女杜拉的梦中寻找,他在精神分裂症的思绪中发掘——恋母情结与恋父情结,战争与强暴,无意识与潜意识……这位老犹太人,手拿放大镜,坐在奥地利特制的转轮座椅上悉心研究,他究竟研究出了什么成果?
癌症,深入到他的肺部。这致命的生与这致命的死,使他暂时遗忘掉疼痛——他脱落的牙齿与灰暗的梦的研究,被收藏进20世纪的收容所——那里,一只黑蜂,正从潘多拉黑匣子里飞出……
谛听
卡夫卡饱受生活的沉重压力,犹如一只掩埋在地底的铜钟,只向紧捂住双耳的人们敲响——在那里,人们不是用耳朵,而是用灵魂谛听……
里尔克
里尔克的灵魂,在世界上四处游荡。哪里有雨夜,哪里就有里尔克,他用诗歌征服了我们称之为虚幻的世界。
我们被包裹在里尔克的巨大的光辉中,一头威武雄壮的豹子在我们的头颅中勇猛地走动。谁在谛听?雨夜中的雨夜,冰在我们的血液中汹涌,暴怒的灵魂,爆裂的石头,掀起巨大的涛声,震撼着没有灵魂的肉身,战栗之心里石柱断裂!
里尔克,诗歌中的王者,风在不断向我们叙说:语言没有边界,灵魂不能逾越,与人终生相伴的痛苦泛滥人类灾难的洪水。
韵律
卡蒂尔的内在灵魂深处,骤然敲响之钟,暴露出钟的秘密心脏。那儿,展开大地一道深刻的裂痕,翱翔着一只黑鹰,鹰之眼俯视一只爬行的黑蚂蚁。
生命之钟展现出黑暗之光搏动的韵律……
春天
帕斯捷尔纳克的内心,轰响着春天的泥泞:二月,墨水足够用来哭泣——那阴郁的调子,萦绕在大地耳际。
黑暗低矮潮湿的屋子,被风拥着。老鼠噬咬的破旧家具,摇晃在疾风里。低沉的伏尔加河,飘动的歌声,结满坚冰。你雪亮的眸子反照着你的内心:一种挣扎的活,比死更痛苦!而你仍努力地挺立骨头活着,比死更痛苦地活着。谁抚慰你忧伤孤寂的灵魂?
二月,梦中不断拓展向黑暗的二月,天空中积满雨的哀音,撕裂你的灵魂。
冰在破碎,诗的缪斯在破碎,你的心在破碎。
在流动的破碎中,一道雷电之光,迸射出眼睛里黑暗的黎明!
青春
瓦雷里诗歌赞美的青春,赞美的自由女神,正在破裂。椭圆形的泪珠,滴落在圣母玛利亚空旷的广场上。
通过天庭的震怒,通过火焰的歌喉,我听到生命冰冷的死亡——青春只属于那些歌者,命运只为勇于开启铁锁的人指示方向——在心灵的悸痛中,在敲响的丧钟里,洁白如玉的女人赤裸着奔跑在大海上——大海掀起汹涌的波涛——
诗人之心被愤怒的雕像的火焰耀亮!
存在
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心中,让-保尔·萨特就是光明的圣者。他在风中叙说:存在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应做出自由的选择。我看到他对资本主义官方意志的坚定拒绝!
在石头垒砌的炼狱中,一个存在者与另一个存在者,就像眺望在悬崖上的两棵树,他们的灵魂是相通的——寒星在寒风中坠落,照见我虚浮苍老的脸,我只能在黑夜里痛苦地写作,这是我灵魂做出的选择。对于我的存在,让-保尔·萨特保持着坚定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