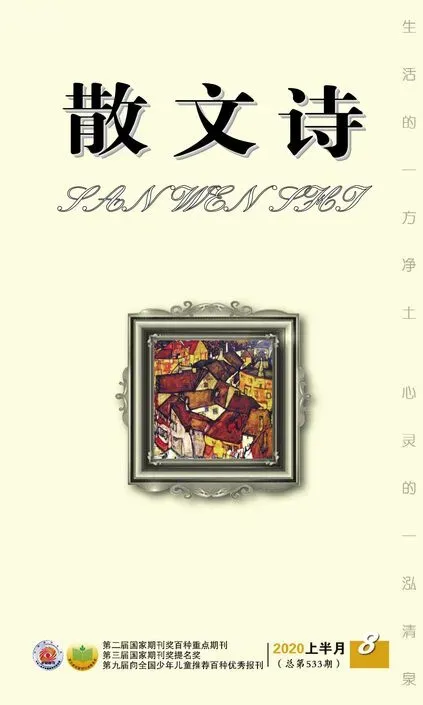洄游的鱼
2020-11-22冯瑞洁
◎冯瑞洁
听涛
离开饭桌上的喧嚣,他赤足走在十里银滩上。湿润的海风消退了白天的燥热,灯火沿着海岸亮起半圈光带,环抱着半弯银滩,黑绸般的海面晃动着月亮的半边脸。
游人极少,偶见成双的身影。
双脚每一次落下,细滑的沙子散开、下陷,再聚拢、覆盖,像她调皮的笑声,躲着他,又围捕他。
海浪涌上来,沙子变得安静、服帖。海浪吻着他的脚丫,他像礁石一样沉默,所有的知觉交给耳朵。像母亲的呼叫,由远而近,有茫然的找寻,有看见的欢喜和责备,然后是慢慢地消减。每一次重复,都把他带回久远的回忆。
那年秋天,他踏上了颠簸在各国海域的远洋巨轮。家乡,一个句点,落在某一个角落。
海涛,于无眠的深夜向他喃喃低语。
无边的海,无尽的涛声。唯有在此,于千军万马的轰鸣中,他能捕捉到丝丝婉转的琴声。那是张羽的琴声,还是他自己的?涛声灌满每一个细胞,他仿佛攥紧鲛绡帕潜入深海,寻找离他而去的灵魂。
家乡的海滩,离母亲这么近;离年轻时遇见的女孩,这么近。
沉船
一伸手,便触摸到“南海一号”纪念馆咸涩的墙。
仿佛接收到来自水晶宫的电波,他手指痉挛,嘴巴紧闭,呼喊却在体内狂奔突围。每一个在海面飘荡的日夜,空茫如海上的天空,巨大、邈远、孤寂、荒凉。
他曾狂傲地说,只有在大海上搏击过的人才可谈生死。
可是,面对这艘消失再重现的沉船,一些从不在意的微小的生命,在脑中复活。一只海鸥的飞翔,一条跳鱼儿的挣扎,一只蜗牛的坚持,一朵小野菊的微笑……谁说它们微小得留不下任何痕迹?昙花一现,弱小的生命也有怒放的壮美。赞美诗从心灵响起。
他深深地呼吸,沉船,不再是不可触摸的话题。
一艘艘沉船,大海为它们唱着赞美诗。传奇的“南海一号”,携带一组巨大的数字,打通人们追寻海上丝路隐秘的通道。存在,消亡,历史在延续。
爱,是唯一的坚强堡垒。他轻叩博物馆关闭的大门,在一圈圈涟漪中触到颤动的枝叶。船,又回到了最初枝叶繁茂的样子。
渔灯
如果说,南海一号让他看到生与死,以及死而后生,那么,一盏渔灯,便是年华老去落下的思念。
他静静地望着漆黑的海面,海风招摇,渔灯星星点点,晃荡再晃荡。落在海面上的光晕,一波波向海里的月亮发出邀请。恍惚间,母亲提着灯从海中升起,一步步向他走来。
往昔,他不屑于母亲的小渔船,他驾驶巨轮驶向更广阔的海域。巨轮上雪亮的灯光,陪伴了无数个异国他乡的夜晚。灯下,他从三副到二副,从大副到船长,一路考试,过关斩将。那些光,是他对远方未知的期待,是他有别于母亲生活的憧憬。
曾几何时,都市繁华和最大利润,成了他唯一的追求。他以为自己原本是落入亚特兰蒂斯的那个唯一清醒的水手,不曾想自己竟和那座沉没之城的居民没有什么两样。
母亲的小渔村,一年一次的归来也只是步履匆匆。如今,母亲在哪里?是前方的渔灯吗?一盏一盏,定是母亲挂上去的,照亮他回家的路。
渔灯暗,徒留梦千回。
篝火
沙滩上燃起了一堆篝火,猛烈上蹿的火苗点燃了整个沙滩的热情。《夏之夜》的旋律破空而响,风声、涛声藏匿。
他们这群已过不惑之年的同学,跳起了热情奔放的草裙舞。不管节奏,不管动作,甩手扭动摇摆,只管任性。是怀念狂热的青春?还是疲惫的中年,骨子里还埋藏着熔岩似的热烈?渐渐地,汗水浸满额头,湿透衣衫。
音乐消停,倒卧沙滩,一群洄游的鱼。大马哈鱼?三文鱼?大家横七竖八地躺着,有挨挤成一堆的,也有远远独自一人的。
木头焚烧,映红了每一张脸。租种百亩水稻的、拉高架电缆的、开摩的的、做医生的、当教师的……小渔村走出的同学,没有人再捕鱼了。隔了二十多年的聚会,只有他是被同学从人海里打捞出来的,他游离得太久了。
沉默,木头炸裂的哔啵声,应和远处的涛声,再也没有人提起同学中早逝的生命。篝火暗下来,暗下来,只剩下一堆灰烬。所有的曾经,不过是灰烬。怀念和展望,不过是留下灰烬,带走温暖。
今夜,他就是一条洄游的鱼,循着故乡,循着生命,怀揣篝火的温暖,重返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