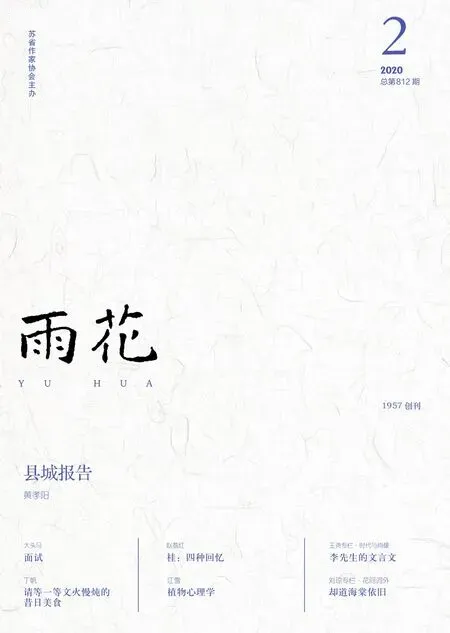李先生的文言文
2020-11-22王尧
王 尧
以前只要到了春天,我就会把《读报手册》一类的书从箱子里拿出来翻晒。我把我喜欢的书放在窗台上,冬天的潮湿在阳光下散出,只要晒一个下午,书页便干脆得蜷缩。转潮的书,你去翻它是没有声音的,晒干的书,你去翻它就像在晒场上翻稻草。但在1972年之后,《读报手册》一类的书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我开始喜欢读古文和小说。
我在河东桑园采桑叶时,李先生隔河喊我:星期天啦,你要不要来读《古文观止》?李先生是在警告我。他的牙齿几乎都掉光了,声音碎而散。我后来跌跤断了一颗门牙,说话漏风,有嗤嗤的声音,这让我想到李先生。我现在只教现当代文学,不教学生读古书,自己也是偶尔翻翻古书,心想,那颗断了的门牙就是悼念李先生的。
那时,我已经读初中一年级了。李先生是老私塾先生,他只教私塾,不懂新学,不会稼穑,成了不能自食其力的寄生虫,他落魄的样子像济公。儿孙满堂的李先生一个人独自生活,那是一间土坯房,周围是菜地。蜜蜂开始在菜地舞蹈时,常常钻进土墙的眼子里。这是我小时候最想看到的情景,拿一个空瓶子,将瓶口对准墙的眼子,不一会儿蜜蜂就钻进瓶子里。你用大拇指捂住瓶口,凑在耳旁,那声音就像现在的歌手在唱歌。李先生看到我同学做这种游戏,站在那里摇头。可能除了我,其他同学都认为他是个疯老头儿,没有人搭理他。我爸爸妈妈这一辈的人都称他老先生,因此我也称他为李先生。人们称他先生,不含尊敬的成分,只是习惯,如同人们习惯地称桌子椅子一样。所有的人都不太在意,也无须在意他。
我很少去那间土坯房,里面太脏了。南墙在门的左右各有一个窗户,所谓窗户,其实就是洞。冬天用旧报纸糊着,其他季节都是敞开的。又一年大雪,老先生只能用砖头堵上窗户,如果不开门,屋里没有光。后来在城里见到路边砖砌的垃圾站,我就想到老先生的房子。我硬着头皮去了李先生家,开始学古文。我问他怎么用文言文称呼我们大队的人,现在大家都叫社员,从前呢?李先生沉吟片刻说:应该叫“氓”吧。“氓”,《说文》曰“民也。”李先生说完,又以《诗经》的《氓》为例。他又纠正我的读音,不是读“流氓”的“氓”,而是读“蒙”。李先生先引《说文解字》,再引《康熙字典》。我没有见过《说文解字》,只是翻过《康熙字典》。李先生床的踏板上堆放着《康熙字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叫线装书的东西。
我对李先生的态度始终有些踌躇,他说的话、教的书,都是旧时代的。我不想读古书,我想学文言文。李先生一笑,既学文言文,为何又不读古书?李先生进一步说,你们的语文老师那样教文言文是不对的。他看我有些惊讶,重复地说:真——的——是——不——对——的。我把语文课本带给他,他说他要先帮我整理一下语文课本。我不知道他的整理是什么意思,就把课本丢在他那儿。上语文课时,老师让我读课文,我说书忘了带。第二天上课,陆老师看到我和同学合用课本,便说:你怎么又不带课本?他对我这个好学生有些失望,下了课找我谈话,提醒我不要骄傲。毛主席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知道吗?语文老师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愧疚,便不再说什么。
傍晚,我慌张地去找李先生。李先生正在舔勺子里的玉米糊,胡须也粘上了。他停下来说,我正要找你。我拿到课本一看,心情比去找他时还要慌张,他用红笔在我的课本上圈圈点点,像老师给我们改作文一样。我不完全懂他说的话。他反复跟我说,时文选得太多了,时文不好作范文。又指着《口干舌燥心里甜》那首诗说,这怎么能叫诗呢?唐诗才是诗。那时我开始对词有兴趣,便问:词呢?李先生说:词乃诗之余。但他并没有和我讨论这些话题的兴趣。他把饭勺搁在锅盖上,背朝我说:我赞成革命,赞成劳动,可谁去读书呢?你要读书。
李先生年轻时候好像也喜欢过新文艺。一次他在讲《诗经》前拿出一本纸张已经发黄变脆的杂志给我看,这上面有他写的新诗,而且用了笔名。我记不清李先生的笔名叫什么,只记得封面上有个吹喇叭的胖娃娃,腋部还长出了翅膀。他说,你知道杂志为什么叫“嘤鸣”吗?我当然不知道。他随即吟诵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又解释这是《诗经·伐木》中的诗句。我问他借《诗经》,他说,没有了,你看到我什么时候有过《诗经》这本书,诗三百篇,你不能背下来,还算初中生?我会背诵,你跟在我后面背诵就行了。
伐木丁丁,
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
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
相彼鸟矣,
犹求友声。
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
神之听之,
终和且平。
磕磕绊绊背了几天,我能记住的也就这几句了。
这显然让李先生大失所望:看看这些小鸟儿,还在叫着到处找朋友呢。友声难求,友声难求。你们都说我是个懒汉,但我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劳动。我是劳心者啊。孔子会种庄稼吗?他会插秧,他会放渣,他会开手扶拖拉机吗?他会养猪,他会拾麦穗吗?他都不会。这影响他成为圣人吗?不影响。当他说孔子是圣人时,我异常紧张。
李先生躺在长条凳子上背诵时几处说到“酒”字。我终于从中学图书馆借到了《诗经》。我先查了他说的《诗经》中的《氓》,再查了《伐木》,抄在纸上。关于“酒”的那一段,许多字我都不认得,李先生最后拉长调门背的两句是:“迨我暇矣,饮此湑矣”。我查了《新华字典》,明白“湑”是过滤后的酒。我不能读懂这两首诗,便去问语文老师。老师说:《氓》?流氓的氓,他也把meng 读成了mang。老师说,这样,我先看一下,再给你解释,好吧?我等了好长时间,老师始终未给我解释,我几次去他办公室交作业时,他只字不提。有次劳动课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又问了。老师说:我不能完全解释清楚,老实说有的地方我也不懂。但我要提醒你,《诗经》你不宜读。你当心点。我这是保护你,晓得吧?
也就在那一天,这位老先生问我:你也在批孔子?他说:你读过几章论语?你能批孔子?你们写的那几首儿歌狗屁不通。你没有读过《论语》,你就不能批孔子。他重复了好几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是我和李先生的接触中他第一次说这么重的话,我很惊讶他维护孔子,也很惊讶他用孔子来为自己解释。他说的这些话正是语文课上老师要我们写批判稿批判的内容。我觉得这很危险。李先生还提到了一个叫“冯友兰”的教授。我在报纸上也看到这个人的名字,李先生说他是北大的教授。李先生很纳闷地问我:这个人过去是尊孔的,现在怎么会批孔呢?我显然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他的这番话让我感到他并不是村上人说的那种书呆子。说完这番话,他又躺到长条凳子上,继续背他的《伐木》。
那时,我已读过鲁迅的《孔乙己》,李先生和孔乙己某些方面有点像。孔乙己去咸亨酒店,排出几文钱,李先生同样是穷困潦倒。哦,李先生想喝酒,哪里有酒?牧童遥指杏花村。除了冬天,李先生一直穿着长衫,上面有无数他自己缝的补丁。有时候天气并不冷,他却在脖子上绕一圈围巾。这条围巾像抹布,抹嘴巴上的稀饭,抹桌子上的汤水。当时粮食紧张,他不是“五保户”,生产队无法给他额外补贴粮食。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用过钱,买过东西。很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如果在另外的家庭出现,村上的人一定会声讨子女不孝敬老人。但李家这种状况,谁也没有觉得异常。
李先生走在路上,不熟悉的人肯定以为他是讨饭的。李先生不讨饭,他去各家借米借油盐,说我会还的。各家都给他一点,告诉他还不还再说。所有人都明白,老先生是无法还的。那时,我爷爷在另一个公社的粮管所,偶尔会买到几斤山芋干,带回来时,我会送一些给他。老先生借东西时,都会向主人作揖致谢。我送过去时,他一样作揖。这种动作的斯文和说还的诚信,透露出这位老先生骨子里的教养和尊严。但老先生的状况越来越差,骨子里的东西很快被穷困潦倒击垮了。那时村上人家办事,会办筵席。通常村上一个和我同龄的瞎子会站在人家门口,主人会盛一碗饭菜给他。后来发现,李先生也这样站在门口等主人施舍。一次,我们家办事,李先生站到我们家大门口。我妈妈说,老先生你进来吃饭吧。老先生吃完饭,跟我说:那个字读meng,不读mang。他说的时候直喘气,好像是发哮喘了。我把他送出大门,在昏暗的路灯下,他弓着腰往前,嘴里咕噜咕噜不知说着什么。
这是个温暖的秋日。放学时,回家的路上经过一片稻田,又听到耕田的胡老爹在打牛号子。我背靠草垛对着田里的稻桩撒尿时,猛地听到胡老爹一阵长长的牛号子声嘹亮起来。我呆住了,觉得这个老头一生的力量都在号子声中了。后来我看到一部写黄土地的电影中有类似的情景,但我觉得胡老爹的牛号子更有一种田园抒情味。老头子打号子的余音给我的感觉,很像我们在河边用瓦片打水漂,瓦片紧贴着水面,一圈圈涟漪向远处扩散过去。我又到生产队场头养蚕房,听到妈妈的摇篮曲。妈妈正一边喂蚕一边哄隔壁家的孩子睡觉,妈妈对着欲睡不睡的宝宝唱着摇篮曲:风呀微微地吹,鸟呀吱吱地叫;宝宝的眼睛像爸爸,宝宝的眼睛像妈妈,宝宝的鼻子嘴巴既像爸呢又像妈……。妈妈唱第二遍时,宝宝不哭了,只有蚕食桑叶的声音。
这一天晚上,李先生突然到了我们家,问他吃过没有,他没有回答。我妈妈盛了一碗粥给他,这才发现他夹了一包书过来。打开报纸,是一部《康熙字典》。李先生说:这字典我用不着了,送给你。我爸爸知道这是清朝什么年间的版本,便说这是宝贝。李先生说,身无长物,只有这字典了。李先生问我:怎么批右呢?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而且不明白,他怎么会对政治感兴趣。李先生说:右尊左卑,自古而然,我给你讲过。李先生说的是文化,不是政治。他又问我:怎么是“师道尊严”,以前是说“师尊道严”。李先生问我:最近在学什么?我说:在学习毛主席的词二首。他说:毛主席伟大。我又送他出门,他说:有这部字典,你不用我教了。
第二天,我傍晚从田里回来后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耐心地用手指剔除脚指甲上的烂泥。爸爸说:老先生死了。老先生昨晚投河自杀了。又过了若干年,老家在翻新房子时,这部《康熙字典》放在一个纸盒子里,我爸爸说下次去苏州带给王尧。但这部字典后来不翼而飞,被谁拿走了至今仍然是个谜。我记得我和老先生接触到的书刊大概有四种:《康熙字典》《诗经》《古文观止》和《嘤鸣》杂志。李先生带着他的文言文走了,但这些书和杂志都还有,只是这个版本的《康熙字典》很难寻觅到了。
我一直对《嘤鸣》这份杂志很好奇。多少年后,我悄悄去看了李先生读书的师范学校。在为学校所在县城的文学爱好者作过一次报告后,获赠了一套当地的文史资料,在翻阅时无意中知道了这份杂志的来龙去脉。资料记载:民国十六年到十七年间,在南通中学高中部就读的学生杨、韩、解三人,受到夏丏尊、叶圣陶先生主编的《中学生》影响,自费在当地编印了这份期刊,封面那个像西方神话中安琪儿的胖娃娃出自丰子恺先生的手笔。此时李先生在师范读书。我兴致冲冲赶到市图书馆,馆藏也没有这份杂志。我在师范学校徜徉时,已经是寒假。除了工友在传达室弄出点响声,校园里悄无声息。李先生为何中途辍学返乡一直是个迷。直到李先生投河以后,有位长者给了一个答案:你不要难过,你的那个老先生也不是圣人,他是偷了学校的书被开除的。我无法辨别他说的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他偷了图书馆的什么书,但我很自然想到了他临死前一天送到我家的那套《康熙字典》。我不知道他偷的是不是《康熙字典》。
很长一段时间,我外出时喜欢在县城或乡镇的老街逛荡,看看有没有可能寻觅到一部清朝版的《康熙字典》。在苏南的老街上,我仿佛行走在家乡的老镇。我后来知道,这些地方可能都曾经是我的祖先行走过的地方。这些似曾相识的砖与瓦,同样浑黄的河水,过于清洁的街道,并没有给我带来亲切感。一次,我从老街上走过时,已是傍晚,老街在阳光消失后突然变得更加幽长,当我看不见自己的影子时,我就想起了鬼,这是小时候大人恐吓我们这些孩子留下的心理阴影。一个孩子心中的阴影就像幽长的老街一样幽暗和狭长。我逐渐明白,愈是阴暗的地方愈适合卖古玩、古典、古董什么的,暗与潮湿会把不同角落的历史统一起来,又能把时尚修饰成古玩、古典、古董什么的。
在幽暗和狭长的街上,我觉得会和老先生、和《康熙字典》相遇。但我一直没有寻觅到线装的《康熙字典》,也很少遇见像李先生一样穿长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