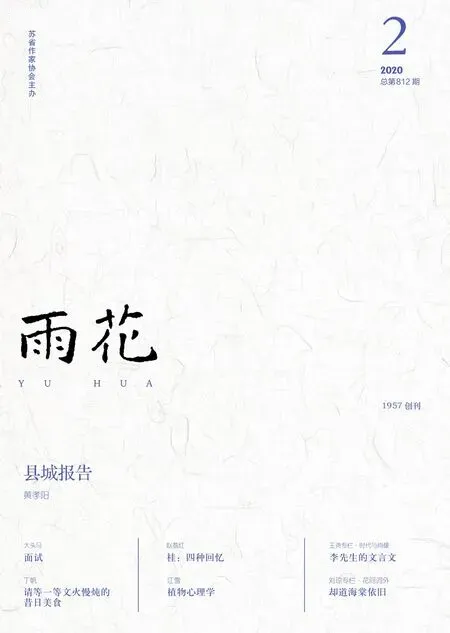逃离南角墩
2020-11-22周荣池
周荣池
我曾用二十年时间逃离一座水边的村庄,并且如愿以偿。
1
我出生的村庄叫作南角墩,从小我就觉得这个村庄的名字和这里的生活一样粗鄙而简陋。南角墩的母亲河叫作三荡河,人们觉得她就像长江一样壮阔,并且确切地认为她是通往东海的。东海在哪里没有人考证过,因为既然祖宗们已经确定这条大河通往东海,那么东海在哪里就不需要去证明了。人们也没有时间去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们要忙着生活。
我的家族在南角墩是外来户,只有父亲兄弟姐妹七人,他们带着画在布匹上的族谱来到南角墩生活,与这里的冯姓大族一起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巴根草”。巴根草是一种普通到极点的野草,它们抓紧了土地生长,无论泥土贫瘠与丰饶,都能够野蛮而倔强地生长。
我们的家族人少力单,族规第一条是:力畎亩。
读了点书的人,喜欢将种地当作一件高尚的事情。比如有一副著名的对联:承先祖一脉相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耕惟读。吃饱肚子是由来已久的天下大事,而种地似乎是天下第一大事。有人研究过这话是隋唐时的士子说的,可是我不用研究就可以确认,在南角墩人的生活里,种地确实是天生的本事,也是天大的事情。
三荡河以及她的众多支流构成了表述里下河平原的一个熟语:河网密布。于是祖先们既要逐水而居又要“人往高处走”,所以“墩”“垛”“圩”成为平原村落的标识密码,因此,三荡河边上“东南西北”墩的命名虽是自然而然但也并非随意而为。“东角墩放鸦,西角墩拉虾,南角墩种田,北角墩卖盐。”每一个村落都有她自己的天然禀赋,也就有着自己从一而终的生计。
我便出生在种田的南角墩。
躬耕畎亩是南角墩的祖训,也是村庄的命运。在靠天收的岁月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日子常常是苦楚的,所以“吃苦”是常有的事情,幸好人们是能够且乐于吃苦的。
日子能苦到什么程度呢?这在今天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确实有很多刻骨铭心的痛楚。从一个家庭的遭遇说起,就可以看到一个村落的过去,甚至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背影。我的父亲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从部队复员回到南角墩的,本来安排在省城的工作因为村干鉴定中所写的莫须有的政治问题而丢失,这一点让当时的村里人倍感安慰——一个外来户的穷小子怎么可以去省城的轧花厂工作?他困顿于此并终老一生的结局安慰了大家的情绪。也因此,他一辈子痛恨这里的生活和土地,这种情绪后来也遗传给了我,成为我要逃离这个村庄的情绪基因。
作为一个外来户,父亲还有一个尴尬的身份——他在入伍前以侄孙的身份过继到老家一户人家继承香火。这个地方是三荡河的河口,叫作三荡口。后来太爷爷过世,父亲又带着太祖母和一对木门、一口粪缸回到了南角墩。这对木门据说是一个家庭的命脉,支撑了几十年的破落光阴。同时更为尴尬的,是父亲的祖辈并不是以种地为生,追根溯源,他们是在江边放鸭子为生的,后来到了南角墩他依旧想重操旧业。这份并不显耀的家族生计,依旧引起了人们的不安,都是在土地上周旋的人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容忍一户人家可以靠着鸭屁股冒出来的生计过日子。于是,在父亲的一趟鸭子正在“鸭上满栏”的时候——这个词是村里一副朴素春联的下联,“鸡生大蛋,鸭上满栏”就是当时最美满的生活追求——村里的人真正是“眼睛一红心就黑了”,一捧和了剧毒农药的稻子让它们成群地惨死在三荡河边。
父亲急得直跳脚。在母亲失声痛哭的时候,绝望的父亲狠狠给了她几个大耳光,然后自己就着冬瓜汤喝了一斤叫作“粮食白”的酒在门口的草堆上睡到天黑。他们曾经自嘲过,“任叫气得哭,不喝粮食白”,但这种价值两块半的劣质酒最终解救了他于绝望。父亲对投毒者是谁心知肚明,我从后来的一件事中看出了端倪。那年冬天有几只鸭子游到三荡河,父亲将它们逮回来杀了,煮了一锅汤。他知道这几只散养的鸭子的主人就是那个投毒的人,他请了鸭子的主人来喝酒喝鸭汤,那人虽心知肚明,但也只得津津有味地喝下去。
后来,我在很多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人心是最毒的药。我这么说并不是我忘记了自己是这个村庄的孩子,我一直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留恋这个地方,即便是一只猫狗都是会记得回家的路的,但我一直将这句话记在心里。
父亲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复。他经常酗酒并和邻里打架,以致于他喝酒打人成为南角墩一件很著名的事情。他有时捞起扁担就打村长,酒醒后又去道歉。那时候人们似乎认为打架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也没有过一次争讼的经历。大概也是为了安抚他的暴躁,村里最终决定将三荡河两岸的一千多棵树交给他看管。他又在水边的小屋子前架起来一网捕鱼的罾。因为“取鱼网网空”,十网九空的日子也没有人再去妒忌他。那一阵子他就像是被家庭和村庄忘记的人,每天在三荡河的两岸来去,清点着那些他已经了如指掌的树木——他用自己带着酒味的鼾声守候了三荡河许多空旷的夜晚。
我很早就开始思考父亲和村庄的关系,也早就隐隐约约地明白了父亲的孤独,而这种孤独实际上是父亲们的孤独,也是南角墩人们的孤独。有一次,我们娘俩深夜去河边找他,因为我们深夜醒来的时候,发现屋顶的一个角落有一条张望着我们的蛇,那蛇的眼睛发着荧光。父亲极不情愿地赶回家中,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他留一下一顿令人绝望的咒骂。
父亲是绝望的,大家是绝望的,村庄也是绝望的。
待我们慢慢长大,对于村庄的这种绝望也认识得更清楚,也慢慢地懂得这确实是大家的绝望。那个下手毒死父亲鸭子的人,学吹唢呐去做道士谋生了,后来一次晚归的途中被车撞死了。我觉得这并不是报应,因为一向老实本分的兔林子也被车撞死了。她的女人哭了很久,可第二年她就和一个光棍生活在一起了,她聋哑的儿子后来没有结婚,哑巴女儿嫁到宝应,后来又离婚了。还有病痛了一辈子的母亲,在我学成归来的时候选择了离开——我后来想明白了,这一切都没有所谓的因果可言,而苦难就是生活本身,是南角墩与生俱来的样子,这大概也是所有村落的样子。
我逃离村庄,是为了逃离苦痛。
2
我是个农民的孩子,即便是我后来发狠离开村落,揣着师范生的录取通知书得意洋洋的时候,依旧没有忘记这一点。
倒春寒的冷风带来了上河的黑水,造纸厂的废液逼得鱼虾在三荡河的浅滩上无奈地盘旋,我们光着脚抢夺一般地收获着这些唾手可得的美味。造纸水的异味和生活的匮乏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没有到来的死亡比起眼下的饥饿也好像算不得什么。母亲有“做汤煮”之称的煮鱼技艺,在浓油赤酱的汤水里,那些鱼虾再次活跃地翻腾。加上卖鸡蛋换来的“粮食白”,父亲喝起来根本不会在意什么污染。即便是捉襟见肘的日子,母亲还是想尽办法去对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艰难,哪怕只是一碗咸菜蛋汤,也把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这也是每一位母亲的本事,让青黄不接的春天在热气腾腾的饭锅头上盘旋——然后万物生长,草木葳蕤,生机勃勃,一切就都有了。
汛期的日子,大水几乎是每个夏天的心头之患。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1991年的特大水灾。三荡河水不断上涨,灾难濒临村庄。所有的人不再有什么恩怨情仇,披着破旧的雨披与村庄生死与共。水性好的父亲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一次一次地扎猛子钻进那浑浊的河水,用棉絮堵上漏水的闸门。大水到来之前,人们短暂性地进入了一种空前团结的狂欢,将所有的物资都无私地奉献出来,就连每家用洋红做了记号的鸡鸭鹅也都一起捉到生产队的大锅中炖了喝酒。所有的机器都用于内涝的排除,倾盆大雨的南角墩突然显得振奋人心。水退之后,南角墩继续着原来叮当作响的日子,该打的架继续打,该骂的娘继续骂,该过的日子也继续过。
三荡河的汛情有时在秋天也会杀个回马枪,闹一场“秋呆子”,但大多数时候算得上是风调雨顺。稻田在逐渐干涸之后,村庄就等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季节。水稻永远是村庄里最重要的庄稼。饭在南角墩专指米饭,这种遗传使得我们出去再远再久,或者吃什么山珍海味之后,如果不扒上一碗米饭,那么这顿饭就是不完整的。割稻是一年中的一个重要节日。相隔不远的一个叫作唐墩的村庄向来出铁匠,他们打的镰刀远近闻名,秋收之前就来村庄里兜售。母亲们一早就将刀砖泡在水里,然后磨刀霍霍去收割秋天。村庄里的秋收,有一个很特别的叫法:收收。收来的稻子其实早就有了明确的盘算:一部分上缴粮站,一部分留作口粮,一部分留给牲畜,还有一些以稍高的价格卖给小贩,给孩子交新学期的学费——然后郑重地告诉他们: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学老子“捧牛屁股”。捧牛屁股的父母们用捧牛屁股的收成告诫孩子以后不要再捧牛屁股,这是南角墩祖祖辈辈不曾改变的信条。
年年难过年年过,破棉袄袖子里冒出的棉絮擦掉了孩子挂下的鼻涕,冰封的河流到底封不住人们的出路。即便是冷到“大风吼,黑鱼吓得躲在大门口”的境况,人们也不曾绝望过半点,甚至苦中作乐地唱起令人脸红的歌谣:“下雨下雪,冻死老鳖。老鳖告状,带着泥匠。泥匠砌墙,告诉师娘。师娘坐在锅门口摸奶子……”男人在前面唱,孩子跟着学,女人在后面骂,骂得一路欢声笑语。
南角墩并非一无是处,她有自己的春夏秋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尽管我们在不断地离开,或者说我们是在逃离,而在离开的路上我们作为村庄的子孙感觉到这种叛离的羞愧以及代价。“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识爹和娘”,这是世间无奈的现实,但在我们的内心仍有一块坚不可摧的地方,是留给这块贫穷甚至恶劣的土地的。
我在读过几本书之后,开始自以为是地写作文。原来村里的那些识字的先生们对此有些疑惑甚至不安。南角墩识字的人不多,最有学问的属那个会读古书的老正祺,看他名字的写法就知道他的不平凡。他蜷缩在自己的小屋里,用放大镜看古书,就连油瓶倒下来都不会去扶。他一直和许多人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道理。读书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的境遇,但他依旧认真地读着那些我们从来不知道内容的古书。他留下一句文绉绉的批评人的话:不告之而取之谓之窃也,之后就在门后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此之后,村庄里再也没有什么正经的读书人。有几个读过初中的人做了民办教师,但大家也并不怎么尊重他们。对于这些一边务农一边教书的先生们,人们总是怀有一种轻蔑的情绪,他们觉得这几个“泥腿子”算不得真正的先生。有一位晚上偷了生产队的粮食,被学生们逮住吊在了房梁上嗷嗷直叫,这成为村里人讲了一代又一代证明老师也是“偷吃扒拿”的笑话。
后来,这些先生丢掉了教书工作,微薄的补助也多成为赌资而输掉,赢了钱的人还会嘲笑他们除了酸文假醋一无是处。有一位先生去世前,我去看望过他,他骨瘦如柴地躺在惨白的床单上,对于我这个后生的到来感到非常地意外和惊喜。我去看他也并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情感,只不过想起他曾经给我们写过春联——有一副记忆很深:积德前程应远大,存仁后步自宽宏。
而当我带着这些故事进城,然后又回到村庄的时候,他们总是对我表示出一种疑惑,他们不明白我这个泥腿子的后代何以能够写出文章。有一个人看过我写的散文,就悄悄地问过我:这些散文都是你散出来的?散,在他看来是写文章的动词。我不给他们任何解释,我知道这是解释不清楚的事情。
3
南角墩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一点我也心知肚明。
她最早的变化来自于一个词:打工。我至今记得那个春节之后一个还很寒冷的早晨,四叔在门口喊了父亲一声:大哥哥,我去新疆打工了。四叔学的是瓦工手艺,后来在安徽娶了老婆成家,生来不安分的他四处寻找生计,唯独不愿意“种死田”。他们打工的收入要比种地强得多,从靠天收到凭手艺吃饭,这是村庄的一次巨大的改变,当然这种改变也是带着不安和争议的。特别是一些女人外出打工,总是要被人猜测议论“不学好”了。但是这种外出一旦形成了风气之后,南角墩通往外部的小路就越来越忙碌。
人出去,钱回来。村庄的日子自然而然地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表情也开始丰富起来,日子也变得不安起来,就连逃债、离婚、坐牢这些过去难得见到的事情也光顾了村庄,这真是验证了一句老话:“穷人发财如受罪”。首先就是砌房造屋。我亲眼看到村子里的楼房一座座拔地而起,也亲眼看到花枝招展的衣服穿上了身。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带来的是人们内心的变化。有一次我在村头看见几个烫着各色头发的孩子,戴着随身听以桀骜不驯的神情等着乘车去城里,我甚至感到了一种陌生和恐惧。
南角墩的村头曾经有一座黄泥坯房子,是过去的一处牛棚。耕牛退出土地之后,这座外表糊着牛粪的屋子还是被保存下来,作为老根子与儿子分爨之后的厨房。这座屋子非常地低矮,大人要弯腰才能进入,里面也只能容下老两口在一张小桌子上吃饭。这个地方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茶馆”。房子边上有两棵大榆树,还有一座两边都可以坐人的桥,一到晚饭时分大家就都聚集到这里谈闲说笑,说到晚风清凉后回家。大人们说,小孩子听,不时还有女人的笑骂声。在电视进入村庄之前,这几乎是人们唯一的娱乐,因为广播上的内容多是听不懂的消息,大家就把这处乘凉的地方称作“茶馆”,把老根子夫妻唤作“茶馆爹爹”与“茶馆奶奶”。
让大家哄堂大笑的话题,其实早就不再新鲜,就是孩子们也早就听惯了。比如说哪家女人偷人,说门口若要是堆着一捆芦苇那就是男人在家,要是芦苇倒下来那就是男人不在,姘头远远地看到心里就清楚了。这些笑话说了很多年,大家依旧乐此不疲。可就在这座房子被拆掉之后,哄堂大笑的场景也随之轰然倒下。屋子被拆对于老根子来说是好事。他的儿子重新修缮了楼房,腾出房间给他们住,分下来的家又合起来这不算是坏事。
但是,从此各家各户的门也都关上了。人们似乎不再需要那些简单的笑话,不需要红白喜事喊戏班子来唱戏,也不再需要一边冻得瑟瑟发抖一边在大队部看电影——电视机里有演不完的节目。
三荡河流域的村落在二十年前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遇,那就是作为农业开发的试点。一种从外国来的虾子爬进了村庄,以几何级生物入侵的速度占领了村庄里的土地。过去南角墩也是种过经济作物的,蚕桑的效益不好,棉花的种植劳累,薄荷的价格波动——父亲还和四叔一起请安徽人来下西瓜,但因为销路不好而又回到稻麦两季的原始模式。但这一次不同,一种叫作罗氏沼虾的外来物种进入了流淌千年的淡水,彻底改变了南角墩的生活。人们在科学的方法下算清楚了一笔账:流转出租的土地租金远远高于稻麦两季的收入,养殖大户又带来了用工的需要,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工人。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笔不划算的账,于是成片的良田在挖土机的轰鸣声中变成了鱼塘,农民变成了渔民,成了工人,甚至成了贩卖虾子的经纪人,好日子在种植退出历史的代价下变成了现实。
三荡河边的草木森森变成了标准化公路两边四时常青的整齐花木,空调调节温度的村落变得更加舒适惬意,只是村庄似乎不再是那个满身尘土的孩子。父亲老了,脾气也没有了,和颜悦色地骑着车子重新干起了老本行养鸭子。那些鸭子依旧是先知春江水暖的鸭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记录过这些变化。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然“被逃离”这个遥远的村落。
我得用一生的时间找回那座水边的村庄,可能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