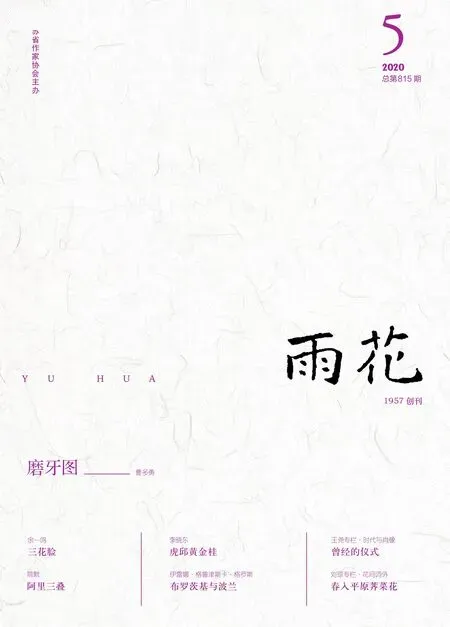青莲
2020-11-22王耘
王 耘
一
有一天,去给小乖做手术,绝育。想起我们教研室刘锋杰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养狗最大的坏处,莫过于它会死在你前面,你必须无可奈何地看着它死去。听到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像是没有丝毫防备,“扑通”一声掉进了冰窟窿里,如今才知道,在那“扑通”一声以前,内心早已如履薄冰。
每次带小乖出去遛弯儿,总觉得她与其他的同类迥异。其他的同类步履迟缓,漠然、厌倦,甚至凶狠地敌视着来往人群,小乖不同,她见了谁都示好,拼命地摇尾巴,又没有尾巴,就摇屁股,动不动就扑上去,舔人家,要人抚摸要人抱,让我很是尴尬,现在,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以前,她的眼睛乌溜溜的像漆黑的两颗葡萄,单纯、无辜而充满渴望地看着我,没有半点戒心。如今,她不肯看我了,总是避开我的眼神,朝另一边去,她的眼神,变得忧郁。看着她棉垫上的斑斑血迹,看着她一次次转过头,我拼命地想,我做错了吗?坐在书桌前,写下这行字的此时此刻,她趴在我的怀里,枕在我的腿上睡着了,一边睡一边颤抖,还打起了呼噜,我想,如果她不醒,我大概会在这里坐一夜。
小乖的生命,一条狗的生命,究竟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由谁来决定?
人生本没有什么绝对的意义,意义皆由人造,而那个人造的意义,在本质上,只属于相对而言的“自己”。艾布拉姆斯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为《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不仅是西方文论的扛鼎拔山之作,也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典型的意象:作为反映的条件——“镜”,和作为烛照的力量——“灯”,这两种典型的意象共通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影子”。
先讲一个关于“影子”的故事吧。
从前,有个漂亮的小伙子,娶了个美貌的女子为妻,新婚夫妇两情相悦,如胶似漆。有一天,丈夫对妻子说,你到厨房里去,拿点酒来,我们喝上几杯。于是,妻子就来到厨房,打开酒瓮的盖子,突然,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为酒瓮里还藏着一个美貌的女人,惊慌失措,回到卧室抱怨她的丈夫,原来你欺骗了我,你已经有了女人,就藏在酒瓮里,以为我发现不了吗?丈夫听了这话,感到非常生气,急忙跑进厨房,揭开酒瓮的盖子一看,哪里有什么女人,分明是一位男子!于是,他勃然大怒,呵斥妻子,明明是你把情人藏在酒瓮里,却混淆视听,恶人先告状!
就在这时,一位老者从他们的门前经过,听到他们争吵,前来劝解,询问他们争吵的原由,夫妻两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老者听后,前去厨房查看,发现酒瓮里既不是丈夫的情人,也不是妻子的情人,而是一位须发全白的老者!他很不高兴,你们两个分明是在假装争吵,戏弄我,拿我作乐!而家中供养的女尼也来劝解,最终,在酒瓮里又看到了一个女尼,亦拂袖而去。一个行脚僧人听说此事,前来查证,发现酒瓮里除了酒以外,什么都没有,于是,他拿起一块石头,把酒瓮砸碎了,酒洒了一地,所谓的影子,再也没有了。这个故事的原型,可以参考《杂譬喻经》。
这个故事的寓意不在于嘲讽人的蠢笨无知,看不透酒瓮里所呈现的是与“我”同形而异质的虚像、幻象;一种更为偏执的“所知障”在于,所有众生在酒瓮里看到的都是“自己”,且把“自己”当作了仇敌。
最后那位砸碎酒瓮的僧侣,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他不过是使众生再也无法看到那与“我”异质的虚像、幻象,破坏看到的机遇罢了。酒瓮可以砸碎,但有些东西,是砸不碎的。所谓的酒瓮,就是处境。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只是我们内心想看到的一切。在我们内心想看到的一切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把自己当做充满恶意的仇敌——我们所仇视的,其实是我们自己。除非,我们看到的是一朵青莲。
二
我常给学生做一个游戏。首先,把学生随机地分为两组,比如,戴眼镜的一组,穿T恤的一组,长头发的一组,学号尾数为偶数的一组。其次,每个组内部讨论,推选一名组长,自定名号,比如烂草莓队、中年美少女队、我舍不得你队。再次,宣布游戏规则,发给两个组长两张牌,牌面有正有反,共有五局出牌机会,每局同时出正牌,双方各得100万,同时出反牌,双方各得30万,一方出正,一方出反,正方得数为0,反方得数为50万。游戏开始,由队长组织组员讨论并出牌。讨论到第三局时,我会加码,把所有得数都乘2,例如双方同时出正牌可各得200万,出反牌可各得60万,一正一反,正方为0,反方为100万,第四局时,再加码乘2,第五局,再加码乘2,这意味着,第五局时,筹码已经是初始值的8倍。十几年来,经过我手,做过这个游戏的人数,大概三四千。一条“颠扑不破”的“魔咒”是,这三四千人里,从来没有一次,双方五局同时出正牌。
命运有可选的部分,有不可选的部分。可选的部分是,每个人都有五次出牌的机会。这五次出牌的机会,是人生的五个路口,五处“坎限”,五次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是公平的——例如,一个人有没有上过大学,有没有读研究生,婚姻的对象以及择业的方向。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五次选择。
每一次出牌都不是终身制,但每一次出牌都意味着必须为“成长”付出代价。我们经常听说一句话,叫作“做自己喜欢的事”,可今天大多数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于是,你得为自己没有“成长”到深刻了解自己“喜欢”什么而补课——试错。试一次,发现选择错误,从头再来。就像大学毕业,没有考研,择业后发现选择错误,重新考研,试错后弥补。就像找对象结婚,婚后发现不适合,离婚,再婚,可以吗?可以。但最好不要错,因为试错的“学费”高昂。最后一次出牌的时候,如果还错,付出的代价将会是最初那个选择的八倍。当然,如果对了,收益也会是最初那个选择的八倍。
不可选的部分是,与他人之关系的前提假设。被分在哪一组里,是自己选的吗?不是,是我选的。我是谁?我是“上帝”。“上帝”为什么要这么选?“上帝”选择的理由是不可知的,你在根本不知道“上帝”如何选择和“上帝”选择的前提时,被迫入局。可以反抗吗?不可以,游戏已经开始,只能接受命运假设。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因为我一定要来,而是因为要来的一定是我——这是自由的前提。直到十六岁那年,我才非常确定,我这一生都无法长成费翔了。为什么我生而为“土豆”的模样?不为什么,这是命运的前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命运的假设,包括费翔。如果我不接受“土豆”的模样,那么我连属于“土豆”的自由都没有了。所以海德格尔讲,我是被抛入命运的网罗的,所谓抛入,必然是不可选择的,没有道理可讲。
如何看待命运,构成了人生的基调和内容。做这个游戏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大概有百分之十五的团队会民主投票——出正牌还是出反牌,依据是投票的结果。然而当一个集体自发形成其组织性的时候,“民主”事实上不是必选项,而主要由团队的“首领”——组长来决定。在我的印象里,这三四千人,没有一个团队出现过“革命”,即罢免组长,弹劾组长,投票另选组长,抑或解散团队、撤出游戏的现象。
一个人如何看待游戏,和一个人如何看待人生,非常类似。有积极的人生,也有消极的人生,有参与的人生,也有游离的人生。有的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何必当真,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游戏,你所遇到的,所见的所闻的,皆是修行,均为道场。与之相应,一个团队中的灵魂人物,通常不是组长,而是团队中的“智多星”,他们会权衡利弊,提出主张;而人群中的大多数是沉默者,或曰个人完美主义者,他们冷眼旁观这个世界,放任猜忌,不主动怀疑。即便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局,对方会出什么牌。
若想通明、深刻,就应当拔离这一切。在这个游戏中,我通常会选择第十一个人做观察员。观察员会记录在游戏过程中,每一分每一秒双方组员各自的动向和语言,就每个人对外在遭际加以分析和判断而做出的改变形成波状图。这第十一个人,明察秋毫、洞若观火。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几率,会有参与者提问:这个游戏怎么算输,怎么算赢?我只会默然不语。你问“上帝”,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算输,怎么算赢的时候,上帝回答你了吗?没有,而时间正在流走,持续消逝,经历了反反复复地试探、掠夺、背弃和证明,该出牌的时候,还是得出牌。问话的人,往往是“哲学家”,抑或“思考者”。有趣的是,当问话的人提出问题的时候,观察员时常是微笑着的,他的微笑来自于他的“高度”,他凌驾在这个世界之上,一种无功利的俯览“孕育”了他的睿智与豁达。所以,想洞彻这个世界,唯一的方法,是在不得不参与其中的同时,实现对这个世界的“俯览”。佛法,起源于一种“俯览”。“美”,是佛法俯览的“青莲”。
无论如何,人生是残忍的,人生的这场赌局,必须自己去赴约,自己去博弈,自己去收获,自己去补偿,夜不成寐,马不停蹄。所幸的是,这一次选择和下一次选择之间,这一轮赌局和下一轮赌局之间,有漫长的时差可以等待,可以置换,你有空发呆,在不得不被符号化的同时,聆听除了所谓人生之旅外的,关于他者的“回响”。
所以我喜欢旅行,做背包客,有一次在莫干山的竹海里独自行走,那些参天的毛竹像一片绿色的海洋,被风抚动,一浪接着一浪,道路被淹没了,无人烟的世界,却并不荒凉。就像你也需要旅行,却并不需要遇见我。无论你信什么,都不要信人性。你信上帝,你信天空,你信神灵,你信万物,你信你五次选择之外的风霜、绿叶、大漠、残雪,都比你信人性要安全。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人性不够抽象,不够遥远。
三
从前有对夫妻,姿貌端庄,耳鬓厮磨,终日尽欢无厌。突然双双失明,目无所睹。他们害怕失去对方,相拥而泣,须臾不肯分离,长相厮守。于是,五服之内的亲属四处寻访名医,从远方聘以重金,请大夫来到这对夫妻的住所,为他们诊疗眼疾。终于有一天,他们同时重见了光明。丈夫见到妻子的第一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呵斥,这不是我的妻子,是谁偷换了我的妻子?!妻子见到丈夫的第一面,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呵斥,这不是我的丈夫,是谁偷换了我的丈夫?!一旁的亲属急忙劝慰他们,你们只记得彼此昔日的容颜,殊不知数十年业已过去,日新月异,沧海桑田,头发会逐渐稀疏,皮肤会逐渐松弛,体力也会逐渐衰弱。容颜的改变一天天发生,常见之人不易察觉,你们虽然生活在一起,却许久未曾谋面,到如今,却还惦念往昔,岂不是“钻冰求火”吗?这个故事,取自《出曜经》。
这是一个佛法“瓦解”审美诉求的典型案例。如果从现实的审美活动来看,这个故事的主题,不是对美的驻守,甚至无关乎爱的加持,而是时间流逝无可挽回的证明,是岁月之于美的无情解构——夫妻二人“华美”的“颜色”,在他人的眼光中,渐次消失了,而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却因永恒持存,继而如被攻陷的城池,瞬间轰然坍塌,化为粉末。佛法所意欲表达的,岂不就是美的脆弱和易损?如果美只是片段的、当时的、无法久驻的,乃至无法用爱来储存、累积的,就必然会遭到佛法的否定。
然而,无论是丈夫也好,还是妻子也罢,他们对于刹那生灭、缘起性空的感知,都是由他们自己得出的。当他们失明时,他们没有问因,当他们复明时,他们还是没有问因,他们只接受那个结果,他们认为,那个结果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五服之内的亲属并没有告诉过他们将要面对的现实,五服之内的亲属只是叙事单元里的帮助性元素,帮助这对夫妻完成了一场穿越了数十年,少年的彼此与老年的彼此当下的“照面”。之于人生,人生之美如同泡影一般这个事实,只能由主人公自己了解。
我们接着会发现,佛法解构的只是美的片段性、当时性,无法久驻,乃至无法用爱来储存、累积,一言以蔽之,佛法解构的只是美的有限和有限性,它在告诉我们,那些外在的、形式的、易逝的、可以被我们的五官感知到的美是不可靠的,起码抵挡不过时间的“流水”。佛法向我们敞开了一个无限的世界——这个无限的世界,是一个本真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能用众生所认为的既定的“美”与“不美”来界定,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在于“空灵”。
再讲一个故事。
从前有位国王,他特别想要有一位美丽的公主,有一天,王后真的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国王满心欢喜,欢呼雀跃。他看着襁褓中自己的女儿,盼望她快快长大,立刻长成一位芳华绝代、亭亭玉立的公主。于是,他把御医找来,传下命令:你快去找灵丹妙药,给我的女儿服下,让她马上长大!
御医想了想,说,我的手上倒是有一副方子,可以让公主立即长大,但要跟您讲一个条件。国王问,什么条件?御医道,这副方子里有几味药,我要到雪山里去寻找,在我没有回来之前,您绝对不可以与公主相见,等我回来,公主服药之后,你们才能相见!
国王为了见证奇迹,一直坚守自己与御医的约定。一转眼,十二年。这十二年里,国王的的确确做到了不与公主见面。十二年后,御医回来了,给公主服下了他采来的仙草,通知国王,现在可以传见公主了。当国王见到公主的那一刹那,他似乎有了恍如隔世的感知,内心狂喜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襁褓中的婴儿,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位婀娜多姿而仪态端庄的少女!他给了御医以丰厚的赏赐,盛赞他是举世无双的良医,找来了举世无双的仙草,居然能够创造如此不可思议的奇迹!这个故事,取自《百喻经》。
如果说第一个故事讲的是美的消逝,第二个故事所讲的,岂不就是美的诞生?美究竟是在诞生还是在消逝,不重要。公主迟早会变老,变丑,直至死亡,与她朝夕相伴的王后也不会觉得御医创造了奇迹,就像第一个故事中失明的夫妻同样可以生下一个美丽的孩子,并在重见光明时看到这个孩子,为什么没有?因为每一个故事有每一个故事的内容和主题。然而,当我们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佛法之所以可与审美相通,恰恰是因为它确实能够使人进入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在这里,故事的主角不是公主,而是国王,第一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的共同点就在于,美的诞生与消逝,都是主人公独立面对的事实。
最后讲一个故事。
从前有位性格乖戾而跋扈的公主,她喜欢下雨,尤其喜欢雨水滴落时在池塘乃至地面上激起的水花,于是她跟她的父王说,我要一只用水花编织的花环!国王为难,水花又拿不到手里来,怎么可能编织成花环呢?娇生惯养的公主撒起娇来,一边跺脚一边哭闹,说得不到用水花编织的花环就自杀!这下,国王可吓坏了,于是召集城中的能工巧匠,吩咐他们必须用水花编织花环,做不到,统统杀掉!
工匠们都傻了眼,纷纷抱怨,您就是砍了我们的脑袋,我们也做不出来啊!不料这时,有位年长的工匠说,我可以为公主编织花环。国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公主,公主兴高采烈地来找这位工匠。工匠说,公主既聪明又美丽,聪明美丽的公主都喜欢水花,我可以为公主编织用水花做的花环,不过有一个条件,请公主为我挑拣出心仪的水花,交给我,我才能为公主编织花环。于是公主就在地上看了又看,选了又选,觉得喜欢,伸手去拿去接去挑拣,结果水花纷纷破裂了,无一例外,最终,一朵水花也没找到,公主瘫坐在地上,既沮丧,又疲倦。这个故事,亦取自《出曜经》。
在这个故事里,佛法与爱、与美,天衣无缝、水乳交融地“糅合”在一起,无分彼此。公主所喜爱的水花,在她眼前一朵朵破灭,如同这世间的各种欲望、情感,捡不起来,丢不掉。在这三个故事里,最伤感。
这三个故事,说的都是“想要”。有的“想要”要到了,有的“想要”要不到,有的“想要”等得到的时候已经变质而不再“想要”,有的“想要”永远也得不到,即便它就在你的面前如魔术一般变幻着生死。人生总脱离不了“想要”二字;佛法所做的,恰恰是对于“想要”的沉思。在一个空灵的带有否定意味的时间“甬道”里,审美是最不可靠、却又最能够让我们在“绝望”的咫尺毫厘间,敞开自己的“青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