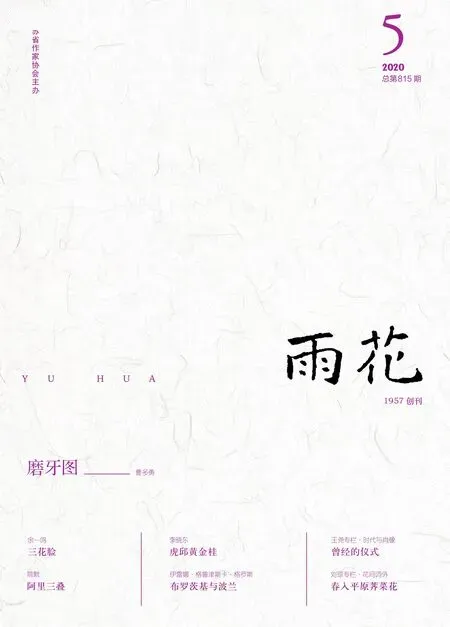阿柳
2020-11-22余静如上海
余静如(上海)
九月末的傍晚,长江大学学生公寓外边人声喧闹,小吃摊上方的空气中弥漫着层层烟雾。炭火、调料和种种食物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夹杂着一丝夏末的气息,钻进阿飞的鼻子里。
阿飞戴着头盔,骑在他的红色雅马哈上,单脚撑地。透过头盔,他眯着眼睛在人群里懒洋洋地搜索,他并不是在寻找潜在的顾客,只是在看那些从公寓大门里走出来的女学生。他看见她们像一条条小鱼苗那样从幽深的门洞里钻出,她们中的许多人穿着短裙、露着大腿,呆头呆脑,脸上带着愚蠢的笑。还有一些女孩灰头土脸,抱着书本或是帆布袋子,对周遭表现出毫不关心的样子,急匆匆地走。
阿飞点上一支烟,嘴里含含糊糊地骂着什么。他喜欢看这些女学生,当其他摩托都停在车站拉客的时候,他只是停在学生公寓外边。
“又在等女学生啊,阿飞?”一辆飞驰的摩托从他身边过去,“找个老婆吧!”
阿飞呵呵笑着。心里又骂了一句。他喜欢女人,但不是每个人都想娶老婆,他有一个固定的相好,名字叫“花”。花住在一间临街的房子里,那地方离学生公寓只有两公里的距离。花和小姐妹们一起租了几间房做生意。临街的那一间便是作广告用途。阿飞把那个地方叫作“老来乐”,倒不是那家店真的起了这么个名字,而是店旁边正好有一家老年棋牌室,“老来乐”的招牌花花绿绿地亮在顶上,顺带替花的店招揽了顾客。花的店并没有名字,但窗帘总是拉开的,大家一看,就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花和小姐妹每天穿着各式低胸裹身裙,尖头高跟鞋,在里面大大方方地,或坐或躺。冬天也如此,开足暖气。有时候她们站起来,走几个猫步,照照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算一算自己的价格。她们从来不往外看,就像商品不会看它的顾客。那里的顾客形形色色,男学生们也会光顾,其中大多来自于阿飞面前这个公寓。花会跟他讲那些学生的蠢事,如何在门口转悠,等待她们出来拉客,花也会讲那些来自后面小区的老年顾客,装作走错了门到了她们这里。花是个有趣的人,阿飞喜欢和她一起聊天,两人总是被对方逗得哈哈大笑。
阿飞脑子里无边无际地想着,一个女生闯入了他的视线。那是个高个子的时髦女生,穿牛仔短裤,卷发扎成马尾。阿飞默默朝她移动,看见她皮肤白净,五官标致,脸颊微微发红。她像是赶着要去做某件事情,孤身一人,神情紧张,左右张望着,看着马路上来往的汽车。阿飞掐灭了烟,转过车头滑到她面前。
“坐车吗?”阿飞按捺住心中的期待,不让它出现在脸上。
女生这才注意到面前的他。“坐。”她立刻回答。她有好听的声音,在回答的同时她高高抬起右腿,一步跨上摩托车的后座。好长的腿,阿飞心里赞叹,目光迅速在那条白花花的腿上掠过。阿飞转过头,目视前方,发动摩托。他内心充满了愉悦,尽管他无法回头欣赏后座上的女孩,但依然想象得出这一刻的场景:他的摩托车上坐着一个漂亮的长腿女孩,她的卷发很快就会被风吹得舞动起来。
“去子山坡。”女孩说。子山坡是附近的一个景区,海拔不到五百米的一个小山包。
“好嘞!”他回答,开始载着女孩在车流中穿梭。
“虽然我很急,但你还是开慢点吧。晚几分钟也不耽误什么……”女孩说。
“好。”他回答,同时感到女孩的身体离他很远,她几乎没有碰到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可能连衣服都没有碰到。这让他感觉失落,这样的话,载着女孩跟载着一袋大米也没什么区别。不如和她说说话吧,他想。
“这么晚了你去子山坡干吗?”他问。
“哦。”女孩轻轻一声,随即急躁起来,抱怨道,“我把社团租的自行车忘在山上了。我还没锁,可别被人偷了。”
“噢,那确实要紧!”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得在天黑之前找到它才行,不然我只能赔钱。”女孩又说。
“对,不然下山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说。女孩的身子突然一抖,她似乎才想起来这个问题。
“对,我还没想到呢!我只想着要在天黑前找到它,因为天黑了不好找。”女孩说着,抬头看了看天空。
天空依然明亮,只是风明显地变凉了。女孩突然打了个寒噤,他感到女孩靠近了自己一点儿。他把右手伸到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找东西,他的指关节碰到了女孩的大腿内侧,柔软的、温热的。女孩又往后挪了挪。他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只打火机,又把打火机放进胸前的口袋。
“不然,还是开快点吧。”女孩说。
“好嘞!”他兴致高昂,加速,晚霞被他们抛在身后。
“多好看啊!血红血红的。”他说。
“什么?”
“晚霞啊!”
女孩又抬头看了看,说:“你又没看见。”
“我每天都能看,不看也知道。”他哼起了歌,是一首很老的网络流行歌。
他唱:“小薇啊,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
天又暗了一些。
“别着急,天黑前肯定能到的。”他说。
女孩不再说话。
他想象着女孩此刻的样子,她有点冷,又很着急,她怕天黑前找不到车,又怕天黑之后看不见路。她一定双手牢牢握着摩托后边的杠子,紧紧抿着嘴。
“这是你第一次坐摩的吗?”他问。
“嗯。”女孩用很轻的声音回答。
“摩的确实不太安全,以后少坐。”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说了这么一句话。
女孩不说话。他觉得女孩似乎又往后挪了一点,他敏感地察觉到,女孩有点儿害怕了。女孩是怕摩托车危险,还是在担心到了山里天会黑?
“你这样挺危险的。”他说,立刻又补了一句恭维话:“你这么漂亮。”
“……是有点危险。”女孩说。他仿佛听见她在说话的时候,上下牙彼此磕碰着。
他确定女孩是害怕了,只是不知道女孩是不是和自己想的一样。他想,女孩现在才觉得害怕,未免太晚。天快黑的时候,叫一个摩的,把自己送到山上去?子山坡只有上山入口处亮着路灯,后边都是一片漆黑。她就不该去找那个自行车,要知道她自己比那辆车值钱多了。
“子山坡上,不久前还出了个案子。”他说。话说出口,好像听见她小小地惊呼一声。
“杀人碎尸,尸块都丢在垃圾桶里。”他继续讲,满不在乎的语气。
“那地方太不安全了。”他感叹。
“你怎么会知道!”女孩尖声问他,他感到女孩的身体整个在摩托的后座上弹了一下。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好笑地反问。女孩却更紧张了。女孩的消息来源是院里的学姐,可怜的学姐是尸体的目击者,晨跑时发现尸体。学姐报了案,接下来的半个月都没有走出阴影。
“新闻又没有报道这件事情!”女孩质问,“你从哪里知道的?”
“我从哪里知道的?”他喃喃自语……他从哪里知道的呢?是花告诉他的,他还知道那具尸体的名字,她叫阿柳,是花的一个小姐妹。花告诉他的时候,他怎么也想不起来阿柳的模样。花开玩笑说,就连自己也想不起阿柳的面貌,她年纪有些大了,长得也不算好看,性格也不好,总是坐在沙发一角,低着头。店里只要不忙,大多数客人不会找阿柳,她只好做外边的生意,用QQ和别的软件找客户。花说,阿柳在网络上很能聊天,跟换了个人似的。跟她聊得热络的人,大多不会在意她不够好看。她也愿意出去做生意。阿柳死得很惨,警察找到花才确认了阿柳的身份,垃圾桶里只有阿柳的身体,头颅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想着这些事情,风更凉了一些。
“你怎么会知道?”她又问。
要告诉她阿柳的事吗?他想,如果她问他的语气好一些,不要那么盛气凌人,他就讲给她听。
“你怎么会知道?”她又重复一遍,让他想起初中的时候,学习委员替班主任检查作业。
“女孩子管这些做什么!”他说,他希望自己也能对当年的学习委员这样讲。
她不说话了,他猜不到她在想什么。
“我有个妹妹。”他迟疑了一下,说。
“噢……”女孩呼出一口气,他脖子痒痒的。
“你妹妹,也在我们学校是吧?是她告诉你这个案子的?”女孩问,语气平缓了不少,但声音里依然带着紧张的情绪。
“嗯……算是吧,离你们不远。”他回答。他并没有妹妹,他脑子里想的是花。
“什么叫算是?她是艺术学院的?”她试探着问,他才不知道什么艺术学院呢,也不知道艺术学院和长江大学有什么关系。
“嗯。”他答。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事,太残忍了,没有人性。”她说。
“这也是人性。”他为自己这一句回答沾沾自喜。
“也不知道案子破了没有,凶手抓到没有。”她说。
“我看没有。”
“为什么?”
“因为死的是一个没人关心的人,不重要的人。”
……
“那她也住在我们公寓?你常来这吧?”她接着问。
“谁?”
“你妹妹。”
“哦,对,我常来这,你们这儿,包括子山坡,我都熟得不得了。”他答。
“你停下。”她厉声说。
“怎么了?”他并没有停下,天又暗了一些。
“你骗我,艺术生根本不住我们这个区。”她嚷嚷,“你给我停下!”
“我管你住哪个区!你管得着我妹住哪个区吗?”他反问,和她拌嘴让他觉得开心。
“停下!”她在后座不安分起来,用拳头击打他的背部,他知道她用了些力气,她想让他明白自己认真要他停车,却又不敢使出全力。他并不觉得多痛,他的好心情也没有受到影响。他很善于和女孩聊天,他载过不少从长江学生公寓里出来的女孩子,和她们都聊得挺开心的,有几次他甚至还要到了女孩的QQ号。不过,再联系她们的时候,她们要么不理会,要么翻脸不认人。他想有些人可能真的忘记加过了他。这也很正常。
“别闹了,你这样我们都很不安全。”他说。
“那你停车。”
“这不就到了吗?还停什么车?”他的话音刚落,他的摩托车就带着他和女孩驶入了一片巨大的阴影,那阴影来自于他们头顶上的马尾松。进山了。
光亮和温度都在这一瞬间降下来。他的速度也降下来,这是上坡路,路上已经没有游客,只有树叶的沙沙声和飞鸟扑腾翅膀的声音。他想到,如果他想对这个女孩做点什么的话,此刻很容易。他只要加大马力,驶上一条小路,在女孩下车的时候把她制服,手套可以堵住她的嘴,也可以直接用拳头把她打晕。他不怕她看见他,他戴着头盔。他可以把她拖去一个最僻静的地方,完事之后把她丢在那里,她最多承受一个恐怖的夜晚,天亮时就会发现自己在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找到回去的路。别管她事发当时怎么想,第二天,当阳光照在她身上,她回到温暖的被窝里,可能不会对任何人提起前一天夜里发生过的事。
这似乎完全可行,他为自己放弃这个机会感到遗憾。
“不要往前开了。”女孩说。
“还没到山上。你不是说停在山上吗?”
“我在这下就行了。”
“你自己走上去?那时天就黑了,你什么也看不见。”
“我男朋友就要来了,马上就来。”女孩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他愣住,随即便明白她在说谎。他没有想到她这样害怕,不过她的害怕是合理的,如果他下定决心把刚才脑子里所想的事情付诸实践。但他怎么会那样做呢?他会保护她,他是一个好人。想到这一点,他感到心里很温暖。用不了多久这女孩就会感激他,向他道谢。
他加快了速度,阵阵山风袭来,他的汗水隔着衬衣在蒸发。他发现自己快到阿柳被发现的那个垃圾桶了,他朝路边看去,一个又一个垃圾桶在他眼前掠过。
“好像是这个吧?”他不由自主地说。
“什么?”女孩疑惑。
“阿柳,那个被杀的女人。”他说,他以为她会因为受到惊吓而抱住他的腰。果然女孩的呼吸急促起来,但是女孩的恐惧超出他的预料,她将手里攥着的人造革背包带子伸向他,套住了他的脖子。女孩扯着背包,惊恐万状地从摩托车后座上向下跃。雅马哈摩托向前冲了几米便歪倒在地。女孩的手松开,侧身落地,像个车轱辘一样沿着山坡滚了几滚,他仰面躺着,脖子上还缠绕着长长的人造革包带。
他后脑着地,晕过去了。女孩的伤势比较轻,只在胳膊和腿上。
女孩慢慢爬起来坐着,她活动了手脚,确认自己没有伤到骨头,然后站起来,呆呆望着仰卧在地上的男人。她在学校社团里学过女子防狼术,虽然没有一招适用于刚才的那种情况,但至少那段学习的过程让她对男性有了防备意识。就在上一秒钟,她还处于极度恐惧之中,那恐惧从她第一次抬头注视天空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她发现自己的决定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但那会儿她还抱有侥幸心理,她想,恶人并没有那么多,她更担心那辆租来的自行车,车子被盗是很常见的事。她可不想赔钱,一分钱都不想拿出来。随后,天越来越暗,而这个开摩托车的男人,话也越来越多。她开始担心自己,她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她很早就从路人和男孩子们的眼睛里发现了自己的好看,她也知道这个开摩托的男人对她有意思,若不是她急着打车,这开摩的的小子恐怕没机会和她这样的女孩说这么多话。许多人都想和她搭话,在平时她可以不理会,可这一次她已经坐上这个男人的摩托车,还指望他快点把她送到目的地,让她免去赔偿的苦恼……她意识到自己和对方力量的悬殊,她越来越倾向于做最坏的打算,他可能是个耍嘴皮子的正经人,但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他是一个罪犯,是一个暴徒呢?那个结果是她不能承受的。
他没有死吧?她走近看了看他,从他的脖子上解开缠绕着的背包带,他的腹部随着呼吸起伏。他戴着头盔,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她安慰自己,但同时又陷入了矛盾,他并没有对她做出任何不好的举动,这样看来,她才是犯罪的那个人。她掏出手机,犹豫着,这得比她点一个外卖耗更多的时间。手机的信号在山里很弱,时有时无。天更暗了,她把手机放回口袋,决定先去找自行车。她朝上山路奔去。
她跑得满身是汗,其实不过是一百米的距离,她站在坡顶了,这里是一块平地,树木被砍伐干净,造了凉亭和围栏。站在这里,她可以俯瞰这座城市的一小部分,远处是灯火阑珊,车水马龙。身旁是月光,周遭的一切被它洗得干干净净。
她找到了自行车。它安静地停在一棵古老的栲树下,像一匹乖巧的马驹,等待着自己的主人。她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若是第二天来找,它一定不在这儿。她走向它,握住把手,轻盈地上车,预备好在山风中滑下坡去,但她只坚持了十米不到便停下了,因为她发现自己被遮蔽在层层叠叠的树影下,夜晚已经来临,高大的树木把月光挡得严严实实,她什么也看不见。
真的什么也看不见,她伸出手,不见五指。
她从车上下来,握着车把的手心里全是汗。陌生的巨大的黑暗挟裹着她,她看不见,身体的其他感官因此变得敏感。树林里潮湿冰冷的空气紧贴着她,她像是落在水里。她仰头,又立刻低下头,她想看清楚,又怕自己看到什么不好的东西,更怕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有什么东西在远处怪叫,高亢又撕裂的声音,不用怀疑,那是某种鸟类。只是她从未听过鸟类发出那样的声音,或许她一直过得太安逸了,她只知道百灵、八哥、鹦鹉会发出什么声音。不知道鸟会叫得那样恐怖、绝望。她还听见别的声音,她才知道,原来自然中不仅有鸟,有虫子,有风,有树叶和草,还有别的,太多的让她分辨不出的声音。那些声音和潮湿的空气黏在一起,紧紧贴着她裸露的肌肤,从她的鼻子、耳朵、口腔,进入到她的五脏六腑去。她想,她不能排除其中也有人的声音,假若此刻有人在附近,他发出的也是自然的声音,他只能和自然融为一体,因为他太微不足道。她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步子,一步比一步艰难,好像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拒绝她,倒推着她。她的心脏紧缩成一团,孤寂有力地跳着,她第一次无比清晰地听见自己心脏的跳动,它跳动在咽喉里,在耳边,在大脑的血管里。她无比怀念曾经体验过的无数个安稳的黑夜,在自己小小的卧室里,她闭着眼睛,知道四面是墙壁,知道自己与墙壁和天花板大概的距离。而现在她什么都感受不到,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里,有些东西离她很远,有些东西离她很近。
她开始大口喘气。心脏跳动的声音和她喘气的声音夹杂在一起。它们发出巨响。她恍惚中被唤起了动物的本能。她知道自己应该静下来,她的动作,她散发出的热量,这一切都会唤醒危险物的知觉。她紧闭双唇,可她的下巴抖得厉害,腿也抖得厉害,她渐渐失去了力气,屈腿坐了下来,倚靠在租来的那辆自行车旁。她抱住双腿,缩着脖子,不敢看周围的一切。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她突然想到了一个名字:阿柳。
阿柳便是那个死者的名字。她想,阿柳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会死在这里,死后仍被残暴地肢解。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当她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她感到可怕,这件事情比其他耸人听闻的案件更可怕,也更刺激。因为它就发生在离学校最近的一个景点,学生们常去的地方,目击者还是学院里的一个学姐。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感到这事情离自己很遥远,那个陌生人的惨剧给她造成的震动,甚至不超过一天。而此刻,她意识到,她离阿柳遇害的地方这样近,也许比她想象得更近。阿柳的命运,终于和她产生了一些联系。阿柳的惨剧,是否也并不如她以为的那样遥远。她恐惧得闭上眼睛,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她脑子里幻想着阿柳在那个罪恶的夜晚经历的一切,阿柳遭受了怎样的绝望,遭受了怎样的身心的痛苦。她终于感到难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阿柳。她的脑袋因为哭泣开始发热,身心却渐渐恢复了力量和勇气。悲哀的情绪短暂地将恐惧清除,她的理性又回来了,她知道自己比阿柳要幸运。她站起来,重新握住车把。她掏出手机,老款的诺基亚手机发出微弱的光,只照亮她脚下的一小块地面,光源暴露了她,几只蛾子慢悠悠地从林子里飞出来,在她的手边绕着飞舞。她紧盯着脚下的一小块土地,不敢往四周看。
她在看不清路面的情况下试着骑车,黑暗中滑行的速度让她胆战心惊,她还是停止了,继续推着车一步一步向前走。不知道走了多久,她的手机耗尽了电量。她只得再一次停下,站在原地。她觉得自己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但时间只过了五分钟,她离出口到底还有多远?她茫然望着前方,她责怪自己胆小、愚蠢,她知道自己一直走就会走出去,或许她与光亮的世界只有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可她就是动不了。她陷入了漫长的折磨。
他醒了,眼前是一片漆黑。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他以为自己躺在出租屋的床上,之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个梦。但很快他就明白了,他记起那个一步就能跨上摩托车后座的长腿女学生和她做出的激烈举动。她跳车逃走,而自己被摔晕。真是倒霉,他没想到女学生竟会吓成那样。碰上杀人犯的概率有那么大吗?他坐起来,把头盔摘下,一只手在脑袋上仔仔细细地摸着,检查有没有伤口,一边想着这个问题:难道自己看起来像个杀人犯?他想起了阿柳,他记起自己和那女孩说的最后一句话便是关于阿柳的,一定是那句话吓到了她。他同时想起来阿柳被发现的地点,那个垃圾桶,就在附近。阿柳死后,花曾经让他陪自己来山坡上走走。她带了纸钱,到垃圾桶旁边烧掉。花在烧纸的时候遗憾地说,不知道阿柳的头颅在哪里。当时他还开玩笑,说可能在山上的湖里吧。花很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如果他是凶手,他就会那么干。花还要问为什么,他也答不出来,说反正要是他,他就会这么干。
他站起来,在口袋里摸索,打火机还在,烟也还在。他打出火,点燃香烟。看见他的摩托车就躺在不远处,他初看时被它吓了一跳,因为它那样子像一具尸体。他没有立刻走向它,而是走向了路旁的垃圾桶。他想,一个活生生的人,竟可以被装进这里。他对那个做出这件事情的人感到愤怒,他的愤怒来自于那个罪犯的狂妄:把尸体放在这里,故意让路人发现,还藏起了头颅,就像开玩笑那样。他想,如果他能碰上那个家伙,他会揍他一顿。他要扭断他的两只手腕,把他的脸按在地上摩擦。他要让他伸出舌头,把这条路上所有的垃圾桶都舔一遍。想象了这一切之后,他的烟抽完了。他将烟头丢在地上,踩灭。
树林里的空气很好,他深吸一口气,活动活动筋骨。随即点亮打火机,走向自己的雅马哈摩托。他抬头看了一眼,他从未发现这里的树木那样茂密,严严实实地阻隔了所有的光。他发动摩托车,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林子里的鸟惊得扑腾起翅膀。车灯将前路照得雪亮,他使这个地方又变得寻常了。他沿着下山路驶去,那女孩的身影又浮现在他的脑中。他并不感到生气。
他调转车头,继续向上山路开去。
当他的车灯照着那女孩时,女孩大睁双眼,身体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那画面让他记起童年时期,父亲带他到山里猎杀麂子的场景。麂子是一种特别胆小的动物,也很美丽,它被手电筒照着便一动不动,两只眼睛像宝石一样发着光。
在他车灯的照耀下,女孩的全身都笼罩着一片美丽的光晕。她一声不吭,呆呆地看着他,眼睛里不知是恐惧还是疑惑,那神态让她显得更加单纯、弱小、无助。就像那只麂子一样。漂亮的麂子,毛色光滑,腿脚细长有力。他摆动着车头,玩笑似的,让车灯在她脸上晃来晃去。她终于有了反应,像是愤怒又像是哀求地看着他。
“走啊!还站着干吗?”他粗鲁地呵斥她。
她的膝关节剧烈地抖动起来,像是个在冰天雪地里被冻坏了的人。
他骑着摩托移动到她身边,侧着脑袋仔细地看着她的脸。她的睫毛像蝴蝶那样抖动着,她怕了,他没想到自己可以这么可怕。弱小可怜的样子并不总是激发人的保护欲望,也会激发人的破坏欲。在她的衬托下,此刻的他真的像一只危险的野兽了。
“走不走?你?”他绕道她身后,朝她吼。
她仍然站着不动,他看见她肩膀耸动,她在哭。
“快点滚!”他用摩托车撞了一下她的自行车后轮。她的自行车重重地弹跳起来,她“哇”地大叫一声,总算骑上自行车,向前冲去。他的车灯把路面照得雪白一片,她瞬间便消失在那片光芒里。
当她离开他的那束光,她便看见了那属于街市的光亮,暖黄色的光,喧闹的人声和食物的热气,她激动得不能自已。她回到人群里了,平凡又安全的俗世,她用力蹬了两下脚踏板,自行车迅速地在街道上划出优美的弧线。又有人在看她了,此刻的她很美丽,脸上洋溢着轻松愉快的神情。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也将把那一切抛在脑后,连同那个倒霉的阿柳。坏事情并没有降临到她的身上。不过,她还是得到了一个教训:以后,她不会再坐一个陌生人的车,在夜里去一个危险的地方。
阿飞抽完一支烟,用轮胎把烟头碾灭,然后重新发动摩托,缓缓驶下山去。他试图在人群里找到那骑车女孩的身影,但是没有找到。女孩最终也没对他说声谢谢,也没有说对不起,甚至没有付钱。他突然觉得载女学生也没什么意思,还是花比较好。他骑着摩托,汇入马路上的车流,打算到花那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