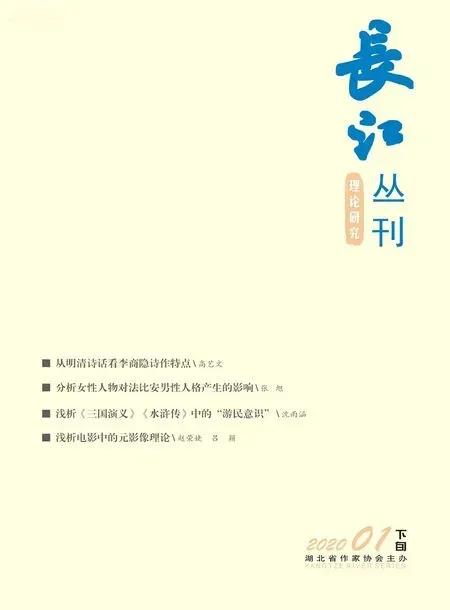对历史书写的反思与解构
——试论叶兆言的“秦淮三部曲”
2020-11-18李玫琦
■李玫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叶兆言相继发表了《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刻骨铭心》,这三部长篇小说在图书市场上被合称为“秦淮三部曲”。作家自己曾说过:“对一个小说家而言,写什么永远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小说说到底还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因此怎么写才特别重要。”在“写什么”这个问题上,“秦淮三部曲”无疑延续的是叶兆言熟悉的南京题材;但如果关注其“怎么写”,可以发现他在这里其实完成了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解构,并且尝试着重新构建属于他的历史书写方式。
一、对宏大历史书写的递进式诘问
“秦淮三部曲”的情节和文笔都极具唐代传奇、宋代说书的传统韵味,但其写作意图却是现代主义的。叶兆言以三部作品为线索对历史书写进行了层层深入的反思,以下将逐一分析。
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叶兆言证明了个人行为可以对宏大历史书写形成干预。假如主人公丁问渔真的可以在某本正史中拥有姓名,那么他的“历史”形象本应是一个头戴红色睡帽、满腹经纶、举止古怪、因一场名为《中外娼妓的传统之比较》的演讲而赢得满堂彩的另类知识分子,如同很多名人传记所津津乐道的那样,他的狂放不羁与他的学富五车会形成鲜明对比。但故事却是从丁问渔在晚辈的婚礼上对新娘任雨媛一见钟情来展开的,这个中年男人对新婚少妇的狂热追求看上去如此滑稽荒谬;后来雨媛在遭遇婚姻危机、丈夫空难去世的重重打击后逐渐接受了他的感情,他却在战乱中被枪杀身亡。这段以殉情告终的风流韵事使丁问渔在“历史”中的身份标签发生转变:由一个浪荡不羁的文人变为一个爱情至上的痴情男子。
“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天,已经步入中年已婚男人行列的丁问渔,在写得龙飞凤舞的日记中,首次抒发了他对雨媛一见钟情的狂热情绪。”作为故事开端的这段话营造出了一种参观博物馆的氛围,而历史的还原正是由这些物证和人证所定夺的。如果没有作为“历史文物”的个人日记和当事人任雨媛的回忆,也许丁的追求只是一场无人当真的闹剧而被历史淡忘;但当我们能够借助遗物和证人还原这场爱情传奇时,丁在“历史”中的身份标签就能得以置换。由此可见,个人对宏大历史书写的干预其实是可以通过他的行为及其影响来实现的。
看似重要的幸存者和遗物,在《很久以来》中却遭到了作者的质疑。如洪子诚所言,“幸存者”的身份意识“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以至认为‘幸存’的感受就具有天然的审美性。”是否要为幸存者小芋虚拟一封来自其亡母竺欣慰的信,正是“我”在《很久以来》中的创作难题。竺欣慰因为演员的身份和婚内出轨的事实而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还遭到女儿小芋的指认批斗。如果从情节逻辑来分析,欣慰应当在入狱前为小芋留下一封感人至深的诀别信以冰释前嫌,让女儿在多年之后为她当年批斗生母而感到愧疚;但是小芋说并没有任何一封足以升华这段母女关系的信,而她直到长大成人也依然对母亲的经历保持漠然的态度。因此,叶兆言在书中直言“真实性成了这篇小说写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竺欣慰的这封信和丁问渔的日记一样,都是故事讲述的关键道具之一。因为道具的缺失、违反典型“文革”叙事模式而流于平淡的结尾会造成读者阅读体验上的不满足,但凡小芋佐证或者作者写出诀别信的存在,结局都会迥然不同。——在读者这种可能的联想中,历史书写的悖谬性不言自明,既然物证与人证本身也是另一种人为因素的干扰,我们何以能保证其客观和理性呢?
在经历了以上“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思辨过程之后,叶兆言在《刻骨铭心》里就借用元叙事手法直接呈现了两种阅读通道,任凭读者选择。第一章第一节名为“烈女游娜”,本来讲述的是一个外籍女子的爱情悲剧,但到了第二节却戛然而止:“一个作家中断正在写的小说,会非常难受。”中断原因是作家去了游娜的故乡后,发现自己“对哈萨克斯坦的认识,积累了一大堆错误”,原先幻想的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等种种文化意象,以及基于此种预设而创作的几万字开头,却在当地翻译充满爱国激情的本国历史介绍面前显得难以为继。
“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其实还想到了两个开头,一个是言情小说,一个是传奇故事,于是就又有了第二章。”从一个故事的戛然而止到另一个故事两种可能性的暗示,这都让这部作品的结构有些像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书中提及一部拥有多重可能性的小说,其主题正是在行文中从未出现的关键词“时间”;推而广之,叶兆言作品的主题大概就是他一直闭口不谈的“历史书写”了。作家通过还原创作过程、暴露所有可能性,将选择的权利交到了读者手中;通过语言文字和叙事技巧来并置这些可能的阅读通道,直接取消了作为书写者的主体性和自觉性。这种做法看似回避争议,其实作家的历史观在字里行间不言自明。
二、推拉留白的说书人戏法
叶兆言是如何借助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呢?从“夜泊秦淮”系列开始,他就喜欢用说书人口吻讲故事,“秦淮三部曲”也不例外。说书人在开讲前已经通读整个话本,因而能够自由地跨越时空埋下伏笔;叶兆言在叙事过程中也并不与读者并驾齐驱,而是像事后诸葛亮一样在执果索因,当读者还沉浸于故事的起承转合时,作者却似乎已经在对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进行分析与评判了。
例如《十字铺》的开头即是如此:“士新和季云在一起,难免自卑。季云眉清目秀,一招一式,天生的那股潇洒士新死活学不来。多少年以后,士新仕途上扶摇直上,春风得意,他仍然怕回忆自己和季云的纠缠。”而《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开头也有一种回顾的意味:“他似乎还看不出元旦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纪念的意义,人们所以知道他感冒了,是他把这一点记录在了日记上面。”这种说书人的口吻会使叶兆言的小说产生超越时空的沧桑感,使它们有别于一般的通俗文学。事实上,“秦淮三部曲”的故事大体上都是常见的才子佳人模式,情节也多是男女情爱、悲欢离合,然而不断回荡的说书人声音,却会在读者将要流露出阅读鸳蝴派作品的闲适情绪时突然出现,从而使他们重新觉察到背景里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行动的存在。
叶兆言对南京是相当熟悉的,所以他可以在行文中游刃有余地随手插叙对彼时宏观背景的介绍。这种介绍有时带着新闻播报腔调:“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不过三年时间,新首都面貌变化非常快,到处都在拆旧房子,到处都在拓宽大马路。”有时候又是幽默俏皮的闲笔:“那时候的南京老百姓对纸面上的数据不感兴趣,报纸总是要看的,看了就扔了。”那些看似官腔十足的背景介绍,带着审美距离阅读时也总觉得是一种含蓄的幽默;而“闲笔”所形成的停顿与延长则更容易让读者从绵延不断的叙事中抽离出来,在这种一推一拉的力量牵引下,读者的思绪往返穿梭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大时代的跌宕起伏之间,可以更深切地感受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的渺小。
由此可见,叶兆言的小说并不是密不透风的,而是处处都有“留白”可供读者自行感受。“闲笔”既是一种与传统宏大历史书写形成对抗张力的笔法,同时也符合叶兆言自幼形成的历史认知方式。他作为叶圣陶之孙、叶至诚之子,不仅所受的家庭教育浸淫着知识分子的气息,而且也有更多机会接触那些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家本人或其轶事,这就使他形成了不一样的历史眼光,不会轻易崇拜或全然否定宏大历史书写,而是理性冷静地寻找着宏观架构中的罅隙,发现可以容纳稗官野史的空间。这也正是他的新历史小说的源头活水。
三、对历史材料的文学化处理
如果说叶兆言的说书人手法是秦淮故事里一以贯之的艺术手段,那么从“夜泊秦淮”系列到“秦淮三部曲”,他开始借助长篇小说的篇幅优势大量融入丰富的历史材料,并且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文学化处理。举例来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正文中就出现了信件、新闻标题、小报报道、民谣、报纸广告、节目单、离婚告示等史料,共同构成了一幅后现代风格鲜明的“文学拼贴画”。《刻骨铭心》中最典型的一处则是引用七七事变爆发期间的报纸——7月7日的报纸上有“卫生常识”的系列讲座,如“衰弱丈夫的急救法”“手淫与遗精的弊害”“发育不全的科学挽救”,副刊还有一篇题为“夏季里的诗的肉感气息”的文章。而7月8日的大标题是“秦淮河上的夏季风光”,小标题是“画舫灯彩辉煌,歌声与笑语齐飞”,注解则是“她像一个风流寡妇会使你沉醉”,第五版还有报道宣称“市府路一带,有私娼集团拉客举动”。直到7月9日,卢沟桥事变才见诸报端,标题却有些轻描淡写:日军前晚在卢沟桥演习突向我驻军轰击。——所谓“震惊全国”的七七事变,在叶兆言笔下却不过是一场关注度极为滞后的事件,南京市民对时政的迟钝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作家通过对一手资料的直接引用,成功重现了一个不同于当代历史描写的民国南京。
虽然叶兆言引用了诸多史料,但能否因此就将“秦淮三部曲”理解为非虚构作品,认为作者有意带领读者回归历史现场,或许还值得商榷。因为在作家看来,“历史小说仅仅是历史,好像真没有什么意思,小说必须要像小说,小说不仅包含了历史,它更是一门艺术。也就是说,阅读活动最好是有趣的,人们在回味历史的同时,还要能够品尝到艺术。”所以他是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有趣分开了的,且其创作可能更倾向于后者。但这种做法其实也隐含着新历史主义者批评昔日历史学家的工作时所指出的缺点,即在使用“情节—结构”模式来串连零碎史料时所运用的“建构的想象力”,正是个人化书写的表现,是有损历史客观性的做法。
新历史主义者发现“历史学家必须‘阐释’他的材料,以假定的或纯理论的东西填补信息中的空白”,而叶兆言看起来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用搜集的史料来填补虚构创作中的缝隙。这样一来,所有说书式的情景再现和拼贴式的史料汇集就只能退居背景,而故事里的小人物才是真正的主角。他希望这些故事“痛在别人身上,也痛在我们心里”,这样充满悲悯情怀的写作宗旨显然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
为了防止读者真的陷入这个由文学语言建构的历史现场中,叶兆言采用了一种较为巧妙的手段,那就是直接让著名的历史人物参与情节发展,构建他们与故事角色之间微弱的人际关系。例如,丁问渔留学时,就和海明威、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分别谈过话;此外,他和徐悲鸿、张道藩、陈毅、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有过往来;而在雨媛丈夫余克润的葬礼上,第一夫人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主持大会并发表讲话。这些显然是虚构的传奇式情节因为与真实历史人物相互牵连而显得虚实难辨。其妙处就在于,作者高超的细节描写与现场还原,不断撩拨着读者阅读时的感性体验;然而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间的关系仅仅是微弱的,读者深受现有历史书写的影响而培养的理性会使他们怀疑这些情节的可信度,进而怀疑整部作品对丰富史料的引用是否仅仅是作者的文字游戏。在这种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击之中,读者受到挑战的不仅是自己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对历史书写的认知方式。
传统的历史观念一般认为史料是确凿无疑的,历史学家会毫无私心地及时用语言文字记录下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而新历史主义者的观点是,历史学家所据有的史料是真实的,但他们在勾连零碎史料时要借助“建构的想象力”,通过“情节—结构”的故事创作模式来使史料发生意义,而这个过程必然是主观化的改写,其真实性值得质疑。作为小说家的叶兆言希望“将历史作为菜肴来做”,这意味着他可以对历史的原材料进行一定的文学加工,甚至让故事中的人物看上去仿佛“确有其人”,达到真假难辨的效果;但这种行为本身就暗示着“历史书写”的可操纵性和所谓“正统历史”的荒谬性。如果历史是可书写的、可探讨的、可回忆的,那就意味着每个人眼中的历史都是独特的,任何一种历史书写都不过是部分人回忆的共同输出,它不能强制垄断所有人对过去的阐释。叶兆言通过对历史材料进行文学化处理这种方式,不仅与新历史主义者形成超越时空的对话,而且也成功地用文学作品呈现了自己的历史观。
四、开放性的元叙事
说书人戏法、史料的文学化处理,这些都是“秦淮三部曲”主体故事中体现的写作技巧,而事实上叶兆言在后两部作品中还使用了元叙事手法,打断故事原本的叙述顺序和节奏,有意制造停顿和留白,这不仅让读者进入作品的通道更加多样,同时也打破了绵密的历史书写垄断读者思考空间的局面,间接地消解了历史书写的绝对性。
《很久以来》的第一章发生于1941年,第二章则突然切换至2008年,叶兆言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改变传统叙述方式,因为“我们的生活并不一定是这么叙述的,有时候是故事先跑起来,大幕拉开至一半,导演再出来说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部戏。”在第二章里,好友吕武说服“我”一定要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一位有钱人家的千金,一生追求进步,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最后在‘文革’中莫名其妙地被枪毙,这里面绝对会有看点。”但后面的故事却并不是依照成长小说或伤痕文学的框架展开,而是借由这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中一对姊妹花的情感羁绊,展现了人性中从未被特殊历史割裂的痛与爱。第九章一下子又跳跃至2011年,“我”在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春兰与欣慰的大学合影,“画面上是两位标准的民国美女,穿着旗袍。胸前别着校徽。一个男人一生中能同时拥有这样两位女人,不是小说也是小说了。”这一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然而全书已近尾声,读者已经发现作品是对“二女一男”模式浪漫色彩的消解,这不是一个平凡男人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而是一对姊妹花在历史动荡中的相互扶持,张爱玲笔下男性的主导地位在叶兆言这里让位给了女性。因此吕武的劝说、姊妹花的合影,都仅仅是在暗示着未曾展开的另一种浪漫风情的叙事可能性,这条本应存在的阅读通道只能由读者自行想象。
这种暗示其实也出现在了《刻骨铭心》里。叶兆言认为“如果读者仅仅想了解过去的掌故,知道一些历史故事,不妨从小说第二章开始。对于许多读者来说,第一章确实是‘冗长的’,完全可以不去阅读。”在这“冗长的”第一章里,“我”已经积攒的关于烈女游娜的几万字故事(同样名为《刻骨铭心》)在哈萨克斯坦的真实面貌冲击下难以为继,这段情节本来与后文中希俨、绍彭、丽君、碧如、秀兰等人的主体故事完全无关,然而叶兆言却要将两个同名的故事文本并置在一起,将自己的创作过程明明白白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一方面,他在主体故事里用说书人口吻和丰富的史料让读者摇摆于理性历史认知与感性阅读体验的冲击之中;另一方面,他却在书的开头使用元叙事手法来为自证清白。他想证明的不是自己没有虚构故事的企图,而是历史书写本就因人而异,谁负责讲故事,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让读者沉浸于其中的真假难辨的历史故事,可能不一定有多少原型,它们不过是作者在多种叙述可能性里反复试错后选择的其中一种而已,正如叶兆言自己所言:
我只是想把自己如何开始小说的思考,告诉读者,读者可以自主选择,选择他所喜欢的开头,认同或者反对,拒绝或者放弃。现代小说应该是开放性的,自由是现代阅读的特定标志,读者完全可以参与到小说创作中。就像点亮一盏灯,光有作者这根电线还不行,还得有读者这根电线,两根电线接上了,灯泡才会被点亮。现代读者不是完全被动的,阅读不是仅仅为了接受什么浅薄或深刻的教育,为了增加某种文化修养,而更是一种精神需要。
在无法确证历史书写真假的时候,选择权就交在了读者手上;读者可以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任何一种解释,但想要通过作为二手资料的历史讲述来进入最真实的历史现场是不可能的。读叶兆言的小说(读历史也许也是如此)不是为了借助这个身份背景有几分特殊的作家去试图接近历史真相——作者会一遍遍警示并打破读者的这种幻想——而是为了满足某种精神需要,获取某种阅读体验;也许读者会对“历史”本身产生了兴趣,但“应该如何学习历史”这个问题已经不属于作家的写作任务范围了。
从“夜泊秦淮”系列到“秦淮三部曲”,我们可以相信南京的素材是写不尽的,叶兆言未来也许会创作出更多秦淮故事,但是文学作品自身对历史的追问却可能有尽头。如果像《刻骨铭心》一样消解了历史书写者自身的主体性,把选择权交给读者,这是否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作家承认了历史书写荒谬性故而放弃寻找解决途径,抑或博尔赫斯式的多重可能性就是作家认为进入历史的最佳方式?在这一点上,因为作家让渡给读者的权利太多了,他本人的历史认知反而在作品中显得模糊难辨,这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一种写作困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