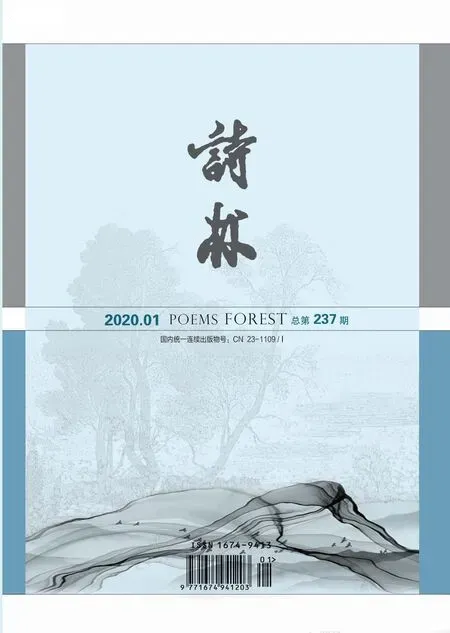李嘉伟诗选
2020-11-18李嘉伟
雪夜访
后来。仙人掌也染上没精打采的花纹
像是许多细线勒紧了,原本的形状就露出来
当然很惭愧。祖父的吊兰嫩得滴水
我痴迷于时令河,叶子成了灰
我要去问问祖父,是不是遗漏了秘诀
或者最关键的咒语。站在门外
我听见室内的手艺正在修剪枝丫
忽然心满意足地离开
我知道推开门的场景。祖父吧嗒着烟
遍地明净。像所有生活的魔术
他苦笑着,别看啦,别看啦
期望下我做不成任何事
嗣宗旧事
一
觅食越来越危乱。
掌中所轻的似乎不是一粒丹,而是必须返回火焰的灵魂
青眼与酒,锤铁那样锤炼着人,波澜只是一生的事
而那水滴石穿的,那不绝如缕的,那整夜整夜
从四周冒出来,以我的形式发出的声音,却不是我的
像野外的黑鸫,那架日趋完美的琴,把我弹了又弹
我仍走在老路上。今日所得的句子,离灰烬又近了一些
墙壁上小小的夹层,四四方方,如悬棺,隔绝昏暗的眼睛
我在无人处又觅得一线生机。啊,造纸术,无用的造纸术
尘土的囚牢让人沾沾自喜。
二
我从外面回来,浑身的清醒抖落一地黏腻的壳
异鸟苏醒,可于凤凰而言还太浅,时刻从自身里捧出
高于这个世界的东西。长啸之后闭关七日
落花盈衣而不知饥饿。我的疲弱,让那个声音趁势而起
时时刻刻以主人的姿态,装点着虚掩的柴门
我在我外面把门拍成一块铁板,越嘹亮的
越遮蔽着低处完美的交响,如何让一个人醒来
如何让他拥有些真正的朋友,而非对称着溺亡于孤独之境
三
我猜想,我甚至需要一点爱。那种绵延不绝的东西
像咏怀,攒满了抵达的毒,又不得不继续
哪里有一个最高的数字,说——停!
这个世界就系在仙人的腰上,静如一盏玉的死亡
整个冬天,我都在城东行散,雪下沉着
我的肌肤,一袭旧丝绸的热病,学习着轻盈
何不把这种形象颠倒。在邻家女子的床上躺下
一切都在飞升,像宇宙之树长回种子
四
我仍在写。外面乱糟糟的,到处都是
另一种暴力在犄角相对的火星中,披上仙人的大氅
瀛洲遣来某种永生的信号,山雨欲来,在静止锋的里面
夹缝中的事物藏着隐秘而微小的美,我依赖她们而活着
也必须因之而死。让那隐秘的彻底隐秘,让那微小的
彻底被一个时代的痛苦覆盖,让那美,直直地奔向消亡
泊在所有的对岸,连我也不例外。我通身清净
透彻如一株失了心的翡翠,终于等不到一个声音
来到这宽阔整洁的孤独小筑。那架日趋完美琴弹奏着
等待另一个耳朵,那也将使她不再是琴
小楼之思
小楼之思·正经
我倾向于看作登楼成瘾的幻觉。你知道的
就像我们去过最远的地方,远到以为再也回不了家
从那儿,生活却像个怪坡,旧轮胎打磨光滑
新的一样。朝向哪儿,我奇怪的眼睛都能看到你
这台精密的错觉仪器,每天忙着制造你
像一只蝉的疲惫,美丽如脱壳之苦
你终于摆脱了平庸——至少看起来
那些连环凶手,对谁都彬彬有礼
那些好人,为偶尔的坏心肠难过一整夜
醒来红着眼睛。如果你一直不开口
像个哑巴,生命像个没有闹钟的好清晨
孩子出去玩一天,母亲说,晚上七点必须回来
你就准时满载孤僻的乘客们去休息
如果你捂紧你的金子。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终生
眼巴巴的甜,都围着那一点点苦兜圈子
而你低下头,声音像一只推敲来路的大雁
“你看,正因为每句话都是真的,他们才自相矛盾”
当闪烁之弓从箭矢退隐,孤零零的东西多像:我
总在我之外枝繁叶茂。你别盯着我看,我从来不是什么
坚定的沉默者。一旦你承诺桑叶的绒毛要展开蝶翼
你的声音温温柔柔,古老的幽灵们从信里苏醒
那些草木的灰呀,所有离别都像孩子的伤口
新雪一过就能愈合。谁也不为了逃离你
谁也不必去高处消磨遍地的寒冷
那些影子拢到一起,双数的手,单数的脚
有多少不协调,就有多少生活,有多少
你的温情。而一生的危险全在温情里
小楼之思·离经
请喘喘气。请拥有一些,离题的耐心。尤其时间
用命消耗着,但仍可以视作一些脂肪,清洁的脂肪
必要的脂肪,温暖的脂肪,代替我们的肺腑
与敌意纠缠着。我们甚至会有些迷恋
像一枚樱桃转化成毛茸茸的白,老人和我说
在某个清晨的花香里,他顿悟一生,绕了那么远的路
只是为了这朵茉莉。他的老伴,忽然不能自己吃饭
怎么也塞不进嘴的菠菜,不是因为硬——她甚至嚼着花生米
她只是用了九十年承认自己厌恶绿色蔬菜
他们的孩子,总是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一片大海的自由
向瓶中船注入适当的盐分和糖。而我,多么惭愧
时刻想逃离这比我更智慧、更健康的家庭
逃离那些美的交谈,许许多多恰到好处的理解
和不理解。我们分享着一点点自信——所有离题
像半径那样,暗示一个更沉重的核心,我们仍妄想
一种最低限度的幸运——并非不死
而是和最后一枚宝石消磨余生
松下问
爱人,请听听这颗心的悲伤,如果找
也只是等待着失败,加入一场落日的游行
悲剧那么寂寞,因我们而一再发生
横竖都是永恒。可一切会死,春去秋来
贪心留下满身穿凿的恨,怕那恨一夜东风似的
错着柴薪,烧得众物疲惫,可除非从根本上摧毁
修剪枝丫多像一个枯荣的谎言,神的狂欢结束
我在边缘的帐篷痛恨手艺,外面,忽然不信
这一切竟是内部创造的。你被隐藏的终点
在我天真的皮肤之内,是否每个自证的日子
生命的弦都得在断裂的边缘再独白一阵子
哦,亲爱的。嘴唇一旦张开,某处沉睡的梦
就要越过大海,光芒殆尽,可我们得信,得用命相信
信任那些根本看不到,也必然整夜不眠的东西
可亲爱的,疼痛仍因为必然的联系而产生,为了甘霖
昨天必须奉上久旱之土,燃烧着,一滴水也从更深处开裂
我们忽然觉得浑身的肌肉荒谬地来龙去脉着
有一夜,爱神射完了所有弓箭,我们死状曼妙
后来者或许更爱,可如何也不懂,我们专去采
那称之为爱里,药的三分毒
短 评:
倘若我们暂时把诗视为语言对流逝中真实的决定性摄取,并且果然能在这种充满危险的捕捉行动中找到自身位置和万物之间的联系而不至于使一切沦为徒劳的话,那么隐藏在嘉伟诗作背后的,毫无疑问就是对这个行动自觉而全面的认领和实践。他诗歌中令人惊喜地处处显露出强烈的元诗倾向,这是对语言本体足够沉浸和洞察的诗人才有的风格标志,而且他带着无边的警醒寻找着诗与现实间难言的关联,避免落入这种深度沉浸可能会导致的幽闭性,使得写作本身显示出令人信服乃至难以抗拒的必要性。
他在万变的真实面前磨练着敏锐的洞察力,在每个隐秘的瞬间,也就是诗心最可能发动之处,充沛地使用他身上的感官能力,去努力靠近那个留给所有诗人的最好结果,即世界最终的露出总是伴随着诗艺的不断成熟。他渴望在每一种审美,爱欲,丧失乃至消亡等或朴实或剧烈的人类经验中审视自身和世界的潜在关系,并抓住每个奇妙的机遇,运用卓越的想象力来重建时间与现实。没有谁能抵抗这样的引诱。显然,他在诗中暴露了自己作为早慧受诱者的身份,同时也借这种伟大的引诱来更新自己。正因为他对真实的自我充满了警觉,才会清晰地同时认出“我”不绝如缕的连续性,以及涌现过程中“以我的形式发出的声音,却不是我的”的流变性;正是保持着永不懈怠的心灵活跃度,他才紧握住了诗歌内部那个随时随地都必须追问现实的紧迫要求。
——诗人 404
和李嘉伟相识有两年,两年里我们的交集也不超出在朋友圈互读。李嘉伟曾和我说过一句玄乎的话:“真正的友情大概在互读的边界上。”对于年轻诗人来说,这是准确的,我们从对方的诗里都吸收了养分,同时追求个人风格的成型。这几首诗都是李嘉伟的近作,自然也是诗艺不断精进的他目前为止最成熟的作品。李嘉伟喜好精致的语言,他的诗读下去总是行云流水,鲜有粗砺,口感是纯粹的精品粮,这与张枣对他的影响有关,更多的也关乎他的心性,近似于雍容的温和以及对美妙造物的纯粹热爱。这种为诗歌而诗歌的诗人并不缺乏,他们中很多难免陷入言之无物的修辞游戏,李嘉伟却没有耽于懒惰的享乐,在诗歌表达内容上不断地拓展。他围棋下得好,对诗歌的空间把握也独有风格,《嗣宗旧事》和《小楼之思》都营造出了一种叙说的氛围,句子之间的推拉、拉扯如忽近忽远的声音。《嗣宗旧事》里“我”的独白在感叹、辩解、诘问、肯定中产生细微的情绪波动,故事如线被绵密地缝在情绪里,呈现出来并不破碎,这是高超的技艺;《小楼之思》是浓郁的抒情,面向严肃的当下生活,面向被动的人生与异化的多数人。同代青年诗人把视野落在这里的并不少,但大抵会流于关于现代性的冰冷思考。《小楼之思》的语言是贴肉的,思考未必深刻,但这思考所承担的情感令人动容,像包裹在温热口腔里的一颗苦果,苦涩而不刺人。“有多少不协调,就有多少生活,有多少/你的温情。而一生的危险全在温情里。”整组诗几乎都由这样温厚的抒情句流过,李嘉伟毫无保留地把他作为同样一个“无力的善良人”近几年的所思所感投入在里面。《雪夜访》和《松下问》写的是典雅的日常温情,两个人之间微妙的互动与联系,在舒畅而绵密、流水般的抒情中产生并非震颤、但留余响的张力。对于李嘉伟来说这已得心应手,想写得好看绝非难事,接下来他打算突破的远在好看之上。
——诗人 胡了了
当他叙述和青年写作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焦点:历史叙事。这种情况被许多诗人质疑为“过度成熟的写作”“过度爱的写作”。但这种看法还未能够与历史视野和社会视野取得某种合宜,其本身并不是正确的。在这样的历史叙事背后是文本政治,它是当代写作境况的一个恰切的反映。起码在中文文学世界仍然没有作品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多元的、数据驱动的时代。更糟糕的是,我们经常性地用孤独或者非爱的爱来对照出时代意志。
就李嘉伟的诗歌而言,历史因素同样是很重要的,作为叙述人和角色的主体都不过是一个说书人和指路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主体缺乏的征兆,甚至可以说,诗歌呈现了一种普遍的生灵缺失的状态,自然人的缺位和末世人的惊鸿乍现。历史是残暴的、人是缺位的,这是当代中文诗歌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之一。我们似乎从未将残暴从历史的位置挪入人的位置,这与审美无关,与诗歌无关,而只与伦理有关。
我们是否需要回到人本身呢?我们是否夸大了某种时代变迁?某种情感变迁?我们是否不再相信一些本真之物?一种德性之思?这样的潜流出乎每一位写作者。几乎每个写作者都宿命般地习得独属于自己的风格,在这样的塑成过程里很少是熏染、很多是沟壑。我们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因素,一种巧妙地缝合人与文字之间的裂隙的美感,一种秩序。我也知道其中的一些并非为着划清和断裂,而是在历史之中寻觅一种确定性,在一切之变中保持冷静清醒乃至智慧,并探寻更多的可能性。
我欣赏李嘉伟的诗歌中的历史表达和文体内的疏离感,当文本呈现了一种优美的小说化或情境化时,几乎可以媲美翁达杰。更为精妙的是,它呈现了人异化成历史的一面。在其中的某些部分,我看到了当代的缩影。
《松下问》开始是一个呼唤,这便将读者和文本拉入了一种内部,境遇的内部,舞台的内部和框架的内部。同时,诗人讨巧地给了一个支点,“横竖都是永恒”——爱情问题。整个文本用一个大视野或大全景对其作出映照。在大全景的内部依次展现的是:死亡,众物,神的狂欢——这样一个联通的递进的过程,“内部即外部”所“反转”或点染。这个大全景终结在皮肤之后的生命的弦,这样一个前景,甚至焦点。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从大历史到小众生的过程,也是一个大背景到小前景/焦点的过程。接着把它颠倒过来。嘴唇张开是一个动作,是一个象征,又是一个对于爱情的许可、接受、升华,但这样的升华是脱离人的,甩脱生存感的,同时又将爱情推向了情感的高度、诗性的高度、伦理的高度。“得用命相信/信任那些根本看不到,也必然整夜不眠的东西”说出的是一种带着内在需要的相信和笃定。然后他肯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疼痛,来龙去脉,爱的消失,创伤等等。这就合法化了诗歌。借由诗歌的合法,诗歌就开始了引述,这便是诗歌的升华。在其升华中,引述将抽象精神和微妙创伤结合在一起,主体因而成为了一种对照和联通,而主体的位置也被抽象或情感所占据了。最终,主体和意图都是失落的。
——诗人 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