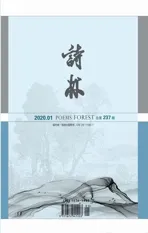传统与个人才能
——简论《沙之书》八位诗人作品
2020-11-18赵东
赵 东
一个诗人终其一生,写诗的最终成果或褒奖是什么?这和名声或者影响无关,可是诗人的写作行动总是要有写作行动的结果(或者收获)的。诗歌写作的成果不是以写作终点的形式出现的,诗人是没有终身成就奖的,也不需要获奖感言,那么诗人的写作行为对于诗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有什么影响(或者意义)?
诗歌写作活动的意义并非体现在诗人最终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名声或者头衔,而是体现在诗人受到诗歌的指引,如何将个人融入到历史之中。这个“历史”不是历史学意义的概念,而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诗的真实”。诗的历史是诗人的专属褒奖,通过写诗活动,个人不断成长,经过各个阶段的感悟和体验,实现生命意识和历史观的合拍。诗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了诗歌行动的参与,诗人的人生就天然地带有一种诗的真实。
就像文乾义所说,“……在有些诗里,我有意对之前的某些理念作了调整。让情感在平静或平淡中较为充分地外露一下——我认为这对我的写作是必要的,因为它表现了我所期待的要表现的东西。”文乾义提到了理念调整和情感的表达策略转换,这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传统与个人才能。《沙之书》的八位诗人身上不约而同地,或多或少地显示出与传统的一种合拍,当然这种传统的继承性不但没有消灭他们的写作个性,反而强化了这种个人的写作特征。
诗歌写作的复杂之处在于,写作的过程不仅是个人天赋和才能不断精进的过程,同时也是诗歌写作个性化不断消隐的过程。诗歌正是这种奇正相生的艺术形式,诗歌写作进程往往可以出乎我们的预料,呈现出一种正反结合的迷人的魔性气质。
艾略特很早就发现写诗本身就是一场冒险行动,越是想把握住诗歌,那么就越是会从诗歌中“跃出”,进入到诗歌的另一种写作状态。他的诗歌实现了对自我的突破,他的写作走进更为深邃的现代主义层面,最终和庞德和乔伊斯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从现代诗歌新传统中汲取养分,将个人才能建筑在现代主义诗歌新传统之上。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是对他个人诗歌成长的极好的描述和总结,此文的观点同样可以运用于《沙之书》的几位诗人身上。
一 消除个性
诗人唯一的财富恰恰是表现在诗人的个性特征上,艾略特说,“我们所应坚持的,是诗人必须获得或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于是他就得随时不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
诗歌的初学者总是极力表现自己与众不同之处,将情感尽量释放,将语言尽量夸张。事实上,这正是从根本上背离传统的做法,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的那样,诗歌传统更多地是来自于经验的集中,这种写作经验需要的是安静的思考和不自觉的感受。很多诗人为了强调个性特色而将传统看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把对优秀诗人的片面模仿当成自己的创造。这正是诗歌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陷阱。
文乾义的诗歌很好地诠释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新传统,他说要让情感在平静或平淡中较为充分地外露一下,这正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现代诗歌一直在坚持发展的新传统之一,诗歌从过高的云端中下降到大地之上,从头上添头的加法走向本真质朴的写作态度。事实上,以浓烈抒情见长的海子在写作后期已经发现了抒情的奥秘并不在放纵,而在适度的逃避,他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谈到现代诗歌写作时曾说过,“她是精神的安静而神秘的中心。她不在修辞中做窝。她只是一个安静的本质,不需要那些俗人来打扰她。”文乾义的诗歌写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直到21世纪以来,一直在寻找一种类似于慢节奏写作的路数,事实上,文乾义的节奏已经接通了这种传统。
早晨拉开窗帘,/正是一天中阳光最新鲜的时刻。/我早该注意到这一点。/阳光照在楼宇迎向它的那一面,/楼宇是新鲜的。/阳光照在面包房玻璃橱窗上,/橱窗和面包是新鲜的。/阳光照在一百年前的石头道上,/石头是新鲜的。/阳光照在散发出臭味儿的河沟里,/河水和垃圾是新鲜的。/阳光照在我仰望白云的目光上,/目光是新鲜的。/阳光照在积雪融化后岩石上的噩梦上,/噩梦是新鲜的。/阳光照在角落里一块腐烂的词语上,/词语是新鲜的。/阳光照在我走向地铁口的身体上,/身体是新鲜的。/这一时刻,我突然醒了似的……/我的灵魂在哪儿?/我一定让阳光照在它上面,/它就变成新鲜的了。
——文乾义 《我的灵魂在哪儿》
这样的句子似乎并不新鲜,甚至稍显平淡,可是有经验的诗歌读者还是能够从中看出一种新鲜感,将情绪和夸饰控制在一个安静或平淡的范围,句子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后劲。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修炼,控制节奏、力度并将之转化为喂养生命的粮食和能量。说到诗歌修炼,不得不说到诗人李德武,作为一个特殊的写作者,他起初并不是以诗歌写作见长,而是以诗歌理论而著称。近些年来,李德武的诗歌写作渐入佳境,他的诗歌写作也很好地见证了现代诗歌传统的另一种路径,那就是从理论出发,最终实现从哲学研究和佛法修炼走向顿悟式诗歌写作的诗歌新传统,这也有力地证明现代诗歌有着万千法门。让人惊喜的是,李德武的诗歌写作中理论家和修炼者的形象逐渐在隐身,让位于诗歌自身的言说。
我尝试着表达黑松石,说出凌晨之静/夜行人还在赶路,我听到一块石头的脚步/摩擦产生火花,产生沉默,火花的沉默/我尝试着理解模糊,与混合物交谈/我发现油漆是个君子,涂抹时毫无瑕疵/小人是一些缺磷者,携带败血症的病因/它需要补充稀土,在骨髓里植入芯片/夜行人同时去往不同方向,无数分身/敲开空中之门,进入石英钟或松树冠/带着日本人的缜密和分裂,我想到雪国/一个作家为纯净的空气呼吸液化气/而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不适合清醒/细分罂粟的花粉与汁液,细分黑暗质地/他需要胡说八道,在脸上涂油彩/以神或妖的面目现身,他对人怀着歹意/每个讲堂都灯火通明,调试离心机/铀等待被教育改造成武器,或爱国情怀/贵重和危险之物都隐埋在山里/我尝试着表达黑松石,什么也说不出。
——李德武 《黑松石》
这首诗出自于海德格尔式的思想者和东方佛法参悟者之手,也反映出修炼者的写作状态。作为他的诗友,我要恭喜作为诗人的李德武在传统的路上开启了更为宽广的路径,将思考和顿悟隐匿在诗歌经验的背后,把诗歌的独特节奏和呈现方式放在了首位。《黑松石》的整体诗歌气息十分通畅,而且多次运用点到为止的表意法,实现了现代诗歌的微言大义和多意拼贴。诗歌的现代气息十足,将繁复和歧义很好地融入到场景的转换之中,在诗中时间似乎并不存在,只有空间结构的自由变幻。李德武是一个对空间极其敏感的研究者,他在自述中说道,“诗对自由的解放是从空间开始的,它是瓦解一切固有障碍最有力有效的方式。这让我相信美就是对形式和语言的创造与摒弃。”李德武对于时空的独特见解来自于他长年坚持不懈的西方哲学研究和东方佛法参悟,他知道哪些在写作中是要避免的,而哪些是要坚持的,李德武的空间意识和诗歌写作经验让他的写作与现代诗歌传统接通。
二 诗歌引领
在这八位诗人中,我最早接触到的是冯晏的诗歌,后来又读到了张曙光的诗歌。幸运的是,我都是在恰当的时间读到二位诗人最好的诗歌写作状态。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诗林》的“开卷诗人大作”读到的冯晏作品,当时她的诗歌写作状态充满了生动清晰的生命动感,保持了东北诗人特有的冷静和大气。那时的冯晏还是抒情至上的写作态度,诗中总是洋溢着一股时代特有的气息。今天再次读到她的作品,不得不感叹诗歌传统的回归之路标志着诗人写作状态的成熟。
光颠簸,一根短发飘落,/横在手机屏幕的西太平洋。/你的位置定在西印度群岛右下角的圣胡安。/存在像虚拟,空灵,被蒸发,/但有重量。飞萤、海藻、变色树枝,物质都在。/你携带视线和一点磁场,随海风变咸,被气流塑成立体图案。/旅行,方向并不重要,/黑色罗盘转动你神秘的纵向。/时间虚拟。/逃出的都市已沉入更深,/嘈杂和质疑声撞向时差,/这片偶遇/被植入野花和青草气味的水和空气,/错觉里,熟人都不在。/鱼群,在海里放空了拥挤在唇上的词,/沉默,轻了许多。/晚霞天际线,/孔雀开屏升起你橘红色外套、唇彩,/的确,你恢复了轻信。/岸边,银沙纤细,/你赤足蹚过,感受光,/你宁愿去鲨鱼胃里下探、上升,/寻找大陆,/住进原住民遗址旁那尊哥伦布铜雕的体内避风。
——冯晏 《错觉是你的偶遇》
诗歌的感觉和经验的协调带来现代诗歌强劲的力度之美,想想早年略显柔弱的冯晏,她现在的写作状态同样在创造新传统的同时接通了她个人的写作传统。她的自述清楚地出她对现代诗歌新传统的理解,“创造力这个名词中携带的‘力’其本质就是出自于生命的内在力量。只是这份力量在诗人创作时偶遇的词语或许已经改变了其原有DNA。天才因素与神秘现象是引领一个诗人走进未来的魔力,每一首诗都应该是一个诗人解体一切固有之后的又一幅全新自画像。”
再稍晚一点,大概是1995年左右,我读到了张曙光的诗歌,一下子就被他执着的知识分子叙事精神所打动,这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似乎他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诗歌史中,甚至在苏轼和白居易的诗歌中也弥漫着这种熟悉的味道,可是这种气息又有着异域风情,似乎来自于风雪弥漫的俄罗斯的原野。《沙之书》中张曙光的诗歌给人以熟悉的陌生人的感受,张曙光现在的诗歌要放松很多,甚至可以读到一丝美国的气息,这也难怪,地球村太小了,诗歌跨洋越海已是举手之间的事。
夜晚的卷心菜长满蚜虫。/大地的耳朵被塞上了蜡。俄底浦斯消失。/沙子像雪。它们是死去的时间,确切地说/是时间的灰烬。无人认领骨灰瓮。谁在哭泣,或是在笑?/风吹过甬道。火烛发出的噼啪的低语/加剧着天空的暗蓝色和餐桌上的阴谋论。/天空一片泥泞。谎言是真理正在显影的底片。/当盒子被打开,却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张曙光 《失明的夜晚——献给基弗》
张曙光的诗歌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求索和诘问,这种天问式的写作塑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人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冯晏和张曙光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现代诗歌传统的生长态势,也读出了诗人的成长轨迹。那诗歌发展背后的本质力量是什么呢?是诗人内心的历练,还是诗歌本质力量的引领呢?我一直是坚信后者的,诗歌作为人类的本质的活动之一,在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于共鸣上来说,诗歌本身就对诗人的身心具有调节作用。诗人通过写作活动,将身心与世界对话,事实上内心世界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写诗也可以看成一种修炼,这种修炼是以诗歌的引领作用作为核心要素的。
三 个人才能
既然诗歌具有引领作用,诗歌写作不是个性的追求,而是逃避个性,那诗歌写作难道不用个人才能的参与吗?情况恰恰相反,在诗歌的引领之下,诗人的才能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不断加强。每个诗人在他的不同写作阶段,都会呈现出独特的个性,李德武说,“我很少读诗,我已经过了需要从诗歌文本中获取写作启示的年龄,无论语言还是形式,无论是观念还是想象力、批判的态度,我都本能地拒绝文本参考(包括大师模式)。我的写作必须建立在我和世界独特的关系上,必须建立在我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消失的问题上。”李德武的冷静和自省状态与他多年的哲学思考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写作引领作用与他的人生以及修炼有效地融合,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个成熟的诗人需要一颗寂静的心。这难道不是个人的才能吗?我从不相信可以从诗歌中迷人的句式或者惊艳的词语本身里读到个人才能,我更倾向于把诗人的个人才能和“诗的真实”的历史以及生命过程的直接呈现作为个人才能的标志。
杨河山的写作应合了陈子昂当年在《修竹篇序》中所言,“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他的诗歌追求硬朗和质朴的写作风格,正是作为诗人的杨河山的个人才能的体现。吉庆的诗歌写作和杨河山有类似之处,吉庆的情绪把握得更为自然一些,节奏张弛有度,而且善于在句式的变化里掺入个性特征,显示出超强的诗歌感悟能力。袁永苹的写作带有浓烈的古典情怀和现代诗歌的无意识特征。她的诗歌带有浓重的精神分析特征,很多幻象夹杂其中,期待她能够穿过镜中之象,通过解析意念形成的奥秘,呈现无意识的结构层次,从欲望的真实性出发,抵达心灵沉潜之美的领域。《沙之书》八位诗人中,老单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也是现代感最强的一个。
他们的才能和气质有北方诗人身上十分可贵的倔强和坚持,简单直接,变化多端,完全摆脱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沉闷的新古典主义写作方法的制约,语言清新自然,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和生活背面的精神分析让诗歌带上心理探索的冒险气质。尽管这种写法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那就是一不小心就会向诗歌示弱,因为心理探索性诗歌需要强大的内心和气场,那种不管不顾、撞了南墙也不死心的气概表现在诗歌写作上就是手腕要硬,绝不屈服,永不妥协。
2019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