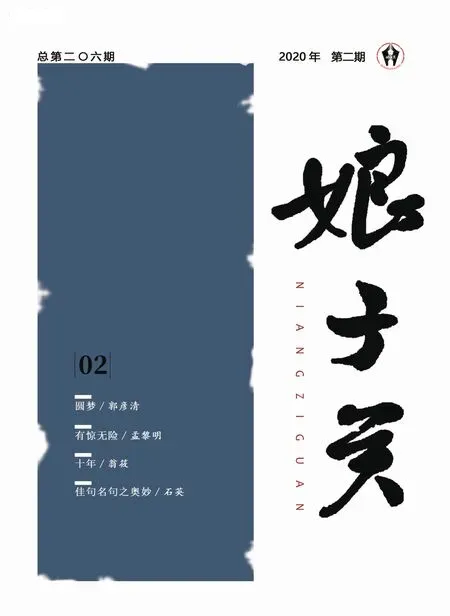燕赵享衢柏井驿
2020-11-18王文尧
文 王文尧
平定柏井,绝对是井陉古道上最古老的驿站之一,也是出入二百里井陉最紧要的关口。直到现在,柏井村古老的西阁上,还保留着两块石刻,一块是“秦晋要路”,一块是“燕赵享衢”,连同那块已经躺在村委会院内很久的“柏井驿”石刻,都向人们昭示了柏井古道的古老以及柏井驿站的重要。
然而,这“燕赵享衢”的说法,着实让我纳闷了许久。是啊,你说连通东西的柏井——井陉古道是沟通秦晋的山关要路,这我能理解;同样,你要说直通东西的柏井——井陉古道是沟通燕赵的必经通衢,我也能认同。可这一个“享”字,怎教人费尽思量,不得其解啊!这意思是明摆着的,就是说这是燕国与赵国共同拥有的一条要道。怎么可能?难道说古人用字只是泛泛而谈,不可较真?还是说,这“燕赵享衢”的背后,还真有什么历史隐情不被人知?为此,我在柏井西天门古老的八叠坂石道上一次次行走,也在柏井一至五村的街头一次次徘徊追问,数不清的摇头与叹息,让我感到迷惘、困惑与无解。
不过,在阅读《史记》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记载,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巨大的想象空间,或许能解开对“燕赵享衢”的疑团。
《史记·赵世家》载:赵孝成王“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也就是说在公元前247年,赵国和燕国交换国土:赵国把龙兑、汾门、临乐给燕国;燕国把葛城、武阳、平舒给赵国。这次交换国土,显然是为了就近方便,赵国把靠近燕国的龙兑、汾门、临乐换给了燕国,而燕国把靠近赵国的葛城、武阳、平舒换给了赵国,这显然是一次互惠互利的平等交换。只是从古至今,这六个地名所对应的地望却一直含糊其词,更多的时候只是大致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真要丁是丁卯是卯地较起真来,往往含糊其辞,不知所云。但是,其中的平舒,我还是略知一二。
徐广在注解平舒的时候说:“平舒在代郡。”当时赵国的代郡范围很广,北起灵丘,南到和顺,都曾经是赵国代郡的版图。《括地志》说:“平舒故城在蔚州灵丘县北九十三里。”而《读史方舆纪要》载:“平舒城在县(灵丘)北。《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九年,与燕易土,燕以平舒与赵。即此。”且不说《读史方舆纪要》的明显错误,将赵孝成王十九年张冠李戴成了赵武灵王十九年,单单是这灵丘平舒的断言,就犯有常识性错误。我们知道,赵简子去世后,他的儿子赵襄子赵毋恤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杀死代王,将代国收入囊中,直到赵武灵王去世之后,还将尸体埋在了这里,正因为如此,此地才被命名为:灵丘,就是赵武灵王的墓地所在之意。这是赵氏立国最坚实的根据地之一,直到赵国灭亡,也从未有将此根据地易手燕国的记载,怎么平白无故到了赵孝成王之时,这平舒就成了燕国的领土,并要拿赵国的城池与其交换,这不莫名其妙吗?
其实这灵丘平舒,就是今天灵丘县北的广灵县。广灵县在战国时期为平舒邑,就属赵国。秦朝属代郡。到西汉韩信下井陉背水一战灭了赵国之后,这里才设置平舒县,与周围的崞县、灵丘县一起,隶属幽州代郡。到东汉时期,属中山国,也叫常山国。张耳首任常山王,中山靖王之后刘备,常山赵子龙,这些人物都来自我们所熟悉的中山国这块土地。这也就是西汉、东汉时期这一带的来龙去脉。难不成《括地志》与《读史方舆纪要》将东汉幽州代郡的平舒,硬是关公战秦琼地安在几百年前的赵孝成王头上吗?此平舒的注解,断断经不起推敲。
历史上的幽州渤海郡,也曾经有过一个平舒县,为区别于并州刺史部代郡的平舒县,所以还特意加了一个东字,就叫东平舒县,也就是今天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的大城县。但是,考证东平舒县的历史,我们发现大城县境内,很早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到春秋末期,境内才有城邑,即今天的平舒镇,而当时名叫徐州,是齐国北部的边城,正处于齐、燕、赵三国交界地带。燕昭王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攻打齐国,占领齐国70余城,其中的徐州才由齐国改属燕国,并更名为平舒。
直到汉王五年(前202年),在今天津市静海陈官屯镇西钓台村附近才在这里第一次建东平舒县。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北大城北部、静海全境和天津市郊海河以南地区。西汉初元二年,即公元前47年,因“海水大溢”,就将东平舒县迁至现在的大城县境内,仍属渤海郡。《后汉书·郡国志》河间国条目下载:“东平舒,故属渤海。”到北魏太和十一年,即公元487年,东平舒县去“东”,才正式称平舒县。后晋时,这里沦入契丹,周世宗显德六年,即公元959年柴荣收复,更名为大城县。
由此可见,渤海郡平舒,从始至终都没有属于过赵国,当然,赵孝成王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47年的“易土”外交,赵国拿旧属齐国而当时已属燕国近半个世纪的平舒,再与燕国交换,岂有此理?
此平舒,也绝不是彼平舒!
这里的平舒只有一个,那就是寿阳平舒。
要是问灵丘平舒未曾归属过燕国,渤海郡平舒未曾属于过赵国,难道说赵国境内的寿阳平舒就曾归属过燕国吗?是的!
因为历史上的平舒,曾经是中山国的领地!这个问题,就说来话长了。
你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灭亡了西周之后,中国历史曾经进入过二十年可怕的真空期吗?
《古本竹书纪年》载:幽王“十一年春正月,日晕。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是为携王,二王并立。”这是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事情。由于周幽王宠爱褒姒,于是废申后及申后所生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申后与宜臼只好逃回申国,寻求申侯庇护。这使周幽王的老岳丈申侯大为恼火。为了夺回失去的势力,申侯一不做,二不休,联合鄫人、犬戎偷袭首都镐京,结果,周幽王及太子伯服败死,郑桓公为护幽王力战而死,周室灭亡。这文武成康创立的西周王朝,在经历了十一代十二王大约275年之后,就这样灰飞烟灭了。犬戎大军焚烧、抢掠周朝京城镐京,杀贵族卿士大夫无数,虏王后褒姒向北而去。
战后,以申侯为首的诸侯秦、郑、晋,在申国共尊废太子姬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但姬宜臼太子位早已被废,其联合敌国犬戎、弑父杀弟、灭亡西周王朝的恶行,已经丧失其继承王位的资格,所以九年之内,诸侯们都不来朝贡他。战国楚简《系年》载:“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与此同时,以虢公翰为首的十多家诸侯,共同拥立周宣王次子、周幽王之弟姬望(别名姬余、姬余臣)为周王,史称周携王。虢公翰一族也从此向东迁徙,立国于中山一带,以拱卫新成立的周王朝。从此,周朝二王并立。
姬望的封地,应该是钜鹿莫国,古钜鹿范围极大,在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山西省东部,而莫国首都,应该在今河北任丘,鄚阳城即古颛顼城,大致就在望都。这望都的名字,应该是一个古老的传承。周携王,名姬望,莫国是他的封国,莫国的首都,后来就被称之为望都。
周携王即位为王时已经二十多岁,政令不易为外臣操控,而周平王还是七八岁小孩,权臣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周携王当政年代,在河北、山西一带和揖北方少数民族,结好上古唐尧虞舜遗族,为政宽裕慈仁,恩能及下,和而不流,能绥四方,南通荆楚,北结燕国,东联齐国,西善旧晋。外有王室支柱虢公翰的强力支持拱护,内有和揖百族的大政国策,所以政通人和,百业并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井陉古道的周围,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小国,鲜虞国、鼓国、仇犹国、肥国以及后来的中山国等等。周礼浸淫的那个时代,人们大概都不知道如何处置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当然也不会把彬彬有礼的贵族都想象成不堪防范的小人。姬望大概就对近邻姬姓晋国,更是丝毫不加防备。
但晋文侯姬仇,却绝对是一个有抱负的人物。他早有向北开疆拓土的野心,其占据井陉要地的东北方莫国的强大,肯定会成为晋国未来发展的巨大阻碍。
终于等来了机会。苦心经营二十一年的周王姬望,有一天,竟然要经过晋国的土地大摇大摆地去巡视黄河边上的虢地,这是西周栋梁虢氏的最初封地。三门峡现在有一座气势恢宏的虢国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了虢国曾经的辉煌。这么重要的活动,竟然就被晋文侯截获了消息。而晋文侯就在姬望必经之地设伏,以姬望无权继承幽王大统之名将其袭杀,并进而派兵攻打莫国都城,鄚阳城也由此毁于战火,从而终结了这二十一年之久的二王并立局面。
自古以来,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然而,在西周灭亡之后的二十一年里,竟然就是二王并立。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二十一年,天下竟然太平,各国竟然相安无事,你不得不佩服周公顶层设计的《周礼》,大概是维持当时大国安宁的灵丹妙药吧?!
袭杀周携王,迎立周平王,确立天子正统,晋文侯由此获得了拥立周平王的投名状,清华简《系年》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拥立平王东迁“中国洛阳”,这绝对是改变历史走向的惊天之举,最大的受益者是原本并无尺土之封的秦,却一跃超越晋国侯爵之上而成为公爵秦襄公;其次是郑,原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策禁令,在此事件之后,郑武公却拥有了讨伐东方诸侯的尚方宝剑,以至尾大不掉,这郑国后来让东周尝尽了苦头;最后就是晋国,晋侯终于可以在成周天子的朝堂上来回走动,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可一世的傲慢,也是风光无限啊!
当周平王得知晋文侯袭杀周携王之后,欢喜激动,溢于言表,那真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喜不自禁的周平王还挥笔写下了《文侯之命》以表彰晋文侯的功绩。《尚书·周书》中有一篇《文侯之命》,那就是周平王专门写给晋文侯的表扬文章,还铸在了青铜大鼎之上。周平王在册命的结尾处极尽肉麻地写道:“族父义和啊!您能够光耀您英明的祖先唐叔……继承和发扬文王和武王的美德。您很伟大,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您保卫了我。像您这样的前辈是值得敬重的,我很赞美!”堂堂天子,对自己的诸侯国君这样露骨地奉承,不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不可能这么掉价儿。
什么叫“礼崩乐坏”?这就是。什么叫坏规矩?这就是。本来周礼规定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晋文侯身上,直接就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自此之后,整个春秋时期,周王朝就一直处于这种打破规矩、自立门户的恶斗之中。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晋文侯姬仇的弟弟姬成师,一直以推翻哥哥大宗这一支为己任,通过七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曲沃代翼终于取得成功,姬仇一族被曲沃桓叔一支消灭的彻底干净,到曲沃桓叔之孙姬称的时候,终于成为晋国国君,并威逼利诱周釐王将其由侯爵封为公爵,是为晋武公。
到他的儿子一代英主晋献公姬诡诸的时候,雄才霸略,创造了“假虞伐虢”的奇迹,在晋国境内,“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到晋文公重耳的时候,晋国霸业横空出世。到公元前632年5月,晋文公以周天子之命,召集诸侯,齐昭公、宋成公、鲁僖公、蔡庄侯、郑文公、卫叔武及莒子,践土为盟。更有甚者,参加会盟的竟然还有周天子。这连写《春秋》的孔子都看不下去,只好以周天子“河阳狩猎”的名义,碰巧遇上了会盟,就来讨一杯酒喝,天子威风扫地到不忍直视,致使史官不可直书,只能隐晦,后人将史书的这种写法称之为春秋笔法。
晋文公开创了晋国一百多年的春秋霸业,同时,也为晋国的灭亡准备了掘墓人。晋国的六卿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公室的权力,也为六卿崛起创造了条件。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后来发生在井陉古道周围的那些事情了。
就在古州平定的周围,一条井陉古道串联着的那些神秘古国,仿佛就在眼前,却又那么遥远,昔阳的肥子国,盂县的仇犹国,阳泉的鼓国,以及太行山里的鲜虞国、中山国,无一例外,我们几乎都说不清他们的来龙去脉,甚至我们都怀疑真的有过这些邦国吗?这些邦国真的都是戎狄之国,和周王朝的分封毫无瓜葛?怎么可能?
大一统的周王朝,禹迹之内,怎么可能允许在井陉古道的周围,突然冒出这么多戎狄之国堂而皇之地生存发展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过是历史的隐情而已,大家讳莫如深罢了。
先是肥子国。光绪版《平定州志·古迹》载:“昔阳城,乡东五十里。《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夏六月,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因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由此可见,这次晋灭肥国,是晋军统帅荀吴伪称与齐国会盟,然后假道鲜虞,进入昔阳,两个月后灭掉肥国,肥君绵皋成为晋军俘虏。我们不知道肥国的来历,只知道肥国的末代国君是绵皋,绵是绵山的绵,绵河的绵,绵蔓水的绵;皋是皋狼的皋,皋落的皋,皋牢城的皋。这绵绵不绝的山山水水,难道和肥子国的国君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可能啊?晋国灭肥后,余部徙居至鼓国,后居住在今河北藁城西。时至今日,山东泰安尚有肥城,是“史圣”左丘明故里,翻看其地的历史沿革,竟也称曾经是肥子国。当是肥国灭亡之后肥族人最终散居的落脚点,到西汉初年,始在此置肥城县。
再是鼓子国。历史上有两个鼓国,《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称:“春秋时鼓子国,祁姓,子爵,白狄之别种。”另一个鼓国为周代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位于晋州市境内。《左传》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称:“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左传》记载较详,大致过程是晋将荀吴包围鼓国之后,鼓国有人提出投降,荀吴不同意,怕助长自己部下轻易投降的风气,并将出城投降的鼓人交还鼓国处置,让鼓人修缮城防。围鼓三月之后,鼓人又请降,荀吴再度拒降,认为对方“犹有食色,姑修而城”。直至鼓国“食尽力竭,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鼓国之君鸢鞮为晋军所俘。
为了安抚鼓氏遗民,不使其逃归鲜虞氏,下令鼓人各复其所,不久又放归鸢鞮回鼓。但鼓人并没有因晋国的安抚而放弃反抗,公元前521年,鸢鞮又率鼓人叛晋,复附鲜虞氏。次年,晋国急遣荀吴率晋军由邯郸、广平北上镇压鼓氏之叛。荀吴命军士乔装买粮商人,在昔阳城止息,乘鼓人不备,攻入鼓都,再俘鸢鞮及其亲从,鼓氏灭亡。这是鼓国的第二次覆灭。随后,晋国命大夫涉佗镇守,鼓地正式纳入晋国的版图。今天晋州市的十里铺村,就是当年鼓聚所在地,鼓聚还有昔阳亭。晋灭鼓,肥子余部又先后徙居今河北卢龙、山东肥城等地,皆依昔阳为都名。
鼓城,就是鼓国之城。鼓国灭亡之后,赵简子又在这里建起了平潭城。随着平潭城的衰落,鼓城也逐渐演变为今天阳泉市区的古城。其实,鼓,非常古老。《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说明是人文始祖黄帝发明了夔鼓,这也是关于鼓的最早记录。
在《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可见,鼓,是伯陵的儿子,也是炎帝神农的孙子,他还是钟的创始人。难怪阳泉大地上鼓文化如此丰富,迓鼓子风韵犹存,成为中国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清代平定州官沟村人张士林,还写出了一本六千余字的《鼓之说》专著,更是给古老的鼓国鼓城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鼓文化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啊。
公元前507年秋,鲜虞出兵晋国平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国勇士观虎,报了晋灭肥、鼓,占领中人城的一箭之仇。
公元前506年,鲜虞人在有险可守的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建国。因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这便是初期的中山国,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
接下来就是鲜虞国。这是聚居在今正定县新城铺一带的白狄族人建立的国家。山西省五台县西南,有一条源于五台山、流入滹沱河的清水河,古称鲜虞水。白狄族是在鲜虞水沿岸发展起来的,所以叫鲜虞族。其实肥国与鼓国,都是鲜虞国的城邦联盟。鲜虞国也曾是晋国旷日持久的征战对象,从荀吴灭肥、鼓,鲜虞尚能挺立,充分表明鲜虞国能征善战,借助地利优势,易守难攻。这个自西周兴起,后又几乎延续到春秋末期的鲜虞国,应该具备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国都就在今天的正定。到公元前489年,赵简子赵鞅率师北击并消灭鲜虞国,从此,鲜虞才在史籍中彻底消失。
下一个倒霉的就轮到仇犹国了。古本《竹书纪年》载:“晋出公十八年,河水赤三日。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这个“穷鱼”,据说就是仇犹。公元前457年智伯送钟,扫灭仇犹的故事,《韩非子》讲过,《吕氏春秋》也讲过。古仇犹国,就在今天的盂县。而在正史中,仇犹国几乎忽略不计。毕竟是一方诸侯,说不清来路,就连用这种下三烂的办法灭亡了也懒得写一句,这很不正常。没有巨大的隐情,晋国不会把这样的战果给抹去。可是,晋国为什么要这么肆无忌惮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吞并古道周边的这些小国,难道仅仅是一句想扩展领土就能说得通吗?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个吞并过程中,除了只有鲜虞国本能地反击过之外,全天下的诸侯国们竟无一理睬,更不要说挺身相救了,这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习惯这种“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了?还是柿子专拣软的捏?这里面恐怕都另有隐情。
最后是中山国。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占领左人、中人(在今河北唐县境内),“一日下两城”,中山国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是,就在这样的胜果面前,这次伐中山的直接指挥者赵襄子却一点都不高兴,甚至面露恐惧神色。《国语·晋语》中记录了赵襄子当时的话语说:“吾闻之: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当雍,雍不为幸,吾以是惧。”他认为这一日下两城的胜利实属侥幸,没有大道厚德,承载不了这样的福乐,所以他感到恐惧。看来赵襄子是深谙厚德载物之道啊。
不管怎么说,这中山国是在夹缝中生存,挫折中崛起,失败中壮大,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奇迹。就在晋灭仇犹仅仅四年之后,强大的晋国轰然倒塌,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名存实亡。前403年,韩、赵、魏被正式封为诸侯,历史在这里关上了春秋的大门,秦、齐、楚、燕、赵、韩、魏七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拉开了帷幕。中山国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开始了自己的复兴。
你要说晋国是为了扩张,才消灭这些戎狄之国,那为什么晋国并没有增加多少领土,自己反而都被灭亡了呢?我很纳闷儿,中山国是个例外。事实证明,中山国不是消灭不了,而是消灭了,他就又能活过来。
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仿效华夏诸国的礼制,在顾(今河北定州市)建立起中山国,重新确立政治军事制度,对国家进行了初步治理。正是百废待举的时候,武公去世,桓公即位。桓公年幼,不恤国政。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远隔千山万里的魏国魏文侯,派遣乐羊、吴起统帅军队,经过三年苦战,于公元前407年全面占领了中山国。魏文侯派太子击为中山君,将乐羊封在了灵寿。乐羊死后,就安葬在灵寿,乐羊的后代子孙就在灵寿安家落户。而中山国的残余也只好退入太行山中。
中山被灭后,桓公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终于积蓄力量,在公元前380年前后,又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就定都在灵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北平山三汲附近。
复兴后的中山国位于赵国中间,把赵国南北两部分领土分割开来,因此成了赵国的心腹之患。公元前377年、376年,赵国曾两次进攻中山国,均遭到顽强抵抗,没有成功。此后,中山国开始修筑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时至今日,平定、盂县境内尚有许多长城遗址,大概与中山长城脱不了干系。到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国,将王尚迁徙到肤施,中山国自春秋末期立国,经过350余年时间,才宣告彻底灭亡。
有意思的是,魏灭中山,可感觉上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占领。古本《竹书纪年》载:魏惠成王“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就是说公元前361年,魏国把属于自己的榆次和太谷两地,都给了邯郸赵国。
而被魏国封在灵寿的乐羊家族,也是名将辈出,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魏将乐羊的后代乐毅,竟然就拜燕国上将军,受封昌国君,公元前284年,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创下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报了强齐伐燕之仇。因受燕惠王猜忌,乐毅又投奔了赵国,被封于观津,号为望诸君。
从前我对一件事情一直感到费解,《史记·赵世家》所记“赵惠文王五年,与燕鄚、易。”这也就是说,公元前294年,赵国将属于自己的鄚、易二地,都全部无偿地赠予燕国。大家头破血流争来的土地城池,怎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给了人呢?
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至少这莫国,本是周王朝正统天子周携王的封都。从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294年,这都过去四百多年了,赵国还是忌惮周天子的土地不好吞占,而燕国作为战国七雄中唯一的姬姓封国,可能也只是名义上接受莫、易二地,不可能实际上去管治周携王的土地。同样道理,中山国也一样,连同那几个小国,他们都曾经是周携王一手扶持起来的附属国,总是与周天子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所以,灭亡你,只是在展示肌肉,炫耀武力。不实际占有,甚至还拱手与人,那也就是卖个人情,把烫手山芋甩给别人,不至于头顶巨大的舆论包袱。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连榆次都曾经是魏国的,中山可谓大矣!
周携王死后,他曾经倚重过的势力,就分解成了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不伦之国,我们不知道这些小国的出处,却只看到他们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在历史的夹缝中人人喊打,几乎所有的正史都将周携王姬望及其相关全部剔除出去,举国上下,避之唯恐不及,谈虎色变,讳“莫”如深。是的,这个“讳莫如深”的成语,就携带了这样一份秘史流传了下来,好在莫国故城还在,莫姓后代繁盛,任何处心积虑的掩盖,总是会真相大白的。《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何也?讳莫如深,深则隐。苟有所见,莫如深也。”这是一种怎样的痛啊?不能说,不可说,不敢说,你就是亲眼所见,也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为了保存一点点原汁原味,我在文中用了莫、鄚二字。而历史上的莫国,就是鄚国,讳莫如深,也就是讳鄚如深。这是非常难认的一个字,在繁体字的史书中,至少在《史记》中,这个鄚字经常就与郑的繁体“鄭”字混为一谈,于是,偶尔还有把莫国的人和事都张冠李戴给了郑国。比如扁鹊,就是“鄚”国人,可也有人说是郑国人。因为“鄚”国,谁知道啊?还有这国?不是弄错了吧?唉,这一隐讳,多少史实百口难辩啊!
晋文侯杀周携王之事极其重大,周人史官绝口不提;向来重视史实记述的鲁国史官绝口不提;讲究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孔子,在作《春秋》时也绝口不提。抑或周平王对这等大逆不道之丑事或曾下过封口令,抑或销毁过相关历史证据,亦未可知。又或许讲究仁义道德的中原诸侯各国自感理亏,主动封口。而只有僻处南蛮的荆楚史官,后期三家分晋而崛起的魏国史官,才分别在楚简《系年》及魏史《竹书纪年》中有所记录,才给我们留下还原真相的宝贵文献资料。
这样看来,明代马中锡写的《中山狼传》,简直就是一篇史记。“赵简子大猎于中山”,这里的中山在何地?在寿阳,在平舒。被誉为清朝三代帝王师的祁隽藻,就是寿阳平舒人,在他的著作《马首农言》中写道:“余家平舒村,在太安村南二里许。《县志》西北乡十七所,其一平安,所辖一村曰太平,距城三十里,是太安、平舒本一村也。今平舒北有唐崇福寺,寺有神功元年经幢,规模宏壮。意当时人烟稠密,连延数里。后乃析为二村,而《县志》因其旧。邑故山国,此独平坦,故曰太平。平舒,两见《汉书·地理志》,代郡平舒,渤海郡东平舒,皆县名也。”很显然,就是祁隽藻也不敢相信他的故乡平舒,曾经属于中山,属于魏国,属于过燕国啊。在谈到寿阳赵简子墓时,祁隽藻写道:“简子墓亦赵氏之九原”,“拾赵陵之瓦(赵简子墓瓦细者可为砚),穿砚堪书。”
不过,看看祁隽藻笔下的平舒,也是由来已久,到唐朝时,这里“人烟稠密,绵延数里”,气势非凡。赵简子在寿阳曾经修造过贺鲁故城,康熙版《平定州志·古迹》载:“贺鲁故城,在县西北三十里。旧志云:赵简子食邑,城址微存,城东有简子墓,前有祠。”而平舒乡南紧邻着的南燕竹镇,就有南燕竹,北燕竹两个地方,在北齐的时候,这里还建有燕州城,为什么偏偏在平舒的旁边就有一个燕州城,而这些地方的名字里还都有一个燕国的燕呢?
还有那个东郭先生,也是平舒人。平舒乡有东郭义和西郭义村,村里还有关于东西南北郭四兄弟的传说与墓地。为什么狼是中山狼,而平舒人东郭先生就与中山国毫无瓜葛呢?那赵简子怎么会在中山打猎呢?从榆次属于过魏国,整个中山国都曾经属于过魏国,而被封在灵寿的魏国大将乐羊的后裔乐毅,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为燕国大将军,这其中有多少令人费解,不可思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魏国占领的中山,一定与燕国有不解之缘,赵国能把莫、易赠给燕国,那魏国会不会与燕国也有这样的眉来眼去呢?至少不能完全排除!
光绪版《寿阳县志·建置》载:“中山神庙,在县东北二十里。俗称大王庙,兼设夫人像。土人以雨辄应,虔祀之。”从这个记载来看,寿阳确实有中山神庙。如果毫无瓜葛,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庙宇,也不会有这些祭祀活动,也印证着这块土地与中山国有不解之缘。
晋代郭缘生《述记征》载:太行山首始于河内,自河内北至幽州,凡百岭,连亘十二州之界。有八陉:第一曰轵关陉;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此两陉今在河内;第四滏口陉;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一名望都关;第七蒲阴陉,此三陉在中山;第八军都陉,在幽州。在这里,郭缘生明确地告诉我们,井陉、飞狐陉、蒲荫陉都在中山境内。那么,中山复国之后发生了什么?还是复国之前已既成事实的又有什么?我们不好猜测。但是,从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寿阳平舒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曾经属于燕国,后来,赵国与燕国交换土地,才把平舒换给了赵国。
既然寿阳平舒曾经是燕国的国土,那么,在连接榆次、平舒、柏井,直至邯郸或燕国的井陉古道上,在柏井这样一个大驿站通道的关楼上镶一块“燕赵享衢”的石刻,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柏井驿的这块石刻,绝不是后人所凿,应是那个时代的作品,那线条优美的大纂字体,也向世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两千多年的东西了,我们应该珍惜!
平定蕴藏着三百多公里的古道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宝库,一块石头就这么多说道,一条古道,简直就是一部华夏文明史。弘扬光大,吾辈责无旁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