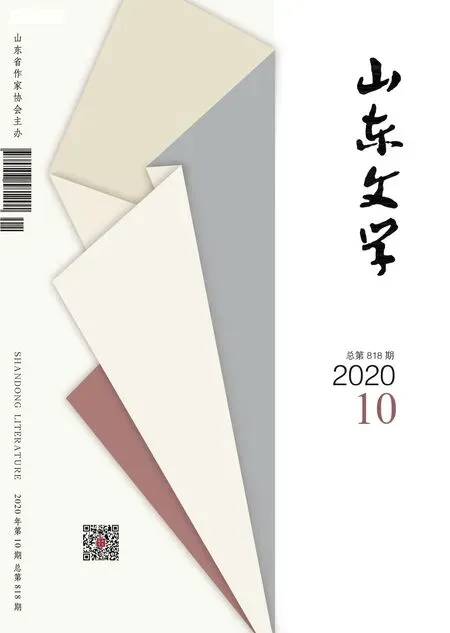汶水汤汤
2020-11-18
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鲁道有荡,齐子游敖。
这是《诗经·齐风》里一首题为《载驱》的诗的后两节,首句都提到了“汶水”。汶水,即大汶河。“汤汤”和“滔滔”都是形容水势浩大、水流很急的样子。逐一解释这首诗也许显得过于冗杂,不如让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白话诗(上面的诗歌和下面的译文,均摘自王秀梅译注的《诗经》,中华书局出版社2015年北京第一版第201页):“汶河流水泛波浪,路上行人熙攘攘。齐国大道多平坦,文姜在此任游荡。汶河流水卷波浪,路上行人如观潮。齐国大道多平坦,文姜往来自逍遥。”
诗中的“齐子”,指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僖公的次女文姜。齐僖公二十二年即鲁桓公三年(公元前709年),文姜嫁到了鲁国,为鲁桓公夫人。被誉为美女和才女的文姜,从小就是父亲齐僖公的掌上明珠,嫁到鲁国以后,鲁桓公也是十分喜爱,当年九月,鲁桓公就在泰安大汶口河岸建文姜城(俗称文姜台),用作文姜省亲时的行宫。文姜从小就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姜诸儿一起游玩,出嫁前,二人虽为兄妹但彼此不忌男女有别,逐渐由兄妹之情变成了儿女私情。鲁桓公十八年(公元前694年)春天,文姜跟随丈夫鲁桓公去齐国修好,已为人妻且贵为国君夫人的文姜,再度与姜诸儿私通。此时的姜诸儿已经是齐国的国君齐襄公。可是,纸里怎么能包住火呢?这件事终于被鲁桓公觉察到了,鲁桓公既羞惭又愤怒,便责备妻子不守妇道。已经被丈夫察觉的文姜这时应当知过思悔,痛改前非,可是,她不但不思悔改,还把鲁桓公责骂她的事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听了文姜的话,不但不劝慰她,二人从此收敛,而且暗暗下定决心除掉鲁桓公。有一天,齐襄公宴请鲁桓公,便将鲁桓公灌醉,随即派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杀死了。一国之君死在了自己这里,这件事怎么也得对天下人特别是鲁国有个交代,而齐襄公自己当然不想承担这个责任,为了掩人耳目,他便把鲁桓公的死嫁祸给了彭生,而把彭生处决了。
鲁桓公被杀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鲁国。国不可一日无君,鲁国的大臣们便拥立13岁的太子同继位。太子同即位后称为鲁庄公。文姜毕竟是出嫁到了鲁国的人,现在她的儿子又即位了,迫于内外舆论的压力,她也不好赖在齐国不走,因此,鲁桓公去世后她又在齐国住了一段时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齐国都城向鲁国走去。当她走到一个叫禚( 音zhuó,一般指春秋时齐国邑名,故地在今济南市长清区)的地方时,“见行馆整洁,叹曰:‘此地不鲁不齐,正吾家也。’”(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十三回)于是,她便在这里住了下来。
住在禚的文姜还是不顾儿子鲁庄公的颜面,继续与齐襄公私通。作为一国之君的鲁庄公,对自己母亲的丑事一直觉得很没面子,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鲁国的上上下下也都知道文姜与齐襄公私通的事,因此,人们便吟咏了本文开头的那首诗歌加以讽刺。那首诗的第三节和第四节,写文姜乘坐着华丽的车子走在汶水之滨时,只见汶河水势浩大,滔滔不息,平坦宽阔的大路上行人如织。坐在车里的文姜看到这些,又想到即将见到的情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鲁庄公八年(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国内大臣所杀。齐襄公被杀以后,文姜的心才慢慢地回到了鲁国。鲁庄公即位的时候,年龄太小,大权都掌握在他人手里,文姜逐渐开始指挥儿子管理国家政事。在处理政务上,文姜展现出了她超凡的本领,她不但迅速让鲁庄公掌握了鲁国大权,而且积蓄了雄厚的国力。公元前684年,齐国攻打鲁国,两国在一个叫长勺的地方摆开了战场,鲁国由于指挥得当,一举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长勺之战”。长勺,在今济南市莱芜区东北约二十公里处的勺山村东南。关于这次战争,《左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而且由于《左传》的记载,让一个叫曹刿的名字闪耀在了中国历史的星空。
文姜辅佐鲁庄公三十余年,其间,两国虽发生了诸如长勺之战这样的冲突,但两国关系还是以和为主。这难得的和平为鲁国发展创造了条件,故继任者鲁僖公时期,鲁国的强盛达到了顶峰。这不能不说与文姜有极大的关系。鲁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3年),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姜去世。文姜对鲁国的贡献得到了鲁国贵族的肯定,后来,孔子在编订《春秋》时,不但没有对她有丝毫贬损,而且在惜墨如金的文字中,竟有14处记载了文姜的事迹。文姜还是诗歌吟咏的对象,在《诗经·齐风》中的《南山》《敝苟》等诗篇中,都有对她精美的描写。
两千六百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无须去评价文姜。但是,因为文姜,我们的大汶河,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里,留下了她那澎湃激越的涛声。
从《诗经》里一路涓涓流来的汶河水,跌宕起伏,经过了秦时明月汉时关,流进了唐朝的江山。
有一天,有一个叫李白的诗人,长途跋涉来到了山东,好客的山东人在大汶河边摆下美酒佳肴,热情地为他接风洗尘。酒酣耳热之际,李白不禁吟诵道:
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
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
意气相倾两相顾,斗酒双鱼表情素。
双鳃呀呷鳍鬣张,拨剌银盘欲飞去。
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肌花落白雪霏。
为君下箸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
这首诗的题目是《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
李白是在他24岁那年也就是唐开元十三年(725年)离开蜀地故园,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那年,他乘舟沿江出峡,“朝辞白帝彩云间”,幻想着到京城长安去建功立业,开始他鹏程万里的飞翔。可是,直到他42岁的时候,才见到了当时的皇帝唐玄宗。如果说,离开蜀地那年,李白还是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文学爱好者,而此时的李白已经是誉满天下的大诗人了。唐玄宗对李白的才华很是赏识,礼遇隆重。李白的族叔著名文学家李阳冰,在他的《草堂集序》里说,玄宗皇帝一听说李白来了,便“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绮皓,秦汉间“商山四皓”之一),还“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当玄宗皇帝问李白一些当世事务时,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的社会观察,不假思索,慷慨激昂对答如流。玄宗皇帝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陪侍左右。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玄宗皇帝每有宴请或郊游,便让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记实。
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段时间以后,玄宗皇帝就对李白不满意了,将他“赐金放还”了。无奈的李白只有发出“行路难,归去来”(李白《行路难》)的感叹,离开了长安,从此结束了他三年梦一样的帝京生活,浪迹江湖去了。李白来到了山东,山东人的盛情让大诗人暂时忘记了他的忧愁和烦恼,他决定在美丽的汶水之滨居住下来。从此,他与汶河流域的韩凖、裴政、孔巢父、陶沔、张淑明等山东名士隐居汶水之滨,饮酒赋诗,啸傲山林,时人称“竹溪六逸”。
在山东的这个时期,李白在许多首诗中写到了汶水。《送梁四归东平》中写道:“殷王期负鼎,汶水起垂竿。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手提美酒强作欢颜的李白,对送别的朋友说,当今皇上正期待能人,就像殷王期待伊尹负鼎一样,你在汶水边就收起你的钓鱼竿吧,莫学谢安东山高卧,那样会老却英雄的。在《五月东鲁行答汶上君》中写道:“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你看我没有去考进士做官,反而到这里来学剑术,在我骑马举鞭问前程的时候,你汶上老翁却笑话我来了。此诗的前节八句着重写诗人初抵东鲁时的真实感受,后节十句是李白对汶上翁嘲笑的明快答复。这答复,也是诗人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
李白还把家人从湖北安陆接到东鲁兖州任城(即今济宁)来。在东鲁居住期间,他还曾去南方游历了三年。游历期间,诗人对远在山东汶水河畔的田地、酒楼、桃树等等,十分牵挂,尤其是对自己的一双儿女更是倾注了无限的思念之情。在《寄东鲁二稚子》一诗中写道:“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他想象自己的一双失去了母亲(李白的第一个妻子许氏那时已经去世)的小儿女在他亲手种下的桃树旁玩耍的情景,此时,作为父亲的他不在他们的身边,不知有谁来抚摩爱怜他们?想到这里,诗人不由得心烦意乱肝肠忧煎,无奈之下他只能取出一块洁白的绢素,写上自己的万般牵挂,寄给远在汶河之滨的家人。
天宝四年(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汶水之滨再次相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二人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二人却建立了兄弟般深厚的友情。这期间,二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泛舟东鲁门,行吟汶水滨,遍游古迹,谈诗论文,还曾一道寻访隐士高人,同去齐州拜访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这是李白、杜甫同游齐鲁在兖州分手以后,李白写下的《沙丘城下寄杜甫》一首诗。沙丘城,位于山东汶水之畔,是李白在鲁中的寄寓之地。诗人高卧沙丘之上,远望城内与杜甫一起观赏过的古树,不禁喟然长叹。汶水西南流向,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长安也正位于鲁地的西南,所以李白说,我的思念之情犹如这浩浩荡荡的汶河水,紧随你南行。
李白与杜甫在汶水之滨的交往和友谊,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珍贵的一页。他们的友谊,就像汶河水一样,千百年来浩荡不息。
大概是在天宝四年(745年)秋天,唐朝另一个大诗人高适从河南来到地处汶水北岸的东平。时任东平太守的薛自劝是高适的朋友。来到东平的第二年夏天,高适和同在山东游历的李白杜甫应北海太守李邕邀请,前往济南大明湖历下亭聚会,此后,高适随李邕一起到东平郡游历,且有诗相互赠答。从高适写于此间的诗歌来看,得知他在山东的活动以东平为中心,由此辐射齐鲁。
高适曾与卫县(今河南淇县)少府李宷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高适来山东后,卸任的李宷来东平与他话别。李宷走时,高适去汶水边送他,并写了一首著名的《东平别前卫县李宷少府》送别:
黄鸟翩翩杨柳垂,春风送客使人悲。
怨别自惊千里外,论交却忆十年时。
云开汶水孤帆远,路绕梁山匹马迟。
此地从来可乘兴,留君不住益凄其。
诗中回顾了两人长达十年的友谊,抒发了客中离别的悲凄之情。云开日出,友人乘一叶扁舟顺汶水而下,水面上那一点帆影越来越远以至看不到了,而河岸上骑马相送的诗人却迟迟不肯回返。这里的“远”与“迟”两个字十分精妙。所谓“远”,不仅表现了汶水河岸上的诗人目驰神往,极力眺望友人“孤帆”远去的神态,而且还曲折传达出了此时诗人内心的复杂心理活动:此去一别,山长水远,今生今世不知道还能否相见?而一个“迟”字,正是此刻诗人这种主观感受的写照。诚如清代赵臣瑗所论:“去者去矣,帆非远,我偏觉其远;归者归矣,马非迟,我偏欲其迟。此二句写一种恋恋不舍情事,逼真如画。”(《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卷一)此诗在以豪放著名的高适诗中别具一格。
高适入朝,杜甫写一首《奉寄高常侍》的诗以赠,诗的首联写道:“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故人何。”这里的“高常侍”是指高适。
唐朝除李白、杜甫和高适以外,还有许多诗人的诗作中提到了汶水,如岑参、王维、戴叔伦、韩翃、刘长卿、刘禹锡等,唐朝以降,苏轼、黄庭坚 、王安石、王禹偁、范成大、辛弃疾以及元朝的王冕、清朝的龚自珍等,也在自己的诗歌中写到了汶水。
大汶河发源于济南市莱芜区,在莱芜区的一段叫牟汶河。牟汶河向西流入泰安,一路又与嬴汶河、柴汶河、石汶河、泮汶河几大支流相汇,最终在泰安大汶口镇东南形成了一道宽广的河面。在历史上,这里曾经是泰安八景之一的“汶河古渡”。明成化年间,泰安知州戴经来到这里,看到河岸上杨柳依依,芳草青青,河面上烟波浩渺,舟楫往来,遂作诗一首:
五汶萦洄一脉深,巡崖转壑下千寻。
飞流画艗波光动,界道长虹草色侵。
曲水亭边云漠漠,文姜台畔雨沉沉。
渡头凭吊当年事,却羡渔舟傍绿浔。
“江河滔滔向东流,唯有汶水倒流西。”作为我国古代文明发祥地和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摇篮之一的大汶河,和众多的河流不同,它那滔滔不息的河水,一路向西流去。“汶水西流”便成了齐鲁大地上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时至今日,这西流的汶水依然是人们津津乐道和游览的好去处。
明朝嘉靖年间,牟汶河岸边的莱芜县来了一个新科进士担任县令,这个人是福建莆田人陈甘雨。陈县令在任之时,编纂了一部《莱芜县志》,志中,他将“汶水西流”列为莱芜“八景”之一,并为这西流的汶水赋诗一首:
银潢一脉自龙湫,涤荡长涵千古愁。
只为朝宗寻禹穴,涓涓沿涧向西流。
诗前有小序:“(汶水)在城南门外。发源于原山之阳,西南入济,因达于海。水皆东流,唯此流西,故纪其异。”银潢,指银河;龙湫,指悬瀑下的深潭,犹言龙潭;涵,包含;朝宗,比喻小水流注入大河;禹穴,俗称女娲洞,位于陕西省旬阳县县城东约五十余公里处,相传大禹治汉水时曾于洞内歇息,因而得名。陕西在山东的西方,汶水之所以涓涓西流,原来是去寻找朝拜大禹的住处啊。当然,这是站在河岸上望着滔滔西去的汶河水的陈甘雨,情不自禁引发出来的诗意的想象。
陈甘雨之后,“汶水西流”便不断地流进了诗人墨客的笔尖。
赐履分茅事可稽,何缘归鲁复归齐,
纷纷予夺迷蕉鹿,此日平畴雨一犁。
这首题为《汶阳田》的诗,作者是萧协中。萧协中(?—1644),字公黼,明朝末年泰山知名学者,其自幼工于诗赋,十八岁时因作《绿远楼赋》而蜚声文坛,后以父(萧大亨)荫入仕,退休还乡后寓居泰安城酝檀园,致力于泰山地理风物的研究。赐履,语出《左传·僖公四年》:“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杜预注:“履,所践履之界。”后以“赐履”指君主所赐的封地。分茅,语出《尚书》,古代分封诸侯时,用白茅裹着泥土授予被封者,象征授予土地和权力。稽,查核。蕉鹿,典出《列子·古注今译》。有一个郑国人在野外砍柴,看到一只受伤的鹿跑过来,就把鹿打死了,他知道这只鹿是被一个猎人打伤的,因担心猎人追来,就把打死的鹿藏在了一条小沟里,又砍了一些蕉叶覆盖在死鹿的身上,把鹿遮藏起来。等到天黑了,那人便想把死鹿扛回家,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只死鹿了,他就安慰自己只当是做了一场梦。后遂以“蕉鹿”指梦幻。了解了这几个词语的意思,整首诗就不难理解了。当年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应该是很清楚的,汶阳田到底是属于齐国还是鲁国,应该是有据可查的,可是,为什么在那一段刀光剑影的历史上,它一会儿属于齐国又一会儿属于鲁国呢?这可真是让人感到迷惑不解。
对于“汶阳田”的具体位置,历来有各种说法。通常的解释是:汶阳田是春秋时期鲁国属地,因在汶水之北,故名。关于“汶阳田”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鲁僖公元年(前659年):“冬,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鲁僖公是鲁庄公之子,春秋时期鲁国的第十八任君主,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7年在位。季友是鲁庄公的弟弟。从这段距今已有两千六百多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汶阳田是在鲁国境内——如果不是在鲁国境内,鲁僖公怎么会把那里赐给叔叔呢?《论语·雍也》中有一段话:“季氏使闵子骞为费(今山东费县城西北约10公里处的上冶镇南)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你看,人家季氏派人来请孔子的学生闵子骞去做费邑的长官,闵子骞却对人家说:“请你好好替我推辞吧。如果再来找我,那我一定跑到汶水边上去了。”《水经注·汶水》中有:“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县东北泰山,西南流,径汶阳之田。齐所侵也。自汶之北,平畅极目,僖公以赐季友。”清康熙年间叶方恒所撰《山东全河备考》中,有“牟汶(即汶河),以古牟城得名,在县南二十里,发香水湾。两山夹石盈亩,清流有声。合鹏山赵家泉,至盘龙庄,合浯汶西流,即古汶阳田处”的记载。赵家泉、盘龙庄均在莱芜城以东二十里余处。然而,“汶水之北皆为汶阳,其地多矣”,“汶阳田”应该是指泰安莱芜一带大汶河两岸的大片肥田沃土。
那个年代,农业在一国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的根本,两国交战、侯国内乱以及外族入侵的纷争,常常是为了取得更广阔、更适宜子民生存的土地,从而稳固政权、开疆辟土。因为肥沃的汶阳田处于鲁国的边界,强大的齐国为了争夺这块地方,便多次侵犯鲁国并把汶阳田占为己有,而鲁国当然不会甘心把祖上的基业拱手让于他人,因此,两国便因汶阳田多次发生纠纷。熟读历史的萧协中来到汶水岸边,不禁就有了“齐鲁必争汶阳田”之叹,也才有了“何缘归鲁复归齐”的疑问。后来,袁枚《随园诗话》中亦有“先失楚弓,旋归赵璧。汶阳田反(返),合浦珠还”的句子,由此引申出“汶阳田反”这一成语,足见“汶阳田”影响之大。
齐鲁两国对于汶阳田的争夺,许多史料上都有记载,最有名的应当是发生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的那一次。那一年,齐国的齐景公和大臣晏婴想和近邻鲁国等中原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吴国的威胁,恢复齐桓公的霸业,就写信给鲁定公,约他会盟修好。因那次会盟是在齐鲁交界处的一个叫夹谷的地方进行的,史书上便称作“夹谷会盟”。“夹谷会盟”是春秋时期的一次重要会盟。《左传·定公十年》中有这样的记载:“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孔子以自己的大智大勇迫使齐景公把先前侵占的鲁国的汶阳、龟阴等土地归还给了鲁国,并以此向鲁国道歉。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6年),鲁国为楚考烈王所灭。到了公元前223年,秦军攻破楚都郢城,楚国就此灭亡。公元前221年,秦又灭了齐国,齐虽然于公元前208年复国,但仅仅过了六年,到了公元前202年又被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所灭。齐国和鲁国从此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齐鲁必争汶阳田”也就成为了历史。
数千年以来,“汶阳田”一直是骚人墨客们的向往之处。《论语·雍也》中的那个闵子骞不肯去做官,躲到汶水边上去干什么呢?大概就是想在那里耕种汶阳田,过与世无争的日子吧。也许,就是从闵子骞以后,“汶阳田”便成了“归隐田园”的代名词,后来的诗人便常常在自己的诗歌里,借此发泄自己不被当朝重用或对贬谪不满的愤懑,来表达自己归耕田园“退而甘食其土之有”(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愿望。
早在唐朝,“汶阳田”就常常出现在了诗人们的笔下。高适在《东平路作三首》的第二首中写道:“扁舟向何处?吾爱汶阳中。”岑参在《送孟孺卿落第归济阳》一诗中写道:“献赋头欲白,还家衣已穿。羞过灞陵树,归种汶阳田。客舍少乡信,床头无酒钱。圣朝徒侧席,济上独遗贤。”刘长卿在《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当苗税充百官俸钱》中写道:“春草长河曲,离心共渺然。方收汉家俸,独向汶阳田。”韩翃在《送高别驾归汴州》中写道:“久客未知何计是,参差去借汶阳田。”曹邺在《奉命齐州推事毕寄本府尚书》中写道:“截断奸吏舌,擘开冤人肠。明朝向西望,走马归汶阳。”刘沧在《旅馆书怀》中写道:“客计倦行分陕路,家贫休种汶阳田”等等。
北宋诗人王禹偁,是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等,因敢于直言讽谏,屡受贬谪,他曾写下了一首《酬太常晁丞见寄》的诗:
当年布素定交情,恨不同为出谷莺。
犹作三丞君最屈,偏寻两制我知荣。
湮沉莫厌青衫在,彼此俱嗟白发生。
重入玉堂非所望,汶阳田好欲归耕。
“玉堂”代指宫殿。一生坎坷起伏,而今白发丛生,重入朝堂为官不再是我的希望,而今啊,我只是想归耕汶阳田聊度残生。
苏东坡在他的《送李公恕赴阙》一诗的最后写道:“世上小儿多忌讳,独能容我真贤豪?为我买田临汶水,逝将归去诛蓬蒿。安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政治上的受挫,仕途上的失意,使得东坡一生坎坎坷坷,但是,他绝不愿意“俯仰随人”,一直想“买田”过田园生活,此番好友李公恕北上还朝,路过汶水之滨时,可为他买下一块田地,他将辞去官职躬耕田园。当然,这只是苏东坡的理想,也是他借此表达的一种愤懑之情。
明代著名文学家济南历城人李攀龙,在陕西为官时,曾写有一首《出郭》:
出郭随吾适,人家杜曲边。
溪流萦去马,山路入鸣蝉。
禾黍殷秋作,茅茨入昼眠。
可能祛物役,归买汶阳田。
全诗大意是:在一个秋天,我骑马走出任职的城郭来到一个叫杜曲的地方。行走在山路上,我看到溪流边有几户稀疏的人家,听见秋蝉那一声声的鸣叫。现在正是深秋时节,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农夫们正在收获,那不远的茅草屋虽然简陋,但足以小憩酣眠。看到农人们是那样洒脱无羁,我不禁产生了归隐的想法,我多想放弃利禄官位,回归故里,在汶水之滨买下一块田地,和这里的农人们一样,躬耕田野。全诗表达了作者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千百年来,汶水之滨的“汶阳田”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样,成了人们向往的理想之地,但是,“桃花源”扑朔迷离如梦如幻,无迹可寻,以至“后遂无问津者”,而“汶阳田”却实实在在的存在于鲁中大地上。
硝烟散尽,化剑为犁。汶水两岸,千里平畴。
汶水汤汤,
汶水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