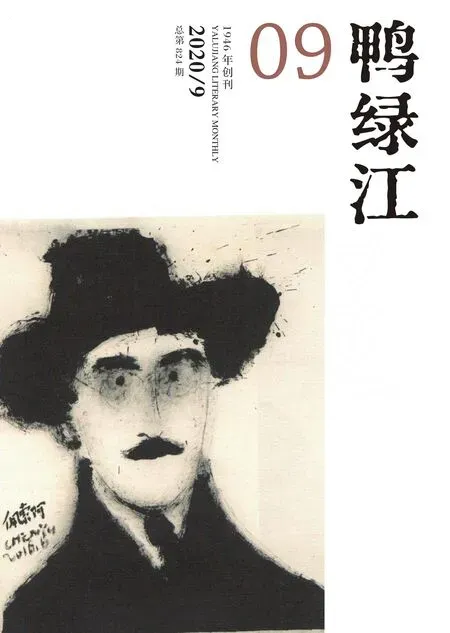另一种青年精神(评论)
——重读闻捷的诗歌
2020-11-17褚云侠
褚云侠
时隔多年,重读闻捷的诗歌,我们仍能被一种青春的蓬勃所打动。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或许很难再从诗艺的角度探讨那些建国初期一体化表达语境下的诗歌了,但正如闻捷当时的创作就呈现出迥异于李季、阮章竞、李瑛等诗人的风格一样,至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给他带来极大辨识度的气息,而这种气息的核心是一种青年精神。一如“生活,生活在召唤啊!我漫游沸腾的绿洲和草原”(《天山牧歌》序诗),抑或“苏丽亚伫立的地方,山丹花开得更红更旺……”(《送别》),无论是欢乐还是忧伤,都充满着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这不仅仅是慷慨激昂的抒情,而更多的是他站在更贴近青年自然属性的角度上确证了另一种精神的存在。
慷慨激昂的抒情,是20世纪50年代诗歌的普遍特征,楼梯体、感叹词的大量运用和雄浑、沸腾场景的密集呈现是当时的时代氛围和文学环境造就的,也是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在个人和祖国的青春时代特有的热情与赤诚。和大多数作品一样,创作于此间的闻捷诗歌,也始终被一种赤忱的热情所贯穿。那时他不满三十岁,正值自己的青年时代,在李季的回忆中,1948年前后的闻捷,“总是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地,挺起他那宽阔的胸膛,以他特有的男高音,引吭高歌。他的嗓音那么嘹亮,歌声里饱含着炽热的感情,在习习的晚风里,激荡着延河的微波,叩击着人们的心弦。”(李季《清凉山的怀念》)但是如果闻捷的诗歌只有这种炽热和激荡,我们可能就很难将它们从类似“我的寸金的时间,我的寸金的热土”这样的句子中区分出来。
相比于政治化的需要和统一抒情模式的收编,闻捷诗歌一进入人们的视野,似乎就有着鲜活的画面感、诙谐的故事性和丰富的细节。正如《向导》《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熟了》等几首诗作一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辑们就惊喜地发现这些诗歌中有着崭新的生活、新颖的构思、鲜活的语言和纯朴的感情。的确,闻捷的诗歌是具备这样的品质的,而这和他自身的经历以及新闻记者的身份密切相关。闻捷1949年随军到新疆,在新华社西北总社任采访部主任。1952年之后,又担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而他最初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的诗歌,以及后来结集的《天山牧歌》,正是来自他在新疆生活的切身观察和创作准备。闻捷的理想就是要在祖国的边地建起一座座青年城,他在写于1955年10月18日的《列车开动以前》中,用一个行将出征的青年垦荒队员的口吻说道:“我们在天安门前曾立下誓言,要在大荒原上建一座青年城,倘若是支援未曾实现,我们就永远不回北京。”无论是建国初期到新疆,还是20世纪50年代又辗转各地,他几乎白日和年轻人一起劳动,夜晚听老艺人弹唱古今,可以说这种生活不仅实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青年和工农兵相结合,而且使他的报人职责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发挥。闻捷对新闻工作始终是充满热情的,他甚至认为当你以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去写作时,新闻和诗已经不存在多大的差异了,这也促使他以一种“本报讯”的眼光不断去发现、去观察、去抒发、去捕捉每一个画面。正如他在《天山牧歌》序诗中所说:“记载下各民族生活的变迁,岂不就是讴歌人民的诗篇?热血在我的胸中鼓动,激发我写出了所闻所见。”有些诗歌甚至就像报纸对人物、事件的记录,比如《给饲养员》《给记账员》《给胆小怕事的同事》等,可以说闻捷充分发挥了他写作“本报讯”时对故事的讲述方法和对瞬间画面的抓取。其实他的那些诗篇正是从这种所闻所见中来,而当他与这些年轻人亲密无间地劳动或者构建他想象中的青年城时,也总是能发现青年的所思所想。这些不是被革命想象出的青年问题,而是更加贴近他们自身生活的真实体验。
事实上,如何为青年写作的问题也正是当时文艺界需要关注并且有所忽视和欠缺的。老舍在1955年学习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之后,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文艺从来没有注意过为青年写作的问题,自然也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号召。虽然青年形象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但是并没有在风格上为青年做打算,因此还没有被青年承认。“我们似乎都听说过,青年们有许多问题,像恋爱、升学、选择职业、如何热爱劳动等等,可是我们并不因听到这些而去了解青年的生活,于是就总也想不起写一写这些问题”(老舍《多给青年们写点》)。不仅如此,老舍还提倡用更加通俗、精练、鲜明的方式为青年去描写山河的奇丽、宝藏的丰富和长期忽视的冲风破浪的海洋生活。闻捷的创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老舍提出的号召并满足了“为青年写作”的大部分想象。他从一发表诗歌就将一派祖国边地风光带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天山牧歌》中,博斯腾湖无边无际,水天相连,“湖面上掠过雁群,白天鹅飞上蓝天,散布在湖滨的帐篷,飘起淡蓝的炊烟”(《远眺》);吐鲁番的葡萄甜、泉水清,“金色的麦田波起麦浪,巴拉汗的歌声随风荡漾”(《金色的麦田》)。在《河西走廊行》这部诗集中,闻捷跟随朱德同志行走在河西走廊,随着列车一路西去,所到之处他都留下了自己的诗篇:初进走廊时他看到“高高的白杨吐绿叶,低低的红柳冒青尖,天上飞过南来的雁,地里布谷鸟叫得欢”(《初进走廊》);在月牙泉边的鸣沙山,“五色的沙山忽然通体透明,恍惚是古代壁画里的金色幻城”(《沙岭晴鸣》)……武威风沙、张掖古郡、阳关遗址、三危山、莫高窟、兰州,无一错过了闻捷的笔端。而他在东南海岸和水兵一起生活的经历,还使他写就了不少关于水兵和海上生活的篇章,这部分诗歌包括了结集在《祖国!光辉的十月》中的《黎明出航》《我走在街道上》《水兵素描》《白海鸥之歌》《海上的号兵》等,而这也恰好弥补了老舍所提到的对我们绵长海岸线的遐想。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闻捷发现了青年关心的问题,比如择业、比如奋斗、比如恋爱。在《志愿》中,牧人们趁着酒兴谈论如何把和硕草原变成一个人间乐园,席间一个小姑娘林娜“仰起火光映红的脸,她愿终身做一个卫生员……让老爷爷们活到一百岁,把婴儿的喧闹接到人间”,这是青年质朴、平凡但又志存高远的职业选择。在《海上的号兵》中,“我虽不是一尊巨人的塑像,但体格却又似青铜铸成。我活着,手旗就应当摆动,这是祖国赋予我的使命”,这是青年所应有的英姿勃发和家国情怀。在《赛马》中,“他的话像小河流水,句句渗进我的心田”,这是青年男女之间的彼此爱慕和惺惺相惜。闻捷真正了解青年,而他创作的经验也正源于此。
因此翻阅闻捷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很多都与青年命题有关,尤其是爱情,爱情诗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闻捷笔下,这种爱情自然、纯朴地发生在青年男女身上,还不时有着对他们恋爱隐秘心理的幽微呈现。细观这些爱情诗,它们至今仍然有着动人心魄的力量,甚至也正是这些爱情诗,让闻捷在当时成为一个别致的个案。比如《舞会结束以后》是一首追求和试探之诗,年轻的琴师和鼓手在舞会结束后左右环绕着他们爱慕的姑娘吐尔地汗,含蓄而又大胆地表达着他们追求幸福的细密心思。“琴师踩得落叶沙沙响”“鼓手碰得树枝哗哗响”,这些对细节的捕捉恰到好处地渲染了追求的氛围,隐约传达出表白之前的激动和紧张,而制造出的响动又似乎在一决高下。紧接着两个人谦逊、平和地把选择爱情的主动权交给了面前的姑娘。姑娘的拒绝明晰又不失礼貌,并坦陈和坚定了自己早已选定的幸福。虽然结尾把对爱情的持守和祖国建设联系在了一起,但整首诗对恋爱心理的把握和对爱情大胆、自由的追求却格外细腻生动和引人入胜。再如《苹果树下》是一语双关的爱情表达,小伙子悄悄爱上了在苹果园里一起劳作的姑娘,随着姑娘种下的苹果树一天天长大,也如他们的爱情一样等待着开花结果。小伙子内心的火热使他影子一样包围着姑娘,共同守护着姑娘栽下的苹果树,或者说是他们隐而未发但已渐渐成熟的感情,但羞涩和矜持却让他始终不知该如何表达。在诗歌的结尾,作者似乎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和期待,他打断了全诗田园牧歌般自然展开的悠扬节奏,跳脱出来告诉“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你不要、不要再唱歌;姑娘踏着草坪过来了,她的笑容里藏着什么?……说出那句真心的话吧!种下的爱情已经收获。”在一个个人情感被集体情感普遍压抑的时代,闻捷鼓舞着青年人去追求那些发自内心的纯朴爱情,虽然这种爱情最终难免会和社会氛围中所萦绕的劳动、建设、奖章联系在一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爱情问题是与自然人身份的青年人密切相关的。
在建国初期,如此书写爱情的诗歌已经很难找到了,当时的恋爱更多是一种革命加恋爱,而个人的情感往往也让位于更高意义上的阶级之爱或被其引导与规约。而就在大多数情感话语沦为空洞的修辞或符号性的意义能指时,闻捷似乎从不想失去他抒情的“具体性”。他以一种青年的共情细致入微地体察着年轻人的隐秘心理和真挚情感,在爱中的回避、猜疑、纠结、别离,以及劳动的神圣和新生活对他们热情的召唤。在一个青年的自然属性几乎被抽空和遗忘的年代,闻捷用诗歌提供了有关青年自身的诸多“细节”。而现在看来,这些细节是至关重要的,它让我们看到在历史发生断裂的时刻,人的情感始终是延续的。而更多有关历史的秘密,也恰恰保留在这些细节中。
从闻捷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分辨和体认出一种青年的精神,而这种“青年”和当时的普遍想象是不尽相同的。其实在整个20世纪50—70年代,“青年”是频频出现的词汇但又往往语焉不详,甚至有学者将它与青春、爱情、生命等指认为是一种“空洞的能指符号”(黄子平语)。青年的确在这一时期有着尤其边界不清的宽泛范畴,它不仅包含了知识分子青年和学生青年,还有工农兵这一更加庞大的群体,新中国要赋予他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要使命,同时也要进一步将他们规约到一种划一的组织中去加以管理和引导。这时我们普遍理解和构建的“青年”不仅偏离了五四时期按照知识分子形态所描述出的形象,而且更是和青年本身的叛逆不羁、愚蠢莽撞这些反规约的自然属性相去甚远。而闻捷似乎用文字的方式,在一个社会使命为青年赋形的时代,试图召唤回那个接近本体意义上的青年,他们有七情六欲,也大胆追求,热情勇敢。但毕竟这样的写作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的,因此最终引导这些朴素的青春、热烈的爱情升华的,仍然没有脱离20世纪50年代建设祖国和走向新生活的话语体系。虽然这种召唤只是对“青年”自然属性的有限解放,但我们不该对那时的诗歌有过多苛责。况且闻捷对这样的青春设想是足够真诚的,因为他始终对未来抱有真挚而狂喜的憧憬,热切地渴盼新日子到来。他鼓舞各民族的青年歌唱青春,因为这不仅正值自己的青春,也是祖国的青春。他想用一年跨过一个世纪,甚至还在1958年的兰州畅想过1972年祖国的具体情景,他坚定地认为“我们有权利透视十五年后的未来,因为我们掌握未来的命运”(《我们遨游一九七二年》)。正如李季所言,闻捷总是“英姿勃勃,热情开朗,盈溢着才情的奕奕眼神,把他内心的一切,都展露在我们面前”。的确,闻捷的一首首抒情诗就可以看作是他内心最真诚的期待,但是历史没有按照他的幻想和希望向前发展,他也终因赤诚遭到无情的戏弄,而没能遨游1972年祖国的天空。
芦芒在《忆闻捷》中对诗人有这样一句评价:“一片心田,仍不失为单纯有时带些稚气。他无害人之心,不过常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些。”正是因为他的心中充满阳光,甚至单纯得带着稚气,才成就了他诗歌中一种更加接近青年自身的气象,也让他的抒情不乏真诚地失之简单,或许当一个人热情地诉说那些让他激动不已的事物的时候,这就是最好的抒情诗。而当我们今天一点一点剥去历史负载在文本上的沉重内涵,闻捷用文字所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或许正是从悬置着的青年本体中析离出的那些有限的,但却是永恒的、很不一样的青年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