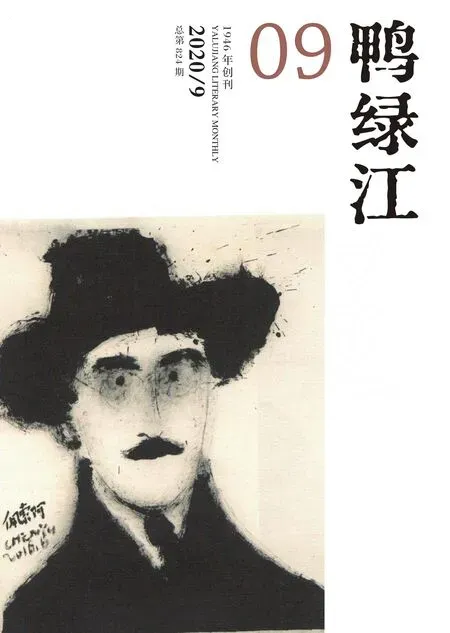《鸭绿江》与新中国文学经典·闻捷
2020-11-17宁珍志
宁珍志
主持人语:
对闻捷的认识当然是读他的诗。1965年由《诗刊》社选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朗诵诗选》,伴我在“文革”后期的农村度过了下乡的最后阶段。单纯的感情、单纯的理想、单纯的命运,加上十几岁年龄的单纯向往——对优美辞藻的膜拜,《我思念北京》顷刻进入我的脑海。“我思念北京,难道仅仅因为:/知春亭畔东风吐出了第一缕柳烟?/西苑的牡丹蓦然间绽放妩媚的笑容?/蝉声催醒了钓鱼台清流里的睡莲?/谐趣园的池水绣满斑斓的浮萍?/金风飒飒染红了十八盘上下的枫叶?/陶然亭欣然沉醉于月桂的清芬?/或是傲岸的松柏覆盖了天坛的积雪?/红梅向白塔透露早春的来临?……”少年记忆,一背一节。后来在县文化馆旧书库,我又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出版的闻捷诗选《生活的赞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闻捷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第一部《动荡的年代》、第二部《叛乱的草原》……由此,闻捷“情结”便萦绕在身、久驻心田,以至于作为“七七级”,在大三写的第一篇论说性文字竟然是关于闻捷爱情诗的《生活与情感孕育的美》。感谢闻捷的诗,让我的“论文”得以在学术刊物公开发表,收获了20世纪80年代之初的明丽、清和与美好。
弹指间四十年一晃儿而过,怀旧便爱回溯历史,在《鸭绿江》的“文艺红旗”年代,我又读到闻捷组诗《列车西去》(载《文艺红旗》1959年第2期)、长诗《英雄的行列》(载《文艺红旗》1960年第11期)。此时的目光与我的闻捷诗歌情结自然衔接,读的过程格外用心。《列车西去》副题为“河西走廊行”之六,是当年出版的诗集《河西走廊行》的一部分,八首诗后来被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闻捷全集》收在第一卷“抒情短诗”中,排列顺序都无多大改变。《英雄的行列》副题为“选自《复仇的火焰》第二部第四章”,即《出征》《攀山》两个部分。《复仇的火焰》共三部,第一、二部分别由作家出版社1959、1962年出版;第三部《觉醒的人们》20世纪60年代前期也完成了初稿,第五章曾以《一支古老的哀歌》为题,发表在《上海文学》1963年10月号,尾声《故事在这里结束》发表在《河北文学》1963年2月号,其他所有部分却在“文革”的一次次抄家中遗失散落殆尽。这是中国诗歌界痛心不已的损失,《复仇的火焰》的史诗性价值并没有完全被感应认知出来,它的民间歌谣、古典诗歌、现代自由诗“三位一体”完美融合的叙述方式,的确独创一家风范,我以为现在还无人超越。面对当下缺少史诗且无力写出史诗的诗坛困局,《复仇的火焰》值得往复体味鉴赏。当然,不排除它的欠缺。
闻捷的才华,闻捷的激情,闻捷的热诚,闻捷的勤奋……令他诗创作的成绩一个连接一个。《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祖国,光辉的十月》《东风催动黄河浪》《我们遨游一九七二年》《我们遍插红旗》《长江万里》《我思念北京》……抒情,抒情,再抒情;歌颂,歌颂,再歌颂……新中国、新生活、新景象、新人物,在闻捷笔下,都具有了光一样的魅力和精神气质。闻捷相信党和人民的事业,相信上级媒体的所有声音。当《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5日发出降低稿费的倡议之后,闻捷毫不迟疑,立即与雷加、李季一起签名,表示热烈赞同。在《河西走廊行》的“后记”,闻捷写道:“我想:如果世上没有太阳,鸟儿怎么能迎着黎明歌唱呢?……我总觉得:在我们的时代,文艺创作也带有极大的集体性,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执笔者,最后完成了它。”甚至在“文革”遭受迫害最为严酷的日子,闻捷宁可毁灭自己,懊悔自己的作品,也不质疑曾经的生活和信仰。杜鹃啼血而亡般的诗人闻捷,其赤胆忠心天地可鉴。在文学创作的个人化空间不断被拓展的今天,我们尊重和理解闻捷诗歌生命的连续性、一贯性,他的诗,感染和激励了几代人。诗歌表达,太自我,太“私有”,难免“经验”覆盖面窄小,人类的普遍性体验狭隘,感情共鸣、思想共识毕竟是诗歌内涵的重要构成。
闻捷的诗,今天再读,是品味历史,品味一个时代在诗人内心的几番投影,究竟能获取多少裨益,见仁见智不同。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性的美学意义?答案并非是否定。即便我随口吟出《我思念北京》的诗句,随手翻阅《列车西去》《英雄的行列》的诗行,单从词汇、意象、修辞、节律等语言学角度,获得的美感即能脱口而出个三五百字。在诗歌之外,不妨读一读戴厚英的两部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作为曾经的闻捷爱人,她的述说,能帮助读者全面理解诗人闻捷。但是,没必要把整个故事和一些细节与闻捷的生平画等号。小说,有原型,但还是虚构、高于生活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