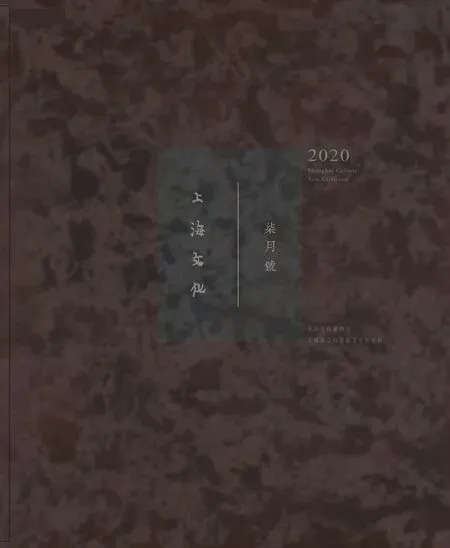月色满庭院
2020-11-17王辉城
王辉城
大约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位算命先生。他向母亲要了我和弟弟的生辰八字,然后开始为我们推断人生。结果被他用毛笔写进一叠白纸中,再订成一本薄薄的线装书。白纸黑字,郑重异常。母亲很是小心地用袋子把书包好,收藏至衣橱深处。
在我没有走进社会之前,一度非常惦记着这本书。于是,我翻箱倒柜,把它找出来。书早就泛黄、页面稀松、纸张脆弱,一些文字亦被虫孔所破坏。我翻阅着这本命运之书,发现算命先生所断的命运,细致到每个年龄段。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十四五岁会有个小灾难,需要防水;二十五六岁,可能会遇到爱情;三十岁以后,事业会进入上升期;四十岁之后,事业可能遇到挫折……
算命先生断的命运准吗?不那么准确,但也不是错得离谱。现在回过头想想,算命先生只不过把普通人的一生简单地归纳了一遍。十四五岁的少年,不知天高地厚,整日成群结队,喜欢到大河里凫水,稍稍不注意,可能就会被水流所吞噬;二十五六岁,正是成家立业的最佳时期;三十岁以后,工作多年,精力与经验都足够,事业自然会处于上升时期。而到了四十岁,不就面临着中年危机么?
我读大学那几年,父母几乎每年都会叫人帮我算一次命。而当我工作后,真正开启自己的人生后,赫然发现他们慢慢地就放弃了算命。如今想起,读大学那几年确实是他们对我未来最为焦虑、最不确定的时期。算命先生推测出那些模糊而又言之凿凿的命运,确实会给人一种奇妙的安定感。不管未来人生走向到底如何,不管算命先生是否真的“神机妙算”,父母对孩子未来巨大的焦虑,得到了纾解。在那本泛黄的命格书里,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清晰的、确定的未来。
一
假如真的有算命先生能窥破天机,能从生辰八字里推断出某个人一生的命运。推算的结果何止是不好,简直是糟糕。那么,这个人将如何面对自己残酷而多蹇的命运呢?
显然,多数人或奋力反抗,或极力躲避,没有人会乖乖接受,就此认命。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坦然接受多蹇的命运。唐人牛僧孺所撰的《玄怪录》卷二有《韦氏》一文,讲的便是韦氏勇敢面对自己惨淡人生的故事。
韦氏是豪门之后,家住京兆。在待嫁的年龄,面对着裴家、王家的求聘,她跟母亲说,“非吾夫也”。好在韦母是个开明之人。在韦氏二十岁时,母亲跟她说,进士张楚金前来求亲。韦氏听了,笑着说:“我的丈夫就是他了。”既然女儿已点头,母亲怎会不同意呢?于是,两家就择日成婚。
当一切都搞定后,母亲对韦氏问出自己埋藏在心底已久的困惑,你怎么就这么笃定张楚金是你的丈夫呢?于是,韦氏就向母亲道明真相。原来在她及笄之年的某个深夜,她做了一个凄美的梦,昭示了她一生的命运。
在梦境之中,韦氏二十岁时嫁给了清河的进士张楚金。刚开始,家庭、生活颇为顺利,张楚金亦“以尚书节制广陵”,家族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岂料,旦夕祸福,风云突变,张楚金伏法,满门皆死。整个家只剩下韦氏与刚过门的儿媳妇。两人被拘进皇宫,罚作奴婢,“蔬食而役者十八年”,才得以赦免,“蒙诏放出”。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大赦的诏令在中午已经传达到韦氏与儿媳妇之处,可等到她们出宫时天色已暮。两人只得匆忙赶路,走到一条河时,夜色已浓,罩住了四周。韦氏与儿媳妇四顾昏然,不知何往,只得在河滩上相拥而泣,相互勉励,说:“这里不宜久留,我们趁早过河吧。”渡河之后,韦氏与媳妇往南行,走进了一条破败的里巷。两人自西门入,沿着墙垣而往北走,犹如丧家之狗。自西而东,于东大门处遇见一所大屋。疲惫不堪的两人,前去造访,想得到休憩之地。大屋冷冷清清,大门洞开,无人把守。两人一路深入,走到戟门,又是门户大开,“亦入”。紧接着,韦氏与媳妇“逾屏回廊四合,有堂既扃,阶前有四大樱桃树林,花发正茂,及月色满庭,似无人居,不知所告”。
于是,韦氏与儿媳妇“对卧阶下”。岂料,刚刚躺下来,就出现一名老人,边骂边驱赶她们。韦氏与儿媳妇实在太过疲惫,便向老人说起自己的遭遇,以博取同情。两人的求情起到效果,老人的心顿时软了下来。他转身离开,算是默许。两人刚坐定,西廊处忽而传来脚步声。一少年“来诟,且呼老人令逐之”。
韦氏的遭遇实在是令人心酸至极,好在老人同情她们,苦苦为之求情。到了此刻,事情终于出现转机,少年低着头离开。过了一会儿,他穿着“白衫素履”出现,哭着跪在阶下。原来他是尚书张楚金的侄子。少恸哭不已:
“无处问耗,不知阿母与阿嫂至,乃自天降也。此即旧宅,堂中所锁,无非旧物。”
原来,这是张家旧宅。少年恸哭着打开堂门,里面布局与陈设,“宛如故居之地”。韦氏在这里生活了九年后,离开了人世。
韦母听了韦氏的话,心中颇为奇怪,“且人之荣悴,无非前定,素闻之矣,岂梦中之信,又如此乎?”韦母对女儿的梦兆有所疑虑,并未完全相信,“乃心记之”。果不其然,韦氏此后的命运,梦中之事,一一应验,“其褰裳涉水而哭,及宅所在,无差梦焉”。
以梦来昭示人生,乃是古典笔记常见的主题,唐人尤为喜欢。如著名的黄粱一梦、南柯一梦等,卢氏与淳于棼历经繁华,最终却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梦幻,转眼即空。当他们察觉世事无常后,便幡然醒悟,自此归隐山林。
梦兆所指向的命运,仿若深渊。梦中所昭示的人生,对于卢氏与淳于棼来说,是醒世警言,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人生的目标与意义。于是,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命运,他们低下头去,绕道而行,选择了一个最安全与稳妥的人生。
韦氏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就在于她没有逃避自己的命运,而是果敢地选择迎难而上。她不是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至少有两次绝佳的机会,摆在她面前。面对着裴、王两家的求婚,但凡答应了其中一人,她的命运就会截然不同。与张楚金相比,裴、王两人乃望族出身,韦氏嫁给他们,人生应该不会变得更糟糕。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韦氏为何会反其道而行之,坚定地走向命运的深渊?
二
必然会有超越苦难的存在,让韦氏愿意地接受自己的命运。人生若是只有苦难,只被动地“活着”,那么人生的意义将会消解,滑向彻底的虚无。充满绝望的人生,有什么价值呢?重复着苦痛的生活,有什么奔头呢?人们容易被苦难所魅惑,进而歌颂之、赞美之,并从中获得熹微的成就感,以抚慰自己贫乏的人生。苦难的价值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正如灾难过后的废墟,仅有的价值也许是回忆。
韦氏的人生,并非全是不幸与苦痛,至少在四十岁之前是幸福的。对于自己的婚姻,韦氏拥有知情权与自主权。韦氏父母并未因政治与家族的因素强迫女儿接受一段她不认可的婚姻。可见,韦氏是京兆夫妇的掌上明珠。在他们的保护与宠爱之下,她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而嫁给张楚金之后,丈夫事业步步高升,官至尚书;儿子健康成长,顺利成家。一切迹象显示,张楚金家欣欣向荣。
就在张楚金如日中天之际,一场猝不及防的政治灾难袭击了他。“在镇七年,楚金伏法,阖门皆死”,张楚金因何而伏法,伏法是何年何月?这些至关重要的细节,韦氏并未如实向母亲禀告,而是轻轻地带过,留下迷濛的空白。
谜底在后文才解开。原来张楚金伏法,乃是“神龙中以徐敬业有兴复之谋,连坐伏法”。又,《旧唐书》中有关于张楚金的记录,则透露了更多信息与细节。在武则天临朝时期,张楚金可谓荣耀极矣,“历位礼部侍郎、秋官尚书、赐爵南阳侯”,直到后来,才为“酷吏周兴所陷,配流岭表,竟死于徒所”。
那么,这是否说明张楚金伏法过程不重要呢?恰恰相反,是过于重要,才导致韦氏选择性地沉默。这短短几行字,便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忽起忽落,其落差之大,犹如云端坠入泥地。韦氏的复述,冷静、节制,私人的、具体的痛楚被巨大的历史情况所遮掩。这出《红楼梦》式的悲剧,韦氏选择轻轻带过,是对母亲、也是对自己最深的悲悯。
文学所要照亮的,不只是宏大的、跌宕的时代,还有幽微的、独特的时刻。果然,在家族的灾难结束后,韦氏从冷酷的历史中走出来,进入独属于个人的空间。韦氏所遭遇的困境,所遭遇的苦痛,变得细腻、具体、真实。婆媳两人天暮出宫,涉水过河,东奔西走,一段艰苦的“行路难”,宛在眼前。她们相顾茫然,一路上的诸多挫折,疲惫在慢慢累积。两个人来到堂屋,身心的疲惫已经达到极点。一幕摄人的美景,映入眼帘:
“阶前有四大樱桃树林,花发正茂,及月色满庭。”
在韦氏人生的暗夜里,终于出现了一抹温柔的亮色。似乎,韦氏此前所经历的困难与波折,都是为了这一刻而准备的。韦氏内心所郁结的疲惫、困顿、委屈、怨气,逐渐散去。于是,她内心的阴霾,被一扫而空,开始澄净、明亮。所有的苦难,都内化为柔韧的力量。那皎洁的月光,那盛开的樱桃花,对于韦氏来说,是超越狭隘仇恨的爱,是超越善恶的力量,是人生废墟盛开的美,是人生的永恒时刻。而这,将会照亮韦氏的人生。
与别人不同,韦氏因知晓了自己的命运,事实上是经历了两遍相同的人生。在纷繁而漫长的梦中,韦氏怀着对未知的恐惧,走向了未来。她不知道命运的转机在哪里,也不知道灾难会持续多久。她怀着战栗与恐惧,探索自己的一生,进而发现人生的意义。当她从梦中醒来,回到现实后,将会再次战栗地踏上人生的旅途。只不过,这一次她不是为了发现自我,而是为了验证自我。有时候,验证并不比发现困难。在新的人生里,她将会在怀疑与夷犹中度过。“花发正茂,及月色满庭”,也许将会是她在信念动摇之时的支柱。
三
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一书之中,对死亡作出了典型英式幽默的阐释,“他的去世是他短暂一生之中显著又英勇的事实,余下的不过是平日里普普通通的欢乐点滴”,当朋友谈论起死者,“发言者们拼命地想要扩充并抓住逝者一生中那些美好又平淡瞬间,填满从1968年到2012年之间的每一个日子,这样我们离开教堂时想起的就不再是他的生命的起点与终点,而是其间永恒的时刻”。
死亡让流动的人生静静地凝结在某个时间点上。进而,人生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抽象的事件,而不是延续的、流动的生活状态。从漫长的噩梦中惊醒过来的韦氏,从此成为一个阅读者和探索者。她必须像阅读一部小说一样,阅读自己的人生,并重新挖掘生活的意义。
“阶前有四大樱桃树林,花发正茂,及月色满庭”,自然是极其瑰丽唯美,摄人心魂。可人生路途,漫长而遥远,即使如韦氏提前知晓路况,亦需要更加坚实的力量来支撑。若是人生只依靠“永恒的时刻”,那么她将面临着彻底悲剧。因此,韦氏所要挖掘的生活意义,是“平日里普普通通的欢乐点滴”。这些细小的欢乐,才是生活的魅力所在。如果说“月色满庭院”让她超越苦难,而日常的、点滴的欢乐则是生活本身所具备的光亮。
韦氏在掖庭宫服役十八年后,“蒙诏放出,自午承命,日暮方出宫阙”。她明明是中午就可离开,为什么在日暮时分才出宫阙呢?行文即将结束时,牛僧孺揭开了谜底,原来是宫中有人留食,“午后受诏,及行,总监绯阉走留食候之。食必,实将暮矣”。一顿饭吃了整个下午,这才错过了最佳出宫的时间。换言之,韦氏与儿媳妇在路上所遭遇的困难,其中缘由就在于这顿饯别饭。
这是一顿重要的饭,“及行”“走留食候之”等字眼,足以说明这顿饭准备得很是匆忙。似乎,掖庭宫的同事们刚刚得知韦氏特赦的消息,于是才开始慌里慌张地准备饭菜。这种散发着喜悦的慌乱,不禁令人想起老杜的《赠卫八处士》。所以,也正是这些字眼,证明了这顿饭不只是例行公事,不只是一个出宫的仪式,而是日常生活里的欢欣与喜悦。
韦氏在宫中服役十八年与同事们建立起了深厚而又强劲的情感。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某个夜晚,她们会聚集在一起,说说知心话,交换彼此生命里的欢乐与苦楚。她们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掖庭宫里相互依存,温暖彼此的生命。也只有这样,韦氏才能在掖庭宫里安然度过了漫长的十八年,不至于被难以计量的苦难所窒息。所以,这一顿吃了一下午的饭,是喜悦与伤感并存。喜悦的是,韦氏就此脱离苦海;伤感的是,这是一场艰难的别离。韦氏与宫中好友,几乎都是迟暮之年,余生或难再见面。
一蔬一饭,是人生赖以生存的根基。人情冷暖,是社会得以运转的纽带。而在日常生活里,因其琐碎与普通,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之中,琐碎与普通的日常生活,才会显得弥足珍贵。当饥饿成为常态时,人情冷漠成为惯性后,普普通通的一顿饭,简简单单的一段情谊,就会超越日常,成为生存下去的依靠。
韦氏以戴罪之身进入掖庭宫后,肯定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惊惶与恐惧之中。一双无所不能的大手,扼住了她命运的喉咙。危险就潜藏在身边。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与掖庭宫里的太监、宫女们建立起联系。从陌生到熟悉,从心怀警惕到相互依存,韦氏一步步改善了自己在掖庭宫的生存环境。家破人亡给她带来的身心创伤,可能渐渐被日常生活所遮掩、所治愈。可以预见,韦氏十八年的掖庭宫服役生涯,并非全是悲哀的底色,应该还有一些坚实、朴素的温暖。
有一个问题,急需我们的回答:既然这顿饭如此重要,为何韦氏并没有向母亲讲述呢?答案当然可以是牛僧孺的叙述策略,但这样未免太过“正确”。以我个人的理解,即使韦氏在梦中度过了一生,但二十岁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这顿饭的重要。年轻的韦氏,衣食不愁,生活顺利,悬挂在人生半途中的灾难,她得走好长一段路程才能触摸到。一蔬一饭的情谊,日常生活里所蕴含的爱与力量,她是“只道当时是寻常”。人不都是这样么,年轻时爱起来轰轰烈烈,恨起来斩钉截铁,喜欢跌宕如飞的生活,只有老之将至,才会去珍惜身边的庸常与日常,才会承认生活的底色是“寻常”,而非跌宕的“传奇”。
四
就在韦氏十五岁那一年,她像所有唐朝少女一样,对未来充满期待,暗地里想象过自己未来的夫君。可是,在某个夜晚,一个古怪的梦袭击了她。在梦境之中,她度过了自己漫长而又坎坷的人生。
也许是清晨的鸟鸣,也许是母亲的叫唤声,惊醒了少女韦氏,让她摆脱了古怪的梦境。当她睁开眼那一刻,看到的是熟悉的房间,听到的熟悉的声音,心底里也许会庆幸,自己所遭遇的并非是真实的,而是梦境。此后,秀才裴爽、前参京兆军事王悟陆续前来求婚,让她感到战栗与恐惧:梦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会降临于现实;梦中所昭示的,不只是她个人的命运,还是整个家族的苦难。此后,韦氏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面对着来势汹汹的人生,她决定勇敢地迎难而上。
韦氏是勇者。生活中有两种勇者值得我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一是与命运搏斗者,一是命运肩负者。在凶险、动荡的命运面前,大多数人会选择消极逃避,常常陷入自怨自艾的情绪之中,进而导致人生不断下坠;命运搏斗者,可能会有短暂的迷惘与绝望,但他们很快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在看似不可能中撞出全新的未来,从而改变自我的命运;至于命运肩负者们,并非没有搏斗的力量,亦不是没有闯出新路的魄力,而是他们已然认清命运的面目,仍坚定地接受自己的人生,肩负起命运赋予自己的使命,并为之牺牲,为之奉献。这,才是最值得钦佩的,也是最艰难的选择。
梦境降临于少女韦氏身上,让她提前知晓了自我与家族的命运。就在她醒来那一刻,她就成为一名先知。而先知的力量,并非是预知一切,而是内心坚定的信念,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念,是勇敢接受西西弗斯式的苦难。
当然,韦氏不是西方式的先知。在知晓一切后,她没有去启蒙大众,而是选择一个人独自承重。她在母亲面前,守口如瓶。只有当命运成为现实后,她才选择遮掩最惨烈的苦痛,透露一二,解答母亲内心的困惑。在韦氏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女性的缩影,隐忍、坚韧、强大。在苦难面前,往往会牺牲自我,独自承担家庭的重任。可以说,韦氏是为了张、韦两家,而牺牲了自己。她也始终相信,自己所做的选择,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家族。
韦氏的选择,很容易被人误解成是宿命论。在《韦氏》一文结尾,牛僧孺写道:“梦信足征也,则前所叙扶风公之见,又何以偕焉。”可见,韦氏的经历仅是被当作宿命论的一个例证(宿命论的故事,在古典笔记中,多如牛毛)。当然,这并不是牛僧孺的错。因为宿命论一直笼罩在古人心中,阴霾不散。社会动荡、生老病死……宿命论用简单、粗陋与武断的答案,回答了繁杂的人生难题。而正是简单、粗陋与武断,让宿命论收割了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难以计数的信众。
五
现在,让我们盘点一下韦选择接受命运的理由:月下盛开的樱桃花、一顿匆忙准备的饭菜以及沉重的家族责任与使命?目前看来,她所做的努力,所做的牺牲,似乎都是为了他者。因此,当我们追溯韦氏的力量来源时,也许要正视她那颗更加自我的私心。不为义务与责任,不为日常生活,而是真正属于韦氏的“自私”。
韦氏两次“笑曰”与“终不谐”,引起我的遐想。在《韦氏》开篇,“既笄二年,母告之曰:‘有秀才裴爽者,欲聘汝。’女笑曰:‘非吾夫也’。虽媒媪日来,盛陈裴之才,其家甚慕之,然终不谐。”此后,王悟求聘的情况,亦“终不谐”。直到张楚金的出现,韦氏才“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
古文的简练,让两次“笑曰”,模糊一片。拒绝裴爽时,韦氏脸上挂着的笑容,是无奈的笑,还是从容的笑?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裴爽令韦家“甚慕之”,韦氏却倔强、坚定地“终不谐”。至王悟求亲,韦母已经动用了亲戚的力量,直接开口劝韦氏,与逼婚无异了。而韦氏的内心与意志,仍坚定如一,“亦终不谐”。可以想象,少女韦氏面临着巨大的家庭与世俗压力。
有了裴、王两家的前车之鉴,家世不及他们的青年才俊们,自然会知难而退。韦氏的婚姻问题,就此被悬挂着,状态很是尴尬。在韦氏二十岁那一年,张楚金出现了。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穿着他最好的衣服,带着他最好的礼物出现了。他的“最好”,在豪门韦家面前,还是显得寒酸。他最值得一提的,便是他的进士身份。种种迹象表明,张楚金想要求亲成功,着实是“难于上青天”。然而,他并没有畏惧失败,仍毅然前往韦家,给自己一个机会。
“进士张楚金求之,母以告之”,无媒人帮衬,韦母像是走过场一样通知女儿。韦氏数次拒绝,可能让她感到挫败乃至绝望。在她看来,张楚金就像是以往的求婚者一样,结局注定会是苦涩的失败。出乎意料的是,韦氏却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 张楚金的勇敢,得到了回报。
那么,韦氏为何会下嫁张楚金呢?其中原因,也许只能解释为爱情。古人婚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成亲之前,男女双方并无多少机会相见。韦氏本没有机会在婚前爱上张楚金。可她十五岁时的那场梦,让爱情有了可能。
高傲的韦氏为何会选择“寒酸”的张楚金呢?一个不负责任的猜想,韦氏可能厌倦了豪门之间的联姻,她想要掌控自己的爱情。她拒绝裴爽、王悟的行为,无疑给后来者传达一个信息:只有超过裴、王两人的家世与条件,才有资格提亲。殊不知,这只是韦氏设置的障碍,最终只有张楚金跨越了,只有他是捧着崇高的爱意前来。
张楚金并未见过韦氏,他的爱情何以可能?秘密是在故事中。韦氏拒绝裴、王后,她的行为与事迹,必然会以八卦的形式流入市井。随着故事不断地传播,韦氏的形象逐渐失真与扭曲,最后呈现在听众面前的是一个被定义、被塑造的韦氏。赞美有之,诋毁有之,真真假假,难以辨认。在众多青年才俊中,只有张楚金穿越故事的泥淖,抵达了韦氏的内心。
在韦氏与张楚金接触那一刻,爱情便发生了。两人成为夫妻,养儿育女,一起度过了甜蜜与幸福的前半生。家族遭遇厄运,并未摧毁彼此之间的爱情。韦氏对张楚金的怀念,将会支撑她走过最艰难的日子。真正灾难在于韦氏梦醒那一刻。因为在韦氏睁开眼睛那一瞬间,就预示着爱情是虚幻的、破碎的。所有的幸福与甜蜜,都是不存在的。
现实正在复刻梦境。当韦氏发现这一点后,肯定会激动。因此,回过头来看,韦氏第一次“笑曰”(若是梦境跟现实一样,那么韦氏的“笑曰”,其实发生了四次),可能是她意识到现实正在按照梦境的轨迹推进。这就意味着,本来不可能发生的爱情,正在成为现实。接下来,韦氏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张楚金到来,等待爱情降临。她的人生,因此充盈、丰满。她没有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爱情让她坚定地选择了自我命运。此后,她所遭遇的苦难,其实是她那伟大选择最强有力的佐证。
六
韦氏最大的困境,不是苦难,而是命运已知。关于人生的一切,关于未来的期许,都被剧透了。上天给了她一副明牌,甚至出牌顺序都已经安排好,何其绝望与被动也。令人钦佩的是,她并没有自暴自弃、自怨自艾,把牌随手一甩,而是以刚健的姿态,去迎接人生,去发现生活的意义。
命运是什么?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答案亦因人而异。与韦氏相比,无需面对剧透的命运,是我们最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