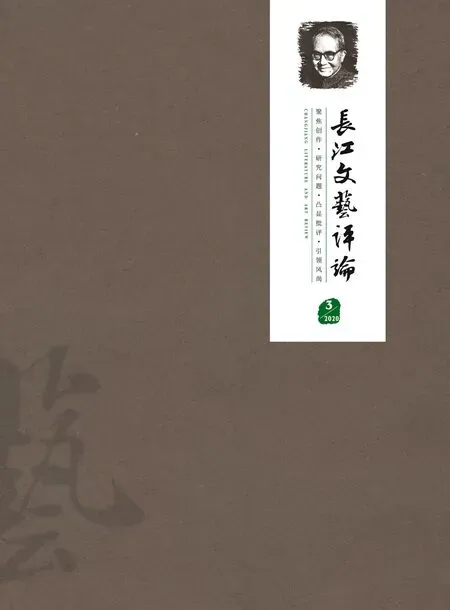温新阶散文集《一抹春色》之人类学批评
2020-11-17桑大鹏胡倩
◆桑大鹏 胡倩
原乡,作家出生和成长的最初地界。就地理环境而言,原乡大体应属乡村,具有乡村地理特有的封闭、保守、闲适与宁静;就精神意义而言,原乡具备提供作家生命成长与文化体验的精神资源;就隐喻意义而言,原乡具有召唤功能,它的地理、器物、传统、人事、烟火是作家心智或梦境构成的最基本精神要素,都会对在外的游子形成强大的吸摄。在此意义上,原乡就是作家最始源的精神故乡,是其文学想象的起飞点。
图腾,本为文化人类学概念,源自印第安语totem,意为“他的亲属”,表示原始初民在最初涉入自然的过程中所认定的与某一个人或种族具有亲缘关系的动物或植物,这些动植物由于其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而被认定为与个人或种族具有神秘关联,成为他们信仰的力量符号,龙、蛇、鹰、虎、竹、树、山、河乃至于土地都曾作为图腾符号载入个人或种族的记忆之中。
原乡图腾本质就是一种土地图腾。温新阶散文集《一抹春色》就记载了这种土地图腾在作家心中生成与幻灭的历史记忆。
一、原乡地理:图腾的空间表象
《一抹春色》中关于土地图腾之空间表象的描摹显得无意而有意。就其无意而言,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原乡地理早已成为其心中的图腾,只是凭无法灭失的记忆叙述其故园的山岚、河流、田畴、树影、屋舍等地理因素,无意间流露亲缘认同:
响潭园是村庄的中心,这里曾经放着大队部,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那种土墙木结构的房子。大队部前面是响潭园小学……学校往西走,有一片高高低低的房子,榨坊、药铺、商店就在这些房子里……从榨坊药铺商店往西的小山坳上有一口堰塘,死水,并不清澈……堰塘也不用来灌溉,唯一的功用就是供几头水牛夏天在堰塘边滚泥。因为有这堰塘,这个山坳就被称作堰拗,有一间瓦厂,满足周边盖房子的人的需求……响潭园的东边,是上河,一直往东走,上了荒崖,就是资丘的地界了……响潭园往北,是杨家冲,村里几十户人家,沿着一条小河而居白墙黑瓦的房子,一栋栋伏在庄稼地里。(《一抹春色·一个村庄的地理》)
作者凭记忆勾勒出故乡的地理形胜,但着墨偏重于房舍的功能布局、关联的传统手艺以及与自我的亲缘关系。这表明,作者之所以对原乡地理的空间表象有着如此清晰的记忆,乃因各方位都关联着作者青少年的成长,此中既有生命体验,又有人生经验的充实,记忆源于无法变更的心理认同。
亲缘关系的认同是图腾得以成为图腾的经验基础。按作者叙述,作者的远祖并非本土姓氏,但乡人因其淳朴并不排斥外来姓氏,而是热情接纳,这使作者能够毫无障碍地融入土著文化、乡民乡情的体认中,他能亲见肖校长教育学生、和乐乡民的伦理力量;在榨坊里亲睹吴师傅对榨油机的操作;在药铺里感受土方郎中对中药抽屉的闭目熟认;亲历瓦匠施行巫术烧出瓦蓝的盖瓦;亲闻磨坊旁边阴阳先生指点风水的神奇等等。所有这些对乡风、乡民、乡情的体认都使原乡图腾在其心中最终发生、成长、定型,并凝练为原乡召唤功能的精神核心。
由于作者对原乡地理的清晰勾画本非有意,因而不能视作土地图腾意识出于其原初的自觉;又因其原乡意识是基于如此深厚的亲缘体认,导致作者对原乡的敬畏与皈依带有某种宗教情怀而最终走向图腾生成,因而我们只能说是某种属于集体无意识的图腾观在今人个体潜意识的自发生长,而个体意识显然促成了原乡图腾的最终发生。
二、乔木:原乡图腾的间架筋骨
《一抹春色》对原乡乔木的关注与描绘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图腾形制构成的重要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乔木当作图腾空间表象的一般要素来处理,而是深度刻画使之成了原乡图腾的骨架。作者在描写泡桐、漆树、香椿、柿树、枇杷时,往往同时叙述它们关联着的人伦,释放这些乔木的生活、历史、人文意涵,使之具有了作为图腾构件的精神旨蕴。
泡桐是速生树种,生长速度是其他树种的几倍……泡桐的共振性非常好,所以是制作乐器的极好材料……在鄂西,倒是有用来做家具的……主要是用来做箱子,因为泡桐轻便且隔潮效果好,最适合做衣箱。泡桐木做的衣箱,刷上漆,木纹清晰可见,一波一波粗犷的木纹从左向右或者从右向左散开,生动极了……由于泡桐长大后都会出现中空,鄂西人会就势挖成木桶,再做上盖子,用来盛诸如茶叶之类需要隔潮的东西……把茶叶装进泡桐木桶里,密封好,放在阴冷的地方,到了春节,打开木桶,一股清香溢出,未饮先醉,待开水冲泡到茶碗里,碧绿的汤汁,鲜活的叶片,浓浓的春色就在一只青花碗的茶碗里弥满开来。(《一抹春色·乔木小记》)
此中对于泡桐的描写,侧重于对其参与人间生活的价值开掘。泡桐可用于制作乐器、衣箱、盛放茶叶的木桶,表明乔木早已越出了一种物化本位,在人的使用中具有了以人的生活为依归的人文价值,这是“物”作为图腾构建物的意义基础,隐喻图腾意义的空间维度。
在鄂西,过去多用香椿做房梁,而且这房梁一般不是自己准备的,房子做好了,立屋的那天,由至亲送来,在乡下,称为送梁树……送梁树的场面壮观极了,十来个小伙子抬着小脸盆般粗细笔直的一棵香椿,树上缠着几丈长的红绸子,敲锣打鼓,放鞭放炮,直奔我们的新房而来,梁树抬到新房的稻场里,父亲母亲在稻场跪迎。木匠师傅在梁树的中段砍出一个平面,在平面上画了太极图以及彩色的绶带,两边还写了八个大字,左边是“荣华富贵”,右边是“长发其祥”。(《一抹春色·乔木小记》)
这是乔木的另一种价值功能:指向深久的文化理念和历史传承,并承载人们持久的生活理想。建房历来是生活的大事,因而房梁的质直结实就意味着生活的安稳幸福,至亲送来房梁隐喻血亲之间的共同帮扶,太极图的标示意味阴阳之气汇聚于平衡,“荣华富贵”“长发其祥”昭示未来生活的希望。而香椿不仅仅是乔木,更是意蕴饱胀的文化符号,是隐喻图腾意义的时间维度,是空间之物向时间的转化,有时空兼具的性质而成为图腾构成的骨架。
三、器物:原乡图腾的精神语码
图腾一旦被认定,它的原生物或偶像所具有的精神特征也就被乡民所接受。龙、蛇、鹰、虎之高贵、灵动、锐利、勇猛就在乡民心中因被反复揣摩而与图腾意志达成感通,这是乡民接受图腾的一般心理过程。如果图腾本身并无生命,那么乡民会用取于图腾之身的物件制成适以自用的器物,灌注他们对图腾内在旨蕴的感悟,凝定为图腾的精神语码。换言之,人们可将器物理解为图腾偶像的分肢,是传载图腾之局部精神的物化符号。《一抹春色》对此有详细的叙述。文本对五尺、罗柜、石碓等器物制作之精详的描写,流露了原乡人对他们手中之物近乎图腾般的虔敬。
文本叙述了山区农家建新房请来的木匠远华师傅,他手中拿着一根五尺长、上有刻度、四边棱角、用量房梁而同时辟邪的细长棍子,徒弟道坤说是起屋用的五尺,代表木匠手艺、身份、名声、地位和精确度的重要工具。远华对五尺珍爱之至,用擦拭刨子的油抹布把五尺擦得锃亮,小心翼翼放在门背后。不想徒弟道坤量主梁时走神,差了尺寸,主梁废了,被师傅用五尺打得浑身是血,买下主梁。道坤从此兢兢业业,把新买的主梁“打磨得像婴儿脸蛋一样光滑圆润”,画好太极图,写好“荣华富贵、长发其祥”,终于立屋成功。
我们家的房子立了屋,道坤就要出师了,出师仪式就在我们新屋里举行的,仪式的最后一项是师傅给徒弟亲授五尺,这大概类似于和尚传授衣钵。当远华大叔把那杆五尺传递给道坤时,我看见远华大叔的泪水湿了脸庞,“师傅用这五尺打了你,是因为只有沾了徒弟血的五尺才会灵验,才会镇得住邪,师傅不得不下手狠一些,徒儿不要记恨师傅。”道坤扑通一声跪下来,双手接过五尺。之后道坤送给师傅一个主梁的小样,师傅用废掉的主梁做了个洗脸架送给道坤,“你每天洗脸时都要照照镜子,检视自己有没有对不起木匠这门手艺。”(《一抹春色·器物志》)
从文本对相关事相的描写中我们至少可解读如下意义:1、手艺传承即道业传承。任何民间手艺都是积淀了无数匠人的生活体验与行业经验的知识累积,其中有道术、有智慧、有对万物之道的理解与领悟,故以虔敬之心承接手艺本质是对道业、传统的献祭;2、对器物的敬畏是原始拜物教思想的遗留,拜物教正是发源于早期图腾崇拜,在原乡人中,拜物意识仍被保留于对器物的敬畏中。虽然器物经由人手创造,但人们并不深究这个对象,“他者”其实发端于人,反映人类理性意识发生前夜、不顾及事相矛盾的“原逻辑”之思;3、匠艺以器物为载体,而承接匠艺需以徒弟之血为代价,只有匠艺融入血中,道业才得到真正传承。这是一种巫术思想,是以图腾为核心而展开的原始巫术的遗留,而此巫术就以血融的方式代代留存于道业传承中,作为记忆铭刻成累代相续的传统,成为人们理解原乡图腾的精神语码。其余对罗柜、石碓的心态无不如此。
四、土匠:原乡图腾的精神血脉
鄂西的民间手艺覆盖各行各业,被后人概括为“九佬十八匠”。“九佬十八匠”因势就便的创造成果最终以各种器物体现出来,成为人们体认原乡之文化意义的精神要素。而就道业传承之各色各艺的“术”而言,其实有着更深更高的价值,它们是体现原乡图腾的极其深微的精神血脉。骟匠、土匠、篾匠等均具有此种价值功能,这在“土匠”手艺中集中体现出来。
土匠,即夯土的版筑师,商代就有了,传说奴隶傅说混迹于建筑队伍中讨生活,被商王武丁拜为相,此事《史记》有叙,这是有关土匠的最早记载,大约是土匠职业和道术传承的源头,版筑之法至汉代已趋于成熟。
汉代以版筑夯土为墙与木框架的混合结构的建筑方法一直沿袭下来,特别是在山区,沿用了几千年,旧时鄂西的房子绝大多数都如此修建,几丈长几丈宽几丈高的房子,那土墙都是土匠师傅一杵头一杵头打出来的。石头墙脚下牢靠了,土匠师傅提着一副墙板进了门,墙板搁在墙角上,讨个平水,放个垂线,一担一担的土挑过来倒进墙板里——挑土的是打下手的,工钱只得三成,拎杵头的是师傅,一杵一杵把土夯紧,再倒上一层新土,又一杵一杵打过来,一个墙圈子得几天才能转圆,这还要不下雨,下了雨,一道的杉树皮盖在墙上,似如古时城墙,有几分古朴和神秘。
土匠师傅不仅要有一副好身体,还要通些法术,有些懂妖术的人会“驾墙”,他们念出咒语,让你打的墙总是倒,总是招不了山子,对土匠来说,这是最令人丢人现眼的事,倘是没有招数破解,日后定然端不成这个饭碗了。(《一抹春色·故乡三匠》)
这段文字意义深微:由于山区的封闭,原乡人在四面望断的空间环境中只能将视野投注于脚下的土地,土地图腾就在与人的神魂关涉中生发,土匠成为图腾精神的人格载体。土匠是直接从土地取物而转向人类遮风挡雨之居所的关键一环,是将土地之奉献用之于人造物、使土地之“物”的表象具有“属人”的意义的灵魂人物,是使土地意义延伸于人的根本牵引力。不仅如此,土匠还因巫术的施行强化了版筑手艺的神秘色彩,版筑屋本身成为图腾的一部分,而土匠就成为传承图腾意义的精神血脉,人们可通过理解土匠去理解图腾本身。“九佬十八匠”各以其精湛的道业引导原乡人进入对图腾意义的体认中,并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尊崇。
五、歌吟:原乡图腾的灵性表达
《一抹春色》有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清江。
清江,古称夷水,因“水色清明十丈,人见其清澄”,故名清江。清江发源于利川市汪营后坝龙洞沟,流经利川、恩施、宣恩、建始、巴东、长阳、宜都等七个县市,在宜都陆城汇入长江。(《一抹春色·清江,一条流淌歌舞的河流》)
河流,是土地图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流动、灵性、艺术,是图腾意义向艺术领域的显现。《诗经》中的《关雎》《蒹葭》《溱洧》等与河流有关的篇目都是原始宗教意涵的诗性表达,今清江歌舞同此一理。
按作者所叙,清江歌吟有山歌、哭嫁歌、跳丧歌和南曲几大类,歌体形式多以五句子歌为主,功能价值各异。人们劳作之余,在山间歇息的间隙有山歌;女儿出嫁有十姊妹陪哭的哭嫁歌;为亡者送丧有狂歌劲舞的跳丧歌;水滨月下有闲适雅致、宫廷谪仙的南曲。
一条河流孕育出个性独特、类型各异的歌舞,本身就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人类学事件。在土地图腾崇拜的视域中,我们可将此四大类歌舞理解为图腾意义的灵性表达,歌舞承载着指向图腾意义的价值功能。
在这里,山歌随处都可以听得到,特别是在夏季锄草时,太阳西斜了,炙热渐渐退去,时不时还会有一阵微风从包谷林穿过,吹动着包谷叶子哗哗作响,锄草的人们正趁着阳光降落的光阴抓紧劳作。这时必定是有山歌的,山歌可以统一劳作的节奏,又能焕发劳作的热情和活力。
清江岸边的长阳到处是山歌的海洋,乐园又是闻名的山歌之乡,当年一个一万多人的小公社,歌手就有数千,除了田间劳作,婚丧嫁娶、村上开会,只要有人聚会,必定就要唱歌。(《一抹春色·清江,一条流淌歌舞的河流》)
这么说,山歌就有舒缓劳动紧张、群聚、交流的功能。根据作者所述,山歌盛行于鄂西的土家族和苗族之间,那么山歌对唱就不仅有聚众成群、聚群成族的民族“塑型”价值,还有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功能。这是走向图腾理解与互认的渠道。
此外,跳丧歌舞以狂欢形式礼送亡者,事死如事生,是道家生命观的表达;哭嫁歌以悲剧形式处理喜剧事件,也是道家“福兮祸所倚”之悲喜一体辩证观的流露,这表明土家人的生命体验深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并将此种理解移植到图腾表意之中。而南曲颇为另类,表明粗犷狂放的土家歌舞对南曲的接受,土家人以粗犷为特征,但并不拒绝雅致,丰富和提升了图腾观念的灵性表达形式。
六、幻灭:原乡图腾的历史解构
建立于土地表象之直觉认知以及器物、道艺、歌舞之上的原乡图腾既然是由历史涌生而出,以时间为根本皈依,也将随着时间流逝而幻灭。马克思说:“一切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东西,必将在历史过程中消亡。”鄂西山区的封闭终究无法抵挡现代意识的侵袭,在新时期四十余年经济改革和现代意识的濡染中,鄂西山区人们构思、崇奉了数千年的原乡图腾与现代观念因格格不入而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幻灭,作为具有建构能量的历史也无情地流露出解构力量。
原乡图腾在历史的解构力量摧毁之下趋于幻灭并不是图腾的土地表象与乔木骨节的散失,而是图腾关联着的器物手艺失传,是道业传承的终止,是人伦传统的失范。致使图腾虽留表象,但其本质、神韵已被抽空,其精神已逆时间之流向历史的深部渐行渐远。
《一抹春色》提供了太多“九佬十八匠”消失的案例。窦瓢匠的瓢匠手艺就是其中消失的一例:
窦瓢匠活到九十二岁才辞世,他是人们知道的最后一个瓢匠,自从十几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就不挖瓢了。现在人们用的都是金属和塑料做的瓢,只是偶尔在非常仔细的老年人家里还可以见到木瓢,他们拿起木瓢舀水时往往会牵出一大串窦瓢匠的故事。(《一抹春色·逝水》)
可见,在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的逼仄之中,窦瓢匠的手工技艺是因为需求的丧失而失传,他只能把器物手艺带进泥土,留下的是人们关于瓢匠的传说。现代技艺一方面向人们传达着对物质的精准理解,另一方面又引导人们更深地沉迷于“物”而异化,而由手工技艺散发出的人与器物之“物我同一”体验就此灭失。“九佬十八匠”的消失无不在反复重演着同一主题。
幻灭的还有信念与道义。作者叙述德业精湛的上头婆婆槐香一生为三百多位新娘子上头(为即将出嫁的新娘子用丝线绞去脸上的茸毛),并教以善处婆媳关系、为人妇,为人母之道,广受乡人尊重,槐香有一个原则:只为处女新娘子绞面。当她看到桂枝未婚而孕三四个月时,当即谢绝桂枝的重金相聘,拒绝为她绞面,桂枝只好到城里请理发师服务——新时代的价值观并没有对忠贞观的要求;另有一对未婚夫妇来请槐香,不料当晚车祸身亡,槐香依诺对死亡女子的面容整旧如新,同时殷重默语送“新娘子”安心上路。但按规矩槐香上头手艺也必须终止,不可再与人绞面。
为死人扯脸上头,槐香的手废了,从此再没有人请她为新娘上头……上头婆婆们都失了业,她们每一年春天都约了到槐香家聚一天,回忆些往事,讲些趣闻,看满山的映山红开得鲜艳热闹,听溪沟里的春水汩汩流动,她们就唱一些五句子歌谣。(《一抹春色·逝水》)
槐香以及一众上头婆婆们的绞面手艺,其实还有一种对职业规则的坚守和古老忠贞观的认定,然而新时代理发师们却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无视此种忠贞观,面对新的价值观,槐香们无力抗拒;同时槐香因为死人上头又自觉废掉职业,表现对规则的尊重。一面是时势使然,一面是内心选择,一种职业就在此种内外趋迫中无奈地走向灭失,从个人与时势、信念与道义层面诠释了“九佬十八匠”的精神幻灭之路。原乡图腾至此仅存意义空洞的表相符号。
结语
《一抹春色》忠实地描述了某种原乡图腾在鄂西乡民心中的真实面相,此种图腾既有土地表象,又有乔木骨节;既有器物载体,又有“九佬十八匠”的道业传承,更有歌舞的灵性表达。此种图腾是如此真实而具体,从里到外向原乡人发生着召唤与凝聚:召唤原乡人千百年来时时皈依于图腾释放的精神伦理,凝聚散处四方的原乡人走向族群的统一。与此同时,正因为原乡人对图腾的至爱入骨、至敬入心、至畏入神,乃有图腾在族群中的浑整心像与至大能量。唯其真实,乃能感召。然而,原乡图腾既然是在时间进程中渐聚而成,也必因历史的催迫涣然冰释。在时间的维度中,原乡图腾就这样演绎着一条有情而无情的生成与幻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