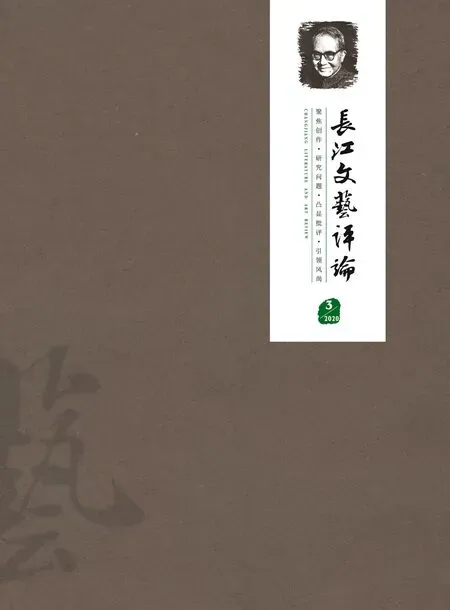南方日常诗性的忧伤与慈悲
——以钟求是小说集《街上的耳朵》为例
2020-11-17鲍良兵孙良好
◆鲍良兵 孙良好
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可谓久矣。从古代“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塑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的体认到近代刘师培对“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的分析,再到现代鲁迅与沈从文对“京派”与“海派”文学的争论,恰如学者吴承学所指出的:“地域风格论贯穿在整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3]事实上,相较于北方的厚重,南方的作家总体上显得更为细腻,正如青年学者刘浩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我们读吴越作家的作品不难获得灵秀、柔慧的美学印象。在这一美学特征的影响下,我们很难在江南作家的创作中看到硬朗刚健、孤烟大漠式的北国叙事。江南作家擅长的是以委婉细腻的笔描述恬淡冲散的日常琐事,笔触轻盈中带着细腻,像深街古巷里悠久绵长的喃喃古语,……人的情感在庸常的烦恼与善变的情绪中被一点点蚕食、耗尽,展现的是淋漓尽致的人生情致。”[4]作为江南(出生于温州,工作于杭州)的作家钟求是,可以说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江南地域文化的影响,在一次访谈中他曾谈到:“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我知道自己的擅长和短处。我待在热闹的城市,生活在趋同,我吸收的经验和别人是相似的。一般地说,我难以制造吓人一跳的离奇故事,我只能着力去探摸人的内心深处隐秘的东西。这样,我就能与生命本身走得很近。”而对小说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关系,虽然钟求是表示不是很确信,但从自身创作出发认为:“小说的风格应该与作家的性格以及地域有很大的关系。我不是个狂放的人,又成长于南方小镇,这使我的小说语言显得安静和湿润。”[5]也正因如此,“在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熏陶、浸润下,钟求是那颗敏感、温润而又略显感伤的江南诗心日渐成长、丰润,这也形成了他细腻精致的叙述语言风格。”[6]这种美学品格在他最新结集的中短篇小说集《街上的耳朵》中得到充分地展现。小说集收入了钟求是近几年陆续发表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上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钟求是对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关注,他以委婉细腻的笔触着力挖掘和描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人性隐秘的部分。在他的笔下,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方面是遭遇现代生活中的“不儒雅”及其情感上的挣扎,正如其在小说集后记中所说的:“我写了流淌的岁月和潜伏的情感,写了生活中日常但隐秘的东西”[7]。但另一方面,他笔下的普通人也不无对诗意美好生活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每一个人,每一种生活状态都有自己心灵的困境,这是需要作家触摸与慰问的重要内核。”而“有重量的作品能让更多人发现并关照自己更广泛的精神世界,这个过程通常表现为阅读后产生的共鸣”。[8]也正如此,他的小说常常以一种淡然而舒缓的笔调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氲氤着一种淡淡的哀伤,触碰读者最敏感的情感神经,开启温暖而又百感交集的旅程。这部小说集中展现了他“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
一、“隐物”:日常生活中的伤痛与爱欲
诗人穆旦曾在诗篇《冥想》中说:“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9]在一个“小时代”,现代人要度过普通的一生并非易事。事实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固然是庸常琐碎的——他不是英雄式的,也不是飞扬的,但是从哲学的角度上看,又不乏神圣性本真的一面。张爱玲谈及自己的文学观:“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而“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相比壮烈,她喜欢悲壮,但更喜欢苍凉:“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是一种参差的对照。”[10]类似于张爱玲不喜书写“超人”而对“不彻底”人物情有独钟,钟求是创作重心亦不在“人生飞扬”的一面。他笔下的人物展现的更多是普通人的生活。然而,普通人的生活在庸常琐碎的下面是暗波汹涌。他们就那样活着,爱着,痛着,累着,默默地咀嚼生活的所有“馈赠”。而从根本上来讲,普通人“生老病死”又蕴藉着生命的“本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小人物独特的生命历程都可能蕴藏着伤痛、失意和死亡。是以,普通人存在着,并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展现着人性深处的区域。而正如作家王安忆所言:“它们(日常生活)正是那些最单纯又最有力的能量,人性中的常情,是跟随着生存滋长,又滋养着生存的最基本的规律。”[11]
现代生活是不平等和不儒雅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肩荷者。普通人在貌似波澜不惊的生活表层下面是“千疮百孔”,生命中有太多事,看似轻如鸿毛,却让人难以承受。而且,这些肩荷着“伤痛”的普通人在生活里更多的不是大喊大叫,而是将其隐藏,一如小说《练夜》中的团顺说的,“把我的不好全看走了,我不划算。”对此,钟求是在一篇访谈里面曾经说过:“对生命的尊重和维护有多种方式,其中最基本的方式是让生命自在地活着。在眼下这个年代,要活得自在何其难呀,无论是有钱人、当官者还是市民农人,大家都认为值得幸福的东西越来越少,挤兑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多,大家总觉得活得累活得重。就是说,经济越发展,离生命的自在反而越远。当然,把尊重生命这种话题按在有钱人或当官者身上会比较没意思,因为至少从表面看,他们活得够有面子够风光了。这种发言的机会应该交给赵伏文、林心这样经历过心灵苦难的底层人,他们的声音虽然很轻,但听在我们的耳朵里会觉得挺有力量”。[12]所以,作家钟求是始终将目光深入到这些“隐物”——“人的内心深处隐秘的东西”。在他看来:“人的内心是个辽阔而诡幻的世界,存在着广大的未知领域,值得我们去行走。”[13]钟求是特别擅长将复杂隐秘却又纯粹的情感挖掘出来,“文学的目光可以盯住大苦大难,也可以打量日常生活。在大多时候,人们都过着平淡的日子,花开花落,数点年月。但平淡之下,又潜伏着复杂的悲欢情感。小说的擅长之处,就是能将日常中的特别东西拣出来。”[14]
所以在《街上的耳朵》中,小说写一个强者“式其”。年青时的他练过武术,又喜欢酒,掐架斗狠讲义气,整天游手好闲活脱脱一街头小混混,后来做过装修公司的小老板。小说中出场时,虽然他已经将公司交给了儿子,“成了日子边上的人”。但他在酒桌上仍是一个受重视的人。但正是这样一个“声音温和”,在普通人眼中“成功”的式其,他的长发遮着一个私密——年青时因一次酒后失言说了一个自己的桃色梦,招致受辱者叶公路与之打斗,并被咬掉半边耳朵,而叶公路也因此坐牢,客观上造成了王静芸的生活有了个“窟窿”——失去的耳朵成为他隐秘的伤痛的象征。而在小说《练夜》里,团顺作为一个盲人,“平时老坐着,又能吃,身子慢慢长膘,没几年就变成了糯米团子。”胖且盲使他单调的日常生活只有一锅花生和一杆秤,遭遇三十年没有和女人亲近的情感挫折。《星期二咖啡馆》中则写了一对老人,遭遇儿子因为车祸而去世的悲剧。因为思念,他们寻找到了获得儿子死后视网膜的徐娟,每个月在咖啡馆里见见徐娟成为生活的寄托,但是妻子“渐渐地没了力气”。更加不幸的是,徐娟因为看见自己的未婚夫出轨而失踪,扫地机器人这一充满烟火味并代表着普通生活的象征没有办法送出,再一次地经历情感上的怅然若失。《第二种诉说》中“我”的爱情不顺利,只能向一个聋哑姑娘诉说,并不经意间给聋哑姑娘带来情感伤害。《送话》里的法警王琪出于职责处死了忧伤的叶枣,自身也遭遇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创伤。《愿望清单》里面写的是两个“孤独”年青人的爱恋,苏颐因为父母离婚带来的“苦味”和年轻诗人树井作为一个“养子”以及与周遭世界抵触的忧伤。《两个人的电影》里则写已经退休的老教师“昆生”看似平淡的一生,背后曾经“坐过牢”并和患癌去世了的若梅有过一段牛郎织女般的爱情故事。
事实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开始,现代文学对“普通民众”的关注可谓是一以贯之。但仔细审视这个传统,可以发现,无论是对底层普通民众的批判或赞颂,此类书写背后关联着“民族国家”这一整体性的宏大时代命题,普通人的命运更多的是时代和社会的“镜像”,因而文本的意涵焦点更多指向造成伤痛的外源。而从这个角度来看钟求是的书写可以发现,在他的小说中,造成伤痛的外源具有偶然性,而且这个外源更多犹如扔进池塘里的“石头”,石头引起情感的涟漪才是他的书写重心。因而他的写作向内探寻,书写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情感世界所遭遇“伤痛”,而且这种遭遇的情感伤痛具有日常生活的本真恒常的一面,这亦是每一个现代人在现实生活都可能遭遇的情感“伤痛”。
二、“做梦”:普通人的爱欲镜像
审视整部小说集,这部小说集里面一再出现的意象就是“做梦”。比如小说《街上的耳朵》里面引发冲突的式其酒后说自己做的春梦,“梦中他搂住一个年轻女人谈心,似乎说些连哄带骗的话,然后把该办的事都给办了。”再如《练夜》中团顺说:“我昨天晚上做梦了,梦见……一个女人。”“我在梦里听到了女人的声音,那声音好听。”《星期二咖啡馆》中“一年后的一个深秋,他被冬媛推醒”。冬媛坐在床上,幽幽地说:“老方,我做梦了,我梦见儿子的眼睛。”在《星子》里面,“昨天下雨我躺在棺木里打了个盹,迷糊之中出来一个奇怪的梦,梦里这棺木被四个人抬着,后面有一支送葬的队伍,队伍里的炮仗像流星一样升到空中。”而在《慢时光》里面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丢了钥匙拎着包袱出了房子。“知道我刚才做了什么梦吗?我梦见年轻时候的自己啦。”小说《送话》里面,法警王琪“半夜时分,她作了个乱梦,把自己弄醒了。醒了一会儿,梦里的内容已捉拿不住,白天的情境却似乎从远处一点点走近。”在《第二种诉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我在路上正走着,突然空中下来一块砖头砸我脑袋上,把我放倒了。我昏迷了好一会儿,睁眼一看,旁边躺着的不是砖头而是一只布袋,有好几捆人民币,但不够买房。”而且静姑也让弟弟告诉“我”说,她做过一个梦:“有一天夜里我跑出一个梦,梦里我耳朵长好了,你的每句话我真的都听见了。”在《愿望清单》里,苏颐做了一个梦,梦见树井躺在木屋的床上,而自己坐在旁边。在《两个人的电影》中,“我在监狱里,睡眠里会跑出梦,梦里的若梅轻易就能溜出来站在我眼前”等等。在小说中,钟求是之所以一再书写“做梦”,其不仅构成了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内在肌理,也成为普通人生活的重要表征。
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理论,人的意识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梦属于“本我”,受到“自我”(现实生活原则)和“超我”(良知和道德)的抑制,属于潜意识的“变形”表达。事实上,潜意识这一人性“黑暗”地带,成为诸多现代先锋派作家一再探索人性的写作主题。但钟求是与此类写作不同,他并没有往人的“潜意识”掘进,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普通人的“受困”挣扎和“爱欲”的表征形态,正如民谚有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于普通人来说,所思所梦的内容就是属于日常生活中被压制的部分。而对“梦”的言说,某种意义而言是生活对普通人的抑制的创伤修复。可以说,小说中钟求是写梦的背后固然表征了普通人的爱欲,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现实生活“受困”的镜像。
三、“亮光”:日常生活的超越
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来看,随着个人意识的增强,文学也经历了一个由“宏大”叙事向“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逐渐成为文学书写的重心。然而有学者指出此命题暗含着的反命题:“日常生活叙事内部包含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日常生活中布满了重复、琐碎、放纵的陷阱,是欲望放纵和生命沉沦的天然温床,它时刻准备着给感官的放纵提供机会,使日常生活叙事的力量显得极为有限。”所以,欲望固然是日常生活的题中之义,但若作家一味将其放大,结果只能是“把日常生活变成非理性的领域,从而再一次把人抛到了生活世界之外。”[15]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钟求是的写作,他在着力探求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境和内心隐秘伤痛的同时,并没有像一些作家那样陷入一种描写人性被压抑的、极端和病态的欲望。钟求是笔下的人物虽然遭遇着日常生活的困境,也有挣扎,但并没有走向极端。作为对普通人的描写,钟求是用一种慈悲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所以,在他的笔下的普通人固然有情感的伤痕,但同样不乏精神上对美好的向往。也正因如此,钟求是笔下的普通人显得更加丰盈和立体。比如在《街上的耳朵》中,年轻的式其完全是一个充满“力比多”野性的“小混混”,喝酒、打架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但即便如此,当某一次他和别人相约打架,在雨天的巷子里面遇到王静芸的倩影,烦躁的内心被洗练得很宁静:“当时我还有一感觉,就是不想打那场架了,至少认为那会儿打架挺没意思的。”而多年后,当叶公路将王静芸的照片给他看,现实生活中王静芸和那天雨巷中遇见的倩影可谓是恍若两人时,他才领悟到,“我不是喜欢上巷子里的人,而是喜欢上了巷子里的那种情景。那一会儿呀,王静芸只是情景里的一个人物。”可以说,雨巷中的那个倩影,是那个充满荷尔蒙、烦躁、精力无处发泄的年轻人内心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象征。在《练夜》中,作为盲人的团顺,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一团糟糕,但当小学生帮他打扫房间的时候,他在床头柜上放了一本书,他说:“我想让学生们知道,知道我除了花生还有别的……”在这里,这本书不仅代表着他的自尊,更代表着他曾经融入正常人生活的努力。而团顺因为池老师的女性声音勾起的“三十年不知道女人是啥样的”问题,以及当他经历过一次女性的“安抚”,被失足女嬉笑为瞎胖子后所尝试的洗冷水澡、跑步和爬九凰山石阶的减肥,无不表征着一个残疾者对爱情的向往。再如《星子》里面的韩先生,面对因为癌症而即将到来的死亡,并不怕死的他却陷入那种垂死前的内心挣扎,试图在小山村“找一样东西,一种叫作心安的东西”。而钟求是在小说中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让他在棺材(死亡象征)中通过“星星”的对话寻找到了精神性的安慰。《第二种诉说》中的“我”从一个小镇少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城市成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在平庸的城市生活中慢慢变得“没趣”和丧失了“精神气”,并导致同居女友离开。“我得承认,先前推动老Q出走的原因主要在我,是我掉了精神,对日子拎不起兴致,”陷入萎靡之中。正如小说中说的:“城里的稀奇倒是不少,可都不是我十多年前想找的东西。”而乡村朴素宁静的“静姑”无疑映衬出了“我”对“有趣”生活的追求。《皈依》里面的松芝和“我”过着平淡的生活,“先是生了儿子,又攒了些票子,后来买了房子,再后来买了车子。”和别人相比“称不上太好也没有掉队”的日子。正是在这波澜不惊、“一种汗渍渍的感觉”的生活中,松芝“皈依”了,并对日常生活有了新的感觉。小说中描写皈依后的松芝听到寺庙的钟声,“当时寺庙里的钟声响了,那钟声跑到耳朵里,像是跟平常的不一样了呢。”“干净,那钟声很干净。”而“我”这个“以前有点远的想法,也早被年月淘没了,只想对付好眼前的日子,上个闲班,喝点啤酒,再让身体欢乐一下”,认为“把这些加起来,即使再无聊,也比虚远的来世实在些”的人,事实上也同样有着对精神的追求。恰如小说中宋谣所指出“我”的懒里还存了一点不甘心的东西:“你的心里藏着一些不安分,时不时地会往远的地方挣扎一下。”正是这样“不安分”的东西,使得“我”在和宋谣的偷情欲望被山上寺庙里的钟声所“净化”,“我心里忽然飘起一种异特的感觉,这种感觉应着钟声,仿佛将自己整个儿托出车厢,缓缓送向远的地方。”而在《两个人的电影》中的若梅作为军人家属,在特定的年代里生活无忧。但若梅是个“念过几年书还喜欢讲究的人”,其丈夫——当兵的大奎——却是一个无趣的人。正是在这样“平淡”的生活中,喜欢看电影的若梅和书生气的“昆生”有说不完的话。正如小说中描述的:“若梅去看电影不光是为了看电影,她还乐意跟我待一块儿说说话。从这一点想开来,我又肯定了两点:一是我平日藏着的心思若梅早就瞧出来了,二是她跟家里的那位排长找不着话。这后一点,我心里早有些明白。大奎如果脱掉军装,其实是个粗心又粗俗的人,身上没有太多若梅喜欢的东西。结婚一年半中,大奎回来探亲过一次,若梅似乎也没显出特别的高兴。对平常的通信,若梅的兴致也渐渐地淡下去。”在小说中,若梅和昆生因为观看电影产生了奇妙的感情,但电影和昆生更多表征了若梅在平庸生活中的短暂逃离。如文中若梅所说:“我是过平常日子的人,日子里掺着杂碎,这个烦那个恼太多了,隔一会儿就会遇着累人的事儿,可累人的事儿再多,也挡不住一个日子的到来。这个日子可以看电影,可以跟你待在一起说说话,这多么好呀,比过年还有味道。”而昆生也指出:“她(若梅)和我在一起,就是要让一年中的这一天变得脱俗一些,安静一些。这种对付生活的态度无疑有点特别——应该说,她在平淡日子里待着,心里那么的淡,可又比别的女人多了一点点东西。”而这多一点的东西,就是精神需求。正是基于此,钟求是对这些普通人在平庸生活中对诗意生活努力追寻中闪烁着的“精神之光”的书写,让他笔下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充盈。
四、“忧伤”:沉重的中的“慈悲”
纵观钟求是的创作发展过程,其一以贯之的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但近年来,在风格上也有所变化,相比以前的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受困和挣扎”的“日常生活”书写,比如说在《零年代》中,小说写到林心决绝的自杀;《你的影子无处不在》中见梅父亲对儿子的虐杀;《未完成的夏天》中因为偷窥事件导致大真的死亡和五一爷自己刺瞎双眼的悲剧。钟求是在冷静的叙事背后是不动声色的残酷。而在《街上的耳朵》这个小说集中,一如作家东君的评价:钟求是的小说写得越来越“轻”。虽然同样写日常生活的“沉重”,但小说读起来则充盈着“柔软”,自觉或不自觉地展现了卡尔维诺意义上的“轻逸”之美。
相比“以重写重”,卡尔维诺钟爱的“以轻写重”则显得别有意味。有论者指出:“卡尔维诺的目的是以轻逸的书写方式显现生存的重负,通过轻逸的书写来重构世界,将沉重而庞大的世界轻化。”[16]而事实上,文学作为现实的另一种“真实”,“小说未必要写得沉重压抑让人绝望才是深刻、才有价值,它完全可以表现出另一种美学风格,在内容与形式的轻盈里体现出另一种深刻与真实。文学的‘轻’并不意味着浅薄轻浮,它可以严肃而庄重,消解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承受的沉重与苦难,虚构出一个与我们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艺术世界,从而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而微妙的阅读体验、生命体验,进入到人思想、情感的另一精神维度。”[17]在《街上的耳朵》小说集中,钟求是正是以“淡然”的语气从平淡生活中的“小事”出发展开其对普通人生活的内心观照,引领读者深入情感世界,感受本真生活的“沉重”。如《街上的耳朵》中,若干年后式其在吊唁王静芸的葬礼上与叶公路再次“约架”,嘴上动武重新演绎当年的招式背后时:
④双链的制作:模型中化学键一律用银色细铁丝代表,将各部件根据化学键连接方式连接在一起,并用水晶弹力线将DNA链固定在底座上。
式其说:“我的力气的确没以前大,不过你的力气也变小了。”叶公路说:“可有一样东西你没算计对!”式其问:“什么东西?”叶公路说:“虽然我的力气小了,但我的肉盘大了。我现在的身子你能举得动吗?”
青春已逝,赘肉徒增,二人在那一瞬间都惊觉岁月不饶人。他们“盯了几秒钟,嘿嘿笑了”。会心一笑中,埋藏了多少生活的辛酸。
再如小说《练夜》,小说中“我”带团顺去嫖娼,以这一看似很不道德的事件来写一个瞎子虽“身体残疾”但有正常的男性欲望和对女性温柔的向往。再如《星子》里面,韩先生患了癌症,原本是来到小村子里面买点空气。但是在穿着寿衣的老孙头的建议下,韩先生买了棺材来辟邪,然后又举办了一场类似于“闹剧”式的“葬礼”,最终完成了对死亡沉重感的超脱。再如在小说《皈依》中,作为“饮食男女”的“我”因为妻子松芝的皈依而生活失去了平衡,重新开始增加跟朋友们聚酒的次数。并在一次斗饮斗食中认识了宋谣,然后在接下来的接触中彼此变得暧昧。事实上,这一相斗过程中,宋谣喝了过量的啤酒,“我”则吃了过量的红烧肉,可谓是表征了饮食男女“口腹之欲”的“饕餮”。而小说独具匠心之处在于,当“我”和宋谣正要享受“鱼水之欢”时,远山寺庙的钟声仿佛天启一般,让“我”的身体“顿悟式”地停住了,欲望消散,内心一片宁静。天籁般的钟声与沉重的肉体欲望,下半身的轻浮与佛家的庄严沉重以及宋谣的一声叹息构成了最动人的时刻。正如钟求是在后记中说:“作家不是眼戴墨镜、手持斧头的武夫,即使困斗挣扎,内心仍然是柔软的。柔软帮助作家形成了诗性,诗性又帮助作品生成了跃离地面的轻灵。这一点不需要多说,因为一个有经验的写作者会去把控作品中的重与轻。我乐于相信自己的文字也是这样的。”[18]
小结
学者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曾将叙事分为“宏大叙事”和“小叙事”。“宏大叙事,是指由‘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等主题构成的叙事。”[19]而作为与“宏大叙事”相对抗的叙事,“小叙事”具有具体的、零碎的特征。从这个意义而言,“日常生活”叙事显然属于“小叙事”,钟求是的《街上的耳朵》这部小说集中对“普通人”的叙事,属于“小叙事”。“小叙事”因为“它以个体的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往往同个体生活中的琐屑、平淡乃至平庸联系在一起,在重集体的宏大的、彼岸的大叙事看来,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20]然而正是这种“小叙事”构成了人生的常态,其背后勾连着的是辽阔深远的人性和情感,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与此同时,这部小说集除了对普通人情感的深刻描绘之外,钟求是一如既往地贡献了“陌生化”的诗性语言。例如《练夜》中以“不经用”和“凉意”这一主观感受来形容忙碌中的时光飞逝和气节变化(“忙碌之中,日子便不经用。不觉间,秋天已过大半,空气加入了凉意。”)充分地将一种时间状态和感受写了出来。再如《星期二咖啡馆》里以“不再摇晃”来形容失独老人的内心的忧伤(“他的日子因为多了一家咖啡馆而变得不再摇晃。要换,那是多么不好的感觉呀!”);《慢时光》中用“汗渍渍”形容日子(“人有的时候就这样,老被一个念头逼着,日子便汗渍渍的,把念头去掉,人倒轻松了”)等等,正如出版社的推荐语所言,本书贡献了当代汉语中动人的诗性文字。
注释:
[1]【唐】魏征:《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2]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载劳舒编:《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3]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4][6]刘浩:《地域文化观照下的南方写作——钟求是小说论》,温州大学硕士论文,第29页。
[5]刘浩:《钟求是深度访谈录》,《地域文化观照下的南方写作——钟求是小说论·附录二》,温州大学硕士论文,第51页。
[7]钟求是:《街上的耳朵创作谈:文学的距离》,《收获》,2017年第3期。
[8]张锐:《访〈江南〉杂志主编、作家钟求是:写作是捕猎日常里的隐秘》,《深圳特区报》,2018年6月6日第B1版。
[9]穆旦:《冥想》,载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
[10]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载陈子善图文编纂:《流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页。
[11]王安忆:《我读我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12]钟求是、姜广平:《像生活一样永久的文学小人物——钟求是访谈录》,《朔方》,2013年第12期。
[13]阚兴韵、钟求是:《人的内心辽阔而诡幻——钟求是访谈录》,《文学港》,2009年第4期。
[14][18]钟求是:《街上的耳朵·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28页,329页。
[15]董文桃:《论日常生活叙事》,《江汉论坛》,2007年第11期。
[16]杨晓莲:《轻逸之美,沉重之思——〈看不见的城市〉与卡尔维诺的“轻逸”美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7]柳琴:《再谈文学的“轻与重”》,《文学报》,2013年7月25日第20版。
[19]【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20]董文桃:《论日常生活叙事》,《江汉论坛》,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