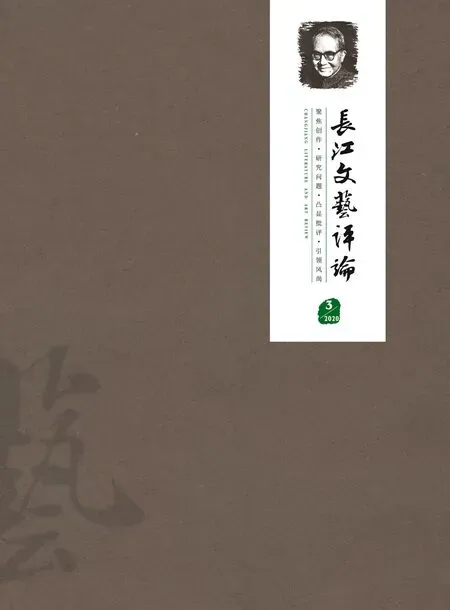地域文化中的精神价值与集体人格
——《俗世奇人全本》文本细读之一
2020-11-17刘海涛
◆刘海涛
2018年冯骥才的笔记体微型小说集《俗世奇人》斩获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本“俗世奇人”系列小说创作了近30年,传承了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的神韵精髓,创造性地将精短文学的故事性、传奇性、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融为一体,展现了笔记体微型小说新的文体形态。《俗世奇人全本》由20世纪90年代的之一(1995年)、之二(2017年)和之三(2019年)共54个各自独立的微型小说组成,立体状绘了清末民初底层能人的生存状态和个性特征,使天津本土奇士的“集体人格”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上一道奇特绚烂的景观。
研读《俗世奇人全本》,一个“笔记体微型小说创作思维”的理论逐渐清晰。美国人工智能专家朱迪亚·珀尔在《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一书中曾这样论证:“客观世界是不按因果规律运转的,但我们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是通过人类对大千事物建立因果关系来展开的,因此,因果是人类主观的一种思维方式。”[1]从这个因果思维的观点来看“俗世奇人系列”,考察冯骥才是怎样运用微型小说因果思维来认识、体验生活,来构思、表达生活,特别是如何描写奇人的个性与命运,不失为研读笔记体微型小说的一种视野和方法。
冯骥才对天津这块独特的地域、对这里的乡土意识和市井奇人有着与他人绝不相同的艺术感受和文学体验。当他站在当代思想家和文化学者的高度,用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民族文化心理,探讨这批奇人的生存状态,探讨奇人们的独特个性和传奇命运形成的深层历史原因、时代原因、人性原因;特别是当冯骥才对奇人们的人性内涵和集体人格采用微型小说文体来做表达载体时,便形成了《俗世奇人全本》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一、微型小说中的“清明上河图”
《俗世奇人全本》取材于清末民初天津卫的特定地域,冯骥才用笔记体微型小说的文学形式,创造性地采用“经典+现代”相融合的文学叙事方法,塑造了54个不同的风神意态的天津卫奇人,生动鲜活地描绘了那个地域的风土人情,艺术地展现了奇人们身上凝聚着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集体人格,创建了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的一座艺术高峰,使新笔记体小说这种续接中国文学文脉的文体在新的文学时代大放异彩。
把54个奇人赖以生存的特定环境组合起来,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天津卫)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了。54个奇人基本上都有着自己谋生的职业,以致自己这个谋生的职业出神入化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生活绝技。
《认牙》《苏七块》《神医王十二》生动鲜活地渲染了医界奇人的医学绝技。苏大夫只要接到了7块大洋,那他的“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王十二更有着“神医”的称号,他可以突取洋货店的马蹄铁把铁匠眼中的铁渣子吸下来;他可以用滚烫的湿毛巾捂住大汉的嘴,让大汉用自己的力把钉在墙缝里的肋叉子退出来。这些神医们个性鲜明,有着让人尊敬的职业精神和妙手回春的医术,他们的身上写满了传奇。
“俗世奇人”写盗贼的也有3篇:《燕子李三》是专偷大富人家的飞贼,他偷总督大人的官印,在总督大人的眼皮底下把“活”干了,让总督大人目瞪口呆并遭到嘲笑。《小达子》中的小达子在电车上巧手轻取了一个中年男子的怀表,但没有想到,这个中年男子不声不息地又反盗回来,这个中年男子的盗技让小达子从此“洗手”不敢再上电车。《绝盗》中,那批盗伙竟然冒充新婚夫妇的爹,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新婚家庭的财物全部搬空。冯骥才对这3种“绝盗”行为和各自的人格有着不同的评价,但他们都概括了那个时代天津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般的盗风盗技。
除了医技、盗技,《俗世奇人全本》还写到了许多有谋生超能的匠人:做糖堆的“四十八样”;做“狗不理包子”的狗儿;船夫们的“快身手和好水性”;“好嘴杨八”里做芝麻汤的厨艺……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都用一种工匠精神,把自己的谋生职业做成了一种“神活”,各行各业的职业奇人的传奇故事让这块“水路码头”大显神采。这样的人物长廊组合展现了清末民初天津卫《清明上河图》的核心内容:“俗世奇人”们通过一件件几乎不可理喻的奇事铺开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民俗长卷。
《龙袍郑》写一个普通的渔夫郑老汉遇到乾隆皇帝上了他的小渔船,吃了他熬的面鱼,最后还赠送给他龙袍,但故事的意外结局却是:“真龙袍郑亡命天涯,假龙袍郑日进斗金”;郑老汉给皇帝吃的面鱼就这样成了天津卫小吃品牌。
《背头杨》的时间坐标是光绪皇帝“维新变法”之后,社会上的男人们开始剪辫子,而此刻的奇人奇事便是大富杨家二小姐赶时髦,也学男人把头发剪成了一个散发背头,结果她上女厕所被人当作流氓追打,后来大直沽一带的女厕所竟有人冒充背头杨滋事。
《黄莲圣母》的时间轴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起义,奇人则是红灯照的女首领带着几千女兵进城,但塑造这位女主角的方法是一种“侧写”。“黄莲圣母”带数千人“踩城”,几千人同时跺脚,响声阵地,尘土遮天,并由七天踩一次改为三天踩一次,最后还改为一天踩一次,天津卫从未有过的抗洋氛围成了历史画卷上珍贵的色彩。
《跟会》则从第三人称限知角度来展开故事。一个刚满18岁的少年木头去观看“皇会”,从这个青春少年的眼睛和心灵出发,把那个时代每年的“娘娘会”写得美轮美奂、热闹非凡。18岁的木头与一个美丽俏皮的踩跷少女相互间的搀扶引发了诗美,但木头在“皇会”结束才知道:那个美丽的踩跷少女竟由一个中年船夫扮演。“皇会”特定的风土人情,从少年木头的眼中和心中来展开,把这块地域的风土人情做了极有情趣的文学叙述。
无论是全知视角还是限知视角,无论是正面写人物还是侧面写人物,无论是讲述身怀绝技的神医、神厨还是描绘大时代的大场面、大事件,冯骥才都让奇人奇事的精彩透露出特定时代的风土人情。那个大时代特定的人文生态和民族生态正是这些奇人奇事产生的肥沃土壤。
二、世俗风情里的“集体人格像”
冯骥才描绘那个时代天津卫的风土人情并不是为猎奇而猎奇,他的艺术注意力和描写力是落在那奇人奇事背后凝结着的一种职业精神和人生态度上。苏大夫为什么有个如此令人不爽的“收7块银元才看病”的怪癖?那是他行医处事的一个原则和行规。《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中,一个粗人和一个艺人之所以能肝胆相照、赤诚相助,是因为在天津卫这块地盘,朋友间的情义要远超庸俗的金钱关系。《黑头》更奇了,一条讲义气的狗为了主人的面子和狗自己的面子,竟然可以冲入泥浆里自杀……这些奇人奇事的背后,显露着冯骥才对职业、对人生、对他者的一种文化审美和价值判断。当作家把奇写到了极点,以至于出现人物人性的变形时,作家对暗藏于独特背后的因果理解,一种被全社会认同、共情的理解,便转化为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凝结为一种被多数底层人认可的精神价值,这一个个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奇人们聚合时,那个时代天津卫普通底层人的集体人格便浮雕般地凸现了,这种特定地域文化形成的精神价值开始凝结为汉民族的集体人格。
“泥人张”与“海张武”在剧场的较量中,沉稳干练,不亢不卑,受辱后镇定自若,用自己捏泥像的高超技巧,展示了一种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大关丁》和《腻歪》都写了一个富家少爷,在遭受时代和家庭的突变后,能在家族的衰败中,重新做人、重振家业,这些人物个性和命运的变化,正是中国人“逆境中浪子回头”的理想意识中的集体人格。《崔家炮》里把炮仗做到极致的崔家老三及全家人,敢作敢为,敢赌敢冒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服输”的天津卫地域的某种集体人格。
《蔡二少爷》本也有和大关丁同样的家族衰败的人生经历,但蔡二少爷在卖家产的过程上却走了一条和大关丁不同的道路,他先是做卖家,后是做买家,用一种唯利是图的生意人形象从事古玩的倒卖活动。《死鸟》里贺道台在养八哥鸟的奇事中丢了官帽的笑话,揭示了这类只会伺候宠物和伺候顶头上司的为官之道。《洋相》里的巴皮,学洋人的生活方式,只学了皮毛而被众人耻笑。这讽刺的却是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境遇中,一些失去了民族文化自信的落后愚昧的负面集体人格。
冯骥才在奇人奇事中抓出的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有褒有贬,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还有一种更富有文学意味的故事讲述,那就是对奇人奇事中凝练的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混合式”情感褒贬。
《粒儿》里写到的刘八父女,勤恳快乐地开着一间卖嘎巴菜的小铺子,无意中被“微服私访”的高官欣赏,高官赐给他们将来联系用的一把折扇,当刘八父女找送折扇人时,才发现这个送折扇的人是京城最大的官,于是几千年来中国普通百姓的畏官心理,使得父女俩一次次地错过京城高官的寻访,一次又一次地错失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冯骥才讲述的这个奇人故事,一方面肯定刘八父女勤俭敬业、纯真待人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惋惜、批评底层百姓怕官畏官的愚民意识和负面人格。《焦七》写一个文混混用放了砒霜的肉肠毒死偷他家肉肠的邻居胡老大。当黑衣捕快来抓捕他时,他侃侃而谈,有理有节,把设毒计的起因全推给胡老大。但作家在叙事过程中,却客观地勾画了这个文混混的阴鸷和歹毒,既肯定了他也否定了他。《刘道元活出殡》里的另一个文混混,更是上演了一出令人匪思所夷的“闹剧”,他装死想看看自己“死后”的葬礼及各人的反应,但他“活着”时那些表面真诚的朋友全都躲起来不再露面,而原来的“敌人”却撞上门来恶心他、讹诈他。冯骥才的文学叙事,表层上否定刘道元这种“非君子”式的反常策划,实质上揭示了“小人”当道后,那种“人走茶凉”般的世态炎凉和人性真相。
由此可见,冯骥才通过展现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风土人情,集中塑造了一批凝结着普通百姓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人格的奇人群像,他犀利的眼光和批判的思维,对部分的带有正面价值的集体人格持肯定的审美褒扬;对另一部分持否定态度;一部分复杂的人物生态,他真实地表达着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二元情感,充分显示了冯骥才对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风土人情的全方位的审美审视和理性思考。
冯骥才还通过描写奇人性格的形成以及奇人性格的命运,展现他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和文化人审视地方文化和集体人格时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广度。《冯五爷》里冯五爷在他的家族中书读得最好,中国人对读书人的期盼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当他把读书的聪明才智用在开饭馆时,却被家族中最信任的内贼逼得走投无路,家中那个给父亲做了一辈子饭的胖厨子一次次地在他眼皮底下偷窃,他这个读书人无可奈何,只好关闭“状元楼”歇业。那样的时代里一个读书人再聪明、再有才华,却永远斗不过尔虞我诈的低品小人,读书人的命运很难在那个时代充分施展。《蓝眼》里的鉴画高人,看假画时双眼无神;看到真画时则是“一道蓝光”。但为什么有如此职业绝技的大师最后被一个不出场的黄三爷陷害出局了呢?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生意场,小人当道。
三、笔记体小说中的多种“叙事方法”
用笔记体小说文体来再现那个时代天津卫的风土人情,挖掘奇人们个性与命运里的精神价值与集体人格,形成了冯骥才笔记体小说的叙事特征和文体规范。
冯骥才首先在全书的文学叙事展开时,创造了一个极富个性特征的“故事叙述人”形象。这个“故事叙述人”在叙述奇人们的个性特点时,很能抓住“动作性的写人细节”做介入主观的“夹叙夹议”。在叙述奇人们的传奇故事时,则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机智地设置一个有“反转、曲转、斜升”的意外结局的故事情节。
这个“冯氏故事叙述人”在揭示每篇作品和每个奇人个性与命运所蕴含的文化创意时,常常会采用“立意全点破”“立意半点破”“立意全留白”等3种方法来阐释作品的文学创意。而“立意全点破”时,可能会像《苏七快》那样,“故事叙述人”让故事人物自己的言行来补充形成奇人反常叙述的因果情节,使读者突然领悟故事的文学创意。也可能会像《旗杆儿》那样,由“故事叙述人”直接站出来,用“议论性的金句”直接点破故事的底蕴,在作品结尾的一霎那间升华作品的文学创意。所谓“立意半点破”,可能会像《蓝眼》那样,通过故事主人公自己的心理活动和思绪,把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原因透露一点信息后,让读者通过这个局部情节来想象出完整的文学情节和因果。也可能会像《认牙》那样,由“故事叙述人”出面也用“议论式金句”只点破奇人奇事发生的部分因缘。至于“立意全留白”,则像《鼓一张》那样,“故事叙述人”仅仅是完整地讲述一件“莲年有余”的年画卖疯了的奇事,而对奇事产生的原因,一字不提,全部交给读者去想象了。
《孟大鼻子》是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叙述方法来讲述孟大鼻子这个奇人的特异禀赋和传奇命运的呢?我们从解剖作品的故事情节开始,这篇作品从背景细节、到启动细节、再到发展细节和高潮细节,冯骥才一口气连续用了5个反常奇特的材料来凸显故事主人公鼻子的奇异功能。
A.背景细节是从外在形象上概述孟家二少爷的特大号鼻子;B.启动细节概述他的鼻子什么气味都闻得出;C.发展细节(一)是具体讲述一个奇特事件:一个小偷趁他酒醉时从他怀里偷走了3块银元,半个月后他撞见小偷闻出了自己的银元的味;D.发展细节(二)也是具体讲述一个奇特事件:他到慧罗春饭庄吃饭,闻出了乔掌柜上的鲤鱼不是活的。E.高潮细节则是从反转结局来讲述他的反常事件:如此有神奇功能的鼻子却闻不出与自己老婆有染的“野汉子”廖武官的狐臭味。
这样的五个细节材料是从反常到反常,一个比一个离奇,正是这五个反常离奇的细节和情节把孟大鼻子的独特个性和神奇的鼻子功能,渲染夸张到了极致。故事叙述人在连续讲述这五个反常的奇人的材料时有三个叙事方法,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用夹叙夹喻的文学叙述语言来描写孟大鼻子的外貌和特征。说他鼻子太大,是“膨脝肥实,油光光像个剥了皮的肉粽子”;对着人时,是“龇出一些鼻毛,像枯井伸出的草”。这些“比喻式叙述”的文学语言,有实有虚,有外在特点也有想象空间,突出了鼻子的奇特。
第二,用借代式的“排比叙事”夸张了故事主角大鼻子的奇特功能。他能闻出:“这是木头的气味,这是铁的气味,这是菜叶子的气味,这是旧棉袄的气味,那是脚丫子的气味……这个大鼻子好比一对明察秋毫的大眼睛,大千世界,一目了然,万千气味,无所不知。”故事叙述人利用第三人称全知的功能,灵活地排比句式、灵活地转换人称,有时竟让读者成为了“你”坐在他的对面,听他用夸张的排比语言,并配合着说书的神态动作来对孟大鼻子的神奇做突出特征的夸张式叙述。
第三,故事叙述人最有特点的讲述方法在高潮细节,作家并不是通过反转的意外结局来让读者理解和认同孟大鼻子的奇特背后正常的原因,而是通过反转再一次写了孟大鼻子的奇特表现,这一次奇特是他的鼻子不灵了,他闻不到和他妻子有染的廖武官的狐臭味,这里面的因果是什么?故事叙述人用了“暗示性的留白叙述”方法,把孟大鼻子第四次的反常的真正原因——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绝对知晓这个反常的真正原因,但故事叙述人却故意留白不说,而是借他人之口道出,与他老婆有染的是廖武官,“人很厉害,手段很多,连侯家后的混混儿都不敢惹他。”除了这些留白暗示,故事叙述人又使用“侧面叙述”的方法,说孟大鼻子隐了,老婆不再出头露面了,那些跟他的狐朋狗友也一哄而散了,他的鼻子好像忽然变小了,肉粽子干了……故事叙述人的“暗示叙述和侧写叙述”,将孟大鼻子的“鼻子失灵”的深层原因留给读者去想象。军阀的横霸,奇人的憋屈,了结了一代奇人的奇功。这个故事叙述人的“春秋笔法”把那个时代奇人的命运勾勒成型了。
这篇作品组织了五个反常离奇的材料,采用了典型的“斜升反转”的情节结构。而故事叙述人通过“比喻式叙述”“夸张性借代叙述”“暗示性侧面叙述”等叙述技巧,把一个一奇再奇的反常故事写得趣味盎然。这三个叙述技巧的巧妙使用,使冯骥才的故事叙述人形象获得鲜活的艺术生命,他的天上地下、正写侧写、实讲虚说的灵活叙事,让这个“冯氏故事叙述人形象”不仅能完美地串起故事材料,树立故事叙述人的个性形象,也使这个个性形象成为了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作家从主观情志出发,在内心中酝酿他对奇人奇事的感受和体验,用主观情感认知生活、提炼生活、表达生活,这使得“冯氏故事讲述人”的形象烙上了冯骥才的主观情志,这也就是“冯氏故事叙述人”能够生动成活,“俗世奇人”的系列故事能够精彩讲述并获得众多共情共鸣的根本原因。
四、故事叙述人的限知与隐喻
《跟会》的核心情节比较单纯并美艳,18岁的木头第一次单独出门看天津卫的“娘娘会”,被一个艳丽的踩跷少女吸引了,他“跟会”想看卸妆后的踩跷少女的美貌。谁知这个来自葛沽的“海下派”演白蛇的踩跷少女竟是一个男扮女妆的船夫。这是一个典型的“串联式曲转”的情节结构。就这么一个单纯的误会式故事,冯骥才仍是采用了“折叠+跳移”的微型小说情节结构来打造叙述文本。
作品的第1段起笔就是启动细节:木头怀揣玉米饼急急忙忙去看“皇会”。第2、3段才是“折叠”进来讲“皇会”的风俗及历史。第5至7段是发展细节(一):木头遇上一个美丽的踩跷少女并扶了她一把。第8至15是发展细节(二):一个中年男子热心地托举木头上了高处看会。第16至22段是发展细节(三):一个养花的老爷子教木头“跟会”去看热闹。第23至30段是发展细节(四):跟会的木头再次遇到穿白衣的踩跷少女,这一回是她扶了木头一把。第31段至最后一段是“跳移式叙述”的高潮细节了:木头自此才听到看门人说:那个与木头两次相遇的踩跷少女是个男性船夫扮演的。故事的结局是曲转的,悬念式的真相“跳移”至此才突然解密。
这篇《跟会》和其它大多数作品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第三人称的限制叙述视角——它从故事主人公木头的视角与心灵去感知生活、观看皇会。这个“限定”叙述为冯骥才在这篇作品中的文化创意,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角度。18岁的木头第一次看皇会,在他的眼中、心灵中,一切都是新奇的、热闹的、美好的。娇美的踩跷少女引发了他的青春反应;助人为乐的中年男子和养花老爷子充满了人间的温暖和善意;而各种皇会上的吃的、看的,各种庙会的民俗表演,都让木头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正是从木头的视觉和心理出发,这样一种踩跷少女的美和奇才能得到一种充分的渲染、铺垫,以致最后揭开悬念后的阅读震惊。
然而,冯骥才通过短篇小说常用的“第三人称限制视角”来讲述微型小说故事,充分而恰当地展示了冯骥才在“俗世奇人”系列里的文化创意——作为一个中国民俗文化的著名学者,在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真善美有着一个特有的诗美感受和体验,对民俗文化中的许多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消亡感到痛心和焦虑。他用这样的“微型小说故事内核+短篇小说叙事艺术”的相互融合的长处和优势,来讲述了一个“男扮女装”的奇人的故事,他从一个18岁的天真纯洁的少年人的心理淋漓尽致地写出天津卫民俗人情,并在这种民俗人情的充分描写中,展现了一个民俗文学学者和思想家的悲悯情怀和审美理想,这样的一种创作情怀和叙事方法,拓宽了“冯氏故事叙述人”的形象的审美带宽,丰富了笔记体微型小说的创新写法。
《俗世奇人全本》的最后一篇《旗杆子》印证及阐释“冯氏故事叙述人”的确立与成活。《旗杆子》里面的奇人奇在哪?奇在他的个头最高;奇在他的饭量最大;奇在他的命运最后竟然是被“饿死的”。看这个传奇故事的结构形态:
A.背景细节:天津人把个头极高的人称为娘娘庙前的大旗杆。
B.启动细节:这个从小被人叫做旗杆子的他饭量如虎。
C.发展细节(一):用“概括叙述+具体叙述”的方式讲他因个子高,常常找不到活干,常常要饿肚子;一天夜里他举着小火把过街,巨大的黑人影像鬼一样吓得两个行人落荒而逃。
D.发展细节(二):两个穿戴整齐的中年人要他去公园收门票,这个美差终于让他每顿能吃10个馒头了。
E.发展细节(三):这是个“折叠情节”,把旗杆子接到能吃饱饭的美差的缘故交代了:原来是公园郝园长把他当作公园的“怪物”来让人参观,以增加门票收入。
F.发展细节(四):有人嫉妒他吃了饱饭,便设局陷害他,说他私藏收入,郝园长看到了钱藏到高处后开除了他。
G.高潮细节:被开除的旗杆子饿死了,郝园长知道真相后很后悔,便打松木棺材厚葬他,奇怪的是,死后的他还长了一截,郝园长加钱把棺材加长一尺才把他装进去。
请注意作品最后一段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事者的“全点破立意”:“人间容不得高人,只有死后再去长了”;“从此,此地再无高人,亦无奇人。”这是“睿智思想家”的“议论式金句的全点破”。旗杆子确实奇怪,他死后竟然还能再长个;但是这个奇人生活在那个时代,却得不到尊重和生存条件。他的个高和大饭量,在那个时代,不但缺少基本的生活条件,更被人当作怪物拿去展览挣钱;当他能吃饱时,又被人嫉妒陷害,所以,在旧时代的天津卫,这样的高个奇人是不可能有尊严地生存的。故事叙述人用了一句“人间容不得高人”,就一针见血地点破旧时代底层人的生存窘境,揭示了那个时代唯利是图的冷酷真相。而作品最后一句的点破:“从此,此地再无高人,亦无奇人。”更要做双关的“隐喻”——那样的时代是不可能“出高人”,个子高的人无法生存,智商高的人也没有好的命运。冯骥才所写到的旧时代的天津卫,那54个奇人的命运都只能在书本上和纸面上历史般地存在;当新的时代来临,那些奇人才能得到尊重,也才有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家冯骥才借故事讲述人的这一句“睿智思想家”的全点破,概括了众多奇人们的命运,发出了真正的意味深长的隐喻式点破。
注释:
[1]转引自李南南解读《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得到”听书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