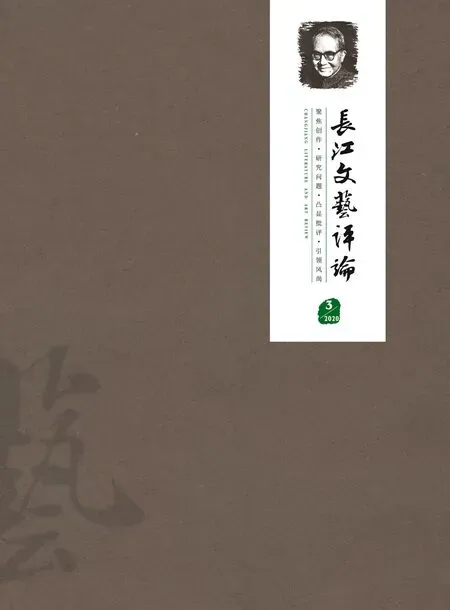叙事学难得的建树型成果
2020-11-17施战军
◆施战军
叙事学在西方文论中无疑具有现代背景,尤其适用于当时新的文学现象,当然西方叙事学也用来研究现代派之前的许多经典作品,解构了许多固定的解读模式,从而生成新的文学研究与批评路径。在中国,叙事学的引进和运用往往集中实践于1985年前后出现的新潮小说。少数学者曾借助叙事学方法对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理论基本上是移植套用为多,而大胆尝试这一武器功能的往往是新文论倡导者和当代文学批评家,创造性转化为与本土传统文学相结合的建树并不普遍和显著。
王彬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从文本到叙事》,此前的《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以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无边的风月》等,恰恰是我们所期待的有关中国文学的叙事学研究难得的建树型学术成果。
尽管他在著作中也举了海明威、巴尔扎克等外国作家的例子,但是重点还是落在了这个层面——中国文本达成世界通解的可能。也就是说,对这些表面上看来是从西方移植过来或者借鉴过来的话语和方法,进行中国式的化用与新创,让本土读者发现中国文学有许多新的魅力和尚未照亮的秘境;也引导国外读者,哪怕是用最新的理论也能悟出中国文本的堂奥与趣味。
书里出现的这些词:场、时间、空间、叙述者、修辞等等,这些引进的文论概念其实已经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通用起来了。不过,王彬有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论语词,比如伪时间、动力元、漫溢话语、亚自由直接话语、叙述集团、滞后叙述、第二叙述者等等,他在国外叙事学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充分地中国化了,对文本是非常实用的。《从文本到叙事》里关于小说中的动力元那一章,尤其精彩。动力元的概念是在理论上说明小说是靠什么推动的,故事和文本样式是怎么形成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以作品来抽样分析、阐释,分为叙事者动力元、人物动力元、语句动力元等层面,揭示了动力元决定小说样式的内在原理。广涉《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以及海明威、巴尔扎克的著作,例子信手拈来,在他的理论里,让你不得不认为作品中真是存在着那么多的底细。而且写得言简意赅,说服力极强,完全可以作为写作班上的教案。尤其是语句动力元那一段,分析孙大圣与二郎神的交手,一般读者对这样的故事只是看个热闹,王彬先生庖丁解牛般告诉你哪儿是动力元、哪儿是次动力元、哪儿是辅助动力元,彼此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原来古典名著别有洞天,这种精妙的解读令人豁然开朗。他在《从文本到叙事》中写道:
却说那①大圣②已至灌江口,③摇身一变,即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②按下云头,③径①入庙里。[1]
王彬分析道:“标号①者为动力元。②者为次动力元。③者为辅助动力元。分析起来是这样的:①‘大圣’‘入庙里’为动力元,‘大圣’是因,‘入庙里’是果;②‘按下云头’‘已至灌江口’‘径’为次动力元,参与孙悟空进入庙里的动作;③‘摇身一变,即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为辅助动力元,对动力元与次动力元进行修饰。如果去掉②和③,即次动力元与辅助动力元,孙悟空的行动并不会阻断,只是缺少了行动过程与色彩。易而言之,①即动力元,处于因果链条的中心,失去了这个中心,便会造成叙述中断。②即次动力元,增补因果关系,但不纳入因果链条内。③即辅助动力元,只提供动力元的相关情况,相对于次动力元,与动力元的关系更为疏远。”[2]
此外,还有一种非动力元,即推动故事发展的单纯的景物描写,比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大段的与人物行动无关的景物描写。
简言之,“动力元、次动力元、辅助动力元、非动力元,构成一个完整强大的动力系统。从小说的发展史看,动力元处于逐步减少的状态,而表现在语句中的动力元亦处于逐步减少的趋势,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早期以情节为重,因此表现在语句上,动力元多,次动力元以下少。反之,非情节小说,动力元相对减少,相对应的,在语句上,便采取了一种缓慢的松弛姿态。”[3]过去我们的文学观念惯于以人文的角度来拒绝科学逻辑,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有些科学性的缜密的分析对创作是非常有用的,不能盲目排斥某一种思维样式和某一种逻辑模式。我们看传统小说,经常是人物和情节设置被故事的线性阅读所覆盖,快意一时而已,但是王彬的研究告诉你,有太多的奥秘有待我们带着关联去破解。探索从文本中生成的实用性而不是移栽的中国式叙事学系统,这大概就是王彬的理论雄心。
营构的耐心是王彬的又一可贵的治学精神。他早在多年前就将叙事学理论探索与《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相洽,并有针对性地在鲁迅文学院教学中用于开拓学员的思路和创作方法。无论是理论评论班还是创作班,许多学员都得益于王彬的叙事学研究心得。由于他是先用文本研究的方式呈现他的理论,因而在理论成熟之前,对于古典名著以及中外文学的精读的学术准备需要极大的耐性,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有多么坚定执著。《红楼梦叙事》这本书,他所用的时间非常长,作为他的重头成果,最早出版于1998年,近年由人民出版社出新版,目前还在持续修订完善之中。这部书一共八章,运用西方叙事学(结合中国的小说研究)对《红楼梦》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文本分析,在这个基础上详细阐述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事方法与叙事特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使之与西方的叙事学具有通约的可能,比如书中的第二章第三节“诗赞”。王彬指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述格局,如果从文体的角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乐曲(唱)与诗赞(说)两个系列。所谓诗赞包括文与诗,在叙述中,以文为主,以诗为辅。为了阐述方便。我们在这里将诗赞作为专指,只是指诗赞中的的诗极其相近的那部分,诗赞中的文,则仍称为文。”[4]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诗赞的作用是描写(人物形象与景物形态)、提示、评述、议论与总结,王彬分析道:《三国演义》第21回,雷雨中曹操与刘备讨论天下英雄,曹操指着刘备说:“唯使君与操尔。”[5]刘备吓得把筷子掉下来,这时恰好惊雷响起,雷声中刘备把筷子拾起来。曹操笑道使君也畏雷乎?于是放松了对刘备的警惕。在这个故事结束以后,文中出现了一首七绝进行总结:“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将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6]
那么,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诗赞,在西方与当代文学作品中处于什么状态呢?王彬在《从文本到叙事》“文体、话语与故事的互为语境”一章中引用了英国著名小说家奈保尔的长篇小说《游击队员》第一章的一段描写,我转引如下:
突然,在这片荒原上,一块崭新的黄红黑三色告示牌出现在他们眼前,牌子最上端画着那个象征性紧握的拳头。
画眉山庄,人民公社,为了土地和革命,任何时间未经事先批准,严禁入内。
——奉最高统帅詹姆斯·艾哈迈德(哈吉)之命。
最下面一条,红底白字上写着立此牌的当地公司的名字:萨波利切。
罗奇说:“我们得叫吉米把语气收敛些。”罗奇正是为萨波利切公司工作的。
“哈吉?”简说。
“就我所知,哈吉指朝觐过麦加的穆斯林。吉米用他指代‘先生’或‘阁下’。只要他记得,他就这么用。”[7]
王彬指出:这个告示属于应用文体,“其实是相当于中国传统小说之中的赞,只是这个赞不仅仅是传统的诗词曲赋,而且涵盖了许多应用文体中的不同样式。换言之,‘画眉山庄’的告示是一种新赞,相对于旧赞,其样式上更为广博。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由赞与文两种文体组成,不同文体的互为语境实质是赞与文的互动,而当下流行的西体小说,也不过是两种文体,应用文体与文学文体,只是赞的形式更加广博。这种赞不妨称为新赞,因此在当下文体的小说中,其不同文体的互为语境,也不过是赞与文的互动而已。”[8]这样的互为语境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也可以寻找到例证。《水浒传》第23回,武松在景阳冈喝酒后,乘着酒兴走到一座败落的山神庙前,看见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上面写道:“阳谷县示:为这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近来伤害人命。见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9]武松读罢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发步再回酒店里来”[10],担心被人耻笑而继续上山。这篇阳谷县告示对后面情节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武松就此止住,一是继续行走。武松选择了后者,从而演绎出武松打虎的情节。王彬进一步指出,武松读到的阳谷县的告示与《游击队员》中画眉山庄的告示,前者是政府的告示,后者是公司的告示,发布者不同,但均属于应用文体,与小说中的文学文体在互补语境中,前者通过武松的思索与行踪,后者通过对哈吉的询问与解释,促使故事进入下一个环节。换而言之,这两处不同文体的互为语境不再是静态而是转为动态,而王彬对赞的分析就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而且成为世界文学的通解了。这样的叙事学研究不仅是本土的,而且是国际的,从而丰富了叙事学的内容,推动了叙事学的发展。
相对于《红楼梦叙事》与《从文本到叙事》,《水浒的酒店》与《无边的风月》对《水浒传》与《红楼梦》的文化语境进行了有趣味的探索,且在行文上更为简洁轻松。其中《无边的风月》对《红楼梦》中的建筑、服饰、器物、官职、经济、阶级、语言、丧仪、人物年龄等进行了深入而耐心的梳理,将原本清晰但被历史遮蔽了的语境发掘出来,透彻地展现了《红楼梦》的主旨。《水浒的酒店》则对《水浒传》中与酒店相关的所有细节和各种符码做了广博的索引与阐释,从而形成了一个有价值且实用的数据库。它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和统筹学,而是将过去我们阅读时未曾留意的,与酒店相关的物件、场景、人、时间、相关数量等等,在分类、图表上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关联网,让我们顿悟:原来我们中国古典名著里面蕴藏了这么多的秘笈,而这些秘笈构成了这部作品成立、完形的重要元素。《水浒的酒店》具体且生动,在某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破解古典名著的路径。
他营构的耐心还体现在对逻辑的纹理方面的探寻。作品的发生、持续的生长,到在解读中延续的完成,叙事学逻辑上可以提供确凿但又无止境的证明,中国文化、中国文本向来以整体建构为宗,王彬的叙事学不同于趣味奇特的碎片发现,而是具有整体逻辑的烛照,即使某个细微的角度也带有全息观照的效应。这种理论上孜孜矻矻点灯熬油的耐心也是罕见的。
坚守学术的初心也是王彬格外突出的品质。对于学术本身,他始终保持着敬畏,秉持细查明辨盘根究底的率真之心。他特别注意学术的价值,他认为学术不是呆滞的,是活润的,但又肯定应该是对的,不会是死的和错的。他专注于文学新意生成的可能,从他的著作中,我们看得出“接着说”和“从头另说”的努力,但那决不是“重复说”和“胡乱说”。过去的诸多名著,前人对于文本的意义解析和由来探勘仿佛已经完全说满了,但他的理论,可以看出另外的意义和根由。以童真的初心和雄厚的功底,在文本内部探险,使他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进入了一个学术的自由世界。这几本书便是他学术上持有初心的明证。
王彬的治学也给我们很多启示。简要来说,第一个启示是理论自觉和创造模式。习惯上我们在评说文本时要么注重自己的感觉,尽管是个性化的表达,但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作家作品的附着物而已;要么就是容易用现成的理论,使作品成为某种理论的说明材料。这两种倾向构成了较为省心省力的文学批评的两种方法。其实,感悟性的批评必须得有史识的支撑和理论的自觉,看李健吾的文章,在随意潇洒的文字后面,却有古今中外的涉猎和思考中析出的理论坐标。王彬的理论自觉和创造模式,在于不轻信现成理论也不依靠感觉任性,在此之上,韧劲儿一以贯之,在厚实的学养基础上保持着创造的主动性,认准一种理论系统,在与文本的交互中不断显出意义、呈现价值,多年后,意义和价值果真一重重地实现了。
熟悉文本是做学问的前提,这是王彬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在《从文本到叙事》中我们看到作者多年的营构,首先体现在学术的储备上,学术储备首先是阅读的储备、博采的储备,看了多少书,研究了多少遍才行的,版本也都标得清清楚楚。这番对原典研究所下的气力,令人联想到上世纪以及之前的学人的学术态度,也道出了王彬先生的治学方法。他所有叙事学的理论来源和指向都是文本。理论架构的显现路径是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因而更加可用、可信、可靠。我们看到的不少评论文章,常有故作高深之态,或者故作惊人之语,激情之下往往暴露出学养的不足和阅读的不精,往往是知道得太少所以太爱多说,而《从文本到叙事》每一章节虽然很短,但知识性丰满,道出了研究的精粹。由此,《从文本到叙事》《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无边的风月》等著作,也应该是文学批评和中国化的叙事学理论值得研究的范本。
注释:
[1][2][3][7][8]王彬:《从文本到叙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1-82页,83页,84页,176-177页,177页。
[4]王彬:《红楼梦叙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5][6]罗贯中:《三国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264页。
[9][10]施耐庵:《水浒传》,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