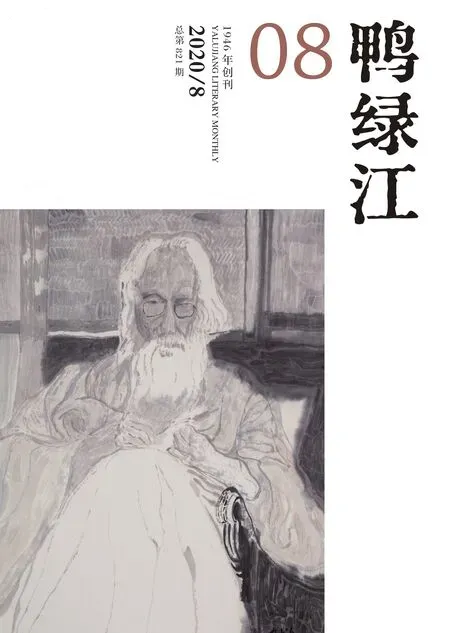精神的建筑(评论)
——汤成难的小说和小说观
2020-11-17韩松刚
韩松刚
汤成难的小说,源于“建筑”的冲动,甚或是一个建筑师的本能,“是一种让别人知道我们是谁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的渴望”,而石头、树木、沙,钢材、砖块、混凝土,棉花、麻绳、布匹,既是材料和装饰,也是语言和张力,正如汤成难自己所说:“可你并不喜欢这种主旨先行的方式,你更倾向于搜集材料过程中,面对一块石头的诚意。而这些真诚、天真、诚恳的部分,正是你当初从事小说创作的原动力。”(见本期汤成难《一个女建筑师的小说认知》,下同)
建筑师想把建筑变成什么样?这当然不是一张图纸就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两者的对立和平衡中,建筑师可以有很多决定。“建筑师的主要职责在于仔细衡量得失,做出决定。它必须决定什么可行,什么有可能妥协,什么可以放弃,在何处和怎么做。”①[美]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周卜颐译,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小说家也如此,在一定的审美范畴之内,小说是对不同生活和未知世界的好奇及探索。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每一种都能在技术上做到无可挑剔。只不过,如果完全按照建筑的科学精神,可能只有极少的小说能向我们传达出确切的诗意。好的小说,和好的建筑一样,是艺术而非科学。
因此,建筑师必须是一位艺术家,如若不然,就只能是蹩脚的建筑工。没有精神的覆盖,小说便如同呆若木鸡的建筑,毫无审美的意义。我们感觉一部小说不吸引人,类似于我们感觉一幢建筑不吸引人,那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它模糊难辨的外表,以及这外表之下所隐藏的不讨人喜欢的美学气质。“那么该如何防止建筑以及艺术风格沦为恶意关联的牺牲品呢?我们只需谨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时间是它们重新焕发魅力的最重要的因素。”①[英]阿兰·德波顿:《幸福的建筑》,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就像汤成难所认为的那样:“一座建筑,必有其使用年限,一篇小说也有其生命长度。”那么构成这种生命长度的内在力量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它耀眼的精神光芒。我们心仪的好小说,和我们喜欢的建筑一样,能够透过其原材料、外形或颜色,表现出令人赏心或震颤的积极品质。大多数时候,“我们对美的感觉与我们对美好生活之本质的理解是纠缠在一起的”②[英]阿兰·德波顿:《幸福的建筑》,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不同的小说风格,就像不同的建筑风格,诉说着对生活不同的理解。汤成难的小说,向我们展示出生命的某种真谛:当下生活中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其实都需要一个家的最深刻的同情。就好比我们需要一座幸福的建筑,来补偿我们精神的脆弱,来安放我们异己的肉体,以阻止真正的自我迷失。《小王庄的往事》如此,《我的舅舅刘长安》如此,《箜篌》亦如此。
《箜篌》主要讲述的是保姆王彩虹与乐器厂的琴师陈笠之间隐秘复杂的婚外情感。写的是日常的逃离和归家,“不奇异,不瞩目,不惊动”,然而,在小说叙述口吻的从容吐纳中,流动的是逃离的短暂喜悦和终不能逃离的永恒忧伤。读汤成难的这部小说,不期然地想起了加拿大的女作家艾丽丝·门罗。比如她的小说《沃克兄弟的放牛娃》,就是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讲述父亲的“婚外情”,但叙述中充盈的音乐气息和单纯味道,让这个故事丝毫没有道德上的违和感。和这位善于描写日常生活的女作家一样,汤成难也喜欢从平庸而热烈的人间中寻找生命的裂缝,她笔下的婚外情感同样复杂而温暖。
好的小说和美丽的建筑,都能够提升我们精神的审美力量。小说取名“箜篌”,当然是象征的隐喻,它意味着对美的欣赏和接受,尤其是在那些生活消沉的至暗时刻,对美的渴望总会不请自来,而“建筑”的渴望也由此而生。箜篌是中国古代一种传统弹弦乐器,唐代十分流行,但明代之后基本失传。唐代诗人王昌龄、李贺等,都曾以“箜篌”为题作过诗,由此展现了箜篌自身所具有的那种浪漫唯美的悲剧性情调。而这一乐器的情感属性,也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叙事基调。
汤成难的小说里,始终密布着无言的惆怅和感伤,但这感伤并不热烈,也不那么令人灼痛,更像是欢愉与忧郁的奇怪混杂,如同王彩虹和陈笠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生活是何等不完美,作者深知其味,但又不甘心如此,于是才有了小说中这些低微形象的高贵塑造,以此来观照周遭世界的平庸呆滞和枯燥乏味。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人性多么复杂,汤成难总能用她建筑师的敏感心灵,捕捉到人们内心深处那些隐秘的阴影,以及阴影之下隐约的欲求和憧憬,并以诗意的形式将人性的光芒呈现出来。
汤成难的小说结构不复杂,也没有多少形式上的创意,甚至有些过于简单了。但这恰恰符合她自己的小说观:“完全新颖的主题可能缺少最重要的要素——普遍性,几乎每个人的生活均具有某些共通性,所以不要尝试着去建一个完全新颖甚至违背自然规律的屋顶,你大可在人字坡屋顶、平顶、拱形屋顶、尖顶等等的永恒的范围内探索更多的因果、理智,和秩序。”在一个尚新求新的写作时代,汤成难的小说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落伍”了。但是,一部好的小说,犹如一座有魅力的建筑,有它内在的规则,也离不开既定而单一的秩序。事实上,对秩序的执着,既是对生活的执着,也是对生命的执着。“虽然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建筑也像文学一样,一件重要的作品应该是复杂的,但是有很多迷人的建筑在设计上却出奇地简单,甚至是重复的。”①[英]阿兰·德波顿:《幸福的建筑》,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在这个艺术形式不断翻新的时代,小说或许要像古典建筑一样,“应该具有甘愿稍显乏味的信心与善意”②[英]阿兰·德波顿:《幸福的建筑》,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汤成难的小说,用的都是日常的建筑材料,甚至可恶到同一个人名可以重复出现好多次,但是这些一定的材料,在她的笔下,经由新的排列组合以及这一奇妙过程的情感发酵,却产生了不定的艺术效果。对于一个优异的建筑师来说,即便是最为普通的材料,也会激发出质朴而野性的诗意创造,就如她自己所说:“突然,你看见一些短木头,它们是某次建筑完工后的边角料,看似无用,但以你目前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你将短木头清理出来,测量,测试,修整,打磨,开孔,隼接,进行力学计算,你居然用它们制造出非常牛掰的木结构桁架柱梁。材料的独特性,使得这座建筑也与众不同。”其实,对于小说写作来说,离不开生活的边角料,甚至于大多数时候,不过是对开裂的人生缝隙的修修补补。
人生活在庸常之中,会面对许许多多难以摆脱的困境,小说家有时候也束手无策,就像建筑师对整体责任的负责并不能完全排除无法解决的难题。然而,正是问题的存在和意义的产生,才使他们的作品成为超越日常的精神产物。《箜篌》中,王彩虹和陈笠这两个陌生个体之间让人困惑的情感就是其中的难题之一,而“箜篌”似乎就是作者试图释难的解码器,它像一个快乐的音符,以理想向生活的平凡致意。对破败生活中纯粹情感的真实渴望,使小说获得了优雅的艺术品质。音乐是“流动的建筑”。“箜篌”就是建筑中的柱梁,支撑起整部小说的结构。作为一种乐器,“箜篌”按十二平均律七声音阶降C大调定弦,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与赋格。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作为一部小说,《箜篌》体现出了巴洛克时期古典音乐的某些特征,其结构有着巴赫般的严谨整饬,但情感没有贝多芬悲壮的雄浑,也没有莫扎特天真的欢愉,而更多海顿的平和、内敛,有些失之深度却不乏神采飞扬。
小说是精神的建筑。小说和音乐、建筑一样,其最迷人之处,还是隐藏在其有序的建筑外观之下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能深刻有力地满足人们心灵需求的简单之美,都来自内在的复杂性。”①[美]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周卜颐译,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生活看上去是那么简单,但每一个简单的日子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的幸福和悲欢。《箜篌》中所描写的两个家庭卑微而日常的现实,其实是无数个不同家庭的时代折射和精神映照,其中深含的困惑和痛苦,很多是相同的,具有一种直白而深刻的“普遍性”。但小说的魅力,是在于其溢出日常生活秩序的部分。诺瓦利斯说:“在一件艺术作品中,透过秩序的面纱必须有非秩序的闪光。”生活同样如此。秩序应该是有限度的,如果没有非秩序的闪光,一切生活都将是暮气沉沉。具体到小说的写作来说,不同角色的穿插和腾挪,多种情感的澎湃和接续,既要遵照一个总的规则,又要施之以特异的差别,从而在和谐与冲突之间实现美和力的平衡。
平衡是小说的艺术,也是建筑的美德。这美德由建筑师来调停。在建筑中对平衡的推崇,其实是某种生活状态的暗示,就如同在小说中崇尚精神的健康。作家对脚下的土地负有投身的责任,他们写出的小说,至少不能劣于我们生活的这方热土。同样,作家对人间的生命亦负有探知的义务,他们用小说给人类认识生活以最真诚的许诺。小说的魅力,离不开“建筑”之美,而“美存在于秩序与多变之间”。《一个女建筑师的小说认知》,可以看作汤成难温和的小说宣言。这宣言中,包含了简单和纯粹,也酝酿着复杂和矛盾,它的真谛就在于这种兼容的整体性。建造一座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建筑,如同写作一部既不沉闷又不混乱的小说,需要一种秩序和混乱之间令人欢欣鼓舞的美学张力。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尾了,一间房子已经大功告成。但是,我还是想对这间毛坯房进行一番修饰,以让大家能够更好地认识汤成难以及她的小说。事实上,除了建筑师的身份,汤成难还可以是一个餐厅的老板、一个业余的画家、一个热衷于西藏的驴友。这些可以说和她的小说无关,却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她的小说写作。
汤成难小说的底色是江南的诗意和日常的卑微。她写人生的无奈,写日常的苦乐,有着实录般的俗世影像,但她小说的动人处,则是在烦恼与愁绪的纠葛中对灵魂和彼岸的精神遥望。她对现实生活的展现,像一个画家,把世俗生活的哀与乐、惶恐与安慰,一点点描绘出来,在白色的纸张上留下复杂又迷人的命运轨迹,在这个意义上,她的小说可以看作“人间的写真”。而意义的复杂以及由此引起的不确定性和对立性,也是绘画的显著特点。汤成难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和绘画之间存在的交相辉映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使她的小说始终弥漫着诗画般的朦胧美妙以及不可言说的肃穆意境。她的前辈作家汪曾祺就深得绘画之妙,并将此巧妙地运用到了小说中,才有了如诗如画的《受戒》和《大淖记事》。因此,我想,她小说的诗意和美好,也定然离不了绘画的艺术熏陶,线条和文字之间,是精神和美学的神韵互通。
汤成难是日常生活的朴实书写者。她是对日常生活发问,她习惯于追问日常的隐秘和生命的困顿,并有思想的暗影覆盖其上。《箜篌》以及汤成难之前的大部分小说,都有一种别样的忧郁之美,这忧郁之中同时隐含着精神的自尊。阅读小说,就是在阅读他人的命运,但又何尝不是阅读自己的可怜。对于生活中的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汤成难似乎有天然的亲密感。她用最简单的笔法,写出了我们以及生活的复杂。她不喜欢杂色的铺染,而倾心于单纯的素雅的写真,她笔下那简洁的速写,展现出的是真实生活的原色,她笔下的生活平淡而隽永,有静水深流的温暖。在汤成难所描写的日常的单调和丰富中,存在许许多多平凡和不朽的时刻。
虽身居闹市,但汤成难笔下的人物,都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艰难跋涉,清贫而密布着烟火气的形象,鲜活动人,清晰可感。汤成难的小说给人以寂寞的感觉。清寂的孤独似波澜泛起,伸展到无边的内心深处,但这寂寞并不带人走进空洞的幽暗之中,而是留有淡淡的希冀。她是人间苦海的歌唱者。阅读汤成难的小说,会想到汪曾祺,会想到扬州的烟花三月,它们都有自己的世界,一个与他人有关,但又不干扰他人的世界。在汤成难的小说里,“事事物物皆是对的,正正当当的,投身,和音,入这明亮的一体中去”(里尔克语)。
在绘画的肃穆和幽静之外,汤成难的小说里还有一股飞动的能量。她的小说释放着奔腾的灵感,有时甚至是忘我的燃烧。《一棵大树想要飞》《奔跑的稻田》如此,《箜篌》也回荡着这种情感的激越。在江南水乡的一隅,汤成难的小说却显示出了令人无法琢磨的西部风情。这种地域上的文化暗示,似乎让她与传统意义上的诗意写作有所不同。在她诗意而残酷的日常里,有着西部的雄浑和壮丽。汤成难的小说是混血的。她的小说里,还有一些梦话的气息。这气息除了天性中隐含的精神质素之外,想必与遥远的西藏也有潜在的联系。汤成难有着强烈的西藏情结,西藏已经成为她生活和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她一次次地驾车奔赴西藏,去那个可以生长灵感,可以使精神飞翔的地方。
我在想,汤成难驾车行驶在西藏山路上的感觉,以及那些印刻在天路上的万物的低语,其实是生命和命运的另一种表达。里尔克说:“艺术作品总是一个人于险象环生中的结果,是身体力行走遍所有路途,至于山穷水尽,再无可更进一步的结果。”她的小说,仿若人的灵魂奔驰在西部道路上发出的持续的灿烂声响,缭绕于那蔚蓝而广袤的天空上。好的小说是思想的奔流,能在生活的无意义处,泉涌出温暖的爱意;好的小说也是精神的火把,能在生命无尽的暗夜里,点亮凡俗的星空。因此,即使在汤成难小说最为萧索的生活画面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诗韵的流光,她在流动的时空里,以飞翔的姿态,展现了生活中的温柔和暴烈。
汤成难说:“小说中张力产生的主要途径是人物关系的变化,人物关系的变化推动故事和情节的发展。尤其是人物关系中的利益关系,欲望与能力,现实与梦想,实力与境遇等等的表面张力,除此之外,还有更深的隐性张力,譬如感性与理性,自由与孤独,爱情与死亡,超我与本我……历史上所有的伟大作品,无一不是在隐性张力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写小说,从根本上说,就是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切张力由此而生。《箜篌》的本质也是关系,保姆与琴师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复杂情感之间的关系。但没有一种关系是单独存在的,一切关系都有交叉,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或者不理解,其实是灵魂的碰撞和焊接之后的不同结果。而结果和张力的不同,是作者价值观的折叠和反映。归根结底,一切写作都源于程度不一的对关系的惶恐,而文学的其中之义,就包含了对这莫名惶恐的暗示和安慰。对汤成难来说,建筑、绘画、西藏、江南给了她诗意,给了她理解各种关系的神秘之钥,她小说中的简朴、朗然与阔大,静静地涌动在她荣辱与共的一切日常之中。于是,在汤成难的笔下,小说被改写了,而一起被改写的,还有这失格的人间,以及一个个庸常之人不确定性的命运。
阿兰·波德顿在《幸福的建筑》中论及美丽的建筑时说:“我们可以将真正美丽的建筑定义为赋有足够多先天的优点,足以经受住我们不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心理投射的建筑。它们赋有真正美好的品质,而非单单令我们想起这些品质。它们因此能够超越其时间或地域的起源,并在它们最初的观众早已消失之后仍能传达出它们包含的意图。不论我们要么过于慷慨要么过于苛酷的联想如何消长起落,它们都能一如既往秉持自己的品质,岿然不动。”①[英]阿兰·德波顿:《幸福的建筑》,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好的小说,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