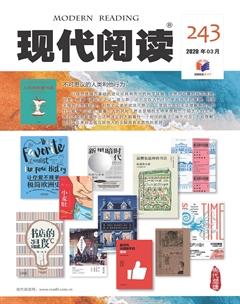不可思议的人类利他行为
2020-11-16阿比盖尔·马什张岩
阿比盖尔·马什 张岩
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是绝对可靠的科学原理。但是,根据“进化论之父”查尔斯·达尔文在大约150年前所作的推测,物竞天择的必然推论是,利他主义者早就该灭绝了。愿意牺牲自己来帮助他人的人当然能够创造奇迹,同时增加他人活下去的机会,但是这样做对他自己的生存发展未必有多少好处。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那些牺牲自己的进化适应能力来帮助他人的“傻瓜”肯定会被那些自私自利的同类打败,人数也会越来越少,并最终被取而代之。
利他主义者明明就存在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确实存在利他主义者。在我19岁的时候,一位与我素昧平生的利他主义者救了我一命,而且,他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只是众多利他主义者中的一个。每年,都会有几十位冒着不同程度人身危险挽救陌生人生命的美国人获得卡内基英雄基金奖章。每年,都会有超过100名美国人冒着巨大风险接受外科手术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献给陌生人,而且通常都是匿名捐献。在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无偿捐献骨髓或者血液,当然,他们作出的犧牲比较小,但是他们的动机同样高尚:对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施以援手。
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无法用清晰的科学原理来解释这样的行为。从查尔斯·达尔文时代开始,生物学家就试图建立各种模型来解释利他行为,但是,这些模型关注的重点是帮助自己的亲属或者所属社会群体成员的利他行为。比如说,可以用内含适应性理论来解释帮助自己亲属的某些利他行为。内含适应性理论认为,只要实施利他行为的一方同受益一方之间的基因重合度高到足以弥补其所冒风险的程度,这种利他行为就会在进化过程中被保留。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群居动物,比如地松鼠,会在发现捕猎者靠近时大声警告同伴。动物发出的警告声会在吸引捕猎者注意的同时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但是这样做能够帮助它的近亲们摆脱危险。内含适应性理论还能够解释人类为什么更愿意给自己的家庭成员捐献器官,而不是捐给陌生人或朋友。如果你把一个肾脏捐给自己的姐姐,那么她就有机会活下来为你生育外甥、外甥女,这些孩子会将你的部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你本人也许不会因为自己的仗义相助而获益,但是你的基因可以,所以,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你所冒的风险是值得的。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针对关系很远或者根本就没有关系的人的利他行为呢?此类利他行为经常表现为互惠利他主义。也就是说,基于受惠方迟早都会报答自己的期待。人类其实一直都有类似的互惠行为,你会借糖给邻居,或者请同事喝咖啡,你当然会期待他们懂得礼尚往来的规矩,互惠利他主义的施惠对象几乎都是利他者所属社会群体的成员,因为比起偶然遇到的陌生人,这些人更有可能愿意在将来回报这一恩惠。这种利他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延迟满足,因为最终利他者个人还是会受益的,只不过要迟上一些时候。
无论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利他主义,还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利他主义都是普遍存在且非常有价值的生物学策略。若不是因为这些策略的存在,带有社会属性的物种极有可能生存不下去。许多关于利他主义的书籍都对利他主义的这些形态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两种利他主义模型的本质都是自私自利的。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利他主义,其直接目的就是使利他主义的基因得以延续;而以合作为基础的利他主义,更是直接以利他主体获益为目的。因此,这两种模型都无法解释利他主义活体肾脏捐献者、卡内基英雄们还有我的救命恩人的做法。他们都自觉主动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陌生人,很多时候甚至连这个人的姓名都不知道。
自身获救的经历激励我运用这些新的方法来探寻利他主义的起源。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此后不久,我把自己的学习重点转向了心理学研究。我本科阶段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专攻实验心理学研究,此后,又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正是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因一些机缘而取得了突破。此前,人们在实验环境中尝试各种方法,试图发现高度利他主义者的标记,基本上都无功而返。而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利他主义与人们对他人恐惧情绪的识别有着紧密联系。那些能够准确标记恐惧表情的人恰好也是那些在受控实验室条件下为陌生人捐出最多钱、自愿投入最多时间帮助陌生人的人。
后来,我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詹姆斯·布莱尔博士主持的实验室中继续深入研究该问题,并渐有所得。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我加入的时候,那里正在开展最早的大脑成像系列研究,其目的是发现导致青少年出现冷血精神病倾向的机理。实验采用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对有冷血精神病风险的青少年进行脑扫描。研究结果显示,这些青少年大脑中叫作杏仁体的那个结构都存在功能障碍。杏仁体位于大脑内部,负责某些基本社交和情感功能的实现。杏仁体结构存在功能障碍的青少年缺乏与他人产生共情的能力,或者说他们缺乏同情心。在看到恐惧表情图片的时候,他们的杏仁体毫无反应。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假设以杏仁体为基础的对他人恐惧表情的敏感性是催生利他主义的重要因素呢?当然,其中也包括我救命恩人表现出来的那种非比寻常的利他主义精神。
而这才是我的故事的真正开端。
5号州际公路上的好心人
在西雅图与一位童年时代的好友共度愉快夜晚之后,我驾车返回位于华盛顿州塔科马的家。那是个晴朗的夏夜,午夜时分,路上没有多少车,而我也没有喝酒,所有这些都是幸运的那部分。而不幸的是我开的是老妈那辆老旧的休旅车,这辆车转弯的时候特别不稳。
我也不知道那条狗是从哪里来的。高速立交桥建在一片工业区的上方,周边并没有住户。可是,我就是撞上狗了,更准确地说,我把狗撞死了。我努力想要避开它,我打方向盘想避开它,我的本能反应就是躲避。在高速行驶过程中急转方向,再加上轧过小狗时车身轻微倾斜,休旅车的尾部开始剧烈晃动。车摇晃着向左侧冲去,横穿过两条车道。我手忙脚乱地想要重新掌控方向,结果却导致车回过头又冲向了右边。等到车第三次转弯的时候,车轮扭动的力量太强了,我完全握不住方向盘了。车开始旋转。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停旋转,而我眼前各种景象走马灯一样快速变换,令我头晕眼花:护栏……车头灯……护栏……车尾灯……护栏……然后……
等我回过神来,我意识到自己正停在最左边的车道——这可是高速车道。不过,对我来说,这是最右边的车道,因为我正对着前方迎头驶来的车流。我的车停在立交桥坡顶略偏下的位置,也就是说对面驶来车辆的司机爬到立交桥坡顶的时候才能看到我的车,只有很短的反应时间来避开我。有些车在急转方向的时候离我已经非常近了,甚至在与我的车擦肩而过的时候车身都开始摇晃了。
而且,路边还没有路肩可以用于应急躲避。立交桥两侧都建有护栏,护栏与我的车之间只有几英寸的空隙。而且,就算有应急车道,我也没法把车开上去,因为车熄火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对着仪表盘上各种疯狂闪烁的警示灯……
我不断用钥匙打火,希望能够发动引擎,可是它就是无动于衷,始终保持安静。我很清楚,要是不采取措施,迟早会有一辆汽车,或者更糟,一辆18个轮的大货车呼啸着撞上……
我战战兢兢地坐在车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坐了多久。当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的时候,感觉时间变得怪怪的,时快时慢。突然,我听到了敲击玻璃的聲音,来自副驾驶那侧,也就是靠近护栏的一侧,当时我的车窗玻璃是半敞着的。
我循声望过去,有个人正站在车窗外望着我,我的心不由得缩了起来。我不知这是福还是祸。那个时候,塔科马市区暴力事件频发,他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能够救人于危难之中的马路英雄。大半夜的,他还戴着副墨镜,身上挂满了各种黄金饰品。他的光头就像是颗亮闪闪的咖啡豆。他说话的时候,我好像还看到了大金牙的闪光。
“看起来你需要点儿帮助啊!”他说道。他的声音粗重低沉。
“嗯,我是需要帮助。”我回答道,嗓子干涩得几乎发不出声音。
“那好。我得坐到你的位置上去。”他指着驾驶座。
我顿了一下,点头道:“好吧。”
他绕过车头,观察了一会儿交通状况。每当有车辆驶过的时候,他的头就会向左点一下,就像跳大绳找节奏那样。稍有车流空当,他就迅速移动。很快,他就站在我车门外猛一下拽开了车门。我及时贴着变速器操纵杆挪到了副驾驶座给他让出位置,他猛一下坐到驾驶座上、甩上车门、抓住方向盘并扭动车钥匙。车没有一点儿反应。
“车不能发动了。”我说。他再次扭动车钥匙,车还是没有动静。
他逐一检视了仪表盘和操纵杆,然后他的视线落在了变速操纵杆上,操纵杆还是放在行驶挡。他什么也没说,将操纵杆放在了泊车挡,再次尝试发动引擎。车发动了!他将操纵杆放到了行驶挡,再次找寻车流的空当。当车流出现空当时,他立刻踩下加速踏板,休旅车带着我们划出一条光滑的弧线顺利穿过车道。很快,我们安全了(相对而言),车停在了下桥匝道的斜线区。他松开油门,将车停在了他自己的车后面。那是一辆深色的宝马车,在钠灯下闪着橙色的光。然后,他转向我,此时,我呼吸急促、五官都紧张地拧在了一起,浑身发冷。
“你自己能回家吗?要不要我在你后面跟一会儿?”他问。
我摇摇头说:“不用了,我能行。我能回家。”
我道谢了吗?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是忘记道谢了。
“好吧。那你自己当心。”他说完就下车离开并上了自己的车。很快,他的车就消失在夏夜里。
为什么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救人?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会是希尔德普帮会的成员吗?也许,他只是个着装风格比较夸张的律师、牧师或销售员?关于他,我掌握的唯一可靠信息就是,午夜时分,他正行驶在5号州际公路上。当时他累吗?他是不是要赶到什么地方去?他偶然间看到了一辆被困在快车道上、逆行停放、亮着大灯、打着双闪的休旅车。他能不能看到驾驶座上的我呢?即使看见了,肯定也只是匆匆一瞥。大部分司机在经过的时候都差点来不及躲开我。但是,从他看见我到他停车这短短的一瞬间,他就作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试着救我一命。他将车驶入下桥匝道并停下来。在那样漆黑的夜里,在华盛顿州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他穿越宽达50英尺的4条快车道,来到我的身边。当他站在那里看着身边呼啸而过的高速行驶着的小汽车和卡车的时候,他会不会有片刻动摇?即使曾经动摇,他也没有让这些思绪干扰自己的行动。
然后,他又在这样的交通环境中冒了两次险:先是从副驾驶侧绕到车的驾驶座一侧,然后将一辆原本发动不起来的车发动并横穿高速公路。计算稍有偏差,或者运气稍微差一点,这3次穿越中的任何一次都有可能害他(可能还包括我)死于非命。但是,他还是那么做了。他冒这样大的风险只是为了帮助我——一个害怕他,而且吓得连感谢的话都说不出来的女人。显然,他拥有非凡的勇气,而且非常无私。当时的他肯定也没有考虑过要为此得到什么回报。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他都是不折不扣的英雄。时至今日,我还时时会遗憾自己没有能够告诉他这一点,也没有谢谢他救了我一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开始不停地琢磨我的救命恩人以及他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当然,他的作为并非个例。见义勇为之举在全世界都多有发生。卡内基英雄基金每年都会奖励几十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每个人都曾听到过新闻报道中类似这样的事情:有人跳到河里救起溺水的儿童,有人冲进燃烧着的建筑物救出受困的老妇人。但是,这些故事都显得遥远而苍白。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读者很容易忽略救人者所面临的风险(冰冷而湍急的水流,灼人而肆虐的火焰之类)以及救人者救人时的感想。对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对能够生动还原当时场景的人来说,救人者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太匪夷所思了,我们根本想象不出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到底有什么感觉?他们会害怕吗?如果会,他们又是如何克服自己的恐惧情绪而做出那么英勇的事情呢?我想,正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有些人为什么能够下定决心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是牺牲生命来挽救一个陌生人的生命,我们才会把能够作出这样决定的大脑看作一个封闭的盒子,遥不可及、不可理解,同时又在某些方面与其他人的头脑具有本质性的差异。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人性中的善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