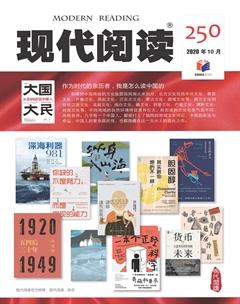从家国天下视角看当代中国
2020-11-16苏力
苏力
当代中国不仅仅是历史中国的延续。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确实经历了,而且仍正经历着,“数千年未见之变局”。许多中国知识人由此遭遇了一个“认识论危机”,对中国制度文化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有了认同的危机,全盘西化是他们真诚的判断和主张。但就在这片绝望之地,更有几代志士仁人和无数普通行动者凭着最原始的求生本能,以殊死的行动,而不只是反思,才令古老的中国重生,并正在崛起。中国经历了又一次自我重构,重大程度至少与西周和秦汉时的变革相似;在深刻程度和规模上,则是空前;由于当代中国的人口规模以及时间约束,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
对中国国家制度影响最大的一个变量是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突出表现为,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尽管中国到2017年还有40%的农民,但中国早已不再是农耕中国,而是一个现代工业制造大国,一个商业贸易大国。这个基本条件的变化必然、已经且还将促使许多制度变化,催生或可能催生一些重要且基本的制度。但曾经塑造历史中国的一些重要约束条件,如正缩小但存量仍然巨大的农耕社区,辽阔疆域地形复杂,多民族多族群等,加之近代以来中国外部条件的变化,如以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全球化,仍然规定了当代与历史中国在宪制上具有某些连续性。
农耕中国之宪制,一定不是,至少不能只被视为,当代中国宪制变革的对象。“家国天下”并非一个已经过去,从此属于过去的传统,它还可以甚至必然是当下的一个正持续着的传统。社会不仅是生者间的合约,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言,也是生者、死者以及未来者之间的合约。无论现当代中国政治家、民众或政法学者是否清醒意识到这些根本问题,也无论愿景、决心和努力如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以用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传统视角来概括当代中国的宪制难题。
如果将“齐家”理解为农耕村落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共同体的组织构成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国家最基层治理的问题(“治国”向社会基层延展),那么,不但可以深刻理解近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也可以以一以贯之的思路来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三农”政策措施,看起来似乎迥异,却是以不同方式回应着中国社会不同转型阶段中的农耕村落共同体的构建和变革,纠结着现代中国基层政权的建设。这就是在创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中,“皇权”下乡,现代政治组织管理、科学技术知识文化下乡,将农民、农村和农业都整合成为现代国家的有机构成部分。无论是1950年代的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后废除人民公社但随即建立的功能替代公社的乡政府,以及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因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法取代农耕村落,中央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有了更多担忧和关切,以“村民自治基层民主”为目标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
即便如此,随着城市工商社会的发展,农耕村落生活共同体和基层政权的建设——“齐家”——还是变得越来越难了,因为农村的政治文化精英,随着上大学、当兵和进城打工,一去不复返地大量流向城市。由此可以理解,21世纪以来诸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以及近年来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建设的自然和必然。
但“齐家”对当今中国的告诫或提醒还不只是一般的农村基层治理问题,或许还有城市地区普通人生活共同体构建问题。这不大可能是城市生活自然就能化解的难题。小区大妈的广场舞,可以说是在城市中重构类似村落生活共同体的一种自发力量。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来自农村的老人很难融入因太喧闹而孤寂的水泥森林,最后选择回到因熟悉而温馨的故乡小城镇。城市生活共同体建构的另一正在迫近的难题或许是,在独生子女国策实践了将近两代人后,许多人退休后突然发现无“家”可归了。“家”并非城市里的一套商品房。
由于明清两朝尤其是清代的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及现当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现实,传统中国的“平天下”在今天基本转化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或边疆治理问题。就此而言,在地理疆域上“平天下”与“治国”重合了。但在文化上,政治治理的制度和策略,这两个问题还不完全重合。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坚决反对并打击以各种名义分裂国家和社会的各类国内外势力,这会是当代中国长期面临的“平天下”问题之一。单一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党管干部制度),以及以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为目标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宪制上确认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中国经济发展、国力日益增长也增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实力和能力。但也必须充分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在国际以及央地关系这两个层面“双重弱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文化信息的全球流动以及“多元文化”有可能侵蚀国家的文化凝聚力;社会流动性很可能令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从边疆向各地渗透,一个原来的“天下”问题因此会变成常规的“治国”问题之一。
这也就意味着“治国”的重大变化。不仅是国家权力下乡重塑“齐家”,也不仅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和单一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重塑“平天下”,这两者如今有相当部分已融入“治国”。更重要的是“治国”领域本身也正在脱胎换骨,或是必须脱胎换骨:一系列社会变量或约束条件的重大变化,包括“齐家”和“平天下”,都在挤压“治国”于蜕变中维新,乃至创新。
恰恰是借助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辅之以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面对现代中国革命中历史形成、客观存在的众多党内军内的派别和“山头”,新中国成立两年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就撤销了基于根据地历史和各野战军独立或联合作战而形成的六大行政區,将统掌一方党政军大权的地方大员均调到中央政府任职,中央政府直接面对数量大增但面积人口都大为缩小,剥离了军权,因此政、经实力已大大压缩的行政区——省。这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实践,显然汲取了中国历代宪制的政治经验和教训。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同样借助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中国才得以迅速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全球性的经济体制变革中抢占了先机。中央集权制事实上便利和加快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改革。不但先后设立了海南省(1988)和重庆直辖市(1997),而且制度性地或准制度性地设立了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较大的市以及沿海开放城市,直至2015年修正的《立法法》规定“设区的市”,都获得了相应的立法权和管理决策权。这种基于政治经济政策考量的行政区划调整,是中国的创新,不仅在一般的联邦制国家不可能,即便在法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也很难。
历史上为维护农耕中国的统一和政治稳定,中央政府一直更多关注从宪制层面对各地实行“分而治之”或“犬牙相入”的制衡。但如今,由于各地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联系的全面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总体上已大大淡化了他们的地方认同,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要求,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合作在今天已不再是令人生疑的政治事件。在东部地区,这已经为中央政府直接推动,突出的,如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长三角的区域合作,以及粤港澳大湾区。
但也必须承认,与历史上各时期的具体宪制发展创新一样,当代中国的许多宪制变革的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除了必定有试错外,任何制度变革都需要調适和磨合,这意味着会打破并重塑人们的一系列预期和天经地义。例如,许多长期看来有利于全社会的宪制发展,如交通通讯的发达、全民教育、普通话普及,以及“皇权”下乡带来政治治理、社会管理人员甚至专业人员(广义的官员)数量激增,令“异地为官”这一曾有效隔阻官员与其故乡亲友、大大减少徇私腐败、有效取信于民的重要制度,如今风光不再,尽管从适用范围上看,当代异地任职的规则更严格了。
这只是些信手拈来的例子,并非对当代中国宪制发展的系统分析,只为说明历史中国的家国天下宪制问题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有时甚至是规定着当代中国,因为宪制要面对、要应对——即便无法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制度发源于这块土地,扎根于人性,因此制度应对的有些问题甚至许多问题一定源远流长,不会到此为止,还会流向未来。即便应对问题的办法或制度会与时俱进,但只要某些硬邦邦的约束条件变化了,这些制度变革的效果也未必能如人所愿,无论我们的制度想象是否丰满,心愿是否真诚,努力是否持之以恒。因为,有时真还就有这样的问题,就如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所言,“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
也因此,历史中国家国天下的宪制实践挤压出来的学术视角,仍会有助于当代中国学人。
甚至未必仅限于理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实践。因为,如果仅从其涵盖的文化类型来看,而不是从地理空间上看,完全可以说,历史中国从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实践着某种形式的全球化。在这片土地上,必须,也因此一直不得不,包容、兼容并以某种方式整合了——如果还不能说完全融合了——农耕、游牧、绿洲、高原文明以及初步的工商文明,至今如此。在更大程度上如今还在全力整合着现代的工商科技文明。若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条不仅有关过去更有关未来的伟大河流中,这就是在东亚这片有限疆域内展开的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全球化实验!因为,相对于历史上各种帝国或政治体联合(如联合国或欧盟)的实践经验——我视之为其他形式的全球化实践,可以说,这是至今为止在人类自生自发的制度竞争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实验。今天的人们有理由记住这些经验。
在社会科学的层面考察、理解并予以尊重,但我们没有道德或法律义务遵循历史。因为历史有时即便会极大程度地影响今天和明天,却无法完全规定今天和明天。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