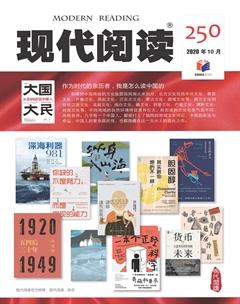“种子使者”钟扬:在武汉植物研究所收获爱情
2020-11-16叶炜高璐
叶炜 高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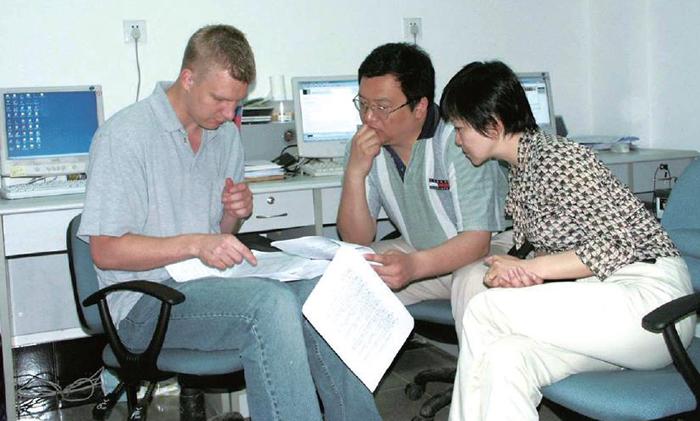
钟扬(1964—2017),复旦大学教授、博导,在植物学、生物信息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他曾率领团队在青藏高原为国家种质库收集数千万颗植物种子;他艰苦援藏16年,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的地区,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赴内蒙古为民族干部授课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2018年,他被中宣部追授“时代楷模”称号。
初到研究所
钟扬学的是无线电电子学专业,来到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让他觉得和自己的专业有些“不对口”。当时,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生物学方面的十几个研究所都配备了计算机,而全国上下,懂计算机的人才又很稀缺。钟扬这一批和计算机专业挂钩的大学毕业生就被引进到各个研究所,以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让少年就已“成名”的钟扬有些心意难平。从儿时的天才尽显到考上中国科学大学少年班,事事都很精通的钟扬眼光不止于此,他的才能仿佛受到了压制。和钟扬有着同样想法的不止一人。钟扬的夫人张晓艳回忆说:“当年我们有三个人到武汉植物所报到,当时是先住在招待所。在去招待所的路上,第一次碰到钟扬和另外一个已经分配过来的人,那人是学日语的。后来,因为大家的家都不在武汉,基本上吃啊住啊玩啊,都在单位里头。我们住的地方,也在植物所的园子里,所以,很快也就都彼此熟悉了。我觉得当时其实大家都想离开武汉植物所,至少我是特别不安心的,离家特别远。他刚分到武汉植物所,说是维护植物所的电脑系统,其实系统根本就谈不上,只有一台很土的电脑。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稳定,我家在西安,我因為毕业以后没有分到西安,就老打算着回西安。他肯定也不甘心只是维护电脑,不甘于在植物所就做那事,在找机会,就会有很多思考。那时,所里陆续分配来的外地大学生比较多,大家都不稳定,植物所的条件也不好,交通又不便,一个小时一班车,下午5点钟就没车了,等于跟在农村没太大差别。”
张晓艳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植物专业。由于张晓艳的家在陕西西安,所以在还未毕业时,她的工作方向就已经确定——回家乡到父母身边。张晓艳的系主任得知这个想法,很是为她惋惜。西安能给张晓艳提供工作的,是一个基层的几乎无科研条件的单位,而张晓艳自身的科研能力又很强,去这样一个单位,国家不仅会少一名科研人员,对张晓艳来说,也很难施展身手。系主任就将武汉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研究的重镇,推荐给张晓艳。张晓艳虽然还是有些动摇,但为了不辜负学校的器重之情,最后还是选择去了武汉植物研究所。
钟扬并不甘心只掌握一些电子学方面的知识,于他而言,这在植物研究所里并无太大用武之地。而同时来植物所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张晓艳,负责植物研究;还有一个是日语学专业的同学,在图书情报室。这三人中,专业最对口的莫过于张晓艳了。冥冥之中,钟扬接触植物学,便有了一个现成的人选,这也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张晓艳来到植物研究所后,分到主要研究荷花的课题组,组长是黄国振。而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荷花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这给张晓艳研究荷花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每天,张晓艳的工作就是研究荷花的品种,以及荷花的这一品种是由哪两个品种杂交的,区分差异性,记录数据,并把它们进行分类。
不仅如此,植物所还交代给张晓艳一个任务——带领钟扬进入植物学的大门。自此,钟扬就跟着张晓艳学习一些植物学方面的知识。钟扬看到张晓艳总是翻一些植物学的书,他自己又对植物学生出了许多的兴趣,就提出了将信息学与植物学进行交叉研究的建议。
钟扬看到张晓艳在进行荷花分类时工作比较烦琐:传统的分类,就像检索表,是按某一个特征定类别,先分成两类,然后再往下分。如果一开始就错了,那后面的正确率就打折扣了。
钟扬觉得可以用数量分类的方法,以避免一些人为因素的差错。有的是数量性状,比如,花的直径大小,它是一个数量性的;有的是定性的,就用1和0来表示。
一开始钟扬认为这是可以用计算机做的。张晓艳就把人工测量的数据送到钟扬所在的计算机室进行比较分析。开始做的时候,他们感觉并不是很好,做出来的结果也不太对,后来张晓艳发现,钟扬用计算机运算所出现的问题是因为钟扬对植物的理解不够。张晓艳提醒钟扬,每一个数据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后来张晓燕要求钟扬清晨和她一起去采集荷花的各项数据,就这样,钟扬逐步对数据背后的意义有了深入的理解,再做出来的模型就会好很多。
有了心仪的对象
钟扬在和植物的亲密接触中,渐渐爱上了这一专业。自此,钟扬的生物学研究开始走向正轨,同时,他与张晓艳的感情也在慢慢升温。当时,北京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有一个基金课题项目,需要进行合作研究,武汉植物研究所就派张晓艳前去参加。而上海也需要张晓艳前去参与工作,自此,张晓艳就奔波于北京植物研究所和上海植生所,在武汉的时间很短。
张晓艳属于古典型美女,当时植物所里追求张晓艳的人不在少数。钟扬意识到要与张晓艳暂别一段时间,就经常跟张晓艳书信往来。也是在这时,他开始展开了对张晓艳的追求。
据张晓艳回忆: “那时候,我和他差不多两三天就通一封信,当时我在上海植生所,来信都放在门卫室,门卫室有个玻璃窗户,所以那些来信放在那里,一目了然。因为钟扬写给我的信特别多,那个门卫就知道了我。有一次,我原来大学的系主任陈俊宇老师——他也是第一个工程院院士,他一直很关心我的成长,当年分配的时候,也是他把我分到武汉植物所的。他大概到上海来写书什么的,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在上海,但不知道我具体在哪个单位,只知道在中科院系统——但中科院在上海有很多研究所。他当时都70岁了,和他夫人挨个到研究所去找,去问。他前面已经问过好几个所了,如细胞所、生化所、有机所等,结果问到我所在的单位时,门卫马上说他知道这个人,说她就在我们这里。陈老师就是这样找到我的,就因为钟扬写给我的信特别多,给门卫留下了深刻印象。”
钟扬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也是因为年纪比较小。当时喜欢钟扬的也大有人在。有一次,一个女同学托钟扬的好友黄梵帮她跟钟扬牵个线。黄梵不知如何做恋爱的思想工作,只得给钟扬写信,告知了这一情况。但钟扬立马回绝了那个女同学的好意。之后,女同学还想确定一下钟扬的心意,去武汉植物研究所找钟扬,但看到钟扬身边已经有张晓艳的陪伴了,也就断了这个念头。
或许是吃了钟扬的“闭门羹”,女同学打算出国。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钟扬还是约好友黄梵一起,给这个女同学饯行。后来张晓艳还收到了这位女同学的来信,信中说:
首先为你祝福,祝福你遇到了能给你带来幸福和爱的真诚朋友、知音。同时,你对他的爱也能被他所接受,这就足够了。你们会很幸福。当然,你碰到了一些矛盾,比如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虽然我没碰到过这些问题,但我认为你的选择是对的,真正的爱能战胜一切。
这也让张晓艳下定了和钟扬结婚的决心。
黄梵问钟扬为何钟情于张晓艳,钟扬认为,张晓艳不仅漂亮,而且热爱科研、事业心重,心思又很单纯,这样的女孩儿,对他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家庭事业两不误
钟扬的恋爱结出了硕果,他的学术研究也是蒸蒸日上。
由于科研工作的杰出成就,1986年底,钟扬在中国武汉植物研究所破格获批助理研究员的职称。同时,钟扬带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成立了水生植物室,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植物学的分类研究中,張晓艳也到了水生植物室,协同钟扬一起做研究。
这一时期,钟扬的研究成果不断:他撰写的《计算机辅助三维重建技术及其应用》(摘要)入编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首届青年生物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和黄德世、马建新合作撰写的《研究所效益及若干环境因素的数量分析》在武汉中国科学院第7次科研管理学术讨论会上交流,并编入讨论会论文集;独立撰写的《相聚在武汉》发表于《中国科大校友通讯》年第4期第2版;和张晓艳合作撰写的《荷花品种的数量分类研究》刊登于《武汉植物学研究》1987年第5卷第1期,该文还获得了1988年湖北省优秀论文奖;1987年,钟扬参加了湖北植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1988年2月,钟扬撰写的《缩短无成果的学习阶段——介绍〈科学研究的艺术〉和〈发现的种子〉》发表于《书刊导报》1988年2月25日第2版。
同时,钟扬也没有耽误自己的生物学课程的学习。他在武汉大学旁听了陈家宽的《普通生态学》,一听就是两年。陈家宽是武汉大学的生物学、生态学教授,他对钟扬这位“旁听生”印象极深,而且两人很谈得来。并且,陈家宽的博士论文,就是和钟扬一起合作的。
钟扬学习十分认真,记性好,又爱钻研,因此很快就掌握了植物学的相关知识,在认植物方面也超过了科班出身的张晓艳。
1988年3月,23岁的钟扬与张晓艳在武汉登记结婚。
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开结婚证明的时候,钟扬采取的是先斩后奏的方式。据张晓艳回忆: “我那时在从上海回到武汉植物所的时候,他这边已经把结婚证明开了。我还在云里雾里,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已经办完了。他说,‘办完事了,我们好安心做科研。这种大事双方应该都考虑下,但他不这样理解,他想的是,我肯定会这样的。我说,‘也不对呀,这证明应该是我自己开,你怎么帮我开了?他的理由是,他代我开完证明,我就不用牵挂此事了,我们结婚以后,就可以安心做事了。我当时确实顾虑比较多,是因为我在家也是独生女,考虑到以后负担比较重;再一个,当时我天天想着回家,因为我爸我妈当时在西安。他老是说我成熟得特别晚,说我也没有那种雄心壮志,而是随遇而安的,没有特别多的想法,比较简单。我当时也说,‘我们都是独子,父母将来年龄大了,以后的负担太重了。他说,‘你幸亏是嫁到我们家来了,看我爸妈对你多好,把你当女儿一样。你要是到别的人家,还有好多妯娌,或者小姑子,你根本搞不定的。我说,‘我又不跟人家计较,又不跟人家生气,还会有什么?他说,‘你不跟人家计较,人家要跟你计较,还不够你麻烦的吗?”
钟扬和张晓艳一结婚,武汉植物所就分了一套房子给他们。钟扬和张晓艳的喜糖,令武汉植物所的科研人员的印象很深。那个时代比较俭朴,喜糖一般都是装在一个塑料袋内,用订书机钉起来,每人送一包。而他们是用订书机把两袋钉在一起,每人送两包喜糖。因为他们就是看重大家的交情,想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之情。
钟扬父亲钟美鸣,原来在黄冈地区教育局工作,由于工作变动,调到了武汉,自此,钟扬父母就一直住在了武汉。钟扬和张晓艳结婚后,能经常回去看望他们的父母。但张晓艳比钟扬回去得更为频繁,她和婆婆王彩燕的关系非常好,她说:“钟扬还在武汉植物所的时候,就经常不回家,待在所里头。他爸妈周末打电话,希望我们周末回去,他就让我回去做个代表。他也不常回去,还是我回去得多一些。钟扬父母跟我父母也没有任何隔膜,这在很多家庭中比较少见,可能价值观都比较一致,都比较好说话。我爸妈以前跟他爸妈也在一起待过,而且他爸妈特别希望我爸妈跟他们待在一起。这是很少见的。”
钟扬对待科研非常认真。钟扬从事的领域叫植物数量分类,他正是和张晓艳合作研究以后,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才意识到这个领域可以成为他的一项事业。当时介入这项研究的人很少,是一个很新的领域。国内没有人研究,是个空白。所以,他的第一本书《数量分类学》,就是填补这一空白的。
(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采集种子的人》)